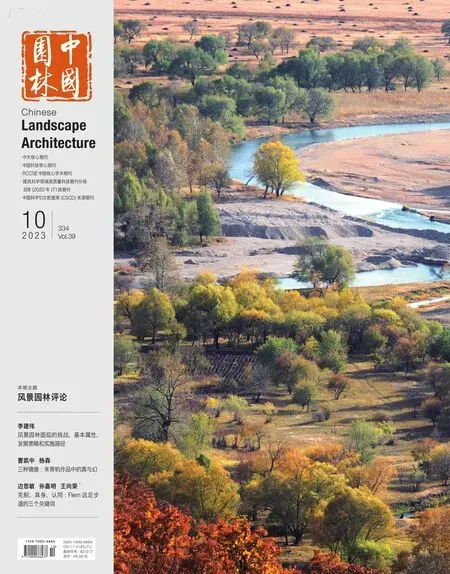“三生”視角下風景區傳統村落轉型發展的系統特征及作用機制研究
孔令宇 徐小東 劉 可 張 然
1 概況
傳統村落擁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體現了當地的空間格局與建筑營造智慧,反映出人類在農耕時期與周邊自然環境融洽共生的和諧狀態,具有極高的藝術與科研價值,是中國千年農耕文明的“活化石”[1]。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體發展路線,將“三生”融合發展的理念提升到空前重要的高度[2]。
傳統村落作為一個活態的物質文化遺產,國內該領域諸多學者長期重視其轉型發展的相關研究,并形成了豐碩的成果。從研究內容來看,在經歷了2006—2011年傳統村落研究成果快速增長期后,學界逐漸進入了更為精細化的研究階段[3],由于各個領域研究的重點不同,產生了人文、生態、空間等多元視角,呈現出百花齊放之景象。近年來,地理學及分支領域的研究者較多聚焦在傳統村落的演變性質及其成因、地域性識別分區等領域[4-5];社會學研究者比較重視社會轉型與村落文化演進,探討了未來鄉村的社會結構及治理等[6];建筑學、風景園林學學者集中在對村落的人居環境特征與適宜性營建保護等方面的關注[7-9]。
從上述研究成果中不難發現,中國關于傳統村落轉型發展的相關研究已經步入了一個多學科、多視角、多方法的新發展時期。但從關注的角度來看,現階段多側重于經濟、空間、文化等某一特定領域,缺乏系統性的綜合研究;從研究方法來看,定性描述較多,缺少具有實地數據支撐的量化分析基礎[10]。傳統村落是一個復雜的復合體,其生產、生活、生態的系統特性、驅動機制及發展轉型規律等內容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風景區內生態資源相對集中,并具有一定的體量規模和旅游條件,區內傳統村落有著較高的生態稟賦,且保存相對完整。其“三生”系統保持著較高的與外界物質與信息交換頻率,系統內部的相互影響機制及其轉型發展過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與研究價值。鑒于此,本文嘗試從“三生”系統的角度,以蘇州東山、西山風景區的不同級別、類型的12個傳統村落為調研對象,在“三生”系統的量化評價基礎上,探索轉型期的傳統村落“三生”系統特點與發展動力機制,討論生產、生活、生態之間的作用機理與系統特征,對于優化傳統村落“三生”協同發展機制及其多元路徑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建構
在課題組已取得的傳統村落評估方法成果[11]的基礎上,獲取風景區內不同類型的傳統村落實調數據,基于“三生”視角對東山、西山風景區內不同等級、類型的傳統村落進行實地調研,并進行量化評價、“三生”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展開對傳統村落“三生”系統轉型發展的系統特征、驅動機制和演變規律剖析。
2.2 基于“三生”視角的傳統村落綜合評價
關于“三生”視角下傳統村落的量化評價,課題組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通過參考與該研究領域相關的文獻評價體系資料,如村落文化傳承評價[12]、鄉村性評價[13]、基礎設施協調發展評價[14]等,篩選出綜合評價的31個關鍵指標,涵蓋了3個大類(B層)、8個中類(C層)和31個小類(D層),并通過層次分析法來確定各因子的權重[15](表1)。

表1 “三生”視角下傳統村落綜合評價體系與權重
通過模糊矩陣運算,得到綜合評價體系完整的A、B、C、D層級的得分結果量表。
2.3 “生產-生活-生態”耦合協調模型
受王成等關于鄉村三生空間功能耦合協調模型的啟發,鄉村三生功能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脅迫的耦合互動關系[16]。本研究搭建了“生產-生活-生態”系統的耦合協調模型,計算如下:
指標的無量綱化處理公式分別為[17]:
計算“三生”系統的各項量化得分,即f(x)、g(y)、h(z)。
式中,C、D、T分別代表耦合度、耦合協調度、綜合指數。同理,可推算出“生產-生活”功能、“生活-生態”功能、“生產-生態”功能兩兩之間耦合協調度。最后,將0~0.2、0.2~0.5、0.5~0.8、0.8~1.0的4個耦合協調度區間分別對應為失衡流動、競爭矛盾、磨合調整、共融協調4個發展階段。
為確保該模糊綜合評價不同維度與層級結果之間的可比性,需在SPSS軟件中歸一化處理評價向量結果,以便擬合出傳統村落“三生”系統轉型發展的演化過程曲線。
2.4 案例遴選
課題組選取了蘇州市東山、西山景區及附近12處具有典型特征的傳統村落,分別為堂里村、東村村、植里村、東蔡村、明月灣村、甪里村、蔣東村、陸巷村、楊灣村、上灣村、翁巷村和黃墅村(圖1)。

圖1 12處具有典型特征的傳統村落分布
2.5 數據來源
2020年8月、2022年6月,課題組20余人對東山、西山景區內12處具有典型特征的傳統村落進行了2次為期十余天的實地踏勘、現場訪談與問卷調查。在“三生”視角下傳統村落綜合評價體系中,指標D8~19來源于實地踏勘,D27、31來源于問卷調查,D1~2、5~7、20~23來源于文獻查閱。其中,部分數據具有多種來源,D3~4、24、29~30的獲取通過現場訪談為主、文獻查閱為輔的方法,D25~28的獲取通過問卷調查與實地踏勘并行的方法。
3 “三生”量化評價與模型分析結果
按照所構建的評價操作流程進行模糊評價,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綜合評價結果
基于“三生”耦合協調度計算模型對結果進行計算,并通過Z-score數據的歸一化處理,轉化為標準差和方差都為1、平均數為0的Z-score標準化得分,以便做非線性回歸分析。最終,擬合出傳統村落“三生”系統轉型的演化過程與“生產-生態”“生產-生活”“生活-生態”的關系曲線(圖2~4)。

圖2 “生產-生態”與“三生”耦合協調度關系曲線

圖3 “生產-生活”與“三生”耦合協調度關系曲線

圖4 “生活-生態”與“三生”耦合協調度關系曲線
可以發現,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三生”系統內部兩兩耦合的發展狀態顯示出較大的差異性,該耦合過程此消彼長,呈現出顯著的非線性發展特征。
4 傳統村落“三生”系統轉型發展的系統性分析
4.1 系統構成及其動力機制
與外界的能量交換是傳統村落“三生”系統轉型升級的必要前提,多元主體之間的相互博弈和協同作用是能量交換的動力之核。研究村落的系統構成及其動力機制需從“生產”“生活”“生態”與“多元主體”4個維度上構建系統模型。
生產系統主要用于度量村落經濟生產環境的變化程度,它為生活、生態系統的發展提供經濟基礎,同時生產的發展也需要村落的生活、生態系統作為支撐。生活系統主要用于度量村落公共服務設施、人居環境建設、村落活力變化的程度,是村民生活的基礎性保障,也是村落活力的根本。生態系統用于度量傳統村落“泛生態”變化的程度,生態文明應是人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的合集[18]。
傳統村落“三生”系統持續發展的驅動力來自多元主體之間的相互博弈與協同適應,由他組織系統與自組織系統兩部分構成(圖5)。

圖5 “三生”視角下傳統村落轉型發展的驅動系統
他組織系統的主體是政府與規劃師、企業、社會組織等的組成,政府與規劃師通過政策引導帶動村民,并對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進行協調與監管[19];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為農戶帶去了就業機會與經濟支撐;社會團體能夠為農戶提供更多的服務支持,以更好地整合“三生”資源。他組織系統對村落的介入,通過外部資源的滲透,將管理、技術、商貿與當地的“三生”資源相融合,促進村落轉型發展,從而產生積極的社會生態效益、生產效益和生活效益。
村民是自組織系統的主體,是傳統村落的主人,也是自下而上自主發展的動力之源。隨著與他組織系統之間的交互愈發多元和頻繁,其空間行為、利益訴求和人地關系等均在持續發生變化,不斷推動傳統村落“三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
傳統村落的轉型與發展離不開農戶自組織系統的發展與壯大,但自組織系統中又有許多弊端,如局限于個人利益、漠視集體、沒有充分發展人力資本等[20]。他組織是“三生”系統有序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如規劃政策、企業資金注入和社會其他機構的服務,都構成了巨大的驅動力,可以克服自組織在發展過程中的效能過低、資本匱乏和眼界狹隘等問題,從而促進了體系的有序發展。在自組織演化與他組織介入相互交替的作用下,傳統村落“三生”系統會產生質的飛躍。
4.2 傳統村落“三生”系統轉型發展的階段特征
在“三生”系統中,隨著要素的不斷交換與積累,原有系統的臨界值將會被打破,系統也隨之發生“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躍升,表現為生產系統、生活系統、生態系統和多元主體的時空演變,其轉型發展的特征從以下4個階段進行討論。
1)失衡流動階段。
“他組織動力”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政策開放與市場效應,帶來了外界資本介入及新觀念的廣泛傳播,村內原本穩定的自組織模式開始向混沌和失衡轉變。內外系統間的要素流動不斷加速,為“三生”系統轉型提供原始能量的積累。在該階段中,景區內村落產業生機向好,但同時也伴隨著諸如人口外流、土地使用性質轉變、社會結構兩極分化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在“三生”耦合協調度模型中,該階段黃墅村與蔣東村的耦合協調度在0~0.20范圍內。
(1)生產維度,風景區內的村落具備優良的旅游資源,隨著市場資本的介入及政府的政策加持,村內土地使用結構將發生轉變,村落原先的生活、生態本底會遭遇到新生產模式的沖擊,景區內大量生活、生態土地流轉為旅游服務、商業、商住混合等產業性質用地。在綜合量化中,綜合經濟活力C1與強勢產業活力D3結果相對突出。另外,由于村民的意識覺醒需要一定時間來醞釀,新理念、新模式融入較為緩慢,“生產-生態”耦合協調的進程發展緩慢,基本維持在0.2~0.4區間內,原始轉型動力積累遲緩。
(2)生活維度,由于新生產帶來新觀念的不斷擴散,整潔舒適的空間與現代居住模式沖擊著傳統觀念,一些村民自發在村落外圍建設新民房,形成了新的村落空間架構。新生活空間無序擴張,帶來諸如土地利用粗獷、基礎設施配建跟不上等問題,即在評價結果中,呈現出水綠面積覆蓋與連續性D7、山水環境質量D8、人居環境設施完善度C7評價不高的特點,人地關系危機初顯。在所調研的該類村落中,“生產-生活”耦合過程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倒退、衰落的情形,數據的預測殘差范圍極窄,耦合協調度不增反降。
(3)生態維度,風景區廣袤的自然資源是村落賴以生存的腹地,新生產與生活模式對生態本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蠶食與破壞,山水自然環境C3與人居環境設施完善度C7均質量不高。但由于新生活模式有著清潔、集約等優點,傳統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居住模式逐漸被取代,新的居住模式有著更多與生態資源互融的可能性。該階段“生活-生態”耦合協調度仍處于低位,但從整個預測過程表現來看,后期將有著可觀的發展。
2)競爭矛盾階段。
隨著他組織系統對村落的不斷滲透,新思想、新模式在村民群體中持續醞釀與發酵,新的機遇與挑戰大量涌現,“三生”系統處于無序紊亂的過程,在該過程中往往伴隨著新與舊事物之間的矛盾競爭,“自組織動力”將起到重要作用,相對于上一階段,村民組織活力D15顯著活躍。在組織的主體結構上,系統將更加多元,外界的社會組織加入了資源的競爭和分配中,與村民、政府、企業將通過競爭、排斥、合作等方式優勝劣汰,將“三生”系統資源做到更優的配置,系統演變進入關鍵期。在“三生”耦合協調度模型中,該階段東蔡村、上灣村、楊灣村及植里村的耦合協調度在0.2~0.5范圍內。
(1)生產維度,社會組織加入對生態資源的利用和競爭中,在社會組織的服務協調下,資源的利用更加高效,當地特色產業的發展可觀,D4普遍大幅度增高。另外,村民組織活力D15也得到良好的帶動,維持在3.00上下。隨著村落主體功能顯現多元化趨勢,村內的復合功能空間開始出現,互融態勢初顯,“生產-生態”的功能界限出現“模糊”和“融合”趨勢,耦合協調的進程則以0.30為界,進入了迅速上升期。
(2)生活維度,由于意識的覺醒,村落居民的階層分化在所難免,較上一階段,致富帶頭人產值D6增長顯著。最先發現商機的富民在村外建構聚集區,人居環境與配套設施向好。另外,貧富差距也逐漸拉大,D31得分均在1.00以下。傳統區域內,低收入者的財力有限,在原本拮據的生活空間下,增設如餐飲、零售性質的生產空間以迎合新生產模式,生活空間進一步壓縮。在該類型村落的調研中,人居環境設施出現了分布不均、區別對待的情況,C7得分迥異。差距不斷擴大,矛盾對立不可避免,“生產-生活”的耦合過程出現了割裂的情況,耦合協調度由0.47起,持續下降到0.24。
(3)生態維度,在評價結果中,該類村落的生態大類B2整體性提高至30分以上,富民占據村落外圍廣袤的用地,并不斷外遷形成新的生活區。隨著基礎設施建設與相關規劃的跟進,在生活與生態的耦合層面,兩者聯系更加緊密,并呈現出功能融合態勢。“生活-生態”的復合功能空間不斷發展壯大,其耦合協調度普遍提高,東蔡村甚至達到了0.58,反映了發達地區傳統村落生活與生態系統更易和諧共生的特點,“生活-生態”耦合頻率與速度不斷加快。
3)磨合調整階段。
由于多元主體間的無序競爭,造成了系統雜糅混沌的狀態,此時急需強而有效的力量發揮引領作用,外組織系統中的政府與規劃師將扮演重要角色,政府、規劃師活力D16顯目,普遍在2.50以上。政府、規劃師通過管控與引導的方法作用到系統中去,對村落的轉型發展方向起到決定性影響。在政策的主導下,各方主體的活動得到制約與引導,“三生”相互之間的耦合進程呈快速提升態勢,自組織與他組織系統開始相互協同,“三生”系統整體發展向好,并加快了村落的磨合調整演進。在“三生”耦合協調度模型中,該階段翁巷村、甪里村、東村村及堂里村的耦合協調度在0.5~0.8范圍內。
(1)生產維度,在政策的指引下,自組織與他組織系統的協調更為流暢。為提升品牌效應與商品規模化,村民自發尋求企業與社會組織等主體合作,加大宣傳力度,適應市場化的需求,特色產業D4的發展提速,保持在3.00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D1與村集體年收入D2也實現了可觀的增長,均達到了“1+3”的級別。而上一階段中貧富差距大的狀況也得到了好轉,D31達到了2.00以上的得分。生態資源市場得到了高效開發的同時,政策的剛性管控有效限制住了生態環境破壞、粗制濫造等市場弊端,綜合經濟活力C1、山水自然環境C3、村落空間環境C4等都有著較高水準。“生產-生態”耦合協調度均在0.5等級以上,且協調速度持續加快,呈現指數級的增長。
(2)生活維度,隨著景區內民生投入比重的加大,村落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得到完善,人居環境設施完善度C7進一步提高。良好的人居環境吸引了村民回流創業打工,反向刺激了生產維度的再繁榮,村落年輕人回流狀況D29與外來人才數量D30增長顯著。另外,隨著村民收入的增加,消費需求更向健康、教育等方面傾斜,新的需求刺激了更大的市場,“生產-生活”的割裂開始縫合,在經歷了翁巷村的0.29低點后,耦合協調度觸底向好,逐漸向“協調”的方向邁進,此特征也是該階段的顯著性特點。
(3)生態維度,在政策的積極引導與管控下,一系列的發展保護規劃得以實施,如風景區旅游發展規劃、人居環境整治規劃等,自然生態空間得到了良好保護,山水自然環境C3、村落空間環境C4的提升有目共睹,均達到6.50與9.50以上分數;村民的日常活動與節慶得到了保護和持續,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村落活態化進程顯著,文化活力C6與村落人氣活力C8都得到了75%以上分數的較高水平發展。“生活-生態”耦合到達了高位,增長速率趨于穩定,且持續向好發展。
4)融合協調階段。
在融合協調階段中,村落實現了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型升級。村落的自組織與他組織系統充分協同,“三生”系統整體健康發展,組織活力C5突破15.00的等級。在“三生”耦合協調度模型中,該階段陸巷村與明月灣村的耦合協調度在0.8~1.0范圍內。
融合協調階段的最大特點是自組織與他組織系統的充分協同發展,村民組織活力D15、企業活力D17、社會組織活力D18都達到了得分上限的90%分數,屬高活躍度的階段。生態資源得到了最大效能的保護和利用,風景區旅游等產業資本的注入刺激了村民的回流,保障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性,村落整體達到了活態化的狀態。良好的政策組織不僅提升了村落的基礎服務與人居環境水平,更限制了生產、生活活動對生態的蠶食,保障了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多方主體的積極參與和融合,使得村落“三生”系統不斷優化提升,生產、生態、生活3個維度都進入了高水準發展階段,“三生”耦合協調程度達到“融合”狀態,“三生”系統厚積而薄發,實現了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型升級。
5 結語
傳統村落的轉型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三生”系統內部子系統的兩兩耦合發展狀態顯示出較大的差異性,該耦合過程常此消彼長,呈現出顯著的非線性成長的特性。集中發展“三生”中的1或2項并不能使鄉村達到“三生融合”的狀態[21],須尊重系統內部的發展規律與特征,循序漸進地對待系統內各子系統的發展轉型,在策略引導上做到有的放矢。
注:文中圖片均由作者繪制。
致謝:感謝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吳錦繡教授、張玫英副教授、王偉副研究員提供的幫助;感謝課題組內吳正浩、白雨、范靜哲等同學對調研村落數據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