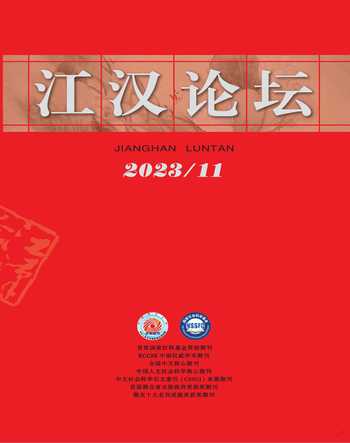1990年代詩歌的“聲音”問題
陳昶?
摘要:1990年代詩歌語言普遍呈現日常性、口語化的特征,作為詩歌語言重要方面的“聲音”,反映了詩人在形象建構上的思考進路與詩學觀念,由語言風格尤其是“聲音”所體現的觀念轉向,引發了詩人對于中國形象表達方式的轉捩,上述現象在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詩人如于堅和伊沙的作品中尤為突出。較之前一時期詩歌的啟蒙與浪漫傾向,從聲音語詞到中國形象,90年代詩歌更加重視日常經驗對于意義生成的直接性和效用性,將形象的建構內化于聲音、語詞的形成和運動中,在詩歌語言和中國形象之間,在詩人主體與詩歌客體之間,建立了更為直接的語義機制,經由聲音語詞的價值實現中國形象的豐富與完善。可以說,90年代的創作經驗與審美標準,為新世紀詩歌樹立了價值典范,逐漸成為當代詩人向世界文學貢獻中國價值、弘揚中國精神的一條重要路徑。
關鍵詞:1990年代詩歌;新世紀詩歌;中國形象;詩歌語言;聲音;語詞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80年以來詩歌中的中國形象研究”(21BZW139)
中圖分類號:I20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3)11-0098-08
1990年代詩歌擔負著承上啟下的責任:一方面,在80年代的啟蒙話語逐漸消失與經濟社會高度發展帶來的人文精神缺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詩歌在90年代呈現出與前一時期風格迥異的面貌,因而對于當代詩歌傳統的承繼變得尤為關鍵且困難重重;另一方面,90年代末的詩歌論爭,逐步確立了以“民間”“口語”等日常書寫為關切的審美優先地位,持續影響著新世紀詩歌創作的路徑與方向,進而規范了與聲音和詞語相關的中國形象的表達方式。聲音和詞語,以及由詞與詞的關系和內在節奏所形成的結構,作為詩歌的基本形式,承載著形象建構與表達的方式,由此完成價值與意義的呈現。90年代出現了詩歌語言的日常化傾向,從語言到形象的過渡變得更加自然。形象的價值寓于聲音和詞語內部,由內及外地生成意義的本質。將聲音和詞語作為詩歌創作的核質,重視從聲音語詞自身出發塑造中國形象,從而拓展詩歌于歷史空間的存在向度,實現中國形象從詩歌或文學向民間生活的持續生成,達成了中國形象自身的完善。于堅和伊沙這兩位詩人在90年代的創作成就表明,從聲音語詞出發,足以支撐中國形象內涵的不斷豐富,從而經由詩歌語言的鍛造,傳遞“中國聲音”。有理由相信,這一點在將來的詩歌發展中依然可以作為一條值得借鑒的創作路徑。
一、墜落的聲音:90年代詩歌語言的日常性與口語化
作為詩歌語言兩個本質特征的聲音和詞語,或并稱為聲音語詞,從語言起源的角度看,代表著人類語言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馬克思曾以感官知覺作為人類歷史的開端:“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1)當人類獲得關于自身的感知能力后,他們便開始尋求自我保存,最初的部落得以建立,由此誕生了原始語言,即“由含糊不清的喊叫聲、許多手勢以及一些模擬聲音組成的。而在不同的區域,人們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一些帶有音節的和約定的聲音”(2)。于是赫爾德說:“發聲的動詞是語言中最早的生命要素”,進而由動詞產生了名詞,而“語言的全部構造方式正是人類精神的發展方式,正是人類發展的歷史”(3)。此外,“通過聽覺,每一種感官都有了語言能力”(4),聽覺是其他感官的本源。總的說來,聲音和詞語正是人類知性在大自然的刺激和引導下所最初生成的兩類產物,因而對于語言來說具有本質意義,而詩歌語言也已被認為是人類歷史最早誕生的專門語言之一。
詩歌或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最早便是古人記載歷史事件的工具,于是孔子說“文勝質則史”,起初的詩文是在歷史記載之外多出來的那種韻味,即所“勝”之物。因此,作為聲音和詞語載體的詩歌,其語言核質仍可從聲音和詞語兩方面加以捕捉;由于詞語又是起源自聲音符號的表意,故而聲音語詞這一提法本身即是對于聲音的強調,聲音或者說作為聽覺經驗的語詞意象,既是語言的本質,也是詩歌的本質。
聲音既然是人類感官的本能產物,源自聲音的詩歌語言則同樣具有直觀性和自發性。這種直觀和自發的詩歌語言乃至文學語言,就是通常所說的口語或白話。對于白話之“白”,胡適定義為:“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5)按照這一標準,發源于2500年前《詩經·國風》的中國文學,其生命力的象征便是白話作品的創造和普遍流行,無論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還是明清小說,都可歸結為白話文學在民間的勃興以及除此之外的文學形式的僵死,胡適由此指出:“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6)這種觀念的影響延續至1990年代,以“白”為詩的傳統將90年代詩歌中的“聲音”納入同一歷史脈絡中。
伴隨著1991年振聾發聵般“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7),朦朧詩的“一個小小的傳統”(8)漸漸歸來,對于食指的重新發現開啟了這個十年“把詩歌還給人民”(9)的進程,人民的詩歌就是個人書寫,90年代正是在這樣一個關注個人書寫的精神起點上開始的。同樣是在這一年,后來載入大學以及中學課本的《帕斯捷爾納克》帶著“北京的轟響泥濘”(10)響徹人們耳畔,那難忘的“靈魂的顫栗”(11)雖然來自一個素昧平生的外國人,然而似乎可以通過神交將它捕捉到。人們還聽到“自由的小喇叭始終吹響在他的體內”(12)以及“肖邦的音樂無可爭議地融進/一八六五年以來所有鋼琴的形狀”(13),一時間詩人的聲音和話語稱得上喧響而嘈雜。關于聲音的獨特體驗,成就了這一時期諸多詩人的經典作品,于堅和伊沙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位。
于堅多次撰文回憶自己的童年經驗,這被批評界一致視為他最初的創作源泉。其中有關聲音的記憶至關重要,使得詩人在成年以后對聲音意象的建構尤為深刻。在《墜落的聲音》中,詩人記錄了一次由聲音所引起的沉思。他通過平凡的詞語排列:“水泥 釘子 繩索 螺絲或者膠水”、“書架和書架頂上的那匹瓷馬”、“光線 地毯 水泥板 石灰 沙和燈頭”(14),營造出豐富的混響圖像:不同材料、不同種性、不同音質的對象紛至沓來,它們在詩句中維持著形式上的統一感,在獨自或共謀制造出那匪夷所思的聲音方面享有平等嫌疑,暗夜中無處不在的懷疑令人感到緊張,“就像革命年代”“從另一層樓的房間里下來的”“穿越各種物件”“從一間囚房傳到另一間囚房”的“容易被忽略的”(15)聲音,引發了詩人近乎戰栗的反思。這聲音穿透詩人的整個生命體驗,向他敞開了紛繁復雜的物化社會里日漸被遮蔽的生存本質。這聲音是捫心自問的瞬間,是靈魂出竅的體驗,是足夠喚醒人們沉睡的理想的那個醍醐灌頂的聲音。在這聲音自上而下“墜落”的運動中,重要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聲音所昭示的日常生活之上的意義:“經由詩的通道, 找回了生命的真實與言說的真實。”(16)這一切,都是由那聲音墜落過程中令人揪心的緊張和不安所直觀呈現的。
90年代詩人們熱衷于以日常道理與現實題材入詩,致力于改變80年代以來詩歌創作越發不接地氣的局面,從而還日常生活一種直觀、具體、言之有物的詩歌類型。正如于堅在《事件:寫作》中所表達的:“在舌頭那里 一動就是說出的地點/從最明亮的地方開始 一頁白紙 一支鋼筆和一只手對筆的把/握 這就是寫作”(17);“手”與“舌頭”(或“口”)的同一關系,即從“說”到“寫”不經任何中介的對象化過程,反映在作家或詩人的主體經驗上,就是作品的生成過程。“我來了 我看見 我說出”(18),基于對“舌頭”“說出”“命名”等聲音語詞的符號化與對象化把握,詩人一方面創造出“手口合一”的詩句,另一方面則實現了自我意識的新一輪確立,從而完成自我存在主客體兩方面的雙重建構。于堅進而寫道:“在我們一整代人喧囂的印刷品中 寫作是唯一的啞巴/哦,神啊,讓我寫作,讓我的舌頭獲救!”(19) 90年代初期詩歌語言的雜亂無序,可以稱得上“喧囂”,詩人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必須經歷從“啞巴”到“舌頭獲救”的辯證否定過程,通過短暫的失語忘卻昔日種種與現實生活相悖的詩歌形式,然后重新反思并實踐創作的本質,最終收獲有生命力的作品。
伊沙在口語詩寫作方面更為激進,他以標志性的反諷風格解剖了陷于困境的時代,其主要作品因此成為連接90年代與新世紀的一個精神紐帶,持續影響了一代人的寫作立場。荷蘭漢學家柯雷曾以《結結巴巴》作為范例,分析伊沙詩中獨特的聲音魅力,稱之為“在美學和學術領域里均有著根本性的意義”(20)。這聲音與于堅“墜落的聲音”有所不同,是話語的見證,它即便對于聽不懂語言的讀者依然可以引發詩意互動,因此是通過語義的剝離抵達聲音的本質,在此基礎上賦予話語者與聽眾這對關系結構以徹底斷裂,即“你們瞧瞧瞧我/一臉無所謂”(21)暗指不合作的立場。伊沙成名作《餓死詩人》:“我呼吁:餓死他們/狗日的詩人”(22);形式上緊迫而短促的節奏,與驚世駭俗的內容相呼應,仿佛進行曲式的戰歌。
再如《感嘆》:“用雪白的象牙牙簽在牙縫里剔出一個字眼:希臘/希臘啊希臘!令我祖國的詩人心猿意馬/希臘啊希臘!瞧我祖國的詩人使勁拉稀。”(23)三行詩將反諷力展露無遺,“xi la”與“la xi”的對偶,也可以說是個俗不可耐的“諧音梗”,字里行間流露出詩人對于濫俗創作現象的鄙夷與唾棄。“象牙牙簽”與“牙縫”的語義組合,通過一個“剔”字產生了直觀而強烈的聽覺想象,對于精心裝扮的低劣創作手法嗤之以鼻,借助于聲音語詞的形象化以及對于視覺意象的聽覺化手法,使現實主義的批判入木三分。
伊沙詩歌中的日常生活景觀無處不在,如《每天的菜市場》:“那是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君子動口不動手/我臉紅脖子粗地/與人吵架/有時也當看客”(24)。在“手”與“口”的辯證法中,詩人顯然更在意后者,后者擁有對于前者的優先權,也是“菜市場”這一煙火民間的象征場景下最為普遍的生存手段。“手”與“口”的辯證統一,則代表著“君子”與“勞動人民”的“打成一片”。詩人不滿足于充當“看客”,因此“臉紅脖子粗地”親身參與“口”的戰斗。這正是“手口合一”創作觀和白話文學理念的產物。
伊沙另有《傷口之歌》:“我對傷口的恐懼/是發現它/像嘴/吐血/我對傷口更深的恐懼/是露骨的傷口/呲出了/它的牙/我的周身傷口遍布/發出了笑聲/唱出了歌”(25)。歌即是詩,是“口”的杰作或聲音造就的藝術載體,詩人對語言暴力及其傷害有清醒的認識,他盡管感到“恐懼”乃至“更深的恐懼”,也仍要堅持在這條崎嶇道路上探索前行。這是90年代詩人們的責任心使然,又彰顯出大無畏的自我革新精神,“發出了笑聲”且“唱出了歌”。90年代,正是在這一群“我手寫我口”的詩人們共同努力之下,綻放出了文學史意義上的獨特魅力。
二、從聲音到形象:90年代詩歌的中國形象建構
詩歌乃至文學的“聲音”,在八九十年代經歷了向下運動的過程,這一過程可比擬為事物的墜落,尤其是“詞”的墜落。這種“墜落”的聲音,作為一種回響,反映出社會觀念向日常生活逐階“降一格”(26)的運動形態。一方面,80年代那種理想在云間高蹈的浪漫主義精神,伴隨著詩人和詩歌的庸俗化而掉頭向下,與民間野蠻生長的白話語言不期而遇,形成一種雜糅著浪漫與現實的口語詩體形式;另一方面,90年代文學生在民間、長在民間,它天然脫胎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這一趨勢下詩歌也不得不求新求變,不僅在形式方面突破80年代的藩籬,而且從主題、抒情、敘事、意象、隱喻、節奏、旋律等方方面面都呈現出嶄新面貌,由聲音的“墜落”所引發的詩歌語言形象的遷變,將作為語言形象重要方面的聲音性呈現為敘述詩歌史的一種獨特視角。
文學語言的“聲音”性,與白話文學史的發展一脈相承,與時代大勢保持同頻共振,在戰爭年代表現為“呼喊的詩歌”(27),鼓舞并塑造了幾代人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和平年代則依然以“紅色經典”的形式,帶給人們以“崇高的情懷”(28);同時與那種“震顫”(29)的聲音相對,90年代以降出現了來自民間的多元化與多聲部的日常之聲,促使詩歌中的中國形象朝向更加多元化的結構生長。反映在詩歌語言上,就如同北島在《藝術》中所寫的那樣:“億萬個輝煌的太陽/顯現在打碎的鏡子上”(30);在總體性的一元結構逐漸被“打碎”以后,中國形象猶如“億萬個輝煌的太陽”,在無數碎片化的意象中閃現著它的光芒。中國形象從一元結構向多元結構的遷變,主要體現在“現當代文學中一系列關于聲音、或者涉及到對聲音的體驗的詩歌”(31)歷史之中,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就彰顯并還原出聲音語詞或口語之于文學作品的重要核質,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體驗中,優先將聽覺經驗作為區別于古典詩歌的顯著特征,從而建構起來“意在言外”(32)的語言形象體系。
中國形象作為新詩“意在言外”的主體建構,它的不斷豐富與表達,伴隨著詩歌語言的遷變過程;百年新詩史作為白話文學史的一個映照,其間發生著中國形象的興衰遷變,“由于這百年間中國及世界歷史的特殊性,對中國形象的反復尋找、呈現或重構,竟演變成了一個貫穿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紀性傳統”(33)。80年代隨著朦朧詩的興起,詩歌中的白話語言呈現出“大我”與“齊唱”的特征,并由此確立了一種宏大敘事形式的審美風格。這種風格在90年代以后逐漸受到了批評,并伴隨著廣泛的詩歌論爭,它最終在世紀之交分崩離析,徹底為日常生活與“微言”敘事的風格所取代,進而奠定了新世紀詩歌的語言基調。詩人們普遍意識到,講好中國故事,關鍵不在于融入“大我”,更重要的是充分展現“小我”,也就是講好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種語言風格的變換,推動詩歌創作立場全面轉向民間生活,以老百姓的日常口吻發聲,寫老百姓身邊的故事,描繪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形象,理想主義融入現實的尋常百姓家,那種一度在“大我”與“小我”的話語立場之間搖擺的“朦朧”詩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詩人身份開始存疑的背景下,人人皆可創作的當代白話詩或“口語”詩,正如謝冕所說:“擯棄了可憎的豪言壯語,從此再也不確認權威,詩歌再度成為人人均可把握的文體——這對于禁錮已久的詩歌而言不啻一個福音。”(34)
90年代以來,于堅和伊沙相繼樹立了當代口語詩的全新標桿,并由此開創了詩歌語言形象的一種小傳統。這種傳統形成的標志,就是上述“碎片化”的多元語言形象。就形象的多元化特征相對于過去那種一元的“總體話語”而言,于堅將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稱為“突圍”:
寫詩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活計,與語言搏斗是人類最壯麗的事業。我早年寫作,一揮而就的時候多,自以為才華橫溢,其實往往落入總體話語的陷阱。我現在寫詩,有時一首詩改寫多達十幾遍,我是在不斷謄抄改動的過程中,才逐漸把握一個詞最合適的位置。1992年我寫作《0檔案》,這首長詩是我寫作經歷中最痛苦的經歷,在現存的語言秩序與我創造的“說法”之間,我陷入巨大的矛盾,我常體驗到在龐大的總體話語包圍中無法突圍的絕望……寫作既要戰勝語言,也要戰勝自己。(35)
過去一元化的語言形象是與“現存的語言秩序”嚴格對應的,也就是于堅通過“總體話語”所定義的那種在詩歌中發聲的方式。一旦掌握了“總體話語”,或者說被它所吞噬,詩人便喪失了自己的“原聲”(36),也就是將自身的個體生存遮蔽起來,從而再也無法“把握一個詞最合適的位置”。“一個詞”凸顯出詩人個體存在的價值,在“總體話語”的包圍之下,它往往喪失自身的獨立性,屈服于總體性的權力之下,呈現出不真實的生存狀態。于堅認為詩人的天職就是祛除這種不真實的狀態,還原個體存在的本真,其行動就是從總體話語中突圍,將每一個詞的本真含義以“原聲”的形式重新說出來,這也是“戰勝語言”的意義。“原聲”就是日常生活的聲音,是在不戴任何角色面具的情形下,人自然發出的聲音,按照于堅的解讀,也應是人的本真存在所綻出的痕跡。如同《0檔案》所展現的那一代人的一生,原聲的歷史幾乎從他們進入集體生活之后就終止了;然而對于堅來說,由于幼年意外所導致的聽力受損,卻使他在成長過程中避免了被“總體話語”所同化,因此他感嘆:“有時我也很幸運,在這個原聲越來越少的世界上,我也只有依靠這上帝安排的殘疾,才擁有這些幸存的原聲啊。”(37)聲音之于于堅,從那時起就具有了特殊的含義,一方面作為詩人他的言說方式保留著“原聲”形態,使他得以從差異性的角度出發及早辨識兩種話語結構的對立,從而有助于突破“總體話語”的包圍,祛除遮蔽并還原生活的本真面貌;另一方面,話語結構所反映的實質指向思維結構,對于“總體話語”的警惕使他保持著與同代人的思維差異,他關于口語詩所提出的一系列詩學主張,包括“從‘隱喻中后退”(38)“知識是次要的”(39)等,無一不昭示著身為獨立的詩人個體,其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張力。在于堅的作品中,80年代的“總體話語”所表征的整體性的語言形象,被徹底解構,轉而呈現出個性十足的獨立形態,這種形態也成為90年代詩歌的典型特征,概言之就是“回到個人”。在于堅的倡導下,詩歌中的中國形象不再是單向度和總體性的,而是“為我們創造出一群新的平民自我形象”(40),這些“平民自我形象”并未站在過去那個總體形象的對立面,反而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共同構成了一個全新的生動、鮮活、凡俗、有生活氣息的中國形象。
在表現中國形象的多元結構方面,于堅通過《尚義街六號》《飛行》《對一只烏鴉的命名》《0檔案》等口語詩的上乘之作,創造了一套極具個性特征的詩歌話語體系,由此建構與表達了社會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形象,它們有別于80年代整體性的形象,呈現出局部性、個體性的特點,伴隨著八九十年代之際的經濟與文化發展,從而烙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90年代于堅并非孤軍奮戰,他的詩學觀念得到來自伊沙等更年輕詩人群體的呼應,伊沙在詩歌中所創立的語言形象,同樣反映出90年代中國的時代性。無獨有偶,伊沙同樣重視詩歌語言中的“聲音”要素,他對于口語或“說出”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于堅:
唐詩是說出來的——我不過是把可說的唐詩用自己的語言再說出一次罷了。所謂“口語”不過就是強調語言的可說性,是可說的語言。……還有一句話:“把每一年的圓都描標準,你不過得到了一個靶紙,而我要的是自然美麗的年輪。”(41)
從中可見伊沙對自己這部作品的滿意,他將成功歸因于“把可說的唐詩”“再說出一次”,也確實在創作中踐行了這一觀念,以穿越者的視角,從王維、李白、劉長卿、杜甫、孟郊、賈島、李商隱等詩人的作品出發,構筑了當代詩人心中華夏文明的巔峰想象,是在對古典中國的回眸中完成當代中國形象的建構。他化用許多唐詩的名句,改寫了諸多經典的文化意象,對于這些詩句和意象的選擇并非信手拈來,而是注入了十分考究的匠心,從中我們可以領會他關于“唐詩是說出來的”這番觀念背后的深意。譬如“松下問童子”“蒼蒼竹林寺”“近鄉情更怯”等名句,摻合在伊沙90年代的詩中,有著渾然一體的融洽感,這既是唐詩的口語性,又是伊沙等當代口語詩人從傳統中參悟的做詩手藝。伊沙上述言論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他的“年輪”觀;他認為詩人應當樹立“為全集寫作”(42)的理想,這里蘊含著終身寫作或將寫作融入日常生活的觀念,既然寫作是與詩人生命并肩而行的事業,那么每一年、每一日的書寫經驗,都將如涓涓細流匯入“全集”的江河里,這些經驗無疑在整體或局部意義上等同于詩人的日常生活,因而無需刻意的“描”或反復修改完善,“全集”的“年輪”正是因“自然”而“美麗”;當下的書寫屬于過去,未來的時間則將用于新的創作,這既是寫作的意義,又是生活的意義。
90年代以來從詩歌語言結構,即由聲音和詞語所表現的典型特征,向著以詩歌意象為代表的語言形象發生著更為直接和自然的過渡,總體性的意象體系向著碎片化、多元化的結構轉變,其表象為詩歌語言的口語化趨勢,背后的本質動因則是作為創作意向和行動的詩人主體與作為創作對象和目的的詩歌客體之間,不斷糾纏著對抗和遇合的張力,從80年代那種線性作用,悄然地變化為非線性作用,從而失去了高度統一的規律性,其附帶產物則是詩歌語言與非詩歌語言之間的界限愈加模糊,詩人身份的認同和確立也更為復雜。這種非線性作用所引發的矛盾到了新世紀愈加突出,詩歌的存在價值逐漸被消解甚至取代,諸多問題背后的原因尚未厘清,究其本源則必須回到90年代的時代語境中去。于堅與伊沙在90年代的詩歌創作及評論,澄清了諸多模棱兩可的觀念錯誤,還原了日常生活之于詩歌的本真價值,為我們樹立了一道堪稱經典的標桿。當我們從中國形象的角度看待90年代詩歌史,在這一形象學范疇之下,不難發現其基底正是于堅和伊沙等口語詩人所書寫乃至頌揚的日常生活,那么這一日常生活的理念蘊涵著怎樣的詩學觀念,相應的詩學觀念如何與中國形象的建構相輔相成,進而反過來影響詩人的創作乃至人生,就成為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作為“過渡”的90年代:“聲音”與為人生的詩學
以“聲音”為切入點,觀照詩歌中的話語結構和語言形象,形成了一種敘述詩歌史的獨特視角。90年代“聲音”的詩歌史呈現出與前一時期明顯的差異,圍繞“聲音”與中國形象的語義機制,一系列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背后的動因則歸于詩學觀念的裂變;同時在詩人群體內部,針對“知識分子”與“民間”等范疇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并最終在世紀之交匯成曠日持久的“口水”戰,尖銳對立的觀念“聲音”更是將詩學問題直接展示為“聲音”問題,從而為90年代詩歌史的重述蒙上了不可忽視的陰影。“聲音”問題的影響持續到了新世紀,然而當年那些針鋒相對的“罵聲”早已歸于沉寂,“聲音”的豐富性及其語言形象的多元化,在新世紀20余年的詩歌軌跡之上,正在完成新一輪總體話語和統一形象的建構;自80年代以來詩歌中的“聲音”問題,經過90年代的眾聲喧嘩之后,復歸整飭的話語秩序之中,就此而言,90年代更像詩歌史的一個承前啟后的過渡時期。應當看到,盡管這一時期關于“聲音”與中國形象的建構存在著百家爭鳴的個人化趨勢,因而很難用一種“聲音”或一類宏大的形象反映出統一的詩學觀念,但必須承認的是,正是這種從一元到多元、從整體到局部、從宏大敘事到微言敘事的轉變,以及在日常生活的話語體系下,完成從聲音到語言形象的建構,為90年代增添了難以磨滅的注腳。上述從“聲音”問題,到語言形象,再到詩學觀念的研究進路,自然地將我們的關注點引向了詩人們的日常生活與人生哲學。
詩歌中的中國形象,從聲音語詞及日常生活的脈絡出發,在時代的轉型過程中逐漸呈現多元化和日趨豐富的面貌,這一發展過程背后蘊藏著90年代與80年代所不同的思想觀念和精神追求,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來,詩歌中的中國形象變得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80年代那種“大我”與“小我”的對立、“總體話語”的包圍以及詩歌形象與常識觀念的顯著差異,到了90年代末乃至新世紀之后,早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日常生活為第一主題的形象塑造,以及口語詩歌的再度復興;這種詩歌創作方法乃至詩歌語言轉變背后的動因,就是詩學觀念的傳承與遷變。日常生活在90年代成為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彰顯出口語詩歌的獨特魅力,將“我手寫我口”確立為新詩的重要審美標準。聲音、詞語、情感、形象四位一體的表現形式,構成了白話詩歌或者說口語詩歌的核心范式,如黑格爾所說,該范式的終極目標與核心動因主要是其背后的“精神”(43)品質。這種精神品質,承繼了魯迅先生所說的“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44)的傳統價值觀,同時又承載了新的時代訴求;反映在詩歌上,可以說90年代口語詩的復興,既是“五四”新詩活的靈魂,又體現著當代中國社會的時代性與創新性。
“為人生”的詩學或者說“一切世法皆是詩法”(45)的詩歌傳統給予當代詩人的啟示,一方面是以“小我”擔當“大我”,須以極大的犧牲精神探索詩歌語言最恰切的時代表達;另一方面則是從“為詩歌”的詩學邁向“為人生”的詩學,臻于杜甫那般“詩人本身是詩”(46)的境界。90年代的詩人們面臨著更加艱難的身份認同和更加陌生化的價值標準統一等困境,他們中的少數人,在發現日常生活以及口語形式重要意義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找到了一條詩歌的超越之路,從詩歌語言的錘煉,到“詩人本身是詩”的主客體同一,再到融詩學于人生哲學,將創作責任與崗位責任緊密結合起來,致力于擘畫出“世間一切皆詩”(47)乃至詩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48)的宏偉藍圖。在此過程中,當代中國形象以日益多元化的形式得到了持續充分的豐富與完善,成為以“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的典型代表,最終實現“中國精神”的表達。
多年來,于堅潛心雕琢詩藝,始終保持著出色的創作水準,同時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地探求詩歌精神的本源,致力于復興中華文化傳統,將90年代詩歌所刻畫的關于中國形形色色的微觀切片融會到新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加以捏合、型塑及重構,期望提煉超越日常生活的價值與意義,藉此展現中國精神的實質。他踏上西部的文化苦旅,沉思中國生活與中國精神的起源,在布達拉宮找到了“精神生活的載體,屹立于世界最高的高原,活在過去與未來之中”(49);幾赴敦煌發掘“何謂真正的生活”,并領會了詩的精神本質,他說:“詩是通過語言來呈現神之無的最高形式……中國的神是供養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謂天人合一”(50);在嘉峪關找到古往今來洞察中華文明的精神密碼:“和其光,同其塵,以德化之,這就是中國。”(51)在自己的家鄉昆明,詩人朝向日常生活敞開存在之思,從而準確抓取生活之上的詩意。
生活在下,詩意在上,這是于堅關于寫詩的根本立場。正如《故鄉》所揭示的那樣:“我依舊知道/何處是母親的菜市場 何處是城隍廟的飛檐/我依舊聽見風鈴在響 看見蝙蝠穿著灰衣衫/……就像后天的盲者 我總是不由自主在虛無中/摸索故鄉的骨節 像是在扮演從前那些美麗的死者”(52);故鄉是于堅一切詩意的最初和根本來源,那些“故鄉的骨節”永遠存在于他的觀念之內,即使一些建筑永久地被拆除,即使在這個“失傳的時代”(53)世界熱衷于革新、人們不在乎逝去的經典,但它們始終存在于詩人對日常生活的這個故鄉根深蒂固的認識里,只有建立在這個認識之上,詩人才可以和“從前那些美麗的死者”對話,從中領悟詩神的啟示。于堅的“日常生活”“故鄉”和“中國的神”是一脈相承的,過去20年間的精神旅行也可看作詩人追本溯源的尋根之旅,這一行動不論對于詩人自身的創作,還是對于中國精神、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傳承,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除了詩人身份,伊沙還是一位大學老師和譯者,是當代青年詩人的伯樂和導師。伊沙翻譯的布考斯基詩集首次在國內出版,布氏以口語和俚語入詩,對美國底層社會給予深切同情及冷酷揭露,他的語言風格與伊沙本人極為相似,兩位詩人所持詩歌立場更是不謀而合。伊沙的詩尤其適合誦讀,聲音和詞語都恰到好處,沒有繁復的意象,從詞語到詞語,干脆利落,令人過目不忘;在詞的飛翔之上,常以辛辣、戲謔的諷刺,提醒閱讀者關注身邊的人和事,朝向現實生活的實事,用心生活,于日常生活之中體悟人的生存本質。詩人曾坦言布考斯基對他的影響,稱自90年代中期接觸布氏作品之后,無異于打開了新詩路。除了創作和翻譯詩歌作品外,伊沙還是20年來最重要的詩歌發現者與青年詩人引導者,其主要功績便是 “新詩典”的選編及評論工作。對此伊沙十分自豪:“十年來,《新世紀詩典》推薦詩的首數與天數是完全吻合的,一共3653首,出自1161位當代詩人之手,年度大獎——李白詩歌獎共評10屆,系列詩會舉辦了104場。……我毫不夸大地說,《新世紀詩典》是全球中文詩歌的第一平臺,我們的綜合影響力是沒有任何一個平臺可以相比的。”(54)伊沙始終是一位深切關注世情百態的詩人,從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平凡角落汲取詩意,他的詩學主張以及對待其他詩作的接納標準皆源自于此;他在創作之余不忘提攜青年詩人,通過身體力行地創建詩歌發表與交流平臺,見證了口語詩歌在新世紀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繁榮起來。
伊沙一手打造的《新世紀詩典》平臺,團結了一大批“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詩人,他們的“詩生活”或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口語詩歌創作,進一步表達了中國形象的多元結構,正如伊沙所說:“那些當代中國詩人/寫世界的詩/眼前呈現出一幅/遼闊的詩國版圖”(55)。這一“詩國版圖”的意象,無疑是當代中國形象在詩歌中的總體再現,它將眾說紛紜、話語喧嘩的民間詩人在“詩國”的命名之下統一起來,這是新的全球化語境中,中國詩歌帶給世界文學的影響和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詩歌中的中國形象,在80年代呈現的總體性與現代性話語特征,代表著那一時期中國詩人與西方“舶來”文化的融合與抗爭;在90年代呈現的多元性與傳統性話語特征,則代表著這一時期中國詩人超越了西方現代性的思維藩籬,轉而投身中華傳統文化的富礦之中,彰顯了文化自信及創新精神,那么新世紀以來在“詩國”的版圖上,更加年輕的一代中國詩人,他們的詩歌中則絲毫不見西方話語體系下“衰敗而殘存”(56)的中國形象,而是以煥然一新的姿態準備好了創造未來具有“中華性”(57)的中國形象,他們正是站在90年代口語詩人的肩膀上,因而有著不可限量的潛能和希望。
張二棍的詩《在鄉下,神是樸素的》喚起讀者心中關于故鄉、親情以及童年生活的記憶,作為超越之物的“神”在這首詩中被充分擬人化了,其特質在于“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喊冷”;喊便是大聲言說,即“太初有言”,因為人類的歷史便是從聲音語詞發端的,“神”自然也是如此。對“甜”與“冷”的漠然否定,呼應著題中之義“樸素”,“神”于是一方面指稱祖祖輩輩的先人,他們至死保存著沉默是金的品質,另一方面則象征著與當代青年漸行漸遠的精神起源,這起源同時也是歸宿。詩人通過有聲與噤言、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辯證法,批判了當今消費社會物質至上、流量為王的畸形現狀,為日益內卷的年輕人另辟蹊徑,彰顯出“樸素”的神圣意義。向傳統與民間尋求生活真諦的嘗試,在于堅和張二棍的作品中是一脈相承的,新一代詩人正是從90年代這一“過渡”時期的詩歌中收獲了靈感,進而創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外賣詩人”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同樣如此。這首詩有著緊湊的結構和明快的速度,其突出特征便是運用聲音語詞的組合,烘托出接納苦難、戰勝苦難進而在苦難中重生的浪漫氛圍。“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只一個“趕”字就刻畫出與時間賽跑的生活景象,從“風”到“刀子”,從“刀子”到“火”,個中苦難凝聚成響徹耳畔的聲音,這聲音所象征的年代似乎已經離我們遠去,戰天斗地的歲月也許不屬于多數辦公室白領,然而卻是外賣員的日常:“每天我都能遇到/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錘擊”與“淬火”呼應第一節的“刀子”“骨頭”與“火”,這些詞語背后伴隨著奮斗者的聲音,昭示出苦難過后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于堅和伊沙作為90年代“民間”詩人的代表人物,一度站在了詩歌論爭的風口浪尖,他們也曾堅定不移地發出“民間”詩人的“聲音”,如今一切歸于平淡,論爭的回響也漸行漸遠。20多年過去了,他們以及當年在“民間”聲音集結之下為數眾多的口語詩人,依然懷揣著個人的詩歌理想,將詩歌書寫經驗融入自身的生命體驗,依然自顧自地發出獨特的個體聲音,并以此為依托完成中國形象一個個微元或切面的表達與充實,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派“詩國”氣象浩然而生,如同于堅和伊沙不約而同所懷念的唐詩盛世,正在未來的詩歌歷史里生根。
四、結語
從聲音語詞出發,詩人在話語體系的建構中完成語言形象的塑造,并借此抒發特定的情志。如果將不同代際的中國詩人視作一個整體,在他們共同情志的基礎上,一種精神由此生發并不斷豐滿,直至形成不言自明的共同認識,也就是中國形象的觀念。這一觀念具有鮮明的感性特征,同時承載著復雜的理性因素,其形態取決于時代精神的共振,但精神實質始終如一,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依托民間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保持著不朽的生命力。
90年代由詩歌語言轉向引發了中國形象的多元化表達,其中最主要的動因在于,日常生活語言再度成為詩歌語言的主流。日常生活作為詩歌創作的土壤和基底,同時承載著中國形象建構與表達的使命;詩人們踐行“為人生”的詩學理念,通過日常生活語言建構并塑造了當代中國形象的一個個微觀表達,使得詩歌中的中國形象日益豐滿起來。
當我們回望90年代,眼前所躍動的不僅有于堅沉思中國生活與中國精神起源的文化苦旅,更有伊沙攜《新世紀詩典》3600多個日夜對千余位青年詩人的發現與引導。詩人一如既往地扎根現實社會,從日常生活中汲取詩意,不斷拓展人生詩學的領域。“為人生”的詩歌創作立場,是“五四”新文學的寶貴遺產,同時又標志著90年代詩人將民間崗位意識融入詩歌創作的努力嘗試。
在于堅和伊沙的詩歌中,我們看到這種“為人生”的詩學,其產物就是當代中國形象的一個個切面,它們交互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視覺與聽覺體驗共同體。“為人生”意味著詩是為最普遍和最廣泛的閱讀群體而創作,由此決定了詩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從而保證了當代詩歌的藝術經驗與審美品格從90年代延續至新世紀,并標志著一種創作范式的確立與發展,為未來詩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中國形象指出了重要方向。
注釋:
(1)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頁。
(2)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鄧冰艷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版,第81頁。
(3)(4) 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姚小平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7、59頁。
(5)(6)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3、12頁。
(7) 食指:《歸宿》,《食指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頁。
(8) 李憲瑜:《食指:朦朧詩人的“一個小小的傳統”》,《詩探索》1998年第1期。
(9) 朱文:《食指》,《達馬的語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
(10) 楊克主編:《90年代實力詩人詩選》,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11)(12)(13)(14)(15) 萬夏、瀟瀟:《后朦朧詩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8、248、870、870頁。
(16) 沈奇:《從“先鋒”到“常態”——先鋒詩歌二十年之反思與前瞻》,《詩探索》2006年第3期。
(17)(18)(19)(52) 于堅:《于堅詩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88、289、289、7頁。
(20) 柯雷:《拒絕的詩歌?——伊沙詩作中的音與意》,吳錦華、趙坤譯,《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7年第4期。
(21)(22)(23)(24)(25) 伊沙:《車過黃河》,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7、56、99、108頁。
(26)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27)(28)(29)(31) 唐小兵:《不息的震顫:論二十世紀詩歌的一個主題》,《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30) 北島:《履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0頁。
(32)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77頁。
(33)(40)(56)(57) 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7、272、466、466頁。
(34) 謝冕:《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75頁。
(35) 于堅:《關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自白)》,《于堅思想隨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頁。
(36)(37) 于堅:《原聲》,《于堅思想隨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1頁。
(38) 于堅:《棕皮手記·1994—1995》,《于堅思想隨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頁。
(39) 于堅:《棕皮手記·1997—1998》,《于堅思想隨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
(41)(42) 伊沙:《“我是為全集寫作的作家”——“詩生活”網站訪談錄》,《我在我說——伊沙訪談錄:1993—2017》,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4、74頁。
(43) 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5頁。
(44)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45)(46) 顧隨:《駝庵詩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3、35頁。
(47) 于堅:《棕皮手記·1982—1989》,《拒絕隱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48) 于堅:《讀史蒂文森》,《于堅思想隨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頁。
(49)(50)(51)(53) 于堅:《并非所有沙都被風吹散——西行四章》,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182、155、5頁。
(54) 伊沙:《新世紀詩典》(第十季),紐約新世紀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55) 伊沙:《〈新詩典〉的版圖(代編選者序)》,《新世紀詩典》(第七季),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
作者簡介:陳昶,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上海,200092。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