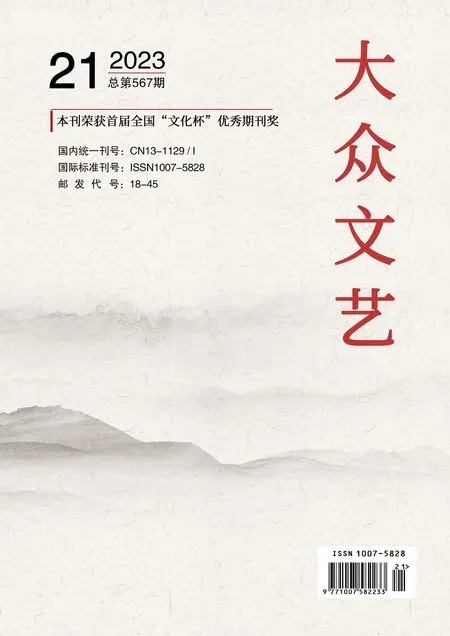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明蒙邊境形勢分析
閆 樸
(內(nèi)蒙古大學(xué),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妥歡帖睦爾北遷以后,北上的蒙古勢力與明朝進行了曠日持久的邊境戰(zhàn)爭。北元初期明朝多次北伐,此時的北元勢力雖然也有數(shù)次反擊,但是總體上看依然處于劣勢,且蒙古各部入貢的不在少數(shù)。從仁宣朝開始,蒙古諸部對明朝邊境的進攻開始增多,而土木堡之變后,明朝對北方蒙古的進攻多采用被動防御的方式。達延汗統(tǒng)一蒙古各部,實現(xiàn)中興,明蒙關(guān)系更加惡化,戰(zhàn)爭烈度變大,最后到嘉靖朝時發(fā)生了庚戌之變,俺答汗帶兵攻入京師周邊,明蒙戰(zhàn)爭進入白熱化。而明朝的邊境政策也從早期的多次北伐,到仁宣時候的縮邊,最后設(shè)立九邊,修繕長城。[1]明蒙戰(zhàn)爭的情況,反映出了蒙古由衰落到逐漸實現(xiàn)中興的過程,也相應(yīng)地反映出明帝國的逐漸衰落。而成化、弘治、正德時期,正是明蒙邊境情況趨于穩(wěn)定的時期[2],相比土木堡之前,邊境線更穩(wěn)定,但是中小型戰(zhàn)斗急劇增加。不過也正是常年的中小型邊境戰(zhàn)爭,促使了明蒙之間的和解,所以了解這一時期明朝北方的邊防形勢對于梳理明蒙關(guān)系的變化,明代對蒙古政策的變化等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三朝明蒙戰(zhàn)爭情況分析
對于兩朝的明蒙邊境形勢,我們根據(jù)明蒙雙方的情況,一共分成成化時期和弘治時期,武宗即位和達延汗統(tǒng)一蒙古后到應(yīng)州之戰(zhàn)時期以及應(yīng)州之戰(zhàn)后四個時期,對于戰(zhàn)爭情況的分析,主要通過明史本紀和外國八韃靼的部分進行統(tǒng)計,輔以各朝實錄和重要人物年譜等。
1.成化年間
1449年之后,也先與蒙古大汗脫脫不花以及繼任者陷入了內(nèi)亂,對于明朝邊境多以襲擾為主。而成化之后,由于蒙古內(nèi)部分裂,這種襲擾開始增多。總體來看,成化年間對蒙戰(zhàn)爭形勢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成化九年之前,然后是成化十六年之后。
據(jù)《明史》記載,成化“元年……秋七月……庚寅,毛里孩犯延綏,總兵官房能敗之。”①毛里孩是蒙古翁牛特部首領(lǐng),他和孛來擁立馬兒古兒吉思為蒙古大汗,自認為太師,以圖控制整個蒙古。馬兒古兒吉思因為七歲就被擁立為大汗,所以被明朝成為“小王子”而其后明代史料中均其后的蒙古大汗稱為小王子。此后,成化“二年…秋七月…戊戌,毛里孩犯固原。八月丁巳,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zhàn)死”②。此時的毛里孩并沒有停手的打算,此后在成化三年三月犯大同,四年十一月犯遼東,十二月犯延綏。其中在十月初六犯遼東,“指揮胡珍率軍來援,被賊射死”第二年,也就是成化五年十一月,毛里孩又犯延綏。面對不斷進犯的蒙古族勢力,明朝在成化六年開始了反擊,首先是正月,“大同總兵官楊信敗毛里孩于胡柴溝”。隨后的三月“詔延綏屯田。朱永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jiān)傅恭、顧恒監(jiān)軍,王越參贊軍務(wù),備阿羅出于延綏。”緊接著同年“秋七月壬午,朱永敗阿羅出于雙山堡。甲辰,總兵官房能敗阿羅出于開荒川”,明朝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此時孛羅忽渡過黃河與阿羅出會合。孛羅忽就是巴彥蒙克,巴圖蒙克的父親,也就是達延汗的父親。此后明史記載,成化八年,“延綏參將錢亮御毛里孩于安邊營,敗績,都指揮柏隆、陳英戰(zhàn)死。癿加思蘭犯固原、平?jīng)觥雹郏撕笫辉仑昧_忽、癿加思蘭屢入安邊營、花馬池,犯固原、寧夏、平?jīng)觥⑴R鞏、環(huán)慶,南至通渭”雙放在陜北和河套地區(qū),也就是今天的鄂爾多斯進行了多次的戰(zhàn)爭,直到成化九年“秋七月壬辰,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敗癿加思蘭于榆林澗。九月……庚子,王越襲滿都魯、孛羅忽、癿加思蘭于紅鹽池,大破之。諸部漸出河套。至此,在河套地區(qū)聚集威脅延綏和寧夏的蒙古勢力被清退。[3]
平靜了幾年之后,從成化十六年開始,明朝北方面臨的主要對手變成了瓦剌部亦思馬因,成化十六年二月戊寅,王越襲亦思馬因于威寧海子,破之。同年冬十二月庚申,亦思馬因犯大同。此后在成化十七年四月,十八年六月,亦思馬因分別進攻宣府和延綏。此后從成化十九年開始到成化二十三年,僅有記載小王子三次入寇,分別是大同,蘭州,甘州。④
綜上可以看出,成化年間明蒙戰(zhàn)爭形勢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分成了兩個階段。成化九年之前,雙方的主要對戰(zhàn)方向在陜北河套地區(qū),而韃靼部是明朝的主要對手。明軍也是經(jīng)過了先期的防御為主,在成化六年開始在延綏屯田備戰(zhàn),此后主動出擊,直到蒙古“諸部漸出河套”為止。此時的明朝還尚有一戰(zhàn)之力,并且取得了紅鹽池大捷,搗毀了韃靼部在河套地區(qū)的老巢。經(jīng)過了幾年的平靜后,成化十六年開始,明朝面對的侵擾主要來自瓦剌部,但是大都是搶掠,明軍也沒有主動出擊。而此后多年邊境較為安靜,韃靼部有幾次小規(guī)模的入侵。
第二個特點是成化前期,蒙古搶掠和入侵主要集中在冬季的十一十二和正月,而明朝的進攻集中在夏季。首先這與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有關(guān),冬季物資匱乏,蒙古各部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物資,于是便對明朝邊境進行擄掠。其次,冰封的黃河有利于蒙古軍隊的南下。而在成化后期,小王子多次犯邊卻多在夏季,由此可以證明,此時的蒙古各部已經(jīng)基本在河套地區(qū)駐牧[4],不需要冬季黃河結(jié)冰才能大量集結(jié)部隊進攻明朝邊境了。
2.弘治時期
弘治時期的邊防情況要比成化年間略好,明史記載,成化元年三月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弘治六年“五月,小王子犯寧夏,殺指揮趙璽”⑤,成化八年春正月壬子,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小王子于涼州。這里說到的小王子就是達延汗了,此時的達延汗還并未完成對東部蒙古的統(tǒng)一,但是已經(jīng)開始屢次犯邊了,但是其進攻方向主要是甘肅和寧夏一代。
弘治前期明蒙之間的戰(zhàn)爭并不多,但是從弘治十年開始,情況產(chǎn)生了變化。弘治十年,夏五月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十一年夏五月戊申,甘肅參將楊翥敗小王子于黑山。秋七月己酉,總制三邊都御史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后,敗之。弘治十三年到十四年,雙方進行了比較激烈的戰(zhàn)爭,明史記載十三年夏四月,火篩寇大同,游擊將軍王杲敗績于威遠衛(wèi)。五月癸亥,火篩大舉入寇大同左衛(wèi),游擊將軍張俊御卻之,秋七月小王子諸部寇大同。十二月辛丑,火篩寇大同,南掠百余里。是年,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這里的火篩是遼東蒙古人,為達延汗統(tǒng)一東部蒙古立下赫赫戰(zhàn)功的將領(lǐng)⑥。接著十四年,四月火篩諸部寇固原,秋七月丁未,泰寧衛(wèi)賊犯遼東,掠長勝諸屯堡,丁卯,朱暉、史琳襲小王子于河套,閏月乙酉,都指揮王泰御小王子于鹽池,戰(zhàn)死。是月,火篩諸部犯固原,大掠韋州、環(huán)縣、萌城、靈州。己巳,減光祿寺供應(yīng),如元年制。火篩諸部犯寧夏東路,可以說弘治十四年夏天,雙方在遼東到甘肅綿延千里的地方,進行了多次的戰(zhàn)爭。最終,蒙古勢力又一次“出河套”。此后在弘治十七年和十八年,僅有火篩入大同,小王子圍寧夏的小規(guī)模戰(zhàn)斗發(fā)生。
綜上可以看出,弘治時期的明蒙戰(zhàn)爭形勢要比成化年間略微寬松,但是在弘治中期進行了一次規(guī)模比較大的戰(zhàn)斗。雙方都有損失,蒙古“南掠百余里”和明朝“都指揮王泰于鹽池戰(zhàn)死”但是最終的結(jié)果依然是“寇出河套”,明朝此時還是占據(jù)尤其優(yōu)勢的。但是這個時期蒙古對明朝的掠奪已經(jīng)不是集中在冬春季節(jié),而是一年四季都在進行,可見當(dāng)時的明蒙戰(zhàn)爭形勢已經(jīng)轉(zhuǎn)向危機了。
3.武宗即位和達延汗統(tǒng)一蒙古后到應(yīng)州之戰(zhàn)時期
明武宗正德元年,達延汗也正好完成了對東部蒙古的統(tǒng)一,此時期的明蒙對抗形勢變成了掠奪情況略微減少,但是因武宗本人經(jīng)常親自駐守邊防導(dǎo)致出現(xiàn)了比較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的情況,比如弘治十八年五月戊申,小王子犯宣府,總兵官張俊敗績,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
此后在正德四年閏九月,小王子犯延綏,圍總兵官吳江于隴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戰(zhàn)死。正德六年時候,小王子入河套,犯沿邊諸堡。冬十月丁酉,甘州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于柴溝。正德九年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辛丑,小王子犯白羊口。己未,小王子入寧武關(guān),掠忻州、定襄、寧化。九月壬戌,犯宣府、蔚州。在一個月內(nèi),小王子在京師不遠的宣大附近進行了大肆地侵犯。而次年,秋七月乙未,小王子再犯薊州白羊口。⑦
可見正德中期,小王子對明朝邊境的掠奪態(tài)勢加重,這時也正好是達延汗統(tǒng)一東部蒙古后最強盛的時期。而在正德十二年,小王子犯陽和,掠應(yīng)州。丁未,親督諸軍御之,戰(zhàn)五日。辛亥,寇引去,駐蹕大同。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特點是隨著小王子統(tǒng)一東部蒙古,對明朝的進攻掠奪增多了起來,而明朝大部分處于被動防御的情況,而恰在正德時期,明代內(nèi)部叛亂四起⑧,牽制了明朝對于北方的邊防,直到應(yīng)州之戰(zhàn)。
4.應(yīng)州之戰(zhàn)后
應(yīng)州之戰(zhàn)后,武宗本紀只記載正德十五年七月,小王子犯宣府大同,而《明史外國八韃靼》中直到嘉靖四年之前,都無蒙古犯邊記錄。
關(guān)于應(yīng)州之戰(zhàn)的情況,總體來說是一個比較荒誕的戰(zhàn)爭,明軍從上到下出現(xiàn)了謊報戰(zhàn)功,浮夸戰(zhàn)爭的情況。但是從梳理觀察中看出,應(yīng)州之戰(zhàn)也對當(dāng)時明蒙戰(zhàn)爭形勢的變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為統(tǒng)一東蒙古左右翼的達延汗必然不只是想對明朝進行掠奪,從正德九年開始達延汗對明朝加強的軍事行動中不難看出其對于明朝領(lǐng)土的覬覦。《明史外國八韃靼》中記載,“十一年秋,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圍總兵王勛等于應(yīng)州”由此可見,當(dāng)時的達延汗所帶兵力已經(jīng)不單單為了搶劫了。那么在應(yīng)州明軍調(diào)動大量部隊,與達延汗進行野戰(zhàn),達延汗選擇最終退去,應(yīng)該對其的信心產(chǎn)生影響。另外在恰好達延汗也在此戰(zhàn)后很短時間內(nèi)去世,雖無法考證是否與本次戰(zhàn)役有關(guān),但是可見應(yīng)州之戰(zhàn)一定程度上確實是一個明蒙戰(zhàn)爭形式的轉(zhuǎn)折點。
二、總結(jié)
1.戰(zhàn)爭情況分析
首先,綜合以上三朝的明蒙邊境形勢,明史本紀中記載,成化年間明蒙進行了27次有一定規(guī)模的戰(zhàn)斗,明軍有都指揮焦政,柏隆、陳英、指揮胡珍等四位高級將領(lǐng)戰(zhàn)死。取得了威寧海子、胡柴溝、紅鹽池等幾次大捷,基本上處于進攻態(tài)勢。而在弘治年間,明蒙進行了17戰(zhàn)斗,都指揮王泰,指揮鄭瑀,趙璽等三位將領(lǐng)戰(zhàn)死。正德年間,明蒙進行了10次的戰(zhàn)斗,總制尚書才寬戰(zhàn)死。取得了柴溝、應(yīng)州等勝利。另外,成化年間明朝取得的大捷最多,但是犧牲的將領(lǐng)也最多,因為這個時期明軍有多次主動出擊,尤其是對于河套地區(qū)的爭奪。武宗時期的戰(zhàn)爭規(guī)模最大,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達延汗出兵數(shù)量遠超之前的情況。

表1 三朝明蒙戰(zhàn)情情況表
2.明代對蒙形勢逆轉(zhuǎn)在嘉靖朝開始
(1)應(yīng)州之戰(zhàn)的作用
應(yīng)州之戰(zhàn)雖然明史記載較少,戰(zhàn)果也比較荒誕。但是,此戰(zhàn)后,進入了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以來北方比較安定的一段時間,直到蒙古土默特部首領(lǐng)俺答汗崛起。對于此戰(zhàn)的特殊性,既要了解其成為三個時期最荒誕戰(zhàn)爭的原因,也要分析在此戰(zhàn)之后產(chǎn)生較長安定的原因。荒誕體現(xiàn)在武宗在位期間,各種玩世不恭的操作,而應(yīng)州之戰(zhàn)更是成了他一個娛樂秀場。而此戰(zhàn)后明蒙雙方迎來了相對比較長時間的和平,通過文章梳理,造成此的主要原因應(yīng)該是達延汗的去世導(dǎo)致的蒙古諸部的分裂,各部無暇顧及與明廷的戰(zhàn)爭。次要原因是正德時期對抗統(tǒng)一的蒙古入侵時明軍表現(xiàn)出的尚可一戰(zhàn)的戰(zhàn)斗力,雖然更像是正德皇帝的個人表演,但是在蒙古諸部看來,此時的明軍在北方依然可以大量地集結(jié),并且有一定的戰(zhàn)斗力,進攻明朝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做法。
正是因為這一時期,明蒙的對抗導(dǎo)致雙方都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沒能解決各自的內(nèi)部矛盾與需求,導(dǎo)致了明蒙雙方開始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明朝對蒙古政策開始發(fā)生轉(zhuǎn)變,最后成就了俺答封貢,明蒙關(guān)系回暖。同樣的,這一時期漫長的戰(zhàn)爭和對抗,也極大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而并不被我們重視比較荒誕的應(yīng)州之戰(zhàn),也許在明蒙戰(zhàn)爭史上有其更突出的作用。
(2)明代對蒙的劣勢和丟掉河套是從嘉靖朝開始的
根據(jù)之前的戰(zhàn)況分析,直到正德時期,明廷與北方蒙古尚有勝跡,柴溝、應(yīng)州皆算勝利。加上達延汗的去世,此時的北方邊境形式本來偏向于明朝,整體平穩(wěn)。但是嘉靖朝卻急轉(zhuǎn)直下,可見明代對蒙劣勢和丟掉河套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嘉靖朝對于邊境的不作為。首先,嘉靖上臺后,明廷中央就進行了長達三年半的大禮議之爭,嘉靖放任黨爭,致使明廷內(nèi)部烏煙瘴氣,內(nèi)閣首輔更換頻繁,政令無法有效地下達到地方。例如,明代最重要的軍事重鎮(zhèn)大同在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發(fā)生了兩次兵變。兵變原因皆為中央疏于管理邊政,以至于地方將帥貪腐橫行,地方兵丁不但無法得到應(yīng)有的獎勵,甚至還要被長官剝削。“官軍冒死斬獲賊級,向也多為主帥所奪,以媚權(quán)貴。或多為家丁所奪,以罔財利,是使之不戰(zhàn)也。劉灣曰:‘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⑨可見嘉靖初年,地方軍備之松弛,邊政問題遠超前朝之嚴重。[5]其次,任用嚴嵩等權(quán)奸,嚴嵩上臺后,朝綱混亂,導(dǎo)致明朝內(nèi)部烏煙瘴氣,為了討好世宗皇帝,嚴嵩以及邊鎮(zhèn)官員只注意獻媚,對于實際的邊防問題卻少報瞞報,而又在事態(tài)嚴重的情況下,嚴嵩鏟除異己,彈劾殺害夏言、曾銑等主張重視邊防的官員,以至于之后的官員們再也不敢提復(fù)套等主張,明蒙的邊境形勢自然也就更加嚴重了。
綜上所述,應(yīng)州之戰(zhàn)之后,本來形勢一片大好的北方邊境,因為嘉靖新朝初立而急轉(zhuǎn)直下,之后,河套地區(qū)已經(jīng)完全被蒙古占據(jù),明蒙互有攻防的狀態(tài)也徹底轉(zhuǎn)變成了明廷的消極防御,正因為如此也導(dǎo)致之后的庚戌之變。不過相對于明前期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三朝邊境形勢相對緩和,民族交流交融也在擴大,為以后的北方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礎(chǔ)。
注釋:
①(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162
②(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163
③(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168
④(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178
⑤ (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187
⑥ (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192
⑦(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0:202
⑧趙希萌.明代安化王叛亂研究[D].延安大學(xué),2022.20-23
⑨峨岷山人.譯語,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M].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2006: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