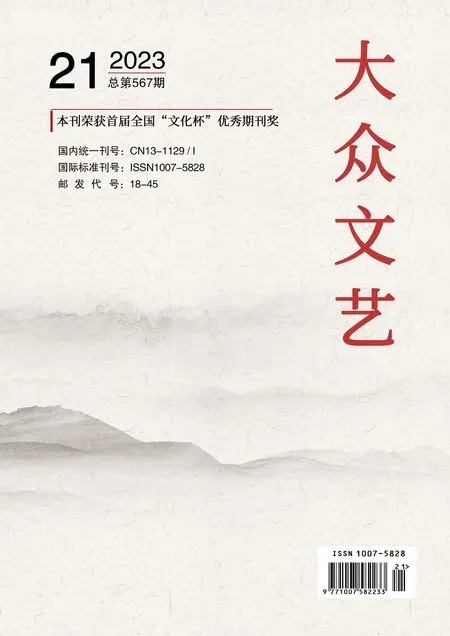淺析伍爾夫小說《到燈塔去》的空間敘事及美學意義*
李 嵐
(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南京 211100)
一、引言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是意識流小說的經典之作,其對傳統小說時間順序線性敘事的打破,致使空間維度的研究被高度重視,體現了英國現代主義小說“在小說形式和技巧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和創新”[1]。小說《到燈塔去》運用時空交叉和倒置的手法,使非線性的情節和內心獨白涉及多個時間和地點,以“燈塔”為線索講述了拉姆齊一家和幾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生活經歷,細致描繪了人物的內心意識流動與情感波動。
然而,伍爾夫的意識流技巧只是表層,表層之下呈現出空間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小說中的空間不僅是故事發生的場所背景,還進一步推動敘事,并呈現波瀾變換的人物內心世界,反映出人物處于精神危機時代等深刻意蘊,傳達作家的思想內涵。同時,伍爾夫作為“世界末日的美學家”[2],以物理空間、人物心理空間等空間類型及空間敘事建構小說事件所涉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的關系,形成空間意識并營造了美學效果,傳達其審美意圖。
二、《到燈塔去》物理空間敘事
時間和空間緊密相連,因此空間也是敘事研究的重要維度,可以指物理空間及地理空間,如人們居住的房屋、領土、山脈等。在《到燈塔去》中,物理空間是敘事不可缺少的場景,我們不僅要探索不同的物理空間以及空間的距離對敘事的作用,還需了解敘事背后蘊藏的伍爾夫的思想內涵。
首先,小說中位于斯凱島的海濱別墅是一個重要的物理空間,它是人物聚集活動且發生聯結的主要場所。小說的開篇場景就設置在這所別墅的房間里,相關人物到燈塔去的想法也產生于此。在伍爾夫筆下,這是一個遠離城市、充滿生機的空間布景,周圍有柔軟的深綠色草地、點綴著怒放的紫花和悅耳的海浪聲。事實上,由于這部小說帶有的自傳性質,赫布里底群島上的斯凱島是以英格蘭西南部康沃爾郡的圣?艾夫斯港為基礎創作而出的,矗立在海灣的房子俯瞰著戈德雷維燈塔,是伍爾夫和家人暑夏度假時的愉快地點,正如她自己所說,“這部作品展示了我父母親的性格、圣?艾夫斯的小島和我的童年……”[3]。小說中對海濱別墅空間的生動描述無疑反映出伍爾夫對早期生活的回溯,暗示著對兒時的想念。
然而,這所房子在多年間見證了世界的變幻滄桑,與第一部分《窗》中房間內外和諧溫暖的氛圍相比,這個空間在第二部分《歲月流逝》中產生了巨大變化,也是小說情節發生轉折的節點。房子因戰爭而遭到了破壞,房屋外曾經柔和的草坪沾滿落葉,大海波濤疊起。伍爾夫運用大量文字描寫夜晚的寒風和屋內的毀滅狀,“噼啪作響的掛簾,嘰嘰嘎嘎的木器,油漆剝落的桌腿,發霉長毛、失去光澤、裂縫破碎的砂鍋和瓷器”[4],一展戰爭殘酷性。同時,這個空間的毀滅也映照著曾經空間的溫馨,這里緊接著進行了時空跳躍,以空間里人們遺棄下的靴子、衣裙等進行敘事變換:“一度曾經多么充實而有生氣,纖纖玉手曾經匆匆忙忙地搭上衣鉤、扣上紐襟,梳妝鏡里曾經映照出玉貌花容,反射出一個空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一個身軀旋轉過來,一只手揮動一下,門開了,孩子們一窩蜂涌了進來,又走了出去”。
燈塔也是小說中的一個重要物理坐標,甚至第三部分的標題就是燈塔,這部分圍繞著前往燈塔的具體旅程,即人物與燈塔的物理空間逐漸拉近的過程。同時,這也可視為人物的精神旅途,因為其承載了人物共同的希望。小說中的燈塔固定在海的遠處,高大、堅實,在黑暗中閃光,具有永恒的象征意義,它代表了小兒子詹姆斯童年的夢想、拉姆齊夫人的內心之光,以及拉姆齊的家人和朋友們的精神家園。小說的結尾部分,當拉姆齊先生等人一齊前往燈塔之時,此時個體與燈塔有著空間距離的拉近。詹姆斯近距離望向他朝思暮想的燈塔,思緒回憶瞬間將他拉到過去的時空里,他感受到“那燈光似乎一直照到他們身邊,照到他們坐著的涼爽的、快活的花園里”。畫家莉麗在望向前往燈塔的船只時,內心同樣波瀾起伏,認為當拉姆齊先生乘船離她越來越遠時,她對他的感覺也在發生變化,直言“距離的作用多么巨大”。
小說中的物理空間及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的交織推動敘事進程,展現情節內容、人物思維的變換。伍爾夫對不同的空間及空間距離的描繪,都是其在啟發人們挖掘個人潛能、深入洞察客觀世界,思考人與世界本質的聯結。
三、《到燈塔去》人物心理空間敘事
空間不僅可以指物理空間、地理空間,也可指精神層面或社會屬性的空間,呈現出多種維度的空間敘事。《到燈塔去》中,伍爾夫運用內心獨白、感知印象等,描寫瞬間感受、回憶、想象等,讓人物直接訴說情感與思緒,展現微妙的心理變化過程以及主觀精神與客觀現實的交織。
伍爾夫筆下人物的自我意識通過身體所占據的空間獲得了空間性。書中不乏強調精神世界的語句——“在精神上和他距離遙遠”,“幾乎沒有一個人的軀體或心靈置身于黑暗之外”。書中在描寫拉姆齊夫人與燈塔燈光的關系時,涌現了大量對其心理的細致描寫,對于拉姆齊夫人來說,“穩定的、長長的光柱,就是她的光柱”。雖然燈塔離她的物理空間距離很遠,但當燈塔的光照射到她近距離的身旁時,她的心理空間已經與燈塔和燈光結合成一個整體,那燈光“深入探索她的思緒和心靈”;當她望向燈塔時,燈塔的光芒給她的內心帶來無盡的歡愉,“好像它要用它銀光閃閃的手指輕觸她頭腦中的一些密封的容器……狂喜陶醉的光芒,在她眼中閃爍,純潔喜悅的波濤,涌入她的心田”。小說中人物的心理空間敘事不僅是人物內心世界的同步,又因為主觀意識也是對外界的反映,其能夠展現出人物客觀世界中的故事進展。
人物的心理空間會把過去、現在、未來穿插在一起,這種意識流技巧下意識的流動本身就具有空間感。“柏格森認為……只有用文藝的、詩意的語言,將心理時間的‘綿延’不加邏輯切割、不加理性改造地記錄下來,才能傳達內心的真實”[5],這使人的主觀感覺和內心體驗占據本體地位,因此記憶在人的存在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記憶不僅和時間有關,它的空間特性也非常明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記憶總是和一些具體的空間(地方)聯系在一起。”[6]伍爾夫將“到燈塔去”的時空旅程構建對曾經的回憶,前往燈塔的途中,詹姆斯回想起已故不能赴燈塔的母親拉姆齊夫人,“他開始尾隨著她,走過了好幾個房間,最后他們走進一間藍光映照著的房間”。同時,到燈塔去的前后經歷也暗示了父子間關系的張力,在詹姆斯的這段回憶中,他意識到,“他的父親始終在追隨著他的思路,監視著它,使它顫抖,使它猶豫”,“他的父親把它打了個結,他要逃脫的話,只有拿起一把刀子把它刺進……他們似乎又互相疏遠了,各人悠閑自在互不相擾”。
小說中每時每刻的時間都充滿了無序、復雜的思緒,思緒中不同、隨機的事件可以延伸到隨時隨地,形成空間感。書中有許多“心理時間”上的綿延,以及對心理形成的新空間的偶遇與進入。在寫到拉姆齊先生精神崩潰的心理狀態時,“他所有的虛榮心……已經被粉碎了,被摧毀了。冒著槍林彈雨,威風凜凜,我們躍馬前行,沖過死亡的幽谷,排槍齊射,大炮轟鳴——突然他和莉麗?布里斯庫、威廉?班克斯面對面地撞見了。”在書寫拉姆齊夫人對自我的探尋時,也呈現了精神世界的廣闊無邊、思緒蔓延的跳躍感與空間感,自由的幻想可以超脫現狀,帶她抵達時空交錯的任意地點,“她內心……有許多她從未見識過的地方,其中有印度的平原;她覺得她正在掀開羅馬一所教堂厚厚的皮革門簾。”
四、《到燈塔去》空間美學意義
《到燈塔去》中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敘事結構給人立體的空間感,文學作為藝術的時空體,時間與空間不停交叉與融合,從美學角度來看,這使文學作品成為一種空間視覺藝術。因此,這部小說呈現出一幅流動的意識、時間和空間的圖畫。伍爾夫對繪畫的認知對她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她早期的短篇小說《墻上的斑點》和后期的小說《海浪》《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中都可以看到文字繪畫的影子”[7]。她自幼深受人文科學各領域的影響,其中家庭中以及布盧姆茨伯里文人團體(Bloomsbury Group)中的繪畫文化,尤其是強調光影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繪畫對伍爾夫的技巧產生極深影響。在此影響下,她堅持自身審美原則和立場,發揮她與生俱來的對世界的認知的非凡才能,創作出的作品往往運用大量色彩,追求光與色的奇妙配置,以取得審美效果。
小說中,伍爾夫運用了大量與繪畫有關的空間美學技巧,她在創作時就意識到色彩對物理空間及心理空間的塑造。書中的許多語句具有明顯的說服力,尤其在描寫莉麗在作畫時對色彩運用的糾結之時,將顏色與畫布上的空間、人物內心空間相連接。棕色的線條在畫布上能夠“圍住了一塊空間”,綠色和藍色在莉麗內心深處形成“難以對付的、蒼白的空間”,一種色彩與另一種色彩的融合不僅該展現畫作外表的華麗,更應形成畫面中穩定的立體感,于是“她開始用色彩一層層填補那片空白”。同時,與繪畫、線條有關的詞語和形式的頻繁使用,不僅使得時空染上色彩,還產生了新的場景。在目光所及的視野空間,她將不同方位的物一一繪色,將面前一望無際的海洋繪成蔚藍色,將遠處煙霧中散發朦朧光線的燈塔繪成灰白色,將右邊野草叢生的沙丘繪成綠色。這些著色的靜物在光色的組合映襯下,構建出了新的空間,綠色的沙丘在海水的激蕩下,“形成一道道柔和、低回的皺褶”的畫面。運用同樣的方法,伍爾夫在描寫色彩斑斕的果盤在燭光光輝的映照之下時,構造出一個神秘的光影空間,“挺直明亮的光輝,照亮了整個餐桌和桌子中央一盤淺黃淡紫的水果……那只果盤似乎有著巨大的體積和深度,就像是一個世界”。不僅如此,伍爾夫還擅用對比色,如紅色和藍色:“走到厚實的樹籬的缺口處,那兒用火紅的鐵柵防護著,它就像燃著煤塊的火盆一般通紅。在籬笆的缺口之間,可以見到海灣的一角,那藍色的海水,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湛藍。”色彩的對比突出了物體的相對位置,形成錯落、沖擊感極強的空間畫面。
伍爾夫還運用了繪畫中的距離法,將遠景的虛幻和近景的真實創造出無限的空間。她精心描繪遠近物體及其光色,遠處光的折射傳遞到近處呈現出多樣的顏色之時,無不呈現出空間感。當寫到遠處燈塔的光芒映照在波動洶涌的海浪上時,隨著時間的流逝,天色變換,光影效果隨之切換,被燈光照射的波濤從白日傍晚時“披上了銀裝”,最終變成“純粹是檸檬色的海浪滾滾而來”。同時,風景會根據觀看者的角度和距離而改變,前往燈塔的帆船隨著航程漸漸變成岸上莉麗眼中海上那個“棕色的斑點”。同樣,燈塔之于詹姆斯也因距離的不同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形象與感覺,他回憶起兒時記憶中的燈塔“是一座銀灰色的、神秘的寶塔”,放射著黃色的光芒;現在,當詹姆斯望向眼前的燈塔,“他能看見那些粉刷成白色的巖石……塔上劃著黑白的線條”。在黑暗的夜晚,遠處的燈塔放射出黃色的光,遙遠的光包含著無限的空間之美,而當近距離觀察燈塔時,它不過是一座棲息在巖石上光禿禿的黑白建筑。
五、結語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到燈塔去》關注空間問題,突出了物理空間、心理空間及其與人物的聯結和對敘事的推動作用。小說的情節主線是討論明天是否去燈塔,但這簡單的情節由不同的空間類型、人物的意識流動以及人與物間不同的空間距離等而被創作成一部小說,展現了物理空間也是一個宏大的、流動的、變幻的世界,人物在客觀世界中的認識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局限性。同時,伍爾夫運用細膩的文字表達了內與外、遠與近、幻與真、光與影的對比,渲染出各種空間距離和視角,使空間敘事有了生命力,使敘事呈現出畫面感,引發聯想和想象,產生空間的美學效果。由此,《到燈塔去》的空間不僅是小說情節發生的場所背景,同時助推故事情節發展,并呈現變換、遼闊的人物精神世界,傳達作家的思想內涵與審美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