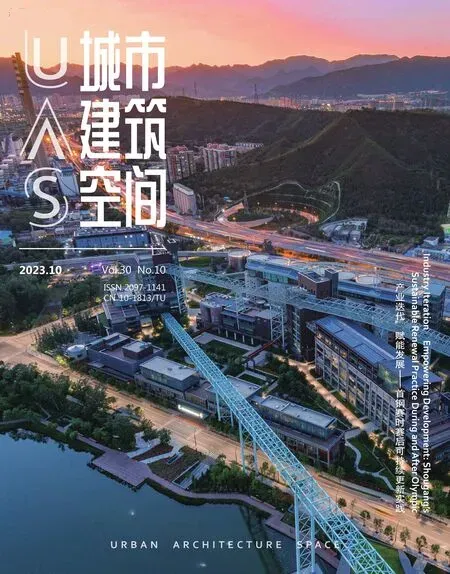場景營城,城景共融
——開封文化景觀營造策略
朱婕妤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傳承與保護面臨巨大挑戰,城市文化景觀營造需創新路徑。現存問題包括遺址文物、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和利用不當導致城市記憶載體受損,地方文化挖掘及利用不足導致其內涵扁平化與異化,遺址文物、歷史文化街區等城市文化載體周邊環境風貌不協調使其成為城市文化孤島。通過場景營造構建“城景共融”的開封文化景觀集群,為其他城市文化傳播與景觀營造提供參考。
城市更新;城市文化;景觀;遺址文物
0 引言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粗放型增量建設逐漸轉變為精致型存量更新。優化城市功能與提升城市品質成為城市更新的核心命題,大刀闊斧的拆舊建新活動使城市面貌發生改變。而現代、精致、高效的城市空間改造使大量蘊含城市歷史文化的標識和印跡遭到破壞,繁榮的都市文化已阻斷還鄉游子的歸家之路[1],城市在更新中逐漸失去集體記憶。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除物質層面的“硬更新”外,還需傳承與發揚城市文化,即文化的“軟更新”,涉及社會凝聚力、地方認同感、文化自信心等要素[2]。遺址文物是傳承城市歷史文脈的有形資產,如何“軟硬結合”妥善保存和延續城市歷史文脈、留住城市記憶、傳播地方文化、營造適宜的城市景觀是風景園林設計師的社會責任。
1 基于城市文化傳播的景觀營造設計探索
1.1 城市文化核心要素
城市文化包括以城市各類遺址所承載的歷史文化、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城市記憶。城市遺址記錄著城市自然與人文的變遷過程;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輔助城市文化的全息展現與城市文脈的延續;城市記憶包括場地記憶、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3],展示城市歷史文化,為城市增添豐富的地域氣質與人文情懷,是城市文化外化表達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1.2 現存問題
1.2.1 遺址文物、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和利用不當導致城市記憶載體受損
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①對遺產自身重要性和價值認識不足,未嚴格落實遺址本體與周邊環境的保護要求;②遺址公園內過量、不合宜的游覽活動致使遺址及周邊環境遭受不可逆的破壞(見圖1,2);③遺址與遺址公園空間比例失調,公園內景觀喧賓奪主,增加大量現代活動的遺址公園激發了游客的負面情緒,使具有“正面價值”的遺址淪為城市中的“負面空間”[4];④從行政區劃的變更,到街區尺度“生活原真性”及遺址本體與周邊環境等物質層面,對遺址的“原真性”造成沖擊[5]。

1 損毀的城墻(開封城墻三期)

2 損毀的地面(開封城墻三期)
1.2.2 地方文化挖掘及利用不足導致其內涵扁平化與異化
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①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城市記憶被忽視,城市文化展示視角狹窄導致人們“沒得看”或“看不懂”[6];②強調城市文化某單一價值而忽略其價值多元性,導致地方文化開發利用的邊際效用遞減[7];③缺乏對地方文化深入研究,其內涵表達相對膚淺、潦草甚至重復,因篩選不當,植入與遺址或歷史文化街區文化無關的景觀最終導致城市文化認知混亂;④地方文化的景觀營造手法單一,嫁接舶來品式景觀導致城市文化表達方式不中不洋、不倫不類(見圖3)。

3 城墻景觀與遺址風貌不協調
1.2.3 遺址文物、歷史文化街區等城市文化載體周邊環境風貌不協調使其成為城市文化孤島
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①遺址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周邊環境日新月異,面臨喪失歷史感和歷史文脈被割裂的窘境;②遺址文物、歷史文化街區逐漸衰退,從城市文化生活中心轉變為生活環境惡劣、基礎設施陳舊、建筑風貌殘損及公共空間破碎的城市待更新區;③環境營造及后期運營方式欠佳,“文化搭臺,地產唱戲”,運營商偏離遺產保護與展示的初衷,致使城市歷史文化載體負面評價增加而受到社會輿論威脅[8-9]。
1.2.4 調研結果
需從以下4個方面解決問題:①保護城市記憶載體免受建設性破壞;②采用適宜的造景手法展現與延續城市文化內涵并保護城市記憶;③采用適宜的設計手法使遺址與周邊環境進行對話;④有效控制與引導城市記憶載體周邊環境風貌。
2 景觀營造手法的傳承、演繹與創新
2.1 城市文化景觀展現方式
城市文化景觀展現方式應重點關注自然與城市、歷史與當代及審美體驗3個維度[10]。宏觀上,利用景觀要素將區域內多元城市建筑空間——點狀遺址文物與片狀歷史文化街區進行連接,形成具有共同記憶和文化內涵的城市意象;中觀上,通過景觀將碎片化的城市歷史重新黏合,喚醒城市集體記憶;微觀上,采用傳統+現代的景觀設計手法,通過有形的物體傳達給大眾使城市文化可領略、可感知。
2.2 城市文化景觀營造手法類型
“巧于因借、精在體宜”是《園冶》的核心思想,借景是我國傳統園林的造景手法。其中“因”指因勢利導、因地制宜[11];“借”指近借、遠借、鄰借、互借、仰借、俯借、應時借、遐想借等手法,所借之物包括形、色、聲、香、人、影等[12]。孟兆禎院士在《園衍》中歸納總結的“園林六法”被廣泛應用于現代景觀設計實踐[13]。我國傳統園林妙造自然、物我混一的“入境式”景觀使觀者身臨其境,并通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方式使其進入設計師營造的“意境”。
城市文化景觀營造手法包括以下類型:①傳承,采用傳統造園手法營造的古典園林案例不勝枚舉;②演繹,基于對傳統園林的深刻理解,采用現代設計手法營造三境——畫境、詩境與意境;③創新,在傳統造園理念和手法基礎上,實現從“中式”向“新中式”、從“造景”向“造場景”、從文物單項陳列向文化矩陣輸出,從封閉公園向開放空間如城市廣場、歷史文化街區的轉變。
3 開封文化景觀營造策略
以“五湖六河”“環城公園”“一渠六河”及“四廂二十坊”為主題的城市空間格局的再現,是開封古城基于自然與“宋韻”的人文、景觀空間重塑。有形的遺址文物與無形的城市文化保護、傳承、展示及城市文化景觀的營造至關重要。基于現存問題,采用《園冶》中傳統造園手法,通過場景營造構建“城景共融”的開封文化景觀集群。
3.1 挖掘城市記憶,通過場景化營造實現沉浸式游覽
《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錄》是記錄開封北宋時期汴梁城的圖文史料,是開封城市更新和文化復興的重要參考。清明上河園展示了開封以宋式建筑、宋式園林景觀等為主的物質文化和以皇家文化、民俗文化、府衙文化、曲藝文化、書畫藝術為主的非物質文化,充分展現出北宋時期開封的市井百態、市井風物。文化景觀形象鮮明、景觀序列清晰、空間層次豐富,描繪出北宋時期鮮活的社會生活畫卷。
通過場景營造,記錄并傳播城市記憶,引起人們的集體共鳴。隨著人們的消費水平提升,游客更加注重游覽過程的新鮮度、體驗感和互動性,體驗經濟應運而生。現代科技為風景旅游賦能,運用數字成像、定位系統、虛擬現實等技術,融合文化創意等元素,讓游客深度參與互動體驗。此種“身臨其境”的沉浸式游覽為游客打開了走進歷史的大門[14]。
3.2 消除文化孤島,通過城景共融實現開封“全城一景”
將開封古城內點狀物質文化遺產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挖掘、景觀重現,使原本孤立的皇家文化、府衙文化、民俗文化版塊連綿成片,構筑開封古城“全城一景”的格局。充分利用各類文字典籍、書畫藝術瑰寶進行創意化“宋韻”主題文化景觀再現,結合各類休閑娛樂活動,實現古城“宋都”場景營造、城景共融。
3.2.1 以《壽山艮岳》引領開封古城東北片區更新
開封古城水系一期與艮岳時空重疊,以《壽山艮岳》為藍本進行龍亭北1號地塊片區綜合開發,中心水系景區仍“按圖度地”進行風貌營造。根據《艮岳記》記載,以大方沼、絳霄樓為中心,北側為瓊津殿-高陽酒肆組團,南側為雁池-和榮廳組團,西側為環山館-神運鋒組團,東側為八仙館-書館組團。外圍布置艮岳園林博物館、新宋式建筑住宅片區和公共商業步行街,打造集居住、商業、文旅、研學教育等功能于一體的北宋皇家園林式街區(見圖4)。
3.2.2 以《清明上河圖》引領開封古城西北片區更新
分析《清明上河圖》空間序列的劃分與變化,充分挖掘清明上河園的結構美學、序列美學,形成既有古韻又有新意的城市文化旅游景區,實現清明上河園景區有機更新[15]。參考《清明上河圖》中的游覽路徑、街區邊界和空間節點的不同處理方式,優化御河北段七盛角處街道尺度并豐富街道景觀,為游覽路徑上的街道風貌提供充分展示歷史文脈和生活氣息的可能性;將歷史文化街區與周邊環境采用循序漸進的手法進行連接,最終實現歷史文化街區、新建古風街區與周邊環境的融合與滲透。多元化業態與多樣化建筑、景觀形式既能保證片區內原住居民生活狀態得以延續,還能有效兼顧游客沉浸式體驗地方文化的需求。
3.2.3 各類體驗活動再現《東京夢華錄》
連通包公湖和龍亭湖的開封古城水系二期(御河)充分展示了北宋民俗文化,分析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的四季節令和北宋習俗,在河道兩側布置瓦肆勾欄、正店、腳店、戲樓、船舫,游客沉浸式游覽于《清明上河圖》;夜間以河南地方曲藝演藝、民俗表演為主,實現三維立體的“聲、像”環繞;宋式橋梁的夜景燈光形成時光走廊,游客行走其間瞬間夢回“汴梁城”(見圖5);在河湖交匯口的北岸布置以文創體驗、休閑餐飲為主的集錦園和七盛角,實現開封古城西北部片區的整體更新(見圖6)。

6 集錦園與七盛角鳥瞰
4 結語
《園冶》與《園衍》均是風景園林設計師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開拓、創新與實踐,實現風景園林理論與技法“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風景園林理論需日新其舊,風景園林技法也需常用常新,城市文化景觀營造需要更多的實踐案例,以更加廣闊的視野積極探索,不斷完善新時代背景下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理論與方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