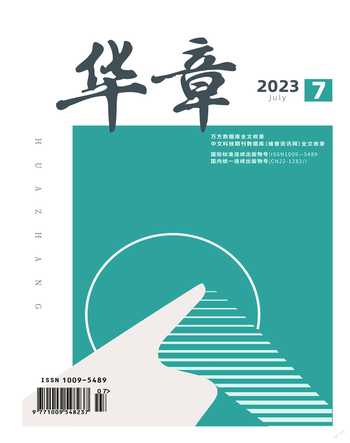大數據證據應用辨析
[摘 要]隨著信息化、大數據的發展,司法實踐日益走向數字化、數據化,傳統的證物等證據類型無法滿足司法實踐的需求。我國現有訴訟程序采用了法定的證據類型,在立法上沒有對大數據證據的類型做出規定;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大數據證據類型的認定沒有統一的標準。在確保大數據的真實性、大數據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以及大數據證據的可信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數據證據的規則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關鍵詞]大數據;證據屬性;大數據證據
一、大數據證據的內涵與特征
證據是載體和內容的統一。證據的留存形式體現在證據載體上,證據內容是記錄事件發展的進程,是完成證明待證事實所存在的可能性的客觀依據。大數據因其特性具備成為證據材料的客觀屬性,構成了從大數據與證據制度角度進行互動探討“大數據證據”的相關問題的邏輯前提。
(一)大數據證據的內涵
大數據是電子證據在發展中所迭代的產物。目前,學界對大數據證據并沒有清晰、統一的概念,有共識的是大數據證據是在對海量數據收集、分析和提煉中得出的相關結論。有學者將大數據證據界定為基于海量電子數據形成的分析結果或報告[1],這種看法難以充分反映出大數據的獨特特征;也有學者將利用大數據技術得到的材料皆稱為大數據證據[2],這種看法過于廣泛,以致對大數據證據的理解更加模糊;還有學者從方法論角度出發,提出大數據證據能產生實用意義上的增值價值[3],這是一種從價值出發的觀點,這種看法實際上是在用大數據來證明,而不是用大數據作為證據。
(二)大數據證據的特征
大數據和電子證據的組成部分都是數據,但是兩者有本質的不同。通過分析大數據證據的內涵及與司法的關聯性,可以較為清晰地發現,大數據證據具有如下特點:1.數據規模大,數據來源多樣;2.數據更新速度快;3.數據元素之間可能有復雜的關聯和相互影響;4.具有大量實時可視化分析,可深入地理解數據;5.更大面積和更快速度促進數據驅動的決策。
一方面,大數據證據的基礎是海量電子數據,規模大且類型多,相較于早期一條一套的電子數據,大數據證據以信息量大為新特色[4]。另一方面,大數據證據不是簡單地列出大量數據,而是經過了復雜處理。目前,將大數據證據視為電子數據二次加工的觀點已為眾多學者所認可和采納,成為大數據證據的公認特點[5]。再者,大數據證據的重新處理是基于數據挖掘、數據統計、數字模型、數據碰撞等技術的應用,使大數據證據具有與電子數據相區別的新的價值增量。對比傳統證據間僅存在一種相關性,或是強聯系或弱聯系,大數據證據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即基本資料的相關性較弱,分析結論卻具有較強的相關性。
二、大數據證據的實踐發展
證據是對案件事實進行論證的基礎,能夠充分地證明案情。但不是每一種材料都可以作為證據來證實案件。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的刑事立法對證據的規定做了許多相應的改變調整。1996年刑事訴訟法將證據界定為所有可以證實案情真相的事實,并將其嚴格限制在七類;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證據類型作了修訂,規定所有能夠證明案情的材料均為證據。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證據類型的規定采取了封閉式的列舉方法;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表述呈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度。在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增加了電子證據的電子數據,電子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促進了電子證據的形成。這種類型的證據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樣,大數據證據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雖然大數據證據沒有被我國立法“正名”,但是在實踐中靠大數據來證實案件的真實,已成為一種客觀需求。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大數據分析,確認其身份,是偵查案件事實的一種重要方法。盡管在司法審判中運用大數據證據的案例很多,但是在法官和公訴人看來,仍然存在著相對保守的觀點,因為大數據證據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很難界定它的形式。此時,法官一般會采用兩種方法:一是把大量的數據資料轉換成書證、鑒定意見等;二是以大數據的分析結果為輔助材料,以證明案情。就目前學術界對大數據證據的認定,大多還是否定大數據證據的獨立法律類型。
回顧我國的法律證據體系,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法律證據的類型也在不斷地被發展與運用,大數據證據也是一樣,這種類型的證據將成為數字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法律結果。
三、大數據證據的適用
大數據技術是大數據偵查的關鍵技術之一。大數據是利用互聯網、計算機等科學技術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偵查方式,利用了現代科學技術對大量數據進行采集、分析、驗證,為查明案件事實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在刻畫事實案件全景圖、證據輔助補強和進行時空的同一性認定等方面上具有重要作用。
(一)全面刻畫案件事實
對案件的全景影像進行描述,能夠更有效、客觀地反映案件的基本狀況。當然,這種偵查手段的實施不可避免地會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產生一定的沖擊,特別是對個人信息權的侵害[6]。通過大數據技術,將大量數據庫進行比對,得出是否是同一個人的結論。公民在做某件事的時候,不僅會留下身體上的痕跡,在網絡活動中,也會在網絡上留下痕跡。案件中的當事人各種信息、數據載體和生活軌跡等行為基本被數據化。這些被數據化的信息,在智能算法和關聯比對中進行串聯溝通,形成證據法學所日益期盼的信息資源與數據庫。日趨完善的資源和信息庫,有利于克服證據法學中的信息數據資源稀缺的根本矛盾。
司法機關在進行大數據調查時,通過大量數據的對比,使其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一致性,全面地刻畫案件事實,快速、準確地鎖定犯罪嫌疑人。通過大數據進行事實刻畫,無限接近還原事實狀態,也將利于事實的認定者以現在的眼光去認定過去的案件。
(二)輔助證明與補強功能
在庭審等司法活動中,大數據證據作為一種輔助性的證據的內涵是:盡管大數據證據的生成和要被證實的對象的出現并不一定關聯,并且二者之間沒有任何的證明邏輯關系[7],但它對其他證據的補充、印證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分析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備犯罪的條件,以及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否重疊等因素,判斷犯罪行為是否有可能影響到證人證詞的可信性。大數據證據對言辭證據的補充,可以避免法庭根據法律規定的證據,直接對案件進行定性。
通過對多項證據進行補充,使其成為一個閉環的證據鏈,達到能夠證實案件事實的目的。例如行賄受賄案件中,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可看出,在一定時期內行賄者與受賄者是否進行過密切聯系,受賄者在同一時間是否提取了大量的現金,接受賄賂的人和被賄賂的人在同一時間是否前往同一地點。這些資料雖不能直接證實行賄受賄事實,卻能對供述、口供和其他目擊者的證言進行佐證。
(三)大數據證據的事實認定
大數據證據往往是以間接的方式來達到證明能力,與其他的間接證據類似,與其他證據相結合,才能充分地證明整個案件事實。
在刑事訴訟中,大數據證據以間接證據方式來證實案件。大數據證據除能證實網絡犯罪中所涉及的數額之外,還對于認定特定的犯罪主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判定犯罪嫌疑人是以集資詐騙罪定罪,還是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論處,關鍵在于確定被告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對主觀要件的認定,需要從客觀上的外在表現著手,例如掌握涉案資金的流向,以及對其實際使用情況的分析、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在實際操作中,對此類案件的資金流向往往又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無法跟蹤犯罪嫌疑人的資金流向。因此,司法機關利用大數據的運算能力,對資金賬戶、賬戶實際控制人的動向、手機上的數據進行分析,能夠得出資金流向分析報告,報告的間接證明能夠起到對案件事實認定的作用,甚至對于定罪量刑也有依據作用。
四、大數據證據適用完善規則
要想使大數據證據在司法中的應用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就必須不斷地積累大數據技術在實踐中應用的案例,總結法官們的實踐智慧,使之成為適用于具體案例的司法慣例規則,為法官和律師的司法行為提供指導。
(一)大數據證據能力的規定
大數據證據在收集、審查、認定、采信等過程中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大數據證據所基于的海量數據、算法分析結果的真實與否,都是影響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關鍵。大數據強調的是一種思想的應用,它可以用特定的方法,洞察到事件的原因和價值。大數據技術通過對特定的算法進行分析,使整個案件的證據鏈更加完整、更加真實,最大限度地再現了案件事實。
建立大數據證據合法性的原則必須基于兩方面:第一,對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數據分析的原始狀態下的數據提取、收集、儲存是否合法;第二,要保障大數據技術的正常運作。對前者的合法性審查側重于偵查階段,后者則側重于技術方面的審查。大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存儲是偵查工作的首要環節,因此,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存儲都必須按照相關的法規來進行。提取原始數據時,必須遵循國家安全局頒布的電子數據收集規則,如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時,必須由兩個以上的調查員同時到場,采用適當的技術措施。
在網絡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不能只依賴于傳統的偵查方式。在偵查階段,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來檢驗大量的數據的合法性,保證原始數據的提取、收集程序合法,偵查材料、筆錄、清單等的規范。
(二)大數據的真實性規制
大數據證據的真實性原則是對信息的真實性進行分析。首先,大數據具有混合特征,體現在原始數據的基礎上。在大數據時代,數據來源廣泛、種類規模龐大,所以很容易出現混雜現象,而人類在數據處理上的表現就是精確性,而不是混雜。其次,數據與數據可以兼容[8]。在小數據時代,所有的數據都是由單個的手工收集而成,數量很少。在大數據時代,在分析和預測行為時,任何一個數據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在應用大數據技術時,面對大量數據的混雜,要力求數據的精確性。從證據的角度來看,對于大數據技術在司法中的運用,大量數據的準確性直接影響數據的真實性。人們對大數據證據的真實性質疑,主要是因為大數據技術所能處理的大量數據的準確性和其內在算法的可信度。要確保大數據證據的真實性,必須從數據的來源保證其真實性。
在建立大數據證據的真實性規則時,必須考慮到大數據證據的合理性和算法技術在大數據證據中的應用。通過與區塊鏈技術的結合,可以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其次,將大數據技術中的算法模型公之于眾,降低算法的“黑箱”,使各方利用庭審技術,對海量的證據質疑和評判。
(三)大數據證據的排除規則
證據排除有兩種情況:第一,對非法證據的排除。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途徑獲得的,比如被告人的供詞、口供、物證等,這些屬于違法證據。第二,對瑕疵證據的排除,以確保證據的客觀真實性。《刑事訴訟法》和“三高兩部”共同頒布的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條文,并沒有將大數據證據納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討論空間,導致這種類型的證據不能排除非法證據。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大數據排除規則。
對大數據的證據類型的判斷,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對證據有無缺陷的偵查也要從大數據的形成過程入手,從大數據集的篩選、提取和技術上對其進行處理。可以參照“兩高三部”關于審理死刑案件的證據審查制度,收集、提取數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收集數據的范圍、對象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如果數據來源、提取、收集程序有問題,則由司法機關作出合理的解釋。另外,在數據集的技術和算法分析中,必須確保大數據技術中的算法經過驗證,證據的出具機構必須具有相應的資質,并且必須有兩個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提供專業意見。如果不符合上述基本條件,且無法解釋其原因,則應將其作為缺陷證據予以排除。
大數據證據排除規則是對大數據證據合法性和真實性規則的逆向處理,不允許偵查機關、控訴機關對不符合合法性規則和真實性規則的證據容忍,允許偵查機關和控訴機關作出糾正和合理的解釋。
結束語
大數據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數據庫收集、儲存、管理、分析的規模。大數據注重思維的應用,可以用一種獨特的方法來分析一件事情的意義和價值。與傳統的信息技術相比,大數據技術具有更高的科學性和現代性,以此在訴訟中運用大數據技術、規定大數據證據有關規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周濤.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J].人力資源管理,2013(3):174.
[2]劉品新.論大數據證據[J].2021(2019-1):21-34.
[3]何家弘,鄧昌智,張桂勇等.大數據偵查給證據法帶來的挑戰[J].人民檢察,2018(1):54-57.
[4]謝君澤.論大數據證明[J].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2):125-137.
[5]王祿生.論法律大數據“領域理論”的構建[J].中國法學,2020(2):256-279.
[6]胡銘,張傳璽.大數據時代偵查權的擴張與規制[J].法學論壇,2021,36(3):5-14.
[7]周洪波.實質證據與輔助證據[J].法學研究,2011,33(3):157-174.
[8]高原,崔增寶.大數據哲學批判[J].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18(4):6-11.
作者簡介:田巍(1999— ),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三峽大學法學系,在讀碩士。
研究方向:民事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