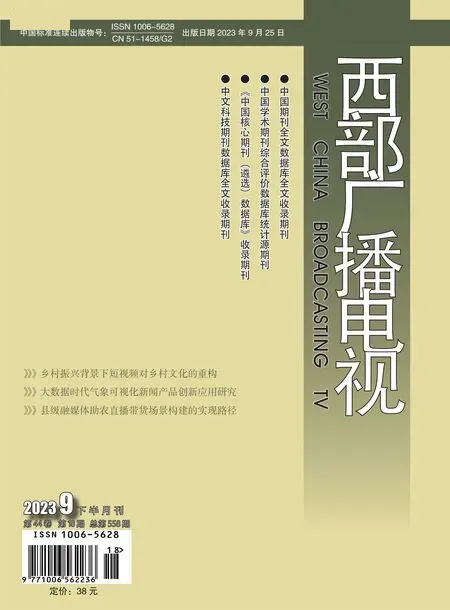現實主義電影《何以為家》的藝術探析
受希文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聯合作戰學院)
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曾提出,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大多通過真實還原社會本貌、暴露存在的現實問題、剖析人性中的矛盾,引發大眾對社會事件的思考。《何以為家》是由黎巴嫩、法國、美國聯合制作,黎巴嫩導演娜丁·拉巴基執導,贊恩·阿爾·拉菲亞、約丹諾斯·希費羅聯合主演的一部劇情片。影片通過講述一個12 歲黎巴嫩小男孩贊恩的悲慘生活遭遇,展現出了黎巴嫩底層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現狀,且贊恩在現實生活中同樣是一個真實的“兒童難民”。本片在2018 年舉行的第71 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獎及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并在2019 年第91 屆奧斯卡金像獎上獲得最佳外語片提名。這部聚焦了黎巴嫩底層人民生活困境的電影因其反映的真實人性糾葛與社會現實問題,也引起了國內觀眾的情感共鳴和深度思考,值得進一步分析和探究。
1 斯德哥爾摩式的悲劇循環
在近幾年中,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呈現出一種復歸影壇的趨勢,從國外《綠皮書》《小偷家族》《寄生蟲》《宿敵》,到國內的《我不是藥神》《暴裂無聲》《學爸》《孤注一擲》等。這些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多以關注社會、直面現實、聚焦問題、探析人性為基點展開各自的敘述,在以宏大制作、感官刺激、明星云集等為主要影視宣傳市場的當下,是一股引人深思的清流。影片《何以為家》上映后,受眾關注的焦點大多在贊恩的父母身上,大部分言論是在譴責贊恩父母的行為,抨擊作為父母的他們沒有盡到最基本的養育之責,因為生而不養,導致“無以為家”。縱觀全片,悲劇的出現原因既在于家庭中贊恩父母對子女的漠視,社會大環境對底層的關注不足,同時又根植于人的奴性。
人的奴性源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也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是指被害者對于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1]。這種情節會使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和依賴性。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一個瘋狂的劫持者,他們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托付給劫持者,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這種屈服于權威的弱點就是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典型表現。
影片中贊恩家房東阿薩德用幾只雞就可以將贊恩的妹妹薩哈娶走,在這個社會中女孩兒成為一種廉價交換的商品。得知這件事后,贊恩悲憤反抗,但他的行為是無力的,在他父母與這個社會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在薩哈的事件上,贊恩的父母屬于“人質”,阿薩德屬于“劫持者”。時間久了,贊恩的父母覺得自己現在所擁有的都是阿薩德對他們的寬容與慈悲——阿薩德租房子給他們住,給贊恩在店里工作的機會,經常給薩哈送蔬菜和拉面,以滿足贊恩家的生活所需。阿薩德成為他們生存的依賴,他們逐漸習慣并滿足于現狀。贊恩的父母也曾因這樣糟糕的狀況反抗過,但是在現實面前他們屈服了,最終習慣性地成為“人質”。在法庭上贊恩的父親這樣陳述:“我們是為了薩哈好,因為我們什么都給不了她,她跟著我們一點活路都沒有,在我們家里沒有吃的、喝的,連一個睡覺的地方都難找,我是想讓她嫁到一個好人家,那樣她就有吃的,還有被子蓋。”
在影片最后部分,贊恩因為生活所迫將一歲的約納斯賣給了人販子阿斯普羅,他從之前的反抗者變成了“人質”,在面對擁有更大權力的“劫持者”時,他只能無奈屈服于“劫持者”。他作出了和他父母同樣的選擇,這個選擇成為他們悲劇的縮影。而悲劇不斷在他們身上循環,成為他們的命運,正是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奴性,造成了他們的悲劇。
2 立象以盡意的空間敘事
從整體敘事結構來看,影片采用了非線性回環倒敘的講述方式,打破傳統敘事中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因此敘事時可以在時間和空間中來回穿梭跳躍,一方面使故事更帶有懸念感,加強觀眾觀影好奇心理和聯想互動能力;另一方面也讓作品更富有藝術性和深刻性。例如,影片開場部分展現了贊恩這樣一個未成年小男孩被戴上手銬進入法庭狀告父母的場面,直接將戲劇矛盾和故事懸念開門見山呈現在觀眾面前。該影片不像線性敘事中正序邏輯那樣清晰明了,因為眾多的信息未加任何解釋和說明,所以觀眾會產生很多疑問:被銬起來的小男孩是誰?他犯了什么罪?他為什么會狀告父母?這一系列的疑惑也正是引起觀眾好奇心,讓觀眾聚焦后續情節,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因素。
電影在現實和回憶的雙重視點交叉展開敘事。在現實視點中,是贊恩在法庭上狀告父母的故事,主要人物有法官、被告(贊恩父母)和原告(贊恩和律師),每個人都通過發言來闡述各方的立場;在回憶視點中,主要展現贊恩真實的悲慘境遇,從贊恩的“被壓迫—抗爭—離家—流浪—回家—復仇—入獄”這一故事線索和現實視點交叉閃回完成敘事。現實和回憶視點中敘事可以并行發展,相互補充,共同塑造故事的觀賞性和完整性。
西摩·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一書中,把故事和空間分成“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故事空間”是故事發生時所在的空間環境,“話語空間”則是指故事的敘述者在講述故事時所在的空間環境[2]。《何以為家》因其影片畫面內容的鮮明性使影片的空間敘事更加側重“故事空間”,以畫面和聲音為表現力的電影藝術,通過鏡頭和聲音記錄著故事的發生與發展。與小說需要讀者具有一定的想象力相比,電影以畫面為表現手段會給人視覺上最為直觀的藝術感受,可視化的畫面更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效果。
影片《何以為家》在開頭通過幾個俯拍鏡頭將黎巴嫩逼仄、凋敝、混亂的社會空間展現在觀眾面前,觀眾看到的是破爛的街道、擁擠的房屋、抽煙打鬧的不良少年。這里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棟房屋都是黎巴嫩貧民窟真實狀態的寫照。關押不良少年的監獄則是混亂不堪的真實寫照,一個房間里關著十幾個犯罪少年,在這里他們沒有得到良好的改造,反而方便他們聚在一起“犯罪”,為了尋找刺激,他們喝“襪子汁”(一種毒品的替代品)。監獄里關著贊恩的哥哥,哥哥卻是贊恩媽媽的“驕傲”,哥哥可以將媽媽帶來的“襪子汁”在監獄賣得比豬肉的價錢都高,媽媽竟對這樣的賺錢方式樂此不疲,這是家庭正向教育完全缺位造成的悲劇。一幅幅真實的畫面讓人不寒而栗,而對于這群不良少年而言,少年監獄卻是一個“好歸宿”,在這里他們不用流浪街頭,也不擔心食不果腹,在這里他們至少有一口飯吃,因為饑餓是大部分黎巴嫩孩子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
在贊恩得知妹妹薩哈要嫁給阿薩德之后,影片中出現這樣一個場景:一個巨大的十字架被懸掛在陰暗的兩棟破敗樓宇之間,十字架上的霓虹燈本應該發光卻沒有發光顯得很暗淡,且十字架畫面周圍充滿了不和諧的晾衣架,破壞著它的構圖,給人以不穩定、不協調的感受。十字架本身象征著愛和救贖,在這里卻暗淡無光,隱喻著在這里人們救贖的行為是無力的,就像贊恩的行為,雖然為妹妹的事極力與他所認為的“壞人”反抗和斗爭,但最后以失敗告終,凸顯出抗爭的蒼白無力,因為在這樣的大環境里,公平得不到保障,正義得不到伸張。
3 隱喻現實的夢魘式臺詞
語言是傳情達意的工具,人們可以從語言中感受到情感與意蘊。在電影中,臺詞是傳達情感的最直接的一種方式,能夠讓影視作品更具魅力和吸引力。同時電影臺詞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關系到電影情節的推動[3]。
影片里梅森的一句話引來了受眾的熱議,梅森對贊恩說:“在瑞士,你有自己的房間,你想讓誰進來誰就可以進來,這是你自己的權利,那里的小孩沒有一個是慘死的。”看似極為平靜的一句話,卻有著巨大的“殺傷力”。因為生活在和平國家的人的日常生活,竟是他們的奢望。這是因為社會環境的惡劣——隨時擔心自己什么時候會餓死、被虐待而死。他們希望自己能被善待,這是贊恩和梅森的心聲,也是每個黎巴嫩孩子的愿望。
贊恩在法庭控訴時,說出一段震撼人心的臺詞:“我希望大人聽我說,我希望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否則以后回憶只有暴力、虐待、侮辱、毆打,在我的生活中聽過最溫柔的一句話就是——給我滾臭小子,走開混蛋。”一個12 歲的孩子說出字字誅心的話,每說一個字都在自揭傷疤,這些傷痛似夢魘般圍繞著他,使他一直都生活在“黑暗”中。他唯一的愿望是沒有能力撫養孩子的大人不再生育,這是他得知母親再次懷孕后發出的“吶喊”,因為他預見在自己家這樣生而不養的家庭誕生的孩子,會重復自己的悲慘命運,他不想再看到更多的孩子遭罪,周而復始形成“個人—家庭—社會”的悲劇循環。在成長過程中他從沒有得到父母的關懷與呵護,他不希望再有孩子像他這樣痛苦地活著。
正如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述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贊恩的家庭經濟狀況糟糕,也缺乏關懷和愛。他大聲控訴道:“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我以為我們能活得體面,能被所有人愛,但上帝不希望我們這樣,他寧愿我們做洗碗工。”正因從未得到父母的關愛、感受過家的溫暖,贊恩覺得生活處處皆煉獄,他只能打電話給電視臺傳遞自己的聲音,寄希望于法庭之上,期待通過法律守護他心中殘存的余溫。
4 形象鮮明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視劇的核心,而人物的塑造是影視創作的重中之重。恩格斯在《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中提出:“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4]該影片在敘事空間的“典型環境”和空間下的“典型人物”相得益彰,貧民區的真實場景和演員本色出演真實還原了社會現實。
自我身份認同模糊和個人身份的缺失現象貫穿全片,分別對應在贊恩和拉希爾身上。在影片開頭兩組鏡頭就分別隱喻了他們的身份問題:醫生通過檢查贊恩牙齒的方式從“生理”上判斷年齡,因為贊恩沒有出生證明,無法證明真實年齡,對應的是“身份模糊”;拉希爾因偷渡來到異鄉,通過畫痣“扮演”假身份證上的女人,在聽到海關人員點自己假名時流露出的恍惚和不安,對應的是“身份缺失”。在后續的劇情中,身份問題一直隱藏在兩人的故事線中,同時故事設定也讓兩人有了交集,讓觀眾更能共情于有著同樣悲慘命運的兩個人,最終身份問題帶來的結果是兩人悲劇的結局。
本片顛覆傳統的人物設置,即孩子的“成人化”、父母的“孩童化”,成為影片的亮點。角色外在表現力的置換是這部影片的主要沖突點,敘事視角也一直圍繞贊恩。在影片中,與贊恩的父母相比,贊恩才真正是家庭中的核心。他小小年紀就承擔起了家庭重任,養家賺錢,不僅上街賣果汁、拉煤氣,還販賣毒品。他的父母卻整天無所事事“養尊處優”,不僅時常辱罵虐待贊恩,還剝奪了他上學的權利,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因為是他們給予了贊恩生命,實則更像是榨干他的“寄生蟲”。這樣矛盾的人物換位設置,更加突出贊恩這一人物的悲劇化色彩。
影片通過兩條敘事線將兩位母親——贊恩的母親與拉希爾進行了鮮明對比。拉希爾沒有身份證明還是一個未婚先孕的單身母親,從一開始就被困難包圍,她不僅身份缺失,獨自撫養兒子,每個月還寄錢給父母,但她并沒有因為這些外在困難就選擇棄養。相反,她為了兒子放棄在雇主家的固定工作,與贊恩和兒子歡樂的“三人時光”是影片中唯一能讓人感到溫暖的片段。雖然最后拉希爾因沒有身份證明被捕坐牢,但她一直擔心兒子的安危,兒子在她心中始終是第一位,因為兒子她才有拼搏的勇氣與力量,相比贊恩媽媽,她是合格的。而贊恩媽媽則是那個贊恩口中、人們眼中不稱職的母親,她的行為是自私的,她只知道將孩子生下來,卻沒有承擔起養育的責任,她給贊恩最多的是拳打腳踢,時常還將贊恩最小的妹妹用鐵鏈拴起來,這種“非人化”的管教模式隱喻著日后一代代孩童的悲劇。畫面極力刻畫出一個不具責任感的母親形象,這樣鮮明的人物設置既加深了影片中的戲劇沖突,也準確傳遞出了影片中所暗含的人文關懷,同時提升了影片的可看性。
5 結語
電影是用畫面和聲音來呈現的[5],《何以為家》通過對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傳承,即拍攝場景大部分運用自然光、手持晃動攝影、大量非職業演員出演、冷峻寫實畫面和哀婉傷感的音樂,真實刻畫了社會底層人民苦難現狀,影片在藝術和票房收益上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優秀的電影是可以改變現實的,如韓國電影《熔爐》上映后,關于性侵學生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韓國相關部門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娜丁導演曾說她不奢求電影能夠改變世界,但她希望電影是改變的開始。影片最后贊恩的宛然一笑充滿了陽光、溫暖和希望,像一道光芒穿破社會現實的陰霾來治愈苦難大眾,給人以無窮力量和勇氣。這正如羅曼·羅蘭所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舊熱愛生活。”這一笑,就是英雄主義的有力象征。這定格在畫面中的笑容,同時寄托著的是導演對本國美好生活的向往,導演自己作為黎巴嫩的公民,希望黎巴嫩能恢復往日平靜、寧和的景象,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人民過上穩定的生活,尤其是讓孩子們能得到應有的關愛與呵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