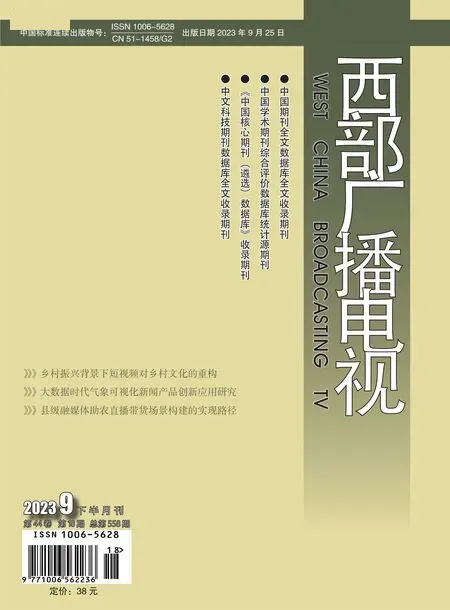《芳華》的空間解讀與記憶重構
劉薇妮
(作者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馮小剛導演“以一張照片破題,又以一張照片結束”[1],從人物蕭穗子的第一人稱視角出發展開講述,保留了《芳華》文本的核心內涵。總體而言,電影上線后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也引起了與主角有同樣經歷背景的群體對當年那段特殊時代記憶的強烈共鳴與反思。影片描繪了時代變遷中的青春,將這段特殊的歷史記憶重構與融匯,開啟了別樣的藝術創制與審美形態,凸顯了特殊的藝術魅力。
1 物理空間:真實感知中的隱喻表達
空間理論的提出者亨利·列斐伏爾認為,空間不再是以普通物質形式存在的三維模式,而是一種被賦予了文化意義的文本。其由三種形式構成,第一種是各種可感知、觸摸的物理空間形態;第二種是內在的主觀的心理空間形態;第三種是包括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的社會空間形態。在亨利·列斐伏爾看來,物理空間不僅涉及故事中人物的情態動作和故事發生的具體地點,還包括其中所映射出的社會內涵[2]。換言之,物理空間包括各種可感知觸摸的空間形態,這些實體的空間形態在電影中的多維度呈現體現出影片中所暗喻的多層寓意。在《芳華》中,張貼的電影海報、部隊文工團大院、戰場以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等,本質上都是真實存在且可感的空間符號,在一定程度上隱喻影片中蘊含的意識形態內涵。影片《芳華》通過呈現在鏡頭前的物理空間,表達出人物青春的流逝與歷史長河中時代的變幻[3]。首先,《芳華》的電影宣傳海報在物理空間中作為標志物而存在,五張預告海報形象地表達了影片故事發展的節奏。第一張海報中,8 位主要人物在泳池邊嬉戲的群像圖景實際上展現出一種愉悅、濃郁的青春氣息;第二張海報則是以血色彌漫的背景為底色,以戰場上軍人的身形剪影隱晦地表達了戰爭的殘酷,與第一張海報所表達的青春愉快形成強烈反差;第三張海報中出現的兩只鞋子分別是綠色的軍用帆布鞋和舞蹈鞋;第四張海報是呈現主角跳舞的彩色水墨畫像;第五張海報是主角劉峰在戰場上的悲愴圖景。影片《芳華》的宣傳海報是人民對高尚藝術的不同追求所存在的差異的表征,舞蹈鞋承載了何小萍這種來自艱苦環境中平凡人物的夢想,但是事實是她努力過后又重新回到平凡的生活,個人追求的情懷與無奈的現實在矛盾中放大,其中蘊含的時間跨度與個人情懷便被表現出來。
《芳華》主要的故事發生地點在部隊文工團,其同樣也是影片中物理空間呈現的首要場所,對特定的物理空間進行詳細的展示也有助于表現出一個群體的性格[2]。從一開場文工團的群像鏡頭開始,影片便對當時的文工團生活進行了生動還原,尤其是開場時大雨滂沱的陰沉色調與文工團里隨處可見的紅色元素以及人物的歡聲笑語形成了鮮明對比,讓相對封閉的文工團空間宛如世外桃源一般。何小萍的軍裝照、跳水臺上蕭穗子入水濺起的浪花,以及仰拍鏡頭下人物的修長身材都成為文工團空間里的物理形態,以符號化的方式過渡到影片敘事。影片用長鏡頭對女兵的身形姿態和生活特寫加以細致表達,其中,文工團宿舍是影片中唯一透明的公共空間,與軍營的靶場、文工團的餐廳等空間場所共同呈現出紅色年代的時代記憶[4]。
影片中的第二物理空間即戰場空間的呈現,是青春懷舊影片中引起創傷記憶的高潮。影片呈現的戰時邊境和醫院的鏡頭,與呈現被伏擊部隊的一鏡到底的鏡頭,都與文工團這個烏托邦式的物理空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劉峰從輕松安逸的文工團被分配到隨時會在戰爭中犧牲的邊境部隊,空間與空間的瞬間轉場直接體現出歷史的殘酷。同樣,何小萍在戰場中的悲慘經歷加重了歷史洪流中普通人物的創傷記憶。破敗的戰場等物理符號表達出影片創作者對戰爭的反感與對和平的向往。
影片中的第三物理空間是改革開放后的海南,經濟逐漸復蘇的繁榮之景與劉峰努力生存卻盡顯局促的境況在這個空間中形成對比。事實上,在劉峰本人身上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物理符號,即劉峰的假肢。劉峰竭盡所能,做盡好事,帶著“活雷鋒”的光環出場,一只手代表著他幫助他人,在青春舞臺中盡顯光芒,而另一只假肢卻暗含著身處硝煙彌漫的血色戰場中普通人物的悲劇意蘊。劉峰從光明到黑暗這一連續的空間敘述,將人性的冷漠自私與其艱難的生存境況展現出來,其假肢的掉落也從側面反映出個人情懷和夢想在社會洪流中被淹沒與吞噬。物與物之間的連續讓空間一幕幕地放映,事物背后所蘊含的內在意義也在其所包含的物理符號中真實地表達出來。
2 社會空間:靈魂碰撞中記憶的連接
亨利·列斐伏爾將具象化的物理空間擴展到了抽象化的社會空間,并在社會空間中對人際關系進行了重點的強調[2]。每一種社會形態在處于一個整體的社會空間中時,都同時生產著自己的社會空間,在空間里,時間的跳躍與流動置換成了空間的凝固和穩定[2]。在社會空間中,多重關系的產生與聯系讓社會空間的發展邏輯更加復雜,但是也讓影片的意識形態更加飽滿。在《芳華》的社會空間所建構的多個空間場域中,包括劉峰、林丁丁、何小萍等人在內的角色都處于個人特定的場域之中,感受著命運的浮沉。影片所呈現的歷史場域中,注定有愛情的遺憾、生死的考驗,以及人生的不平等,人與人的關系在社會空間里縱橫交錯,靈魂與靈魂的碰撞留下歷史記憶的痕跡。
首先,《芳華》中男女性別的關系是社會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時代的洪流下,文工團里劉峰和林丁丁的私密關系沖破了集體公共意識的柵欄;何小萍對劉峰無法言說的暗戀在電影的最后以兩人依偎在一起平靜的結束;蕭穗子、陳燦、郝淑雯之間復雜的三角關系以蕭穗子的退出為結局。主角劉峰復雜隱晦的情感在影片中同他人交織同構,如他在文工團里對何小萍的救贖多使用中景鏡頭,以此來暗喻何小萍對劉峰的暗戀之情,而影片使用了多個特寫鏡頭來表達劉峰對林丁丁的喜歡,男女性別的復雜關系在鏡頭的多面詮釋下成為社會空間中的組成部分,各部分之間的聯系在個人的社會空間里留下青春的回憶。
其次,影片對人物形象這一社會空間的組成部分也進行了細致的刻畫。一方面是主角劉峰與何小萍的人物形象,兩人在各自特定的歷史空間場域里漂泊不定,都經歷著時代的變幻與殘酷。不同的是劉峰帶著光環出場,何小萍帶著落寞出場,但是不變的是兩人都在不同的經歷里成為戰斗英雄,都從文工團成員轉變為舍身就義的戰斗勇士,所以二人最后的結局哀而不傷。影片中的何小萍如同漂泊的浮萍,不被命運善待,在劉峰離開文工團后她選擇了拋棄和放逐自我,在戰爭時期尋找自我時也迷失其中。與何小萍不同的是,從“活雷鋒”到成為戰斗英雄,劉峰經歷了人生的起落,他退役后為生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與在此過程中受到來自他人的欺辱,也不過是偌大社會空間里一首小小的插曲,而正是對其人生變幻的細致刻畫,使得影片表現出人物生活的辛酸。
再次,戰友關系間的對比貫穿了全片,成為串聯影片社會空間的主線。一是戰爭時何小萍不顧危險保護傷重戰友、幾十年后依然堅持去墓園祭奠的場景,與她因軍裝事件被林丁丁、郝淑雯等文工團戰友排斥的場景相對比。二是劉峰因對林丁丁表達喜歡卻遭他人誤解而離開文工團大門的落寞之景,與其剛出場時戰友的歡迎場景相對比。兩位主角與戰友之間的關系在社會空間里呈現出靈魂和靈魂之間的多樣糾纏。而不同的是,何小萍與劉峰在這樣不友好的社會空間里,每年依然堅持祭奠烈士,他們雖然不被生活溫柔以待,但是卻依然溫柔對待他人。在影片的社會空間里,時間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戰友間的偶然重聚與相互幫助將之前破裂的關系縫合。電影還將劉峰面對城管欺詐的無奈和蕭穗子與郝淑雯的富貴生活作對比,這種對比成為新時代群體分化的顯性表征。時間的流逝與圖像敘事深刻地表達出在多變的社會空間里人際關系的多維度劃分,人與人之間的多層關系被電影從多個角度進行闡釋,使故事的敘事張力更加明顯[5]。在歷史的長河中,人與人之間并不明顯的身份差距在時代中被進一步拉伸放大,這種差距讓記憶的重構和情懷的表達有了更明確的指向性,在這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相互交織也讓深處斷層的記憶重新連接。
3 心理空間:歷史場域中記憶的沉淀
亨利·列斐伏爾認為,心理空間的產生離不開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影片中物理空間所存在的具象化符號難以表達的東西,可以在心理空間中完美地呈現,在此,每一個群體中的個人都有一種特別的心理傾向,而這種心理傾向影響著一個人對外界情境的觀察,這些個人的經驗與印象會強化或修正其心理構圖[6]。影片《芳華》在銀幕中折射出人物內心世界的思想行為,戰友的排擠與殘酷的戰爭在主要人物的心理空間中筑起了一道道高墻,這些都成為人與人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而在這鴻溝之下,個人以較為現實的方式對過去不斷變化的回憶進行篩選與重塑,再通過媒介進行展現。
首先,何小萍在《芳華》中是個另類的存在,影片開頭陰沉抑郁的色調便投射出其灰暗的心理空間。她單純善良,卻出于家庭的原因而自卑,并承受著他人或隱或顯的排斥,這種善良與隱忍的斗爭和人性相關聯。在何小萍的心理空間中,她認為軍裝照可以完成她對自我身份的救贖與確認,然而“偷”軍裝事件卻讓何小萍與文工團的群體產生了對抗和疏離。劉峰在離開文工團時,團里戰友對劉峰與林丁丁事件的冷漠讓何小萍徹底對文工團失去了希望,她寧愿裝病也不愿意在慰問演出中出演A 角,并用這種微小的方式去對抗強大的集體。而當她突然成為戰斗英雄時對自我心理空間的封閉,與聽見熟悉的旋律翩然起舞,都揭示出她所經歷的這些事件在其個體記憶中有著普適性,記憶時間的長短變化與記憶里復雜的情感最終都在其心理空間中完美地呈現。
其次,劉峰作為與何小萍命運相似的“活雷鋒”,其經歷再一次體現了普通人民出身的差異所導致的生存步履維艱的狀況。劉峰在文工團里的陽光與善良在其心理空間場域中表現出人民的質樸和單純。他將上大學的機會讓給戰友,他的無私與奉獻使他獲得了“活雷鋒”的稱號。但是林丁丁曲解了劉峰的表白,并認為其思想骯臟。現實與記憶在劉峰的心理空間中呈現出隱性的糾結和纏繞。劉峰心里看不見的空間在影片中被直白地表達出來,劉峰對林丁丁情不自禁地擁抱導致了他的人生成為時代洪流下人性的悲劇。
再次,文工團里其他人物的心理空間推動了影片的敘事。蕭穗子的內聚焦視角貫穿全片,以“間離效應”(由布萊希特提出,指動用美學手段,剝去事物中理所當然、眾所周知的部分,從而制造出事物的驚愕和新奇感,使人通過思考認識到事物真實的本質,幫助人進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創造更美好的世界的實踐階段)來展示歷史語境,講述故事的核心,以平等客觀的態度對待影片中的每一位角色[7]。其對陳燦短暫萌發的愛慕在文工團即將解散時被埋葬,影片中對蕭穗子心理空間的呈現并非只沉浸于自我控訴歷史的悲情場景,而是通過蕭穗子這一客觀的視角去透視他人的心理空間,從而表達《芳華》所蘊含的意義。影片對林丁丁、郝淑雯、陳燦等人的心理空間的敘述表現在事件發生時人與人之間的交錯關系上。在風云變幻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經歷塑造出不同的人生,體現出時代的坎坷。但是他們對青春時代的記憶美好純粹,喚起了一代人的青春記憶,正如影片最后的旁白:“原諒我不愿讓你們看到我們老去的樣子,就讓銀幕,留住我們芬芳的年華吧。”
“芳華已逝,面目全非。”劉峰與何小萍閱盡滄桑,相逢在烈士公墓這一空間時,畫外音的補敘體現出歷史長河中人性不變的善良。無論是物理空間中所透露出的影片本質,社會空間中記憶深處的連接,抑或心理空間中所展現的時代記憶,只有走向多維立體的空間,充分地增強影像敘事的張力,助力情懷的熏陶和記憶的重構,才能讓一代人的青春芳華和一段歷史的記憶在影像的三種空間中完成深度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