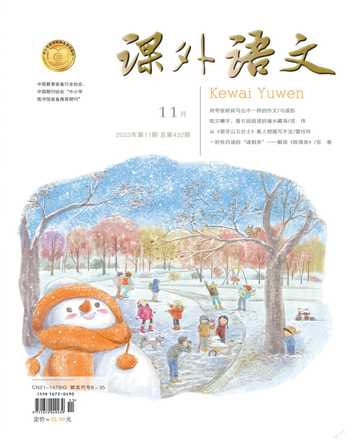從《狼牙山五壯士》看人物描寫手法
雷玲玲
★文學作品中,
人物形象是核心要素,
人物描寫則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途徑,
其目的是展示人物精神面貌,
刻畫人物性格,
深刻表達文章中心。
人物描寫的方法多種多樣。根據描寫對象,可分為外貌描寫、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和神態描寫;根據描寫人物著墨的主次、輕重、詳略,又可分為白描、漫畫式勾勒和深刻細致的描寫。
人物描寫的方式也有不同。根據場景需要,有時候需要對人物進行單獨描寫,有時候又需要對人物進行群像描寫。將群像人物描寫和單獨人物描寫相結合,可以既有深度又有廣度地表現思想,抒發感情。
課文《狼牙山五壯士》就是這樣一篇將單獨的人物描寫和群體人物描寫相結合的文章。文章講述了戰爭年代五位戰士執行掩護任務,在敵我之間展開了一場慘烈阻擊戰的故事。為了不讓日寇發現連隊主力和群眾的轉移方向,他們利用對狼牙山地形的熟悉,將敵人引向主峰棋盤陀,最后英勇跳崖。在這篇課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人物描寫方面的巧妙安排,以點帶面,將群體人物描寫和單獨人物描寫相結合,多用白描的描寫方法,用詞簡潔質樸,圍繞人物的神態、動作、語言、心理塑造了五位壯士的英勇形象。展現群體形象的同時,又安排了主要人物班長馬寶玉,在對其個人進行描寫時集中筆墨刻畫,同時兼顧了另外四位戰士的語言、動作、神態等,實現了人物形象安排的主次、詳略,猶如一尊群體雕塑:每個人都個性分明,但又和諧團結成一體,矗立在狼牙山,熠熠生輝。這就是這篇文章人物描寫的特點。
一、作者將人物描寫融合在事件發展的特定環境中
作者通過接受任務、阻擊掩護、引上絕路、峰頂殲敵、跳下懸崖五個情節展開人物描寫,緊貼環境,讓人物形象可親可敬。在安排五個情景的筆墨上,作者有詳有略,有輕有重。在每個場景中,融入人物描寫,以簡潔、準確的用詞,恰當地將五位戰士的神態、語言、面部表情、行動等精準再現,讓我們看到當年五位壯士在戰斗中和犧牲時的沉著、冷靜、智慧、英勇。
在第一部分“接受任務”中,作者用寥寥數字交代了事件所處的時代背景: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大舉進犯晉察冀根據地,五位戰士所屬的七連六班承擔了掩護群眾和連隊轉移的任務。“六班”一詞,向我們表明這篇文章所寫的是一個集體。在第二部分“阻擊掩護”中,作者進一步交代了執行任務的是五個戰士,詳細描寫了他們有計劃地把敵人引向狼牙山,利用狼牙山險要地形,痛擊緊追其后的敵寇的情形,“把沖上來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在第三部分“引上絕路”中,作者描寫了五位戰士完成任務準備轉移,但權衡后班長毅然帶領大家選擇了絕路——狼牙山頂峰棋盤陀,要與敵人同歸于盡,這部分對五位戰士進行了語言、行動、心理描寫。在第四部分“峰頂殲敵”中,班長負傷,帶領大家打完最后一顆子彈,用石頭砸向敵寇。這部分重點刻畫了班長的行動、語言。在第五部分“跳下懸崖”中,敵人繼續緊逼,班長高呼口號第一個跳下懸崖,戰士們也緊隨其后,舍身保護老百姓和大部隊安全轉移。這部分采用了神態、語言、動作描寫。
二、以生動傳神的用詞展開人物群像描寫
在整篇文章中,作者以群像描寫為主,緊扣標題“狼牙山五壯士”展開人物描寫,用詞簡潔且生動傳神。
人物群像描寫主要集中在“阻擊掩護”“引向絕路”和“跳下懸崖”這三部分,作者從神態、動作、語言、心理等多個描寫角度出發,將戰士們痛殲敵人、英勇殺敵的英雄氣概和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表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先是對班長馬寶玉的指揮狀態用了“沉著”一詞,刻畫了其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戰斗形勢下,臨危不懼、不慌不忙,帶領戰士有節奏地打擊敵人的高強技戰術能力和高超戰斗指揮能力。于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勇有謀的優秀指戰員形象躍然紙上。接著又對副班長葛振林運用了動作描寫,“打一槍就大吼一聲”,“吼”這個詞讓我們感受到葛振林對日寇的憤恨;在對戰士宋學義的動作描寫中,突出他扔手榴彈的特點,“總要把胳膊掄一個圈”,“掄”這個詞讓我們仿佛親眼見到他掄胳膊的力度和勁道,可謂有血有肉。作者對胡德林和胡福才則是神態描寫,“把臉繃得緊緊的”,一個“繃”字將兩個小戰士全神貫注認真殺敵的神態描寫得生動具體。
在第三部分“引向絕路”中,作者再次對群像進行了動作描寫和語言描寫,體現了戰士們在選擇過程中的毅然決然,毫不猶豫。關鍵時刻,馬寶玉斬釘截鐵地說了一聲“走”,簡單的一個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力透紙背,把他果敢堅定、殺伐決斷的性格體現出來。對其他戰士沒有展開語言描寫,是因為作者明白,此刻任何語言都是多余的,軍令如山,戰斗需要的是鐵一般的行動力和執行力。為此作者只寫他們“熱血沸騰”“緊跟”,以及心里的想法,“他們知道班長要把敵人引上絕路”。神態描寫、動作描寫和心理描寫,表明大家和班長想法一致,一心要保全大部隊和群眾,明白一旦走上絕路便是犧牲。但仍然心甘情愿,毫不退縮,沒有多余的語言,只有沉默堅定的行動,用生命踐行悲壯的選擇,踐行對人民超出生命的愛。
隨著情節推動,五位戰士誘敵進入了狼牙山棋盤陀這條絕路,繼而展開了“峰頂殲敵”的戰斗。五位戰士邊打邊退,給敵人營造出大部隊就在前面的錯覺,讓敵寇緊追不舍。此時作者對五位戰士進行了一句簡潔的動作描寫:“一面向頂峰攀登,一面依托大樹和巖石向敵人射擊。”這句描寫雖然用墨不多,卻十分符合實際,五位戰士利用地形地貌,將狼牙山的大樹和巖石作為擊敵的戰斗掩體,與敵人周旋,一是體現了他們的義無反顧,二是說明了戰士們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
在第五部分“跳下懸崖”處,作者又一次對五位壯士進行了群像描寫:“屹立”在狼牙山頂峰,“眺望”著群眾和部隊主力遠去的方向,“回頭望望”還在向上爬的敵人,臉上“露出”勝利的喜悅。連貫的動作描寫、神態描寫體現了五位壯士的從容不迫。這是達到戰斗目的后的喜悅,是對大部隊和群眾轉移的關切,是對敵人的大無畏。
三、單獨人物形象描寫與群像描寫相結合更好地突出了主題
作者在進行人物描寫時,兼顧群像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二者結合,更好地突出了主題,這體現在“峰頂殲敵”和“跳下懸崖”中。
到了狼牙山棋盤陀,戰士們占領有利高度,繼續向緊跟其后的敵人射擊,但無奈敵眾我寡,且戰斗時間太長,五位戰士陷入困境,班長馬寶玉受傷,彈藥也只剩下一顆手榴彈,情況緊急。就在戰士胡福才要擰開最后的那顆手榴彈時,負傷的班長卻“搶前一步”“奪過手榴彈”“插在腰間”,“猛地舉起”大石頭,并且“大聲喊道:‘同志們,用石頭砸!”。這里作者對馬寶玉的行動描寫和語言描寫便屬于個人單獨描寫的方式,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進行刻畫,體現他反應迅捷、英勇沉著、戰斗忘我的精神品質。作為指揮戰斗的核心人物,馬寶玉需要帶領大家打退敵人的進攻,延長戰斗相持時間,給主力部隊和人民群眾爭取更多的轉移時間,讓唯一的一顆手榴彈在最關鍵時刻發揮最大作用。他提醒大家沒有武器就就地取材,用手邊的石頭砸。戰士們立即執行,“頓時,石頭像雹子一樣,帶著五位壯士的決心,帶著中國人民的仇恨,向敵人頭上砸去”。將五位戰士同仇敵愾的心理集中展示出來,猶如憤怒的火山噴出洶涌的巖漿。在又一群敵人撲上來的關鍵時刻,馬寶玉“拔出手榴彈”“擰開蓋子”,用盡全身氣力“扔向敵人”。
在“跳下懸崖”中,作者對馬寶玉進行了語言描寫:“同志們,我們的任務勝利完成了!”還有動作描寫:砸槍、走向懸崖、跳下深谷,動作完成得干凈利落、義無反顧。砸碎槍是不給敵寇留下侵略我們的武器;跳下深谷是對生命尊嚴的保全,對保家衛國誓言的踐行。砸槍跳崖,寧死不屈,五位壯士在狼牙山譜寫出悲壯豪邁、永垂不朽的生命之歌,久久回蕩在山谷,響徹天地。
因為作者在人物形象描寫方面的成功,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深入人心,影響深遠,一時間從晉察冀邊區傳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成為浴血抗戰的楷模。后期圍繞狼牙山五壯士而創作的文學文藝作品、影視劇不勝枚舉,拍成電影,塑成雕塑……如今提起狼牙山五壯士,敬意在我們的心里油然而生。應該感謝這些文字,讓狼牙山五壯士的精神,從文字中凝結出種子,種在我們的心田,自此生根發芽,永遠鮮活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