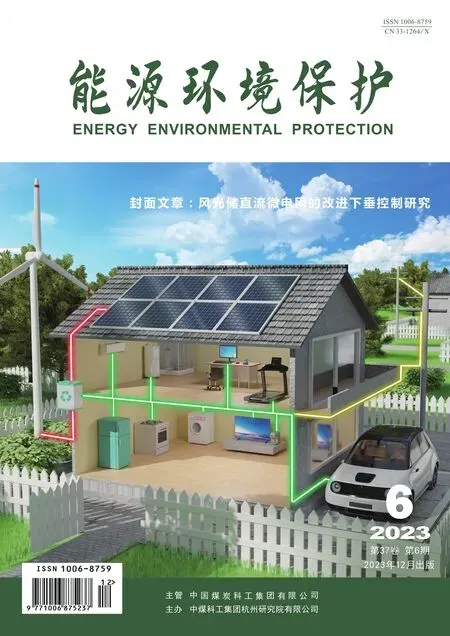活性炭噴射吸附在煙氣凈化中應用的數值模擬分析
袁世震, 郭倩倩, 盧如飛, *, 鄧 凱, 陳穎泉, 曹 操, 胡艷軍, *
(1. 金華寧能熱電有限公司, 浙江 金華 321000;2. 浙江工業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3)
0 引 言
目前我國能源需求處于上升階段,“十四五”規劃提出加強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重點控制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費。因此,在短期“雙控”、中長期“雙碳”的多重目標下,熱電廠煤炭能源利用面臨著新挑戰,亟需全力推進減煤降碳工作、優化低碳能源利用,進而構建多源、低碳、安全、清潔高效能體系。與此同時,我國污泥年產量巨大,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1],2019年我國年干污泥產量高達1 303萬t。污泥中含有重金屬、有機污染物和病原體等環境污染物,對環境造成巨大的負擔[2],妥善處置污泥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2022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污泥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實施方案》,方案指出要合理壓減填埋規模,有序推進污泥單獨焚燒或協同焚燒。由于污泥與煤炭組分特性差異,污泥摻燒對燃煤電廠的穩定運行、煙氣清潔排放、技術裝備等提出新的要求。
煙塵、CO2、SO2、NOx、Hg及其化合物是燃煤電廠排放的主要煙氣污染物[3],但由于污泥組分的復雜性、多樣性和不均勻性[4],摻燒污泥會導致煙氣量、煙氣污染物類型及濃度、灰渣量及理化特性發生變化[5]。曹通等[6]通過小比例工業污泥摻混、鍋爐焚燒現場試驗,結果表明小比例(摻混比例小于10%)摻燒污泥時,煙氣中的主要污染物二惡英、SO2及NOx等均無大幅度增多,但工業污泥的摻混會使爐渣和飛灰中重金屬含量增加。張成等[7]開展了燃煤鍋爐污泥摻燒的測試與數值模擬實驗,研究表明,相同摻燒比時,污泥含水率對污染物排放有影響,污泥含水率降低會使NOx排放量增加;小于20%摻燒比例時,鍋爐燃燒特性、污染物排放物NOx特性與燃煤單獨燃燒無明顯差異;當摻燒比例大于20%時,鍋爐燃燒效果明顯下降,NOx污染特征大幅度上升。鄭成強等[8]研究了不同比例摻燒污泥對燃煤電廠痕量元素排放特性的影響,結果表明:按照6%的摻混比,摻燒污泥中各痕量元素含量差異明顯,其中Zn、Cu元素含量高;但是污泥摻燒對痕量元素的遷移特性并未有顯著影響,且底渣和粉煤灰中痕量元素的相對富集系數在污泥摻燒前后基本一致,Hg元素在污泥摻燒前后均表現出一定的揮發特性。岳峻峰等[9]研究發現摻燒污泥后混合燃料中的S含量決定著SO2排放濃度。SO2在高溫下會與氧化物反應生成硫酸鹽,從而導致SO2排放濃度降低,所以摻燒污泥對SO2排放濃度并無較大影響。因此,隨著電廠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日益嚴格,摻燒污泥的燃煤電廠亟需治理煙氣的新方法。
活性炭吸附煙氣凈化技術具有效率高、工藝技術較為成熟的優點,目前已經成為電力、鋼鐵企業等實現綠色清潔發展的重點選擇之一。活性炭法能夠高效脫除煙氣中的二惡英、硫、硝及重金屬[10],是燃煤煙氣干法凈化技術的重要發展趨勢[11]。活性炭噴射系統常用于電廠煙氣脫汞,是目前最成熟、最可行的燃煤電廠控制汞排放技術[12]。美國在2010年前就對活性炭噴射脫汞技術進行了大量研究,發明了如傳統活性炭噴射技術(ACI)、TOXECONTM、TOXECONIITM和Mer-CureTM等活性炭噴射脫汞技術[13]。國內對活性炭噴射吸附煙氣污染物的效果也進行了較多研究。馬修衛等[14]通過活性炭噴射系統耦合布袋除塵實驗裝置,開展了活性炭對甲苯和氯苯的吸附脫除實驗,結果表明,活性炭對大部分有機污染物都能有一定的吸附能力,且對高沸點有機污染物有較高的脫除效果。周強等[15]在模擬煙氣管道活性炭噴射脫汞試驗設備上開展了活性炭噴射效果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活性炭噴射吸附脫汞的過程中,通過增大活性炭在煙道內的噴射量、延長活性炭在煙道內的停留時間,以及適當減小活性炭粒徑等都可使活性炭對汞的吸附效果顯著增強[16]。
本文首先基于浙江金華寧能熱電廠現有煙氣凈化系統現實情況,提出在煙道系統增設活性炭噴射凈化技術,并采用Fluent數值模擬分析優化設計活性炭噴射方案。然后討論了活性炭噴射吸附技術應用于煙氣污染物控制領域的影響及安全性,為電廠煙氣治理優化提供參考。
1 研究對象模型建立
本研究的對象為浙江金華寧能熱電廠現使用的煙氣凈化系統,所采用的電廠鍋爐耗煤量為30 t/d,機組功率為15 MW,凈化系統進口煙氣流量和溫度分別為267 240 m3/h和140 ℃,凈化系統進口尺寸為3 000 mm×2 000 mm。詳細的鍋爐及燃料基本參數見表1。針對該凈化系統,采用Fluent數值模擬分析了影響活性炭噴射吸附效果的因素,通過對活性炭的噴射點位置、噴射角度、噴口數量和噴射質量流量的計算分析,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17-21],以擴散效果、停留時間、活性炭覆蓋率為判斷標準,獲得了在除塵器前的煙氣通道增設活性炭噴射的較優方案。

表1 電廠鍋爐及燃料的基本參數
1.1 三維模型及網格劃分
基于浙江金華寧能熱電廠的煙氣凈化系統的煙道結構,利用Solidworks對位于除塵器之前的煙道主體部件1-15進行三維實體建模,如圖1(a)所示,網格采用非結構化形式,如圖1(b)所示。基于不同網格尺度獲得了四種不同數量的網格,并針對不同數量網格進行氣相流場的數值模擬,流場中噴射點3處的速度值如圖2所示,因78 w、152 w及236 w網格所計算的速度值偏差低于2%,最終確定網格劃分數量約為78 w,網格平均質量為0.85。

圖1 煙道的三維結構模型和網格Fig. 1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model and grid of flue

圖2 網格無關性驗證Fig. 2 Grid independence verification
1.2 模型參數及邊界條件設置
煙氣入口位于煙道件1區域,其進口邊界條件為速度進口,溫度為155 ℃,體積流量267 240 m3/h,煙氣中CO2占比為12.699%,N2占比為75.667%,O2占比為6.339%,H2O占比為4.954%、SO2占比為0.341%(以上均為質量占比)。煙氣出口位于煙道件15,邊界條件設置為壓力出口(500 Pa),溫度為150 ℃,壁面為絕熱。
氣相湍流模型為標準k-e模型,鑒于活性炭噴射量較小(體積分數小于10%),屬于稀疏氣固兩相流,活性炭噴射計算求解可采用離散相模型(Discrete Phase Model,DPM),將流體視為連續相,將活性炭顆粒視為離散相,跟蹤顆粒運動。DPM模擬將顆粒簡化為質點,對顆粒的形狀及體積進行了簡化,忽略了流動分離、邊界層以及顆粒之間的相互作用力,僅考慮流體和顆粒之間的相互作用,適用于活性炭噴射吸附的模擬。Fluent中通過對顆粒作用力微分方程進行積分,求解離散相顆粒的軌道,根據牛頓運動定律,其在直角坐標系下的形式(以x方向為例)為:
式中:m為單顆粒質量,kg;up為顆粒相速度,m/s;ρp為顆粒相密度,kg/m3;ρ為煙氣相密度,kg/m3;Fd為顆粒所受曳力,N;Fother為其它相間作用力,N。
由于固體顆粒濃度較小且氣相和固相之間不存在相變,采用單向耦合方法即僅考慮流體對顆粒的作用,參考相關文獻[22-25],在DPM模型中選擇壓力——旋流霧化噴嘴模型作為噴射模型,為點源噴射方法,根據方案中的噴射點位置、噴射方向、噴射質量流量三個參量,噴嘴模型的噴射錐角為45°。針對本文研究的活性炭顆粒,其密度為1 300 kg/m3,假設其為規則的球形顆粒,粒徑尺寸遵循R-R(Rosin-Rammler)分布,最小粒徑為8 μm,最大粒徑為120 μm,平均特征粒徑為100 μm,尺寸分布指數為3.5,粒徑數量為10。出入口顆粒行為設置為逃逸(escape),壁面顆粒行為設置為碰撞后反彈(reflect),法向反彈系數εN為1,切向反彈系數εT為1,考慮氣相的湍流脈動對顆粒的影響,采用隨機游走跟蹤法,將Number of tries設置為5,迭代一次追蹤的顆粒數為1 200。
2 結果分析與討論
活性炭對重金屬和二惡英的吸附效果受多重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煙道內溫度、活性炭噴入量、活性炭停留時間、活性炭結構特征(包括活性炭粒度、孔結構和比表面積等)和污染物濃度等。從單噴口和多噴口的噴射點位置、噴射角度、噴射質量流量三個方面,對煙道中活性炭噴射分布均勻性等進行了數值模擬分析;比較顆粒的停留時間,基于Y=7 m處截面活性炭顆粒的分布情況和覆蓋率比較其擴散效果,該截面長度為3 m,寬度為2 m,位于長度為7 m的豎直管道部件9-11中,最終基于停留時間和擴散效果確定不同活性炭噴射方案下的噴射效果。
2.1 單噴口下噴射位置分析
基于單噴口模式選擇五個不同噴射點位置進行模擬,噴射位置如圖3所示,噴點1坐標為(4.04,0,0),噴點2坐標為(4.04,1,0),噴點3坐標為(4.04,2,0),噴點4坐標為(4.04,3,0),噴點5坐標為(2.5,0,0),均采用順流噴射方式。噴射質量為0.004 2 kg/s,噴點位置點為3,坐標為(4.04,2,0)時噴射顆粒的跡線如圖4所示。

圖3 噴射位置Fig. 3 Injecting position

圖4 單噴口下顆粒速度跡線Fig. 4 Particle trajectory under single nozzle
不同噴射位置下煙道內Y=7 m處活性炭顆粒分布結果如圖5所示。圖6為不同噴射位置下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

圖5 不同噴射位置下煙道內活性炭顆粒分布模擬結果Fig. 5 Simulation results of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distribution in flue under different injection positions

圖6 不同噴射位置下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Fig. 6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 coverage at a cross-sectionof Y=7 m under different injection positions
由圖5和圖6可知,當噴射點布置在彎管區域即在噴點5處和噴點1處時,活性炭的擴散效果相對較差,而當噴射點布置在豎直區域即在噴點2、3、4處時,活性炭的擴散效果較好,且越靠近上端,距離彎管越遠擴散效果越好,當噴射點布置在噴點3處時,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最高,為76.79%。活性炭進入煙氣管道后,隨著停留時間的增長,對污染物的吸附效果提高[14],五種噴射位置下煙道內活性炭的停留時間分別為1.26、1.38、1.49、1.41、1.45 s,五種不同方案的停留時間均在1 s以上,噴點3的停留時間最長,達1.49 s。結合圖7氣相速度分布圖及矢量圖可知,在煙道件8即彎管內部,氣相速度的變化較大,在彎管出口截面中心位置即噴射點3處氣相的速度為12.3 m/s,噴射點1處的速度為13.1 m/s,噴射點2位置處的速度為13.6 m/s,因此在噴射點1和噴射點2位置處,顆粒相受到連續相的作用后,動量變化量大,雖然行程相對噴射點3處長,但最終停留時間短。同時噴射點1、噴射點2處氣相在x軸向上的速度相對噴射點3處更大,因此出現了擴散程度相對更差的現象。在噴點3處,活性炭的擴散效果好且停留時間長,確定單噴口情況下噴射點位置為(4.04,2,0)。

圖7 氣相流場云圖及矢量圖Fig. 7 Velocity profile and vector image of gas-phase flow field
2.2 多噴口下噴射位置分析
基于單噴口下的最佳噴射縱向位置,選擇在該位置即Y=2 m處的水平面上布置噴口,為了使噴口之間噴出的活性炭粒子能夠互相交叉覆蓋,填補空隙,結合煙道內煙氣的流場分布,選擇了五種噴口布置方案,如圖8所示,其中方案1的坐標為噴口1(4.54,2,0)、噴口2(3.54,2,0)、噴口3(4.04,2,-0.75)、噴口4(4.04,2,0.75);方案2的坐標為噴口1(4.54,2,0)、噴口2(3.54,2,0)、噴口3(3.54,2,-0.75)、噴口4(3.54,2,0.75);方案3的坐標為噴口1(4.04,2,-0.75)、噴口2(4.04,2,0)、噴口3(4.04,2,0.75);方案4的坐標為噴口1(3.54,2,-0.75)、噴口2(4.04,2,0)、噴口3(3.54,2,0.75);方案5的坐標為噴口1(4.04,2,0)、噴口2(3.54,2,-0.75)、噴口3(3.54,2,0.75)、噴口4(4.54,2,-0.75)、噴口5(4.54,2,0.75)。噴射總質量為0.004 2 kg/s,各噴射口均勻分配,采用噴射方案4時顆粒的跡線如圖9所示。

圖8 多噴口下噴射位置布置方案Fig. 8 Layout scheme of injection position under multi-nozzle
圖10為在不同噴口布置方案下均采用順流噴射時煙道內Y=7 m處活性炭顆粒的濃度云圖,方案1、方案3中活性炭在截面豎直方向上擴散不均勻,集中在截面的上半部分,左右兩側噴口處周圍流場不均勻所導致。方案2、方案4和方案5中活性炭在水平和豎直方向上擴散相對均勻。不同噴口布置方案下活性炭的停留時間分別為方案1-1.50 s、方案2-1.43 s、方案3-1.28 s、方案4-1.44 s和方案5-1.53 s,方案5停留時間最長,截面活性炭覆蓋率最大(圖11),為92.46%,確定方案5為多噴射口情況下的活性炭最佳噴射位置方案。

圖10 不同噴口布置方案下煙道內活性炭顆粒分布模擬結果Fig. 10 Simulation results of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distribution in flue under different nozzle layout schemes

圖11 不同噴口布置方案下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Fig. 11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 coverage at a cross-sectionof Y=7 m under different nozzle layout schemes
2.3 噴射角度選擇
在活性炭噴射位置為方案5的基礎上,對活性炭的噴射角度進行了模擬分析,噴射角度方案如圖12所示。

圖12 噴射角度方案Fig. 12 Spray angle scheme
圖12中方案1~5分別為順流噴射、+45°噴射、垂直噴射、-45°噴射、逆流噴射。圖13為不同噴射角度方案下煙道內Y=7 m處活性炭顆粒分布模擬結果,圖14為不同噴射角度下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由圖13和圖14可知,當從順流噴射改變為其它角度時,活性炭的擴散面積顯著減少,活性炭覆蓋率顯著下降。不同噴射角度下活性炭的停留時間分別為方案1-1.53 s、方案2-1.57 s、方案3-1.52 s、方案4-1.32 s和方案5-1.48 s。逆流噴射時的擴散效果相對更差及停留時間相對更短的原因是噴射點位置處的壓強分布具有較大的曲率變化,導致流場分布不均勻,且煙氣流量遠遠超過噴口處流量,逆流噴射會帶來煙氣對活性炭較大的反向作用力,經過對沖作用后顆粒的運動方向會變化,速度大小會得到強化,反而會使得顆粒停留時間變短,擴散面積變小,不均勻性增強,并不會使得顆粒相實現更好的擴散;在這種工況下,在更短的時間和距離內達到與流場相匹配的流動狀態,更有利于活性炭在流場中的擴散和分布,因而順流噴射方式下更有利于顆粒相與煙氣流相互擴散。

圖13 不同噴射角度下煙道內活性炭顆粒分布模擬結果Fig. 13 Simulation results of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distribution in flue under different injection angles

圖14 不同噴射角度下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Fig. 14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 coverage at a cross-sectionof Y=7 m under different injection angles
2.4 噴射質量流量的模擬分析
在活性炭的噴射位置為五噴口、平行煙氣流的基礎上,進行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的優化分析。圖15分別是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為5、10、15 kg/h時煙道內Y=7 m處活性炭顆粒的濃度云圖。隨著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的增大,截面上的活性炭分布面積迅速增大,覆蓋率迅速升高(圖16)。從停留時間來看,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為5、10、12 kg/h時停留時間分別為1.22、1.31、1.53 s。

圖16 不同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下Y=7 m處截面活性炭覆蓋率Fig. 16 Activated carbon particle coverage at a cross-section of Y=7 m under different mass flow rates ofinjection of activated carbon
從吸附效果角度探討,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為15 kg/h,擴散效果和擴散均勻性好,停留時間最長,吸附效果最好。從經濟性角度探討,與15 kg/h的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相比,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為10 kg/h時停留時間從1.44 s下降到了1.21 s,但是其擴散面積是15 kg/h時對應擴散面積的2/3以上,且活性炭擴散均勻性較好,同時能減少1/3的成本,考慮成本可選用10 kg/h的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
2.5 活性炭噴射系統應用于煙氣治理領域的影響及安全性分析
2.5.1 影響活性炭吸附的關鍵因素
由于噴射的活性炭對重金屬和二惡英的吸附效果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模擬后對影響活性炭吸附效果的關鍵因素進行了分析。
溫度是活性炭吸附重金屬和二惡英的最主要因素,隨著活性炭吸附時煙道溫度的降低,活性炭的吸附能力逐漸上升。ZHAN等[26]研究了活性炭對二惡英的吸附效果,結果顯示,活性炭對二惡英的吸附效果會隨吸附溫度的降低而增強。在同一脫汞效率下,煙氣中炭汞比也會由于溫度的升高而升高,這表明活性炭對汞的吸附能力下降。活性炭物理吸附過程具有可逆性,因此在汞的吸附和脫附動態平衡過程中,溫度的升高更有利于脫附,所以高溫會削弱活性炭的吸附能力,使得在相同脫汞效率下活性炭的噴射量增大。
提高活性炭的噴射量增加了污染物的脫除率,然而,每單位活性炭吸收的重金屬和二惡英數量有所減少,這主要是由于噴活性炭數量增加、煙氣中活性炭濃度增加以及吸附劑濃度增加,導致吸附面積和活性位點數量增加,從而提高煙氣中重金屬和二惡英的脫除率[21]。趙亮等[27]研究表明,活性炭的噴射量可以顯著影響二惡英的排放濃度,并且對不同二惡英同族體的排放影響不同。
停留時間是含污染物的煙氣與噴入煙道內活性炭的接觸時間,停留時間取決于煙道中煙氣流速以及吸附劑噴射口與污染物控制裝置的距離。活性炭停留時間的延長會使重金屬和二惡英的脫除效率明顯提高[26]。CHANG等[28]以某一垃圾焚燒爐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表明,活性炭噴射量與活性炭對二惡英的吸附脫除效果呈線性正相關,即當小于65 mg/Nm3噴射量時,活性炭噴射量與二惡英吸附脫除效果呈近似線性相關,活性炭噴入量越多,二惡英的脫除效果越好。然而,當活性炭噴射量大于150 mg/Nm3時,活性炭對二惡英的吸附脫除效果受活性炭噴射量的影響很小。
吸附劑的比表面積、孔結構和粒度等結構特征對其吸附性能影響較為顯著。活性炭粒度的增大,則吸附效果降低,這是由于活性炭外表面積增加,吸附效果提高。通常活性炭孔徑在2~5 nm較適合吸附二惡英[29]。王家偉等[30]針對活性炭對燃煤電廠煙氣中汞脫除及控制的影響開展了煙氣脫汞研究,結果表明,活性炭的比表面積為304.73 m2/g,孔容為0.52 cm3/g,孔徑為4.30 nm時對汞物理吸附能力很強。活性炭噴射量相同時,初始煙氣中重金屬和二惡英濃度越高,單位活性炭對重金屬和二惡英的吸附量也越大。李娜[29]對載硫活性炭的汞吸附特性及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吸附劑的初始汞吸附速率、整體汞吸附速率都會隨煙氣中汞濃度的增加而提高。
2.5.2 活性炭噴射吸附的安全性
活性炭本身具有一定的安全隱患,溫度較高會有自燃的危險。使用活性炭作為吸附劑凈化煙氣中污染物時,可能存在自燃危險、粉體爆炸危險和熱積聚風險。因此在使用活性炭噴射工藝時,對煙道設備的要求較高。煙氣系統要確保密封性,煙氣管道漏氣,系統中進入空氣后,氧濃度增高,管道變為富氧環境,且高溫會促進氧化,產生大量氧化熱,同時除塵器中堆積著大量粉塵,由于熱量積聚導致除塵器中的溫度持續升高,當溫度高于粉塵的自燃溫度,將有自燃的風險。
活性炭噴射系統一般與除塵設備聯合使用,傳統的活性炭噴射+除塵器技術有效改善了煙氣凈化效率,該組合系統主要包括電除塵器(ESP)和袋式除塵器(FF)。電除塵器本身在氧氣濃度過高的情況下會發生著火、爆炸。因此,在活性炭噴射到除塵器中也會產生一定的安全隱患[31]。活性炭噴射進入電除塵器電場中,如果遇到靜電、明火,無可避免地會有一些著火爆炸的風險,尤其是粉末活性炭的噴射進入電除塵器電場中,易發生粉塵爆炸。
另外,電除塵器電場中產生的靜電會對活性炭應用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影響,但是電除塵器等都應用鋼金屬制作,且都有防靜電接地,所以近年靜電除塵技術已大大降低了安全事故的發生幾率。在除塵器的收集板上也要接有防靜電接地設備。在美國有較多的活性炭噴射耦合電除塵器技術應用案例[32],見表2。

表2 活性炭噴射+電除塵器脫汞技術的電廠應用案例[34]
美國電力研究協會發布的美國活性炭噴射耦合電除塵器測試的案例報告中[33],列舉了大量應用活性炭噴射耦合電除塵器的工業應用案例,但是并沒有說明活性炭噴入靜電除塵器電場中的著火、爆炸等安全隱患,這也說明在電袋除塵器前噴入活性炭的安全隱患是在可控制范圍內的。
2.5.3 活性炭噴射吸附對飛灰的影響
在焚燒后煙氣凈化系統中引入活性炭噴射裝置,使煙氣中的污染物得到更加充分的凈化,但是與此同時,活性炭的加入導致過濾除塵過程對捕集到的飛灰也有一定影響,活性炭吸附污染物后,與飛灰一同被除塵器收集。另外,活性炭噴射會增加飛灰中的碳含量和重金屬濃度,這導致飛灰毒性增大。呂浩[34]對活性炭噴射對飛灰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探究活性炭噴射后對燃煤機組ESP捕集的飛灰品質產生的影響,從電除塵器三級電場的灰斗中分別取出未噴射活性炭時、噴射活性炭2 h、4 h的飛灰。結果表明,活性炭噴射后,飛灰中含碳量有較顯著的增加,在一級和二級電場中,飛灰含碳量增加較多,而活性炭噴射對三級電場中飛灰的含碳量影響較小,而且根據電場的分布,飛灰中的含碳量逐級下降。活性炭的噴入對飛灰的影響主要是飛灰的含碳量[34],導致飛灰資源屬性有所降低。
3 結 論
活性炭噴射對煙氣中重金屬和二惡英的吸附脫除有較好效果,但是同樣受反應溫度、活性碳噴射量、活性炭結構特征、污染物濃度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多噴口噴射相對于單噴口噴射活性炭更加均勻,但是成本更高。當單噴口噴射時,活性炭噴射位置在煙道水平轉垂直的彎頭(煙道件8)出口截面中心位置處時,擴散效果好,且活性炭停留時間長。當多噴口噴射時,活性炭噴射點位于Y=2 m處的水平面上,基于多噴口方案5即噴口坐標分別為噴口1(4.04,2,0)、噴口2(3.54,2,-0.75)、噴口3(3.54,2,0.75)、噴口4(4.54,2,-0.75)、噴口5(4.54,2,0.75)布置時,活性炭噴射效果最佳。單噴口和多噴口下都選擇順流噴射,此時擴散面積相對更大,截面覆蓋相對更高,活性炭的擴散效果相對更好,且在截面中分布相對均勻。在單噴口和多噴口情況下,活性炭噴射質量流量具有一致性。考慮吸附效果,噴射活性炭質量流量選擇15 kg/h最好;考慮效益,噴射活性炭質量流量選擇10 kg/h最好。活性炭和電除塵器本身均有具有一定的安全隱患,當活性炭噴射與電除塵器耦合使用時,會使安全隱患有所上升,但是根據研究情況和工業應用案例,可以確定這些安全隱患都在可控范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