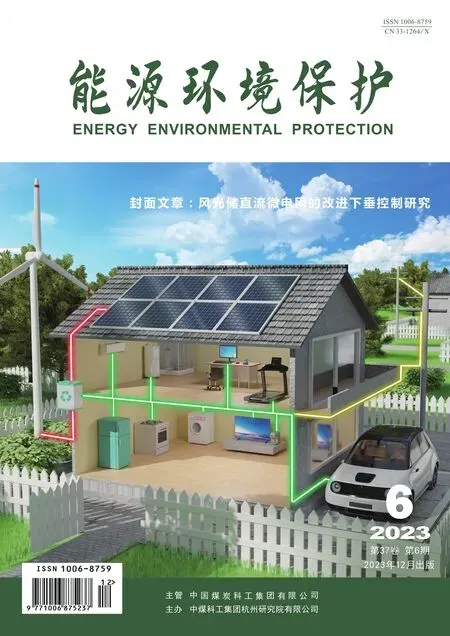混合含氯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的生物降解性能研究
葉 鐳, 尤菊平, 孫海敏, 于 健, 王艷青, 陳東之, *
(1. 浙江海洋大學 浙江省石油化工環境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 浙江 舟山 316022;2. 浙江中藍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25000)
0 引 言
石油化工、醫藥化工等重點行業的快速發展導致的環境污染物問題日益凸顯,其排放的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已成為周邊區域空氣質量改善的焦點[1]。含氯揮發性有機物(CVOCs)作為工業源VOCs的典型代表,排放量大、毒性高,管控嚴[2-4],其安全、低碳處理是化工行業大氣污染控制的難題之一。
目前廣泛應用的VOCs處理技術,如燃燒法、催化氧化法、吸附法,在處理CVOCs時存在易產生二噁英等二次污染、成本高、催化劑失活、吸附劑再生難等不足[5-6]。生物法能利用微生物的代謝活動將CVOCs轉化為CO2、H2O、HCl等物質,安全性高、碳排放少,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關注。ALGHUTHAYMI等[7]利用菌株Alcanivoraxsp. HA03降解高鹽和堿性污染場所的氯苯(CB),通過PCR擴增檢測到該菌株中CB生物降解相關基因,表明該菌株具有在極端環境中降解CB的潛力;CHEN等[8]則從活性污泥中馴化出二氯甲烷(DCM)高效降解菌MethylobacteriumrhodesianumH13,能夠完全降解濃度低于15 mmol/L的DCM;LEITAO[9]在實驗中發現二氯乙烷(Dichloroethane,DCE)的降解與污泥中Dehalococcoidesmccartyi的豐度相關;張克萍等[10]將活性污泥和1,2-二氯乙烷降解菌Starkeyasp.T2接種至中試規模的生物滴濾塔中,發現1,2-二氯乙烷的去除負荷最大可達6.8 g/(m3·h),并且脫氯效果明顯。目前利用微生物降解CVOCs的研究多面向單一污染物,對混合CVOCs協同處理的報道較少。然而,實際生產過程排放的廢氣中污染物組分復雜,污染物之間存在廣泛的相互作用,需要多個菌株協同配合才能實現多種污染的同向同行降解。因此,眾多研究者聚焦于復合微生物菌群的構建[11-12],將具有不同降解功能、能夠互生或共生的幾種微生物按照適當的比例混合并制備成液態復合菌劑和固態復合菌劑[13-15],根據不同環境污染需求有目的地投加到各類反應器中,實現目標混合污染物的高效去除。復合菌劑還具有適應性強、穩定性高、存儲時間長等優點[13-14]。周月明[16]利用制備的降解菌劑實現了苯系物的高效去除,對200 mg/L苯、甲苯、乙苯、二甲苯的降解率依次為93.2%、95.6%、91%、88.4%。陸李超等[17]利用真菌-細菌復合菌劑接種生物滴濾塔,其對350 mg/m3的混合廢氣的去除率超過90%,相較接種活性污泥的滴濾塔提高了30%,另外發現菌劑的加入可有效縮短生物滴濾塔的啟動時間,提高微生物菌群多樣性。
本研究選取某家以氯苯為溶劑的精細化工企業排放的廢氣為對象,探明廢氣中的CVOCs成分,以主導污染物為生物降解目標,選取活化實驗室可降解相應污染物的菌株。其中菌株HY-9、H13、T2皆為課題組從污泥中馴化出的高效降解菌,HY-9尚未在國內外研究中報道過,但在課題組前期實驗中證明其具備高效且穩定的氯苯降解性能,H13、T2根據課題組之前的研究報道也分別具備降解二氯甲烷和二氯乙烷的性能[8, 10]。利用以上三株菌種構建復合微生物菌群,考察復合微生物菌群的生長特性、污染物降解性能、脫氯能力和代謝產物,研究結果可為企業CVOCs的減排提供方法和數據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微生物來源與培養
本研究利用的Roseburiasp. HY-9、MethylobacteriumrhodesianumH13、Starkeyasp. T2三株高活性CVOCs降解菌均由課題組成員前期篩選獲得,以下分別簡稱HY-9、H13、T2。
將-80 ℃貯存的三種菌在室溫下進行解凍,隨后接種到LB固體培養基(9 cm×9 cm玻璃培養皿),在30 ℃恒溫培養箱中活化,挑選單菌落,傳代2次以保證菌種純度和活性。將活化后的單菌落接種至滅菌后的常溫LB液體培養基,恒溫搖床30 ℃、160 r/min振蕩培養至對數增長期,4 ℃、8 000 r/min離心10 min后倒掉上清液,利用滅菌的無機鹽溶液清洗離心三次后,振蕩懸浮并加入至3個含50 mL無機鹽溶液的血清瓶中,加入100 mg/L CB、100 mg/L DCM和100 mg/L DCE作為唯一碳源,恒溫培養作為種子液。LB和無機鹽溶液的成分與先前報道一致[18]。
1.2 試驗方法
采用便攜式VOCs廢氣檢測設備對車間空氣中的氣體成分及濃度進行初步檢測,隨后用空氣采樣泵采集5 L車間空氣至氣體采樣袋中,通過實驗室氣相色譜確認氣體成分及濃度。
所有實驗均在250 mL血清瓶中完成,從實驗室菌種庫選取菌株接種到含有無機鹽培養基的血清瓶中,添加不同濃度對應底物(50、100、150、200 mg/L),30 ℃、160 r/min條件下振蕩培養,并每隔2 h用紫外分光光度計檢測菌液的OD600(指溶液在600 nm波長處的吸光值),記錄單株降解菌在不同濃度梯度下的生長狀況。每隔2 h用氣體采樣針采集血清瓶頂空氣體0.8 cm3,檢測CB、DCM和DCE三種污染物濃度變化。根據單菌單底物不同濃度的實驗結果,結合工廠車間廢氣成分分析結果,將CB、DCM和DCE分別按200、200、150 mg/L的濃度配置,隨后進行復合菌劑構建,將三種菌株的種子液等比例調配成單菌株、雙菌株、三菌株體系菌劑,再將每組無機鹽溶液的OD600值控制在0.03左右。
污染物完全降解后收集2 mL菌液稀釋5倍并超聲破碎10 min(4 ℃,變幅桿Φ3 mm,超聲3 s,暫停1.5 s),破碎液經12 000 r/min離心20 min后保留上清液,利用0.45 μm過濾器過濾后檢測菌液中代謝分泌有機物。
1.3 分析方法
氣體樣品成分通過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Agilent 7900,Agilent 5977B)分析:色譜柱為HP-5MS UI毛細管柱(60 m×0.32 mm×0.1 μm),進樣口溫度為250 ℃,總流量為12 mL/min,分流比為5∶1,分流流量為7.5 mL/min,柱箱程序升溫從35 ℃保持10 min,10 ℃/min升高到190 ℃,保持2 min后以6 ℃/min升溫至225 ℃,保持1 min,載氣為高純氦氣。
CB、DCM和DCE三種污染物濃度通過氣相色譜儀(Agilent 6890B,美國)檢測:色譜柱為HP-5毛細管柱(30 m×0.32 mm×0.5 μm),進樣口和FID檢測器溫度分別為250 ℃和300 ℃,總流量為14 mL/min,分流比為3.3∶1,分流流量為8.7 mL/min,柱溫為40 ℃。載氣為高純氮氣,氫氣和空氣,流量分別為45、40、450 mL/min[19]。
產物CO2通過氣相色譜儀(Agilent 8860,美國)檢測:色譜柱為HP-Plot-Q毛細管柱(30 m×0.32 mm×20 μm),進樣口和TCD檢測器溫度分別設定為100 ℃和180 ℃,總流量為6.8 mL/min,分流比為50∶1,分流流量為7.0 mL/min,柱溫為40 ℃。載氣為高純氦氣,柱流量: 2.0 mL/min。
反應結束后的菌液在4 ℃、8 000 r/min離心10 min后取上清液,經0.22 μm濾膜過濾后取1 mL上清液,通過配備Dionex IonPac AS11-HC色譜柱(4.0 mm×250 mm)的Aquion RFIC離子色譜儀(DIONEX AQUION RFIC,美國)檢測Cl-濃度,色譜電導檢測器溫度為30 ℃,淋洗液為20 mmol/L KOH溶液,流速為1.0 mL/min,若Cl-濃度超量程,則進行適當稀釋再次檢測。
采用熒光光譜儀(島津RF-6000)檢測微生物代謝過程中分泌的溶解性有機物,激發和發射狹縫分別為5 nm和1 nm,激發和發射波長范圍分別為210~500 nm和210~550 nm。
2 結果與討論
2.1 含氯混合廢氣成分分析
菌劑研發之初,調研、采集、檢測某化工企業排放的廢氣成分及濃度。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分析的廢氣成分結果見表1,發現在檢測的12個位點中,主要污染物是CB、DCM和DCE。生產車間CB的濃度高達2 972.0 mg/m3,主要是因為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以CB作為溶劑,CB易揮發擴散,自生產車間進入排氣系統后,在之后的各個采樣口均能檢測到。同時檢測到少量的三氯甲烷、二氯硝基甲烷、氟乙烯、氯仿和三氯乙烯,上述幾種污染物的濃度在0.3~7.1 mg/m3,少量含氯副產物的產生與后續廢氣處理方法有關。上述污染物經過活性炭處理后達標排放,可見企業目前主導的VOCs處理方法為活性炭吸附。

表1 某企業生產車間廢氣成分分析
2.2 高效降解菌的生長及其CVOCs降解性能分析
針對廢氣中含量較高的三種污染物CB、DCM和DCE,活化實驗室已有的三株高效降解菌,并考察其生長情況及對梯度濃度污染物的降解情況。如圖1所示,50、100、150、200 mg/L的CB分別在16、18、24、26 h內被HY-9完全降解,最大平均去除速率為7.69 mg/(L·h),而之前報道的RalstoniapickettiiL2和Ralstoniasp. DSM 8910的平均去除速率分別為2.9、2.2 mg/(L·h)[20-21],HY-9在迄今為止報道的微生物中表現出較強的CB降解活性。降解完成后菌液的OD600值分別為0.04、0.05、0.08和0.16,HY-9的生物量隨CB濃度的提高而增加(圖1(a)),200 mg/L的高濃度CB未對菌株的生長產生抑制,且有利于其盡快進入對數生長期(圖1(d))。DCM降解菌H13在前8 h內生長較為緩慢(圖1(b)),受DCM的濃度影響較小,隨后快速進入對數生長期,50、100、150、200 mg/L的DCM在24 h內平均去除速率分別為2.32、4.35、4.10、5.19 mg/(L·h)(圖1(e)),推測是DCM初步生物降解后的中間產物積累且難以被微生物利用,阻礙了微生物生長,之前報道也證實H13對DCM的降解性能在重復三個周期后下降[8]。DCE降解菌T2的生長遲緩期長達20 h(圖1(c)),可能與DCE復雜的化學結構和較高的生物阻抗相關。進入對數生長期后,T2對四個濃度DCE的完全降解可在12 h內完成(圖1(f)),菌株最大OD600值為0.12,最大降解速率為6.25 mg/(L·h),推測DCE在降解菌的作用下生成中間產物2-氯乙醇,然后氧化生成氯乙醇,之后脫氯為不含氯的有機物[10]。

圖1 單菌單底物條件下微生物的生長和污染物降解性能Fig. 1 Microbial growth and pollutant degradation performance under monobacterial single-substrate conditions
2.3 混合CVOCs的生物降解性能
單菌株、雙菌株、三菌株體系菌劑對混合污染物中CB降解如圖2(a)所示。通過和圖1(d)對比可知,CB與其他兩種污染物混合時,仍能被菌株HY-9在24 h內完全降解,平均去除速率為8.3 mg/(L·h),表明其他污染物未對HY-9菌株的生物降解活性產生抑制作用。菌株H13和T2對混合污染物中CB也具有一定降解作用,但降解速度較慢,分別為3.85、2.03 mg/(L·h)。因此當菌株HY-9分別與H13和T2混合時,200 mg/L CB的24 h去除率由92.6%和48.8%提升至100%。H13和T2雙菌體系對混合物中CB的去除速率為4.13 mg/(L·h),介于H13單菌和T2單菌之間,遠低于HY-9參與的組別。三菌株體系對混合污染物中200 mg/L CB的降解可以18 h完成,降解速率達到11.1 mg/(L·h),相比單菌體系提升33.7%,這與H13和T2對CB的輔助有關,兩種菌與HY-9協同降解CB,因此構建的三菌株體系復合菌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對混合污染物中CB的去除率。

圖2 單、雙、三菌體系對混合污染物中各污染物的去除率Fig. 2 Removal rate of components of mixed pollutants by single, double and triple bacterial systems
如圖2(b)所示,H13單菌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下對DCM的平均降解速率相較于其在單一污染物中受到影響,僅達到1.62 mg/(L·h)。在雙菌株體系復合菌劑中,HY-9+H13和HY-9+T2兩組菌劑的降解速率分別達到1.67、1.63 mg/(L·h),相較于單菌都有提升。H13和T2混合時對DCM的降解性能受到抑制,降解速率僅有1.31 mg/(L·h),甚至低于H13單菌的平均降解速率,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是菌株H13與T2的代謝過程中產生的中間產物或微生物種間分泌物抑制了H13的生物活性,使H13的代謝能力顯著下降,造成DCM去除率不升反降[22]。然而,三菌株體系復合菌劑在48 h內對混合污染物中初始濃度為200 mg/L的DCM去除率達到47.50%,其平均降解速率為1.98 mg/(L·h),是單菌體系的1.22倍。HY-9的存在顯然促進了DCM的降解,使得HY-9+H13+T2和HY-9+H13菌劑相較于其他組別表現出優異的性能。
由圖2(c)可知,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下,T2單菌在48 h內對150 mg/L DCE的去除率僅有72.0%,并且無論復合菌劑還是T2單菌對150 mg/L DCE的平均降解速率均低于單菌單底物(圖1(f),4.69 mg/(L·h)),表明其降解活性受到了共存污染物抑制。PENG等[23]也在研究中發現DCE在其他含氯污染物共存的情況下其生物降解和脫氯效果會受到限制,甚至完全停止。有趣的是,雖然HY-9和H13兩株菌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中對DCE平均降解速率只有1.09、1.24 mg/(L·h),并且HY-9+H13雙菌株復合菌劑對DCE的降解性能沒有太大的提升,但是HY-9+H13+T2菌劑和HY-9+T2菌劑在48 h內對DCE的去除率達到了100%和98.2%,平均降解速率分別為3.13 mg/(L·h)和3.07 mg/(L·h),相比T2單菌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中2.25 mg/(L·h)的DCE降解速率分別提升了39.11%和36.44%。推測HY-9和H13菌對CB和DCM進行先一步降解,緩和了這兩種底物對T2菌的抑制作用,使得T2菌在前期得到快速生長。
通過對比分析發現三菌株體系復合菌劑在混合污染物中無論是對CB,DCM還是DCE都表現出優于單菌的降解性能。在混合污染物中,三菌株共存體系復合菌劑中三種菌并不是獨自降解相應污染物,而是形成了良性的種間互作關系,減緩了污染物對菌株活性的抑制作用,使得降解性能進一步提升。
2.4 微生物生長及代謝分析
單菌株、雙菌株、三菌株體系完成混合污染物降解后的微生物生長情況如圖3所示,單菌HY-9、H13和T2的生物量都分別增長了2倍以上。由于CB降解菌HY-9也具備降解DCM和DCE的能力,同時DCM降解菌H13對HY-9和T2具正面影響,并且DCE降解菌T2也可利用CB和DCM,因此復合,HY-9+H13+T2體系菌劑在降解結束后的生物量OD600值達到0.13相較于其他幾組菌劑較高,表明微生物的生長并沒有受到混合污染物的抑制,從而能夠大量增殖。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多體系復合菌劑的OD600值都比單菌體系高,表明復合菌劑在混合污染物中的生長并沒有受到抑制。微生物多樣性使得復合菌劑可以同時應對多種污染物的降解,從而增強了其生長和代謝,使反應結束后的生物量大幅增加,這與圖2中的降解效果相符合。
污染物被降解的過程也是碳原子和能量重新利用的過程,污染物被微生物利用過程中產生的菌體蛋白或小分子有機物可通過三維熒光光譜檢測,結果如圖4所示,顯示的熒光峰分別是:熒光峰A(Ex:250~285 nm,Em:295~360 nm)、熒光峰B(Ex:300~395 nm,Em:375~475 nm)和熒光峰C(Ex:225~275 nm,Em:425~475 nm)。根據表2,熒光峰A、B、C所代表的物質分別是色氨酸類蛋白質、腐殖酸類物質、富里酸類物質。蛋白類物質主要來源于微生物胞外聚合物的分泌,有利于微生物團聚富集,蛋白質類本身為疏水性物質,可以增強微生物對于疏水性CVOCs的吸收和利用[24]。富里酸類物質相較于其它腐殖酸類物質的腐殖化程度更高,腐殖酸能夠促進CB類物質的厭氧還原脫氯[25-26]。

圖4 單/多體系菌劑降解過程中溶解性有機物的EEM圖Fig. 4 EEM diagrams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during degradation by single/multi-system bacterial agents

表2 五個常見熒光區域與對應有機物類型
通過比較三株單菌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中的代謝有機質分泌情況可以發現,HY-9和H13兩株菌能分泌出大量色氨酸類蛋白質,而T2菌在腐殖化程度上更高;通過多組菌劑的等高線對比,HY-9+T2雙菌體系保持著較高的蛋白質分泌和腐殖化能力,表明其微生物代謝活性較高,而HY-9+H13+T2的蛋白質分泌量僅次于HY-9+T2。以上結果說明了復合菌劑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下依然保持優異的代謝作用,這也是其降解效果良好的原因。
2.5 脫氯率和礦化率分析
Cl-是CVOCs生物降解的終產物之一[27],脫氯率是評價微生物的CVOCs降解能力的重要指標。比較圖5中9個實驗組的脫氯率,發現盡管HY-9降解CB的能力較強,但它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中的脫氯能力較差。根據以前的研究報道,CB脫氯一般是先用羥基取代,生成鄰氯苯酚,間氯苯酚等中間產物,再進一步開環脫氯,降解途徑較為復雜[28],一部分氯離子會保留在中間產物上,因此導致HY-9菌降解CVOCs過程中脫氯率不高。T2單菌本身在混合污染物中的脫氯率也達到了33.1%,優于HY-9單菌(27.3%)和H13單菌(31.3%),而HY-9+H13、HY-9+T2、H13+T2和HY-9+H13+T2體系的脫氯率分別為28.8%、35.7%、40%與39.4%。通過比較可以看出T2菌的加入明顯提高了復合菌劑體系的脫氯率,這可能是由于T2單菌具備脫鹵酶相關的基因[29]。有趣的是,三菌株體系復合菌劑中T2菌在其他兩種菌的促進下,脫氯效率比起單菌更是得到了明顯提升,原因可能是其他兩株菌將部分污染物轉化為更易被微生物利用的中間產物,緩解了環境毒性,使得T2菌活性增強,反過來協助另外兩株菌脫氯降解,形成良性種間合作。
污染物作為碳源被微生物利用時,污染物中的碳原子除了被轉化為可溶解的物質外,另一部分可被轉化為菌體和二氧化碳[27]。各實驗組完成降解后的二氧化碳轉化率(礦化率)如圖6所示,其中HY-9+T2菌劑降解污染物結束后的礦化率最高,達到了37.8%,比三組單菌體系菌劑分別高出9.6%、16.6%和19.9%,而三菌株體系復合菌劑的礦化率也到達了31.5%,僅次于它。一方面是由于HY-9+T2菌劑在混合污染物體系中微生物活性并沒有受到抑制,因此在對三種底物降解方面都保持著良好的性能,其次T2菌優良的脫氯能力與HY-9的降解性能相互配合,有利于污染物分解更快更完全。

圖6 不同體系菌劑降解結束后的礦化率Fig. 6 Mineralization rate at the end of degradation bydifferent systems of bacterial agents
2.6 機理分析
三菌株體系復合菌劑在降解混合CVOCs時,首先,可以利用不同菌株的專長和代謝途徑,增強降解CVOCs的能力。每個菌株都可以針對不同的氯化物或污染物產生特定的酶系統[23, 30],從而實現對不同污染物的有效降解;其次,不同菌株之間可以通過合作代謝增強降解能力:在降解CB的過程中,其中間產物如氯苯酚,苯酚等會累積,從而影響降解速率,而菌株Starkeyasp.被發現具有能降解苯胺、苯酚類物質的酶[31],能進一步利用這些中間產物作為自身的底物,加速降解速度;最后,菌株之間的協同作用可以促進CVOCs的降解速率。HY-9對CB的高效降解能緩和CB對其他兩株菌的毒性,而H13和T2代謝過程中釋放的腐殖酸能反過來促進CB降解[26]。復合菌劑通過多株菌株的應用,可以適應復雜的環境條件,從而增加了降解含氯污染物的適應性和應用范圍。
3 結 論
本研究首先實地考察化工企業CVOCs排放的廢氣成分及濃度,發現CB、DCM和DCE為主要污染物,隨后針對性活化本實驗菌種庫中對應降解菌HY-9、H13和T2,并研究單菌、雙菌和三菌體系對混合污染物的降解效果。HY-9外的單菌在混合污染物中對各自污染物的降解活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H13及T2對DCM與DCE的降解速率只有1.62 mg/(L·h)和2.25 mg/(L·h)。而HY-9+H13+T2復合菌劑中的三株菌之間形成良好的種間互作,對混合污染物中CB、DCM和DCE的降解速率分別比單菌分別提升了33.70%,22.22%和39.11%,并且復合菌劑的脫氯能力和對復雜污染物環境的耐受能力都明顯增強。本研究可以為微生物制備復合菌劑在降解CVOCs的研究和應用提供研究思路和數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