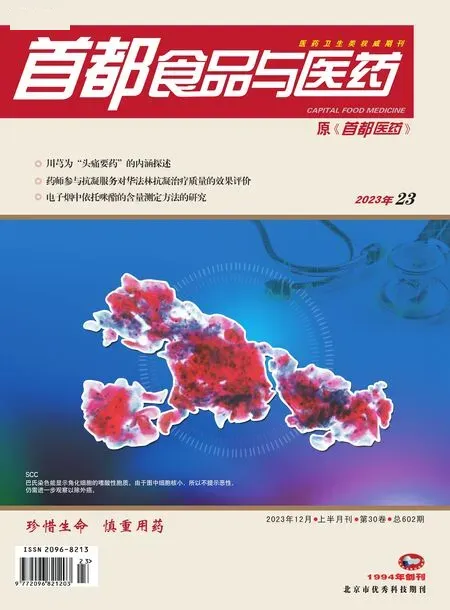溫經湯聯合毫火針對虛寒瘀阻型白癜風患者皮損色素、RCM評分的影響
岳賽(湘南學院附屬醫院,湖南 郴州 423000)
白癜風為臨床常見后天色素性皮膚病,表現為局限性或泛發性皮膚黏膜色素完全脫失。該病發病原因尚不明確,一般認為與遺傳、神經精神、自身免疫等有關。目前以308nm準分子激光照射、他克莫司乳膏外用等為該疾病的主要治療方法,前者通過誘導T細胞凋亡、促進黑色素細胞新生進行針對性治療,后者為外用免疫抑制劑,可抑制T淋巴細胞作用,原多用于中重度特應性皮炎的長期治療,現已廣泛應用于免疫相關性皮膚病的治療。但目前白癜風的常規治療往往周期較長,易發生各種不良反應。中醫認為該病屬“白駁風”“斑駁”“白癲”等范疇,其中虛寒瘀阻型為常見證型,病位于肌膚,源自血液,根在臟腑,臟腑虛虧,風寒濕邪入侵后,致氣滯血瘀、肌膚失養而發病,需進行活血化瘀、疏經通絡等治療[1]。溫經湯為理血劑,具有養血祛瘀、溫經散寒之效[2]。毫火針指將毫針加熱后對目標位置進行針刺,通過機械性刺激及熱傳導作用改善局部血運,達到舒經活絡之效[3]。為此,本次研究選取74例虛寒瘀阻型白癜風患者,探究在對其予以常規治療的基礎上應用溫經湯聯合毫火針治療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22年1月-2022年10月期間收治的74例虛寒瘀阻型白癜風患者為研究對象,隨機分為A組、B組,每組各37例;A組男女比例為21∶16,年齡18-48歲,平均(35.69±5.21)歲;體質量指數20-26kg/m2,平均(23.31±2.02)kg/m2;病程1-7年,平均(3.07±0.85)年;皮損部位:四肢9例、胸背部17例、頭面部11例;B組男女比例為19∶18,年齡18-49歲,平均(36.00±4.28)歲;體質量指數20-27kg/m2,平均(23.59±2.33)kg/m2;病程1-8年,平均(3.10±0.77)年;皮損部位:四肢11例、胸背部15例、頭面部11例;B組患者一般資料與A組相近(P>0.05)。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符合白癜風診斷西醫標準[4];②符合白癜風中醫診斷標準中虛寒瘀阻型診斷標準[5];③年齡≥18歲;④資料完整,可保證完整治療;⑤對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標準:①存在認知、精神障礙,無法有效溝通、治療;②合并皮膚損傷、過敏等皮膚性疾病;③存在心、肝、腎等器官功能衰竭;④合并凝血功能障礙、血液系統疾病;⑤合并惡性腫瘤;⑥合并活動性出血。
1.3 方法 兩組均應用308nm準分子激光治療(XECL308C型準分子激光治療儀由半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及0.1%他克莫司乳膏外用治療。在此基礎上,A組應用溫經湯治療:吳茱萸、麥冬各12g,當歸、黨參各10g,芍藥、桂枝、半夏、牡丹皮、川芎各6g,生姜皮3g,甘草各5g,先用溫水浸泡30min,武火煮開后用文火燉煮取汁,每日1劑,早晚兩次飯后溫服。B組在A組治療基礎上,聯合應用毫火針治療:毫針規格為0.35mm×25mm,皮損部位皮膚表面消毒后,取毫針在酒精燈火焰中外焰上炙烤至針體1/3熾白后,在皮損處由外至內快速刺入,至皮膚輕微潮紅,兩次穿刺點之間間隔0.2-0.3cm,使皮損部位獲得均勻針刺。每次針刺前均于酒精燈外焰炙烤,每周治療1次。兩組患者均持續治療12周時評價療效。
1.4 觀察指標 ①治療效果:治療前后對患者進行中醫證候積分[5]評價,包括皮膚晦暗/青紫/發黑,皮膚邊界不清,四肢冷,舌紫暗/瘀點,脈沉細,癥狀評分范圍0-3分,分數高表示癥狀嚴重,舌診、脈記為0分、1分,總分范圍0-11分;治療后積分較治療前下降>75%為顯效,下降50%-75%為有效,下降<50%為無效,有效率=(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②比較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③比較兩組治療前后皮損色素評分[6]:皮損分數0-3分,分別表示正常顏色、淡膚色、發白、完全變白;④比較兩組治療前后RCM評分[7]:應用反射式皮膚激光共聚焦掃描顯微鏡(RCM)檢查,包括色素環(色素環完整/部分缺失計+1分,色素環缺失計-1分)、邊界(邊界不清計+1分,邊界清晰計-1分)、邊界炎性浸潤(皮膚處真皮與表皮交界出現高折光性細胞計+1分)、新生樹突狀黑色素(皮損處出現高折光黑色素細胞,并呈現樹突狀計+1分),總分-2-+4分,分數高表示癥狀嚴重;⑤比較兩組治療期間安全性。
1.5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27.0統計學軟件分析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n(%)]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治療有效率 B組治療有效率較A組高(94.59%VS78.3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治療有效率比較[n(%)]
2.2 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 治療前B組中醫證候積分水平與A組相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中醫證候積分水平均較治療前低,且B組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s,分)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s,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A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后 t P A組 37 6.35±1.22 4.41±0.95* 7.632 <0.001 B組 37 6.40±1.31 3.38±0.88*# 11.640 <0.001 t 0.170 4.838 P 0.866 <0.001
2.3 治療前后皮損色素評分 治療前B組皮損色素評分水平與A組相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皮損色素評分均較治療前低,且B組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皮損色素評分比較(±s,分)

表3 兩組治療前后皮損色素評分比較(±s,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A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后 t P A組 37 2.01±0.23 0.97±0.13* 23.945 <0.001 B組 37 2.05±0.44 0.54±0.10*# 20.356 <0.001 t 0.490 15.948 P 0.626 <0.001
2.4 治療前后RCM評分 治療前B組RCM評分與A組相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RCM評分均較治療前低,且B組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治療前后RCM評分比較(±s,分)

表4 兩組治療前后RCM評分比較(±s,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A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后 t P A組 37 3.10±0.60 1.21±0.33* 16.789 <0.001 B組 37 3.13±0.77 0.84±0.20*# 17.509 <0.001 t 0.187 5.833 P 0.852 <0.001
2.5 治療安全性 兩組治療期間均未出現明顯不良反應。
3 討論
白癜風發生的原因尚不明確,可能與多種因素有關,主要表現為皮膚表面黑色素缺失,出現局部或泛發皮膚顏色變白現象,進展期會出現皮損與周圍皮膚邊界不清晰、皮損面積擴大等情況,可嚴重影響患者外表形象。在對其進行常規治療中,以控制皮膚炎性浸潤、免疫調節等方法為主,但治療時間相對較長,且在停止治療后存在易復發、不良反應發生率較高情況。
中醫認為,該病發生多由外邪侵襲引發,可導致經絡瘀滯、氣血不和、氣滯血瘀、肌膚經絡失于濡養。因此應用中醫方法治療該病的主要目的為活血化瘀、化寒除濕、祛風散邪,以改善其臨床癥狀[8]。溫經湯為寒邪痹阻證疾病的主要治療方劑,出自《金匱要略》。方中吳茱萸、桂枝共為君藥,其中吳茱萸辛熱,可入肝腎,使沖任通達,以行氣止痛,桂枝辛甘,溫入血分,可使血脈暢通,兩者合用可溫經散寒,使血脈通暢;芍藥、川芎、當歸共為臣藥,可養血調經、活血化瘀;麥冬可清熱滋陰,防治溫補太過而使熱毒內生;半夏、生姜可和胃溫中,黨參可益氣健脾,共為佐藥,使脾胃調和;諸藥合用,可活血化瘀、溫經散寒[9]。毫火針屬中醫傳統治療方案,與火針相比,其針體直徑更小,對患者創傷程度較低,治療過程中,通過針尖刺激、針體熱傳導作用,以改善局部血運狀態,促進皮膚血管擴張,達到局部免疫調節治療效果。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B組治療有效率較A組高(94.59%VS 78.3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前B組中醫證候積分水平與A組相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中醫證候積分水平均較治療前低,且B組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在對白癜風治療基礎上,應用溫經湯聯合毫火針治療,可降低患者中醫證候積分水平、提升治療有效率。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溫經湯中吳茱萸具有鎮痛、抗缺氧、抗凝等作用,在對該病治療中,可通過吳茱萸的抗氧自由基作用,降低局部炎癥反應程度,減輕血管內皮細胞及軟組織功能損傷,同時該藥可改善微循環,在清除局部血清炎癥因子水平基礎上,改善皮膚微循環,維持細胞功能穩定;桂枝的主要作用為抗過敏、抗炎等,同時可擴張血管,促使血液向體表流動,促進皮膚細胞功能提高,促使黑色素細胞生長,以改善白癜風臨床癥狀[10];當歸具有抗輻射、抗損傷、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川芎具有抑制血栓形成、改善微循環等作用;芍藥具有抑菌、鎮靜、解痙、抗氧化等作用;半夏具有抗潰瘍、降脂、抗炎等作用;黨參具有抗血栓等作用。因此在應用溫經湯治療后,可通過其改善皮膚微循環、抗炎、免疫調節等作用,促進患者皮損消退或減少;毫火針治療中,通過直接機械性刺激及溫度刺激,可使局部血管擴張,進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環,調節局部細胞免疫功能,消除局部血管痙攣、氧化應激反應等癥狀,促進皮膚組織修復[11]。此外,在毫火針治療中,因其針體直徑較小,所以在針刺過程中對皮膚物理性損傷較小,治療后不易出現滲血、瘢痕等情況,可維持細胞組織結構及功能穩定性,提升治療效果。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前B組皮損色素評分水平與A組相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皮損色素評分均較治療前低,且B組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前B組RCM評分與A組相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RCM評分均較治療前低,且B組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在對白癜風治療基礎上,應用溫經湯聯合毫火針治療可改善患者皮膚癥狀。白癜風發病原因可能與局部免疫異常、皮膚細胞炎性浸潤后細胞色素調節能力下降有關。在應用溫經湯治療中,通過抑制炎性滲出、改善皮膚微循環等作用,可減輕皮膚細胞結構缺血、氧化應激性損傷,改善皮膚細胞質量,促進皮膚細胞功能恢復,但在單純應用溫經湯治療中,若通過升高全身用藥濃度以改善皮膚癥狀,則治療缺少靶向性;而聯合應用毫火針在病灶邊緣向中心針刺治療,可通過針刺作用直接進行病灶刺激,以控制病灶邊緣細胞向周圍組織炎性浸潤的情況,從而改善周圍病灶細胞血運循環,控制病灶面積繼續擴大,并在后續治療中逐漸縮小病灶面積;而且在逐漸向病灶中心針刺治療過程中,可通過均勻針刺治療,改善病灶內皮膚細胞功能,促使黑色素細胞再生,實現靶向治療效果,改善白癜風癥狀[12]。兩種治療方案聯合應用后,局部毫火針治療可在靶向作用下直接改善病灶血運狀況,促進黑色素細胞功能恢復,而使用溫經湯則可持續性抑制皮膚炎癥,實現整體調控作用。在中醫理論中,溫經湯可溫經活血、養陰清熱、益氣健脾,使機體血運調達、經絡暢通,改善患者虛寒癥狀,并在毫火針配合治療下使皮膚得以更好的濡養,改善白癜風癥狀。本次研究中,兩組均未見明顯不良反應,提示聯合治療安全性良好。
綜上所述,對虛寒瘀阻型白癜風患者應用溫經湯聯合毫火針治療,可提升治療效果、降低中醫證候積分,并降低皮損色素評分、RCM評分,且治療安全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