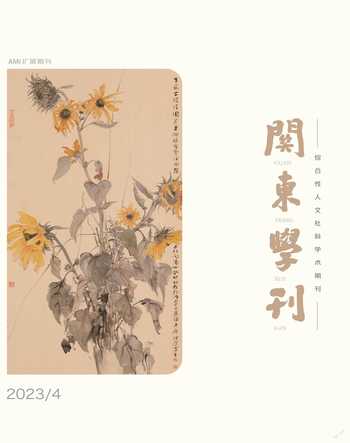論畢飛宇小說中的“漂泊情結”
陳元峰 胡慧
[摘 要]畢飛宇的小說無論是歷史敘事還是現實敘事,都體現出一種無根、無家的漂泊感。人們永遠在追尋歸宿,在一次又一次的短暫停泊后再次踏上了尋找的旅程,“家”成了“火車里的天堂”,近在咫尺卻觸不可及。外在的無根在精神更深層次體現為對自我身份的困惑,人物處于無法認同自我的分裂當中。他的小說中人物既在尋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同時又表現出一種尋而不得的困惑與焦灼,這種無根無家與身份錯位的痛楚使得畢飛宇的小說具有強烈的悲劇色彩。
[關鍵詞]畢飛宇;漂泊情結;身份錯位;悲劇性
[基金項目]內蒙古自治區草原文學理論研究基地項目“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內蒙古小說中的草原書寫研究”(2019ZJD041)。
[作者簡介]陳元峰(1970—),男,文學博士,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慧(1995—),女,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通遼 028000)。
無論是西方16世紀的“流浪漢小說”還是中國自《詩經》就有的“游子思鄉”詩歌模式,“漂泊情結”早已滲入到文學作品中,成為言說不盡的話題。現代文學里的“漂泊情結”則體現在京派文學“回不去的家”和海派作家的“都市懷鄉病”中,四十年代文學的一系列“曠野意象”也有反映。這種情結在當代小說中也被作家反復言說,它是白先勇《臺北人》里陵谷滄桑的痛楚,是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中那種“我們好像被潮水推到沙灘上的魚,徒然地在孤獨與死亡中間掙扎”【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203頁。】的感覺。而“漂泊情結”在畢飛宇小說里則更為明晰,他前期作品重在言說歷史,后又轉向日常敘事,看似轉變了風格,但其有統一的“調性”,其中一個重要的“音調”就是“漂泊情結”。在歷史類小說中畢飛宇帶著懷疑的眼光試圖尋找歷史真相,這體現出一種回溯民族文化記憶的渴望,是一種尋找精神根基的姿態;尤其是近年來他的書寫對象一再轉向虛構的“王家莊”,這也體現出作者因無根而渴望回歸的心態。書寫現實類的作品呈現都市人精神荒蕪,是從另一個維度體現出這種渴望。其歷史小說與書寫當下現實的小說形成一種互為表里的關系,作者以他切身的感觸發現失根之痛,又在尋根中復歸迷茫,“漂泊情結”成為作者與其小說人物共同的生命體驗。
一、斷裂與消弭——歷史敘事中的“漂泊情結”
畢飛宇小說中的“漂泊情結”首先以在歷史敘事中探尋精神根基的姿態出現。父親因為“右派”問題被下放鄉村,畢飛宇整個童年都在“文革”時期文化貧瘠的農村度過,這使得他對那段歷史耿耿于懷,他試圖重新挖掘出歷史真相去填補那塊心靈的空缺。他說:“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特別想補充一點,作為‘文革’的第二代,我認為,中國文學關于‘文革’的書寫不僅不應當草率地結束,而應當重新開始。”【畢飛宇:《寫滿字的空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75頁。】對于“文革”那段歷史,他在小說中進行了追問與探尋。對此有人評價道:“畢飛宇獨有歷史之癖,他對歷史懷有知識分子式的興趣,歷史對于他不是一個給定的背景,歷史是一個未解之謎,有待說明和求證,在他作為小說家的隱秘雄心中,必定包含著達到綜合經驗與哲學的歷史洞見的渴望。”【李敬澤:《畢飛宇的聲音》,《今日中國文學》2010年第1期。】
在苦苦探尋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手電筒”成為畢飛宇反復借用的一個特殊意象。《地球上的王家莊》《枸杞子》《蛐蛐 蛐蛐》《是誰在深夜說話》等小說中手電筒是在茫茫黑夜中的光源,也是探尋的工具,帶有一種滿足求知的懷疑性質。正如手電筒的光芒面對浩瀚天空時是微弱而無力的,人對歷史的追問也復歸迷惘,這使得漂泊感在畢飛宇心中慢慢萌芽,“探照夜空是一件充滿了希望的事,你能夠得到的卻一定是絕望”。【畢飛宇:《蘇北少年“堂吉訶德”》,濟南:明天出版社,2012年,第60頁。】所以,他筆下的歷史也終歸成為一種個人想象,不斷的原景反芻正是由于探索無望。即便是窺見了歷史真相,也無力抵抗根據現實需要去重構歷史的大多數現代人。《是誰在深夜說話》中工人隨手扔進煙頭的泥漿被糊上新修補的明城墻,而且說“修成什么樣明代就是什么樣”,對歷史是一種毫不在意的態度;《祖宗》里的一段話應和了《是誰在深夜說話》:“你弄那么堅固又有什么意思?朝代就這樣,建筑如牙齒,長了又脫。”同樣是失根而無尋根意識。失眠而深夜游蕩在城墻下的“我”在《是誰在深夜說話》中每晚都會看到作為民族記憶的歷史是怎樣被精神失根者修補,但修好后卻驚恐地發現舊城墻的磚多了出來。“我”的恐懼感正是由于窺見了現代人欲以新的“歷史”完全遮蔽歷史原跡而不得的一種疑惑和膽怯。當殘存的歷史原跡在黑暗中探出它的雙手時,作為失根群體中少數清醒者的“我”卻無力挽救。“歷史”終究是屬于那些夸贊新城墻“比下面的舊城墻漂亮多了”的絕大多數者的,這種集體的力量足以淹沒歷史原跡,“因為我們總是從我們當代世界的視角來記憶過去。我們的記憶總是處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位置,作為與過去的有意義的聯系,記憶因此可以依據一個個體或者群體的新出現的需要而改變”。【[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論歐洲文學與歷史》,金壽福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98頁。】“我”的聲音也將淹沒在集體當中。《是誰在深夜說話》中的“我”是說出歷史真相的人,小云是對補修城墻的荒唐做法置若罔聞的人。而救了小云的“我”在向她求婚時卻遭到了嚴詞拒絕。這其實寓意了無尋根意識者與精神尋根者的一場狹路相逢,最終以后者的失落離去而告終,只能看著歷史真相淹沒在了現代時空里。與敘述者站在同一立場的作者對這種拆解歷史的做法持批判態度:“所謂修城墻,說白了就是歷史闡釋。我認為,‘中國特色的歷史闡釋’就在城墻的修理當中了。我們的歷史闡釋是極其卑鄙的,它最可恥的就是邏輯嚴密,它像一個盜賊洗劫一空后布置了一個現場。”【畢飛宇、張莉:《這個時代需要想象,也需要思考》,《花城》2014第4期。】正如現代人追求一種邏輯嚴密的歷史闡釋,《祖宗》里的兒孫也在強迫象征著歷史原跡的老太奶“壽終正寢”。被兒孫強迫拔了牙齒的百歲老太奶倒在地上沒了鼻息,然而兒孫們卻在夜晚驚恐地聽到她指甲摳刮棺材的聲音。這種恐懼感體現出現代人愚昧的歷史觀,“《祖宗》所關注的當然是愚昧。這愚昧首先是歷史觀,我們總懷揣著一種提心吊膽的姿態去面對歷史,所以,要設防。拔牙是設防。愚昧的設防一直在殺人”。【畢飛宇:《寫滿字的空間》,第98頁。】這種愚昧的設防又最終導致現代人進行邏輯嚴密的歷史闡釋,最終消弭了歷史原跡。
正如幾塊代表歷史原跡的明城墻磚頭在《是誰在深夜說話》中寂寂留存在黑夜并最終消弭在現代“歷史”中一樣,《祖宗》中還有生命跡象的老太奶掙扎的指甲最終還是沒了聲響,這一天“我們一家等待了很久”。就這樣,這些探尋歷史真相的人只能是一個個“城墻根”下的“游蕩者”,無法在真正意義上找到精神的立足點。民族真實記憶被埋在深層,家族記憶也同樣無跡可尋。這種歷史的斷裂和消弭,使個人和民族都難以找尋精神的“歸依”,于是“漂泊”之感無可奈何地滋生了。
二、無家可歸——日常敘事中的“漂泊情結”
有了現實中的“家”,身體才有棲息之地,于是畢飛宇小說中的“漂泊情結”又表現在對現實中“家”的渴望。小說中年輕人離開父母后開始尋找自己的歸宿,與相愛的人留在城市中奮斗。“他就渴望能有這樣的一天,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很家常的日子,他一覺醒來了,拉著‘她’的手,在‘戶部街菜場’的貨架前走走停停,然后,和‘她’一起挑挑揀揀。哪怕是一塊豆腐,哪怕是把菠菜。能過上那樣的日子多好啊。會有的吧。總會有的吧。”【畢飛宇:《相愛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224頁。】《相愛的日子》里的這段話將年輕人的心愿表達得淋漓盡致:渴望回歸家園。而在孩子的世界里,母親即意味著安全的歸宿,所以《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才會那樣渴望母乳,《家事》里田滿才會同意稱同齡的小艾為“媽媽”。同樣的,老人也渴望兒孫滿堂,渴望子女陪伴,《彩虹》中老鐵夫婦用“看石英鐘”的方式排解對孩子的思念,代表了畢飛宇小說中一系列老人形象對“家”的渴望。
但是渴望“家”的人們卻又如飛絮飄往遠方,他們或是被“家”逼退而被動離開,或是在尋到歸宿后再次主動逃離,或是在失望中麻木,失去了尋找“家”的理想,滿足于“九層電梯”里的“遙控”生活,最終永遠偏離了回歸的方向。對漂泊者來說,“家”就是“天堂”,是一種理想,尋找到它就可以安放自己的魂靈,但這樣帶有理想色彩的“家”被神圣化了,它就像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中豹子一直尋找的完美的白山羊,在現實生活中永遠也無法找到。說到底,畢飛宇筆下的人物是一群心靈的無根者,即便他們尋到了外在的安棲之地,也會再次踏上“火車”繼續追尋“家”,“火車”成了他們真正意義上的“天堂”。
(一)背井離鄉:漂泊命運的開始
在畢飛宇的小說中,“外鄉人”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們或者由農村遷移到城市,或者由一個村莊輾轉到另一個村莊,故鄉已無法回去,異鄉又無法立足,他們如無根的浮萍開始了無盡的漂泊。《賣胡琴的鄉下人》中,賣胡琴的老人從鄉下來,只能到城市骯臟的下水管道住宿;《美好如常》中一生煢煢孑立,以乞討為生的仙人李死在了自己的茅屋門口;《平原》中的吳曼玲以拋棄女性身份為代價想積極融入王家莊,卻走上了人性異化的道路。停泊是他們的最初心愿,漂泊卻成為他們的最終命運。《充滿瓷器的時代》中藍田和自己的女人渴望“在這兒”停泊,為此,“藍田和他的女人有意無意地學起了秣陵鎮人的聲腔聲調。這是接近異鄉人的唯一途徑”。但是他們的住地又時刻被上一家異鄉漂泊者的影子所籠罩,逃不開漂泊的命運。在畢飛宇的不定點敘述中,豆腐坊的故事是通過藍田家的視角展現,藍田家的故事則由另一個外鄉人講述,每一個來到此處的外鄉人都以為“這兒”是最終的歸宿,但卻又一次逃往異鄉。“在這兒”的外鄉人結局也頗為悲慘,甚至充滿了鬼氣,仿佛“在這兒”成為一個咒語,一旦停泊就必遭厄運,唯有漂泊才能生存。《上海往事》里從鄉下來的“歌舞皇后”小金寶在孤島上似乎找到了自己故鄉的影子并希望留下來,但最終死于孤島。在這里,歸鄉的愿望似乎以死亡為代價,這也意味著“漂泊”與生存構成統一關系。他們的“家”似乎永遠是行在水上的船。由《上海往事》改編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恰是凸顯了這種漂泊意味。
(二)徘徊在“家”的邊緣
背井離鄉固然可悲,但建立家庭也絕非易事,年輕人在“家”的門口徘徊,他們對家的想象恰如沈從文小說中帶有神性的“白羊”,在這個物質世界中無法尋覓,他們建立的“家”如同琉璃般易碎。執著追尋者會注定永遠漂泊,《兩瓶酒》中的“我”即是執著的追尋者。畢飛宇筆下的這一人物既有奈保爾《博加特》【[英]V.S.奈保爾:《米格爾街》,張琪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第4頁。】中將理想寄托在無法觸及的遠方而不甘委于現實的博加特的影子,又有《母親的天性》【[英]V.S.奈保爾:《米格爾街》,張琪譯,第25頁。】中外在樂觀卻內心凄苦的勞拉的影子。《兩瓶酒》甚至也采用了《博加特》中不定點敘述方式【《兩瓶酒》與奈保爾的《博加特》中都只寫到人物多次回家后的諸種表現,卻沒有交代離家時經歷了什么。在大量的留白中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間,結尾才略帶一筆人物經歷。兩者行文結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使得畢飛宇和作為流散作家的奈保爾在精神上有著某種共通之處。《兩瓶酒》每寫到回家都會提到“我”新的紋身,以示有了新的歸屬,證明自己的精神與肉體有了依托。但同時也有一道又一道舊的劃痕,代表著與過去告別。正如畢飛宇在作品中多次寫到的“如果肉體不是靈魂,那靈魂又是什么?”當作為肉體一部分的胳膊不再是完整的青花而成為滿是裂痕的“汝窯”時,“我”的心靈也經歷了一次次漂泊。小說結尾“我”將外在條件優沃的“富二代”給“我”的鉆戒塞在了他襪子里還回去,“我”最終拒絕了這份即將成熟結果的感情,這也意味著放棄了最有可能的一次停泊的機會,“我”將永遠望向遠方,永遠漂泊。那個在小說中被多次提到的高中就離開家沒有回來過的“二妮”,更像是另一個“我”,或者說是“我”的心靈鏡像。
《兩瓶酒》中的“我”尋不到理想中的歸宿而注定繼續漂泊,《相愛的日子》則是在物質社會中“家”的理想被迫向現實妥協。“《相愛的日子》書寫了生活在邊緣世界里的青年們的生存困窘:金錢化倫理關系進入了原本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的血液中。”【張莉:《畢飛宇:作為“記憶”生產者的作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2期。】這種金錢化倫理關系將年輕人對“家”的憧憬撕得粉碎,“回家之后又要出來,還不如索性留在城里”的男孩與同樣處境的女孩相互取暖,但女孩卻在回了一次家之后,便要另選配偶結婚。作者在這里留下了空白:女孩回家后經歷了什么才讓她匆匆拋棄男孩去挑選一個毫無感情的男子結婚?她面對的,或許就是《兩瓶酒》中“我”在家中遭遇“催婚”的膩煩而又無可奈何的經歷。在此兩篇小說有了一種互補關系。回家他們面對重重壓力,在異地城市也仍舊是孤獨無依。在茫茫人海中,他們自我確認的方式似乎也只有《兩瓶酒》中用微信刷存在感,或者是像《相愛的日子》里那樣兩個人近在咫尺,但為了制造一種“有人理睬”的狀態而互通電話。《相愛的日子》中錯過的兩個人的故事延續就構成了《生活邊緣》。在這篇小說里,作者讓主人公小蘇和夏末有了建立家庭的可能。然而他們的家隨時可能土崩瓦解,他們倆也隨時可能分道揚鑣,就像小說中的火車,“火車失之交臂,它們朝著各自的方向呼嘯而去,聲音在兩邊的遠方消逝”。他們的家在這個城市的邊緣,“火車就在窗子底下,離他們十幾米遠,只隔了一道紅磚墻。小蘇在一瞬間產生了錯覺,火車在她的凝望中不動了,仍在旅途的是他們自己”。小蘇盼望生活停下來,正是因為感到自己的生活總在動蕩之中。在這篇小說中,火車成為了一個關于漂泊的意象,它與“家”既是反義,又隨時有可能成為同義。小說結尾那張灰蒙蒙的畫布暗示著夏末與小蘇兩個人的愿望徹底落空。正如小說中所寫:“這個城市居然如此脆弱,僅僅是家的愿望就使一派繁華變成了一張灰”。
(三)逃離婚姻的“圍城”
錢鍾書《圍城》中的“圍城”具有寓言性質,它不僅象征人們的婚姻和生活的困境,也象征著人的精神困境。在畢飛宇的小說中,進入婚姻圍城的人們有了穩定的家庭外殼,但是內核卻依舊不穩固,他們又渴盼掙脫“家”的束縛。《生活邊緣》中的夏末與小蘇在《火車里的天堂》里擔當了路人甲的角色,成為了坐在“我”對面的新婚夫婦。他們恩愛有加,但一場旅行還未結束他們就已將“離婚”掛在嘴邊,隨時都可能在不同的站點下車。火車是動蕩的象征,“火車里的天堂”則似乎意味著只有動蕩與漂泊才是永恒不變的。沒有進入婚姻殿堂的情侶像小蘇與夏末那樣充滿了動蕩,已婚的人則更是像“我”與“她”那樣忙著擺脫這種穩定。正如小說中所寫“離婚是現代人的現代性”。在《火車里的天堂》中,準備復婚的“我”與妻子書信來往,“用這種古典的方式裝點現代人生”,但在火車上又與準備離婚的“她”在旅途上曖昧起來,兩個萍水相逢的人,卻比家人更多了些溫情,似乎人們的“天堂”不在家庭,而是永遠在“火車里”。離婚的人在航過千山萬水之后,卻又思戀起最初的感情。這些擁有婚姻的中年人在離婚與復婚中糾纏,卻依然無法排解內心的孤獨,就像《生活邊緣》中離了三次婚的汪老板雇用小蘇只是為了回家后有個人說說話,他擁有了豪華的房屋卻沒有溫馨的家。寂寞的都市人即便擁有了穩定的家庭也難以抑制自己對別處的向往,即便沒有離婚也試圖過一次別樣的生活。《家里亂了》中能歌善舞的樂果并不滿足平淡且有些清貧的生活,走進了夜總會,迷上了新鮮刺激的生活。小說結尾原本充滿悔意的樂果將家里徹底清理一遍,大有重新做一個賢妻良母的決心了,然而在這寂寂的家里她又情不自禁化好妝,望向了外面充滿誘惑的夜間城市。這意味著她對背叛家庭再次蠢蠢欲動。樂果不能滿足,又始終處于一種不安于停泊的狀態,這是這個人物的悲劇性所在。《林紅的假日》中的青果形象是樂果的濃縮,并由一個實體變成了毫無羈絆的魅影進入了林紅的內心。林紅在被青果“啟發”之后,想親身做一次放縱自己的實驗,然而責任與顧慮終于又將她從肉體出軌的邊緣拉回到只是精神放縱的軌道。但無論如何,對這些已經擁有“家”的人來說,“家”似乎都不再有最初的吸引力,遠方成為他們目光的凝聚處,這也使得他們選擇了主動漂泊。
總之,畢飛宇以“一系列短篇小說書寫了這個時代的熱熱鬧鬧,正如我們對這個時代的表象感受。但與此同時,他也描畫了那個糾纏著我們每一個人無法言傳的體驗:熱鬧之下掩不住的破敗和寒冷,掩不住溫暖外殼下每個人的內心荒蕪”。【張莉:《畢飛宇:作為“記憶”生產者的作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2期。】這種荒蕪其實也就是無根的漂泊感,正如現代作家廢名《街頭》中描寫的那樣,即便是所有聯系世界的媒介與工具都出現,也不能拯救人們內心的孤獨與寂寞。無論是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還是廢名的《街頭》,那種難掩的漂泊感都以幽靈化【“幽靈化”由德里達提出,是一種“不在場的在場”現象,不能明確找到被影響的證據,但卻有繼承和受影響的痕跡。德里達提到“人們在我的早期研究中也可能接觸到這樣的思考。幽靈不僅僅是靈魂,鬼魂,回過來不合時宜地召喚我們繼承遺產的東西,而且還是非死非生、非真非假、把鬼魂的維度重新引入政治的東西,它還幫助我們理解現實公眾空間、媒介、交流等等的結構”。(德里達、達尼埃爾·邦塞依德:《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對話》,杜小真譯,https://ptext.nju.edu.cn/b7/e2/c12196a243682/page.htm,2023年1月11日。)】的方式再現于當代作家畢飛宇的作品中,深刻描繪出當代人的精神狀態。
三、自我認同危機——“漂泊情結”的深化
畢飛宇在《一個人的大街》演講中提到他對“identity”(身份)格外關注。身份是定位自我的一種方式,只有身份自我認同才會得到本體安全感。但是,在畢飛宇的小說中,人物卻發生了自我認同危機,從而引發靈魂深處對自我的懷疑,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失根。正如評論所說:“畢飛宇對‘身份’有天然的敏感,所以,他既能寫出鄉野中的自我及其英雄夢,也能在‘人’與‘身份’的關系中發現悖論所在,并能從悖論中發現人的現代命運。”【胡傳吉:《與舊傳統及新傳統的和解——論畢飛宇小說寫作的文本自覺與鄉土意識》,《文學評論》2017年第9期。】其中提到的悖論其實就是自我認同危機,或者說是身份的錯位,它帶有一種堂吉訶德式的悲劇意味。《阿木的婚事》中的林瑤身上即有堂吉訶德的影子。她帶著一箱箱書嫁進了阿木家,“一直把自己安排在一個無限虛妄的世界里,不肯承認自己是在鄉下,嘴邊掛著一口半吊子的普通話。她堅持把阿木稱作相公,并在堂屋、雞舍、茅坑的旁邊貼上一些紅紙條,寫上客廳、馬場、洗手間”。她對“家”的想象與現實是尖銳的對峙關系,她對另一種身份的幻想也一次次被鄉下的看客無情地戳穿、嘲諷。這樣殘酷分裂的書寫與畢飛宇自身的經歷有很大關系,在《記憶是不可靠的》一文中他寫道:“可是在我的記憶中,‘我家’的生活就是我的父母所敘述的那個樣子,而不是六十年代的蘇北鄉村。這就是我關于‘家’的記憶,這里的分裂是驚人的。”【畢飛宇:《寫滿字的空間》,第174頁。】對“家”的想象同樣造成他對自我身份的困惑,他自己也帶有了堂吉訶德式的悲涼感。在《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中他寫道:“一個黑色的、皮包骨頭的、壯懷激烈的少年,他是年少的、遠東的堂吉訶德,他的敵人是那些高挑的蘆葦,他的心中充滿了沒有來路的正義。塞萬提斯預言到了我,我叫堂吉訶德。塞萬提斯將永垂不朽——我活一天就可以證明一天。”【畢飛宇:《蘇北少年“堂吉訶德”》,第224頁。】作者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與筆下人物身份的錯位共同使得“漂泊情結”深化,成為畢飛宇作品的一種標識。在“漂泊情結”影響下,他筆下的人物所得非所愿,又無法選擇更無法改變自己的身份,從而造成更深層次的命運悲劇。《雨天的棉花糖》中天性溫和的紅豆卻被父親送去戰場,這是人物命運的第一次錯位。當他戰場上做了俘虜歸來,被父親吼“你不是烈士。你活著干什么!”時,他的自尊心一次次被“戰俘”的名號撕得粉碎,這是人物命運的第二次錯位。矯正錯位的身份無疑是一種自我毀滅。“生命最初的意義或許只是一個極其被動的無奈,一個你無法預約不可挽留同時也不能回避與驅走的不期而遇,你只要是你了,你就只能是你,就一輩子被‘你’所鉗制所圈定所追捕。交換或更改的方式只有一個:死亡。”【畢飛宇:《雨天的棉花糖》,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63頁。】紅豆始終處于“鏡子與鏡子之間”審視自己,世界變得內亮而外黑,為了矯正自己錯位的身份,他最終走上了徹底的自我毀滅之路。
語言是構成民族的要素,是身份辨別的要素。《馬家父子》中老馬“堅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時候都要把一口四川腔掛在嘴上”,這表明了他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兒子馬多卻“不愿意追憶故鄉”,他熱愛那一套在老馬看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負責任的腔調”的北京話。兒子馬多不愿意承認自己的身份,造成了一種“生活在別處”的假象。這其實已經失去了身份回歸的渴望,在精神上將會離家鄉越來越遠。地域與語言對人的身份確認至關重要,兩者中的其一缺失都將造成本體的不安與焦灼。失去自己語言的焦慮在畢飛宇的小說中隨處可見,《生活在天上》里“普通話將母親隔離開了”;《彩虹》中老鐵夫婦的三個子女都遠在異國他鄉,他們的孫輩早已不熟習中國話,這使得老人為了與孩子們交流不得不使用英語,還學起了德語,隔膜感不知不覺間被強化;《大雨如注》中女兒為了學習英語而在大雨中病倒,醒來后卻說了一口父母聽不懂的英語,再也回不到使用母語的原點。在畢飛宇的小說中“聽不懂”成為了阻隔人們的外在原因,也阻隔了人們的精神還鄉之路。但筆者注意到,畢飛宇用方言寫作的小說少之又少,這或許也是他沒有固定的地域身份的一種表現。為了使自己身份有所歸依,他能做的只是虛構一個“王家莊”——一個想象中的地理所屬,以減輕這種無根的焦灼感。這也使得畢飛宇關于鄉土的書寫浸透了另一種漂泊的悲涼。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那樣喜愛作為流散作家的奈保爾,以及那條他從未見過卻感同身受的米格爾大街。
結語
畢飛宇作品中的“漂泊情結”與他的自我人生體驗不無關系。畢飛宇在訪談中說“家”對他來說意味著“漂泊”。童年時代父母因為工作不斷變更住地,他在最需要群居時卻一次次失去了玩伴,于是對他來說夏日的午后格外漫長,他只能“沿著每一家屋后的陰涼游蕩,然后再沿著每一家屋前的陰涼游蕩”,【畢飛宇:《寫滿字的空間》,第2頁。】以此打發無盡的寂寞時光。寂寞而無固定的地域所屬是他“漂泊情結”生成的開始,“作為一個‘右派’在1964年所生的兒子,我不是出生在張家莊就是出生在王家莊,不是出生在李家莊就是出生在趙家莊。這是一定的。同樣,我不可能屬于張家莊、王家莊、李家莊、趙家莊,我只是要經歷它們,感受它們,看它們,聽它們,撫摸它們。這也是一定的”。【畢飛宇:《蘇北少年“堂吉訶德”》,第3頁。】同時也帶給他無法言說的惆悵感甚至屈辱感,“我最真實的感受是這樣的:我背叛了自己的故鄉,和‘漢奸’也差不多——你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答不上來的”。【畢飛宇:《蘇北少年“堂吉訶德”》,第4頁。】地域的無根還無法造成伴隨他一生的漂泊感,家世之謎帶來深層的困惑,即自我身份的困惑,這是他“漂泊情結”生成的最重要原因。“我在過去的訪談里交代過,我的父親其實是一個孤兒。他的來歷至今是一個黑洞。這里頭有時光的緣故,也有政治的緣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個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點,我不姓‘畢’,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親姓過一段時間的‘陸’,1949年之后,他接受了‘有關部門’的‘建議’,最終選擇了‘畢’,就這么的,我也姓了畢。”【畢飛宇:《寫滿字的空間》,第127頁。】這種外無故鄉、內無精神依托的痛楚對他的人生產生了足夠強烈的沖擊力,讓他感到生如浮萍,“漂。漂啊漂。漂過來漂過去,有一樣東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遠方。我知道我來自遠方,我也隱隱約約地知道,我的將來也在遠方。我唯一不屬于的僅僅是‘這里’”。【畢飛宇:《蘇北少年“堂吉訶德”》,第4頁。】自此,“漂泊”真正成為一種“情結”在他心中打上烙印,融入他的血液。正如他在《行為與刺激》中提到的:“在合適的作家與合適的文本之間,因為自由感知的存在,作家與文本有效地構成了互文,它們彼此行風,行云,行雨,仿佛一場艷遇,所以驚天動地”,【畢飛宇:《寫滿字的空間》,第79頁。】所以他也寫出了一篇篇含有“漂泊情結”的小說。不經意間,作家的個人體驗就與小說人物彼此互通,共同構成“漂泊情結”的外在音調。
同時,在這些小說中也滲透著作家對現代化的思考,他對為了追求現代化而拆解歷史的行為進行了批判,也對拆解歷史根基后動蕩的現代生活進行了反思。無論是《枸杞子》中人們因憧憬電氣化時代而任由石油勘探隊破壞環境最終導致鄉村遍地狼藉,還是《生活在天上》中人們居住城市而遠離土地根基最終導致精神無依,都滲透了作家對現代化帶來的問題的憂慮。他的憂慮也正如吉登斯認為的,現代性影響下外部世界處于全球化狀態,但內部卻具有斷裂性,這種斷裂性使得個體心靈感受到了動蕩與漂泊,從而無法實現自我認同。【轉引自安東尼·吉登斯:《現代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37頁。】
最后,畢飛宇的小說中一以貫之的“漂泊情結”既包含了他對失去根基的憂慮,又包含了他尋找的希冀。如果說他小說中的漂泊是一種永恒的狀態,那其中的人物也將永遠保持著探尋姿態,以及反思自我生活的可貴精神。這也是畢飛宇小說中“漂泊情結”的積極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