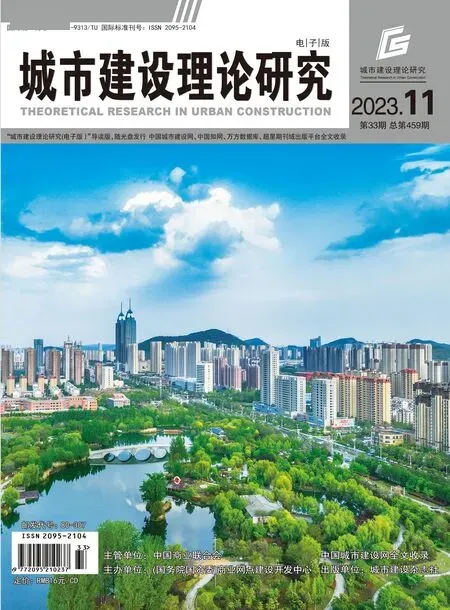“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莊規劃編制的應對研究
孔波
江西省城鄉規劃市政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 江西 南昌 330000
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背景下,“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既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也是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更是我國實現鄉村善治的必由之路,需要在實踐中探索的新路徑。村莊規劃是鄉村地區為實現鄉村振興而編制的綱領性空間管控政策工具,是開展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活動、實施國土空間用途管制、核發鄉村建設項目規劃許可、進行各項建設等的法定依據[2]。從鄉村治理的制度背景上看,如何在村莊規劃編制中貫徹好“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將對促進鄉村振興,提升鄉村地區的治理效能有著巨大的助益。然而現有的村莊規劃編制技術規程多強調宅基地布局、人居環境整治、產業發展、村規民約等內容,而對鄉村地區的系統化治理關注有限,特別是“三治融合”的理念考慮不足。因此,將村莊規劃的編制理念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進行耦合分析,有助于促進村莊規劃編制成果的實用性,理順村莊規劃助力鄉村振興的底層邏輯,提升通過村莊規劃實現鄉村治理的效能。
1 鄉村“三治”的內涵與目標
近年來,中央關于鄉村地區基層社會治理的政策逐漸明朗和確定。2017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指出,要“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在城鄉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弘揚公序良俗,促進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機融合”。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對“三治”的表述順序做了微調,將自治放在首要位置。2020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關于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提出要“以自治增活力、法治強保障、德治揚正氣,促進法治與自治、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自此,“三治融合”作為一種全新的治理模式,成為我國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相互關系總體來說就是“以自治為基礎,法治為保障、德治為先導”。

圖1 鄉村“三治”的相互關系及主要內涵
1.1 鄉村自治的內涵與目標
鄉村自治是指村莊共同體的成員依據法律法規和村規民約等治理規則,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2],它是村民行使民主權力,依法對村莊建設、村民行為等進行管理的一項基本社會政治制度。村莊自治的實質是構建具備高度自治性質的“村莊共同體”[3]。目前在鄉村治理的過程中,許多鄉村地區都在不斷的通過制度探索,激發鄉村治理的內生活力。如部分鄉村摸索出“眾廳說理”的自治模式,將以往的舊祠堂或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改造成為村民“說理”的好去處、“矛盾”的化解地、“監督”的新平臺[4];部分鄉村探索創新協商機制,推行創意工作坊、協商長廊、協商議事亭、協商小院、議事茶吧[5]等特色活動,建立了群眾協商議事會制度,讓群眾更好地參與鄉村治理行動中。
鄉村自治的目標是使村莊具備相當程度獨立管理內部事務的能力,能夠做到有法可依、有據可循,有完善的保障自治活動的空間場所,有可參考的建設發展行動指引。
1.2 鄉村法治的內涵與目標
鄉村法治是指通過法治鄉村建設,強化法律法規在維護農民權益、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權威地位。比如通過基層普法宣傳,使得廣大村民對《憲法》《民法典》《鄉村振興促進法》《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涉農重點法律法規具備初步的認識,增強了村民的法治意識和觀念。
鄉村法治的目標是建立法治可信賴、權利有保障、行為有底線的法治鄉村。一方面,對于村民,要做到普法懂法,在法治的籠子里規范行為,合理申訴居民的空間發展權;另一方面,要為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中的建設行為劃定紅線,明確行為的底線。
1.3 鄉村德治的內涵與目標
鄉村德治是指在鄉村社區中,通過弘揚傳統文化、加強道德教育、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等手段,促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形成和發展,從而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德治是“軟治理”[6],鄉村德治是村莊發展的文化內核,是鄉村文化魅力的靈魂所在,也是彰顯村莊特色與差異定位的重要因素。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鄉村德治的重要價值取向。
鄉村德治的目標是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發揮道德作用來實現鄉村善治。當前社會提倡的德治是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德治思想,以德潤人心,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引導,把激發人民向好的行為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社會輿論,榜樣示范,家教家風、公序良俗、內心信念引領良好的社會風氣。
2 鄉村“三治”與村莊規劃的關聯分析
村莊規劃與鄉村“三治”是手段與理念的關系,其本質上是一種鄉村地區空間性的法治載體,同時也是應對鄉村自治與德治需求的技術表達,村莊規劃的編制內容與鄉村“三治”有著密切的聯系。
2.1 村莊規劃是鄉村法治的重要載體
實用性村莊規劃從規劃編制體系上看,屬于“五級三類”中的詳細規劃,是城鎮開發邊界外是開展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活動、實施國土空間用途管制、核發鄉村建設項目規劃許可、進行各項建設等的法定依據。因此村莊規劃確定的村域控制線與規劃用途分區等強制性內容、耕地與永久基本農田等約束性指標等具有法律的強制性,對空間生態資源開發、空間發展權起到法定的保障作用,同時也對各項生態、自然要素的保護義務進行強約束。
2.2 規劃定位與理念貫徹是鄉村德治的重要環節
當前,許多鄉村道德失范現象時有發生,其中比較顯著的是不贍養父母、不講誠信等,一些年輕人把中華孝道拋之腦后,置道德法律于不顧,逃避贍養父母的責任,使村莊逐步喪失鄉土文化的本真。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德治的空間載體缺失,且沒有形成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氛圍與機制。
從村莊規劃的編制內容上看,村莊發展定位與目標對后續推進鄉村德治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深度提煉鄉村傳統文化、特色文化或高屋建瓴的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村莊規劃的目標和定位才有了靈魂,村莊人居環境品質及村莊風貌指引才有了方向,才能夠驅動各項要素共同發力,促進鄉村特色化差異化發展。如浙江安吉縣孝源街道以“孝文化”為特色理念融入村莊建設;湖南瀏陽市沿溪鎮建設村大力推進清廉鄉村建設等,都為鄉村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2.3 村莊規劃為鄉村自治提供基礎的技術支撐
首先,村莊規劃中的村規民約所確定的治理規則是鄉村自治的重要依據,是村民達成共識并貫徹執行的地方管理條文。村規民約中對于居住用地范圍與建設標準、設施配置、功能區劃、產業布局等涉及建設的內容,以及村民組織建設的相關規定,是推動鄉村治理的重要抓手。
其次,鄉村自治過程中所需的“眾廳說理”“議事亭”“協商小院”等空間載體,需要在村莊規劃予以明確,并通過空間設計的技術供給,滿足鄉村自治的空間需求。
再次,村莊規劃編制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將極大地助推鄉村自治的實現。鄉村地區在日常管理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宅基地的安排與農房建設、“七改三網”、溝渠水系、公共服務設施、鄉村產業發展等項目的建設與鄉村自治中的利益分配息息相關,村莊規劃在編制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內容及采取的措施,都將極大地影響鄉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的利益分配與鄰里關系。
另外,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當前鄉村地區面臨的普遍問題就是,各地農村出現不同程度的“空心化”和“老齡化”現象,鄉村自治也因此受到較為嚴重的影響[6]。根本原因是鄉村產業發展、人居環境品質等留不住人,因此需要村莊規劃通過在地化的產業運營設計,盤活資源,通過產業凝心聚力,并加強人居環境治理,改善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夯實村莊自治的基礎。
最后,村莊規劃實施的制度保障為鄉村自治提供技術支撐。比如為了激發村民改造庭院的積極性而實行的“最美庭院”制度,需要村莊規劃對庭院設計提供多樣化的指引;為了提高本土化施工的質量,保障材料、工藝的在地性而實行的“農村工匠培訓制度”制度,需要村莊中明確村莊建設的正負面清單,及本地建筑元素的提取。

圖2 鄉村“三治”與村莊規劃的關聯關系
3 村莊規劃編制中融入“三治融合”理念的路徑探索
村莊規劃的編制內容與鄉村“三治”是密不可分的。從治理體系的角度看,依靠單一的自治、法治或德治,鄉村治理必將是一盤散沙,只有通過“三治融合”,才能逐步構建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7]。那么如何將“三治融合”理念融入村莊規劃編制工作?筆者認為,應將“三治融合”理念貫穿村莊規劃編制的全過程,并建立“策劃——規劃——設計——實施保障”的規劃編制工作路徑。
3.1 策劃先行
一方面,要在全面整合涉農資源并進行產業整體策劃運維的基礎上,建立“三治融合”的制度架構與組織架構,因為鄉村振興離不開鄉村的組織化[8]。在規劃編制之始,要協助村委會謀劃鄉村自治的組織架構,強化鄉村的組織化水平,建立鄉賢組織、村民理事會、村莊老年協會、兒童讀書會、文化傳習所、村莊議事等組織機構,為后續鄉村自治的組織機構空間安排提供依據。
另一方面,充分挖掘鄉村特色,結合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勇恭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定村莊未來計劃彰顯的文化主題,使之成為統領村莊規劃編制的內在邏輯與規劃理念,夯實鄉村德治的基礎。
3.2 規劃統籌
一是,在空間保障上,通過舊房改造或項目新建,為鄉村治理預留充分的空間。充分利用閑置的農房,空置的學校、企業,村內祠堂等空間資源,通過系統謀劃,打造鄉村自治、德治的空間載體。
二是,在公眾參與上,貫徹共同締造的編制理念。目的是改變政府作為決策和實施單一主體的建設模式,要求各級政府、村集體、全體村民、社會團體等規劃相關利益主體共同參與、上下協同進行規劃建設,實現權力委托和利益分配之間的平衡[9]。在這個過程中,對于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項,需要技術人員深度參與到村莊規劃的實踐過程中,將宅基地安排、農房建設指引、“七改三網”、公共服務設施安排、產業發展項目、生態修復與綜合整治等規劃內容,充分與村民進行銜接,盡可能的將涉及到利益分配、相鄰關系、項目準入條件、行為活動要求等在規劃編制過程中予以溝通解決,為未來的鄉村自治打好堅實的基礎[10-11]。
三是,在產業引導上,通過在地化的產業運營設計,全面梳理盤活鄉村資源,通過“兩山轉化”實現鄉村生態空間資源的價值化變現,讓農民可憑借生態優勢開展生態產業化經營、開發特色民宿、生態資產入股等活動,增加農戶家庭及個人的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12]。從而激活鄉村的內生經濟動力,進而為推進鄉村自治創造堅實的產業基礎。
3.3 設計賦能
村莊規劃通過特定空間的設計指導促進鄉村自治。由于村莊規劃屬于詳細規劃,需要對建設內容有著直接的設計引導,但村莊規劃覆蓋面廣,難以面面俱到,因此村莊規劃中的設計必須是“定制化”的,并按照“用戶思維”選取村民的關注點、痛點、興趣點等展開詳細設計。比如對于村莊內的某個廣場活動空間、村容村貌展示空間、小游園、紀念堂、水系整治、景觀臺等內容,從“小設計改變細節,細節點亮空間”的理念出發,提出設計指引。
對于公共德治空間的建設,可結合祠堂改造設計,通過聲、文、圖、雕等空間藝術載體的表達,潛移默化的傳播鄉村文化。同時對于配合相應制度開展的“美麗庭院”、“清潔人居”等制度性內容,需要在規劃中,重點針對庭院的景觀設計、人居環境整治進行相應的指引,并給出正負面設計清單,引導形成既符合“德治”目標,又富有鄉土氣息的景觀設計,引導村民認識“設計賦能”帶來的發展效益,從而自發自愿采用導引建設方式。
3.4 實施保障
豐富村規民約的表達形式,將村莊規劃的內容銜接融入村規民約,以簡單易懂、重點突出為基本原則,突出鄉村建設與治理的重點內容。如根據村莊規劃內容,將村莊定位、村莊建設用地管控邊界、村民住宅建設程序、村民住宅建設的標準、公共服務選址與建設、道路紅線與建筑退讓、村民建房的具體指標等內容,在村規民約中予以明確。并確定各方主體責權、激發村民積極性,減少后續管理中的矛盾摩擦,降低治理成本。
4 結語
實現鄉村善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政策、制度的創新供給,打破部門管理壁壘,目前仍處于探索推進過程中。本文通過探索研究,認為村莊規劃本質上是一種鄉村地區空間性的法治載體,同時也是應對鄉村自治與德治需求的技術表達。因此,將“三治融合”理念貫穿村莊規劃編制全過程,有利于規劃的實施與落地,有利于化解矛盾,夯實鄉村地區的自治、德治與法治基礎。然而,治理是連續性過程,而規劃往往是“一錘子買賣”,如何建立規劃的動態維護機制?如何在村莊規劃的編制細節中,深入貫徹“三治融合”理念,仍有待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