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莫爾病的多重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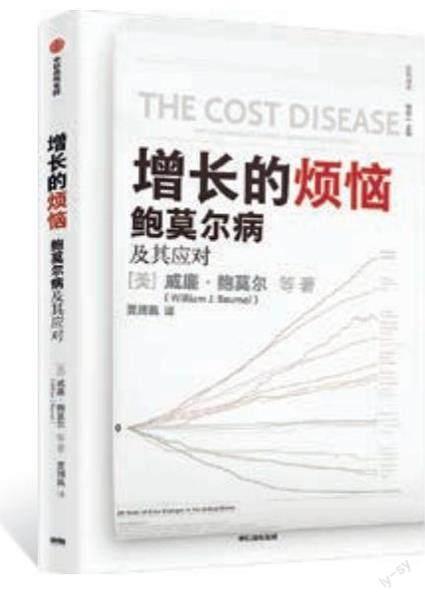
《增長的煩惱——鮑莫爾病及其應對》
(美)威廉·鮑莫爾等著
賈擁民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9月
“鮑莫爾病”是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研究藝術表演的成本和價格時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以下現象:藝術表演的成本和價格一直在上升,而其他商品的成本和價格則呈現下降趨勢。
鮑莫爾本人以及其他經濟學家的大量后續研究表明,這不是一個特殊現象,而是服務業中普遍存在的一般規律,而且無論是在發達國家中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成立。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例如菲利普·阿吉翁,已經把鮑莫爾病稱為“鮑莫爾定律”,與恩格爾定律等經濟學中其他著名定律并列。
在提出了鮑莫爾病半個多世紀之后,鮑莫爾出版了新書《增長的煩惱:鮑莫爾病及其應對》,對鮑莫爾病的形成機理、影響進行了全面剖析,然后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可能的應對政策,并且澄清了公共辯論中的一系列模糊認識。
作為增長的煩惱的鮑莫爾病
鮑莫爾指出,在組成一個經濟體的各個部門中,必定有一些部門(至少有一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在這個觀察的基礎上,鮑莫爾提出了一個兩部門非平衡增長模型,解釋了成本病的形成機制。
鮑莫爾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將經濟劃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技術進步快、生產率持續增長的“進步部門”;另一個是技術進步慢,生產率增長停滯的“停滯部門”。
“進步部門”主要指那些便于應用先進的技術設備、能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的制造業,在這個部門中,創新、資本積累和規模經濟帶來了人均產出的累積增長。“停滯部門”則主要指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保健、市政服務、表演藝術等依賴于“個人服務”的行業。
在這個部門中,勞動依然是最主要的投入,而且不容易實現規模經濟,因此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例如,在現場藝術表演中,300年前演奏莫扎特四重奏需要四個人,300年后演奏同樣一首曲子仍然需要四個人,勞動生產率沒有發生多少變化。
與此同時,為了吸引勞動力,服務業的雇主必須使工資水平與制造業保持同步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工資的上漲,再加上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服務業的生產成本相對于制造業不斷上升。
當服務業的生產成本逐漸傳遞到價格上后,服務的價格自然就會相對于產品價格上升。回到上面那個例子,音樂家的實際工資水平大幅提高了,但是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卻沒有太大的變化。既然勞動成本的上升無法用生產率的提高來抵消,同時勞動作為一種投入要素又不可或缺,結果自然會導致藝術表演的票價不斷上漲。這就是服務業的“鮑莫爾成本病”,簡稱鮑莫爾病。
鮑莫爾指出,“成本病”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由于服務業成本的上升,將會持續下去,因此鮑莫爾病也將持續存在。
但是,他認為鮑莫爾病只是一個增長的煩惱。“成本病”源于不同經濟部門生產率增長的不均等。在競爭社會中,只有當創新完全停止了,所有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增長都變為零,這種生產率增長的不均等才會消失,鮑莫爾病才不會出現。但是很顯然,那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好消息:到了那個時候,“貧困病”“暴力病”等更加嚴重的疾病都會登場。
然而,既然鮑莫爾病是一種“病”,那么就可能會帶來一些不良的影響。人們的擔憂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第一,鮑莫爾病會不會降低長期經濟增長的速度?第二,鮑莫爾病會不會導致我們的社會無法負擔教育和醫療保健等重要服務?
生產性服務業和人工智能可以緩解鮑莫爾病
第一種擔憂似乎不無道理。一般而言,服務業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要比制造業更慢。事實上,現在學界也經常用“鮑莫爾病”來描述隨服務業比重提升而出現的經濟整體勞動生產率下降的現象。
經濟學家江小涓曾經總結過,傳統服務業有如下特點:一是“結果無形”,即服務過程不產生有形結果;二是“生產消費同步”,即服務生產和服務消費同時同地發生,生產完成時服務已經提供給了消費者;三是“不可儲存”,服務過程完成、服務也就結束了,結果無法儲存。
這些性質決定了傳統服務業不便于采用新技術,而且很難實現規模經濟,因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對來說更加緩慢。這樣一來,在經濟結構日益向服務業為主轉型,“停滯部門”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將會越來越高,從而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增長速度也會不斷降低。在各發達國家,工業革命后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是先上升后下降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技術進步以及商業模式和組織制度等方面的創新和變革,可以弱化傳統服務業的上述特點、擴大服務業提升效率的空間,從而緩解鮑莫爾病。
從最廣義的層面上說,服務業本身就有一定“生產性”。最明顯的是教育和醫療保健行業,因為教育和醫療保健,不僅僅是一種消費,也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有利于未來的經濟發展。但是服務業的“生產性”還不限于此,即便是許多純粹制造“即時滿足”的服務,也是有生產性的,因為精神愉悅和心理滿足,不僅是有效需求,而且能夠直接提高人們工作時的效率。
更加值得一提的各種具有“直接生產性”的服務業創新所帶來的改變。事實上,杰克·特里普利特和巴里·波茨沃斯甚至聲稱,實現了IT資本深化后的服務業,已經治愈了“鮑莫爾成本病”。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美國服務業生產率年均增幅為2.3%,高于同期制造業的1.8%。對于這項研究,學界仍有爭議,但是隨著數字技術應用深化和服務業創新加速,傳統服務業的缺點在很多方面確實明顯弱化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鮑莫爾病。
或許,可以把這種創新服務業稱為“生產性服務業”。其中一個模式是通過數字平臺,提高推動服務的匹配精度和交易效率。如前所述,服務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產與消費同時完成的,因此提高匹配效率和交易效率非常關鍵,現在的外賣平臺、出行平臺,都是在這個意義上提高服務業效率的。
另一個模式是利用數字技術來聚合需求,提高提供服務產品的效率,例如,通過網絡傳播來增加教師授課的聽眾。另外,對于原來的服務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重塑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交付方式,以此來提高效率。
對于這種“生產性服務業”,鮑莫爾在書中也給出了一系列精彩的案例研究,值得細細品味。
當然,最重要的可能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這也許會從根本上改變服務業產品的生產和提供方式。
OpenAI公司此前推出的人工智能產品ChatGPT,就已經具備很多“生產服務”的能力了。它能搜索和自動整合信息,能撰寫郵件、視頻腳本、文案、代碼,能完成多種語言的翻譯、繪畫,甚至還能寫論文。
如果人工智能日后可以像人類一樣感受、思考、推理和判斷,然后生成有實際價值的內容,那么傳統上只有通過“個人服務”才能完成的許多工作,人工智能都可以輕松高效地完成,到那一天,鮑莫爾病應該會得到很大緩解。
某些產品成本的下降,是鮑莫爾病的另一面
對于鮑莫爾病會不會導致我們的社會無法負擔教育和醫療保健等重要服務這個問題,鮑莫爾非常樂觀。
他在書中根據美國目前的趨勢估測,美國醫療保健支出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會從2005年的15%的基礎上增加。在2022年,美國的醫療保健支出為4.3萬億美元,占GDP的18%。很多人據此認為,這么重的負擔肯定是我們無法承受的。但是鮑莫爾相信,生產率不斷提高本身就能夠確保未來我們可以獲得豐富的、合乎我們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只要制度能夠保障創新,哪怕醫療保健和教育變得越來越昂貴,我們的收入也會增長,因此無需過多擔心。
他強調,恰恰是“醫療保健和教育等服務是我們負擔不起的”這種錯覺阻礙了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改善,因為這種錯覺會導致種種“政治幼稚病”,從而剝奪我們和后代享受更好服務的機會,進而阻礙創新和技術進步。
鮑莫爾還認為,人類未來面臨的很多最嚴重的威脅都源于“進步部門”的產品成本下降,而不是“停滯部門”(如醫療保健和教育等服務)的成本上升。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悖謬的結論,但其實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洞見。
而這也就意味著,鮑莫爾病還有另一面,雖然人們往往會忽略它,但是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鮑莫爾指出,某些“進步部門”的快速發展,刺激了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等最具威脅性的問題。是它們的成本下降,而不是教育和衛生保健等服務部門的成本上升,對公眾福利構成了更大威脅。例如,軍事武器生產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導致大量威力強大且價格低廉的武器不斷涌現,作為工業制成品,它們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
很顯然,這樣一些“進步部門”的產品成本持續下降,很可能會給人類帶來不利后果。
(編輯: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