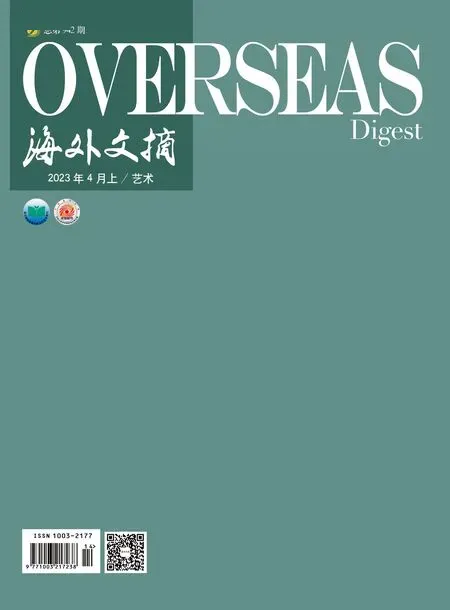淺談西方音樂史的歷史與現狀
□李吉文 張炫/文
西方音樂史學萌芽于18世紀初期,旨在為西方音樂史學的發展與研究設定相應的學術研究標準。19世紀,音樂史的研究范圍變得更加廣泛,研究方法更加活躍,研究視野更加廣闊。20世紀,西方音樂史研究開始用辯證思維,研究重心被放在對以往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上。如今,西方音樂史學有了新的研究趨勢和方向,研究者開始嘗試將音樂研究與其他學科結合成新興學科,在音樂解釋中融入更多的與社會文化的聯系。
1 西方音樂史概念
西方音樂史,是指對西方音樂發展的歷史進行梳理、審視、批判、反思的學問。西方音樂史涉及從古希臘時期至現代時期的西方音樂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音樂學者針對這段歷史所反映的問題和現象進行研究、探討。西方音樂史的誕生,代表著人們對西方音樂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不同時代的音樂學者對西方音樂史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觀點,這些觀點被不斷地累積,為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西方音樂史由音樂學科和歷史學科結合而成,西方音樂史學包含在歷史音樂當中,具有跨學科的性質。西方音樂史學發展至今,各類音樂著作數不勝收,格勞特的作品《西方音樂史》、由眾多音樂名家共同編撰而成的《新牛津音樂史》等,都為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進程貢獻出巨大力量[1]。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我國音樂研究深受西方音樂史學的影響,西方音樂史常年以一種權威的形象在我國音樂學術界屹立不倒,使我國學者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中還是話語權爭取上都陷入一種尷尬的局面。現如今,隨著全球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我國學者也在努力擺脫這種困境,開始建立具有中國性特征的研究風格和方法,更好地在音樂史研究中發揮自身優勢。
2 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歷史
2.1 國內
2.1.1 第一階段 1949之前:奠基
這一時期是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萌芽時期,對我國整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發展起到一個奠基的作用。這個時期,蕭友梅和王光祈是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開山鼻祖,為我國現代音樂的產生、發展和成熟作出突出貢獻[2]。二位都是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在見識到當時國內外音樂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后,都產生了迫切改革和建設國內音樂的心情和熱情。他們理性地分析國內音樂發展現狀,并結合在國外學習的音樂理論體系和音樂發展模式對中國的音樂發展做出改變,促使這一時期的西方音樂史文獻在翻譯質量和著述水平上達到了高峰,至今都沒有被超越。
2.1.2 第二階段 1949-1966:初創
這一時期,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呈現出一種消極、偏激的狀態。由于政治原因和歷史因素,當時我國對西方相關的事物都帶有一定的排斥、抵制的心態,認為西方音樂歷史和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社會、西方的人文一樣,都是“有害的”。雖然當時我國與前蘇聯有過結交,但俄羅斯音樂畢竟不是西方音樂史研究的主流。而且,當時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學者即使不對西方音樂史抱有敵意,也還是對以往的研究傳統持否定的態度。因此,這一時期的西方音樂史研究總體上呈現出消極下行的趨勢。
2.1.3 第三階段 1977-2003:再出發
這一時期,人們對西方音樂史展開進一步探索,產生了很大的進步。音樂期刊恢復了發刊,為西方音樂史研究和學術交流創造了舞臺;音樂院校的重新招生使我國音樂研究人才隊伍迎來了新生力量;學術研討會、音樂交流會為西方音樂史研究開辟了新天地,西方音樂史研究總體上呈現蒸蒸日上的局面。
2.1.4 第四階段 2004至今:持續發展
這一時期,我國的西方音樂學者的隊伍逐漸壯大,越來越多的西方音樂史學大家、海外游學回來的研究人員以及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新生學者各司其職,使西方音樂研究工作達到了空前繁榮。
2.2 國外
西方音樂史學誕生于18世紀,那是一個崇尚理性、強調“以人為本”、追求人文精神的偉大時代。啟蒙運動不僅解放了西方的思想,還推動了西方知識領域的快速發展。西方音樂作為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毫不例外地也快速地發展起來,這一時代是理性的時代,理性的學問、理性的音樂是18世紀西方音樂史學家的研究風格。他們對音樂的發展過程進行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通過科學、系統的梳理來審視音樂的發展過程。18世紀的西方音樂史學術成果頗為豐厚。伯尼的四卷本《音樂通史》是其中代表,伯尼對音樂藝術有著透徹的理解和敏銳的直覺,他為了保證音樂史的正確性和代表性,實地考察了歐洲各地的音樂生活與藝術傳統。
19世紀,西方音樂史的研究進入到蓬勃發展時期。他們對音樂史的研究有了更開闊的視野和更活躍的思維。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音樂著述為費蒂斯的《世界音樂家傳記》,這是一本音樂家傳記詞典。西方音樂家一人獨自撰寫多卷本音樂通史的傳統一直到安布羅斯的三卷本《音樂史》才畫上句號,盡管安布羅斯本人完成的寫作只寫到17世紀的音樂,但他的影響力顯然比費蒂斯的著述更具影響力[3]。到了20世紀,學術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更加深刻,越來越多的專著、文集、博士論文、作品集、學術評注作品將西方音樂史研究推向高潮。20世紀后半葉的西方音樂史學的發展更加強勢,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音樂史著述創作碩果累累,德國音樂家達爾豪斯的作品《音樂史學原理》,被看成西方音樂史學發展的里程碑。他主張“從作品的內在建構中解讀到作品的歷史性質”。
“新音樂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作為一種新型學術力量,對西方音樂史產生了不可小覷的貢獻。“新音樂學”領軍人物之一是伯克萊加州大學音樂學教授塔魯斯基,他創作了《牛津西方音樂史》,引起了西方音樂學界的高度關注。這一時期的西方音樂史學已經深入成為歷史音樂學的一部分,歷史音樂學具有的反思意義已成為西方音樂史學內在的方法論。
3 西方音樂史研究的現狀
3.1 國內
隨著我國音樂研究意識的獨立,國內學者在西方音樂史研究上開始追求建立自己的話語權,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用中國學者的思想觀念和研究方法對西方音樂史進行研究,進而對西方音樂史產生更加深入的了解。
2022年12月3日至4日,“紀念于潤洋先生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以線上研討和網絡直播的形式隆重召開。其中,研討會針對“西方音樂史”這一主題,以“《于潤洋西方音樂史教學手稿》研究”及“于潤洋的學術成就及其對當下音樂學術研究的影響”為議題進行了研討[4]。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對于潤洋先生和現階段西方音樂史研究思想和方法表達了自己的見解。筆者以三條要點總結了楊燕迪的發言:
(1)在史學研究中,應高度重視音樂本身和音樂作品的深入解讀。
(2)研究音樂史應回答這個問題:社會文化怎么進入到音樂作品和音響形式中,在音樂解釋中怎樣融入更多的社會文化的聯系。
(3)音樂史的研究要點:要從作品的內在建構中讀到作品的歷史性質。
由此可見,我國的音樂學者都在用各種可行的方式對西方音樂史進行研究,西方音樂史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為我國的音樂研究添磚加瓦。
3.2 國外
西方音樂史研究的主要學術成果可見于發表的專著或論文。筆者通過梳理、研究國外近十年所發表的專著和論文,將國外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現狀總結為以下幾點:
(1)將音樂與“性別”相聯系。新音樂學誕生開始,女性主義就蔓延到音樂史的研究中。20世紀90年代中葉出版的論文集《音樂學與差異——音樂研究中的性別和性》涉獵了女性主義的相關內容。該論文主張“音樂中重要的差異為音樂作品形式內部深層的社會性別差異”。
(2)將音樂與政治、戰爭、社會相聯系。《引言:冷戰中的音樂》在文章開始就指出,“冷戰”不只是兩個國家或政治集團的沖突,更是兩個集體的“文化”的沖突,屬于思想上的沖突。《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期間的巴黎音樂》分析了普法戰爭對巴黎音樂社會造成的影響和后果[5]。
(3)在研究音樂作品時更重視原始資料的研究。《布里頓書信集1913—1976》按照時期分為六冊出版,對布里頓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了總結。
4 結語
西方音樂史在研究上還有待發展,我國在研究西方音樂史時不能一味地借鑒國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不要為了區別于西方學者的研究而“去同存異”,要吸取精華去其糟粕,建立中國“話語權”。不歪曲也不盲目崇拜西方音樂,爭取做到在西方音樂研究上享有和西方同等的話語權。
“中國話語體系”不是人們隨意創造的,而是人在歷史的進程中創造的。伴隨著西方文化在我國的傳播,西方音樂也快速地影響著我國的音樂理念,而中國關于音樂理論的話語體系也受到了西方音樂理論的沖擊。這就需要我們建立“中國話語體系”,用理智的眼光借鑒和審視西方的音樂理論,“洋為中用”,建立和完善中國音樂的理論體系。■
引用
[1] 王玉.關于西方音樂史的學術傳統及當代視野分析[J].黃河之聲,2018(13):26-27.
[2] 宋穎.宏觀視域下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狀態的冷思考[J].音樂生活,2015(9):79-81.
[3] 孫國忠.西方音樂史學:觀念與實踐[J].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0(2):12-24+4.
[4] 黃宗權.西學東潤成泰斗 樂海向洋緬先賢——“紀念于潤洋先生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J].人民音樂,2023(2):54-58.
[5] 朱厚鵬.近十年間西方音樂(史)研究管窺——英語世界研究現狀與分析[J].人民音樂,2020(5):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