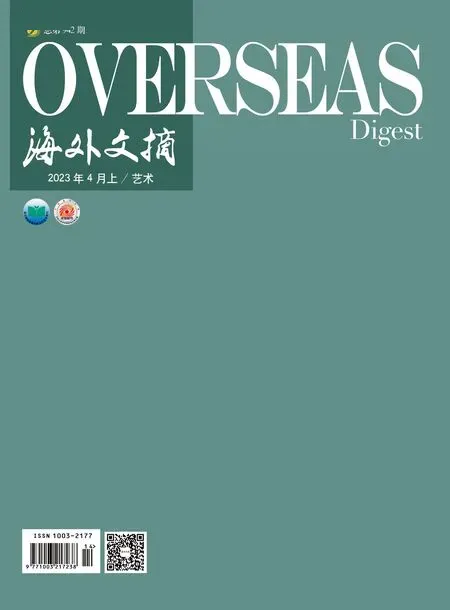德國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民俗文化的傳播
□夏瑞芳/文
自16世紀尋根歷史意義意識的萌發(fā)到18世紀浪漫主義強調(diào)恢復民族精神,19世紀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世紀文化作為重要的力量站在歷史舞臺,民俗研究不僅對本民族文化的恢復有重要意義,在各國的文化交流中也不可或缺。德國是民俗學的發(fā)端國,早在18世紀,以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J.G.Herder)為首的德國浪漫主義者譴責現(xiàn)代文明割裂了人與自然的聯(lián)系,并將詩歌當做堆砌辭藻、玩弄形式的智力游戲[1]。德國浪漫主義者們認為,民間文化是民族文化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表現(xiàn)形式。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承至今,民間藝術(shù)、民間科技等燦若星辰。如果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那么民俗文化就是這座宮殿中最堅實的基座。民族性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傳教士對民俗研究的理論和途徑,共通的價值觀有利于奠定民俗研究者的學術(shù)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確立民俗學的學術(shù)地位并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進而推動世界范圍內(nèi)對民俗學的重視和認識。
本文以部分德國傳教士對近代中國民俗的研究和傳播為原點,采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傳教士的觀點進行分析、歸納、重構(gòu),意在塑造民俗學的群體意識,即由個人描述到群體共識、由個體自覺到群體覺醒,建構(gòu)具有時代意義的民俗價值理論,樹立民俗學的現(xiàn)代價值觀。
1 中德交流的開端
中德兩國交往歷史源遠流長,傳教士是兩國發(fā)展聯(lián)系的先驅(qū)。據(jù)文字記載,早在唐代時便已有少數(shù)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明末清初,德國傳教士來華的人數(shù)日益增加。鴉片戰(zhàn)爭后,來華傳教士的規(guī)模和影響直至巔峰。有關(guān)研究顯示,來華傳教士除進行正常的傳教活動,還在中國大地上廣建教堂、興辦教會學校、設(shè)立教會醫(yī)院等,對近代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多數(shù)傳教士從通商口岸滲入到內(nèi)陸的鄉(xiāng)野村間,廣泛接觸大眾,開展更為深入的傳教活動,同時,親身體會當時農(nóng)村地區(qū)的貧困落后及他們信仰觀念的特性。西方傳教士在傳教同時,以觀察到的普通民眾生活狀態(tài)為主題,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現(xiàn)狀以游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并傳到西方,成為早期西方漢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方便西方社會深入了解和認知當時中國底層社會。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禮俗互動的社會,正如張士閃教授所說,“大致說來,無論是作為社會實在,還是話語形式,‘禮’‘俗’都代表了自古及今中國社會的某種普遍現(xiàn)象與社會思想的一般特征,二者之間的互動實踐奠定了國家政治設(shè)計與整體社會運行的基礎(chǔ),并在‘五四’以來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gòu)中有所延續(xù),因而應(yīng)該成為‘理解中國’的基本視角。[2]”德國傳教士對中國民間信仰的刻板觀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早期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西方看來,中國民間信仰及傳統(tǒng)禮俗皆屬于“異教”或“異端”,都需要徹底鏟除,這種觀念在后期社會實踐中的“移風易俗”建設(shè)提供了某種思想淵源。
近代以來,德國傳教士深入中國鄉(xiāng)村社會,進行大量田野調(diào)查,并撰寫了大量的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生活和信仰觀念的書籍,無論在中國早期社會知識精英群體,還是在西方漢學領(lǐng)域都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近幾年進行學術(shù)研究時對于近代德國傳教士的相關(guān)成果研究方面的關(guān)注沒有達到應(yīng)有的水平。
2 德國傳教士對民俗研究的方面
2.1 喪葬習俗:陋俗事象的微觀細描
中國在漫漫歷史長河之中積淀的民俗傳統(tǒng)是構(gòu)成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性與穩(wěn)定性的具體表征。在諸多民俗禮規(guī)中,葬禮是極其重要的儀式。中國人崇尚儒家的忠孝節(jié)義,葬禮的操辦寄寓著生者對死者的尊重與追思,甚至在許多地區(qū)有“死事重于生俗”的現(xiàn)象。傳教士攜其獨特的角色意識,以社會人類學的視角審視和傳遞著中國社會文化的信息。
戈特弗里德·恩德曼(Gottfried Endemann)的《如何從魔鬼的奴隸變成上帝的仆人》(Wie aus einem Knecht des Teufels ein Gotteskind wurde,l913)[3]和和士謙(Carl Johannes Voskamp)的《在死亡的陰影下》(Im Schatten des Todes,1925)[4]是傳教士詳細載述中國喪葬習俗的讀本,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了傳教士群體對中國習俗的普遍定調(diào)和體認。在《如何從魔鬼的奴隸變成上帝的仆人》中,身處廣東傳教區(qū)的教士恩德曼詳細敘述了中國華南地區(qū)喪葬習俗的典禮儀規(guī),涉及送終、呼號、服孝、買水的喪葬儀禮,其文字敘述頗具人類學田野考察性質(zhì);有關(guān)“買水”的喪禮習俗,恩德曼描述道:“為了召喚河神,她用扇子敲打了幾下水面,在空中揮舞著冒著煙的香供,使火光映入水中。在吸引到小溪(河神)的注意后,她將兩枚硬幣扔進水里,隨即舀滿水,用這個水在家中清潔死者的臉、手腳及心窩。[5]”誠如民俗大典中所言:“在廣府地區(qū),孝子戴三果冠,披麻跣足,手執(zhí)喪杖,隨親屬哭赴水濱,投一文錢‘買水’。[6]”此處,中國與基督教文化中“水”所具有的洗滌邪惡與罪責、潔凈心靈的作用,以及關(guān)涉“罪”的宗教思想彼此貫通。
和士謙多次評價中國的喪葬儀式繁復、鋪張,體現(xiàn)在葬禮的多個環(huán)節(jié)。《在死亡的陰影下》中,和氏記敘中國人將死者下葬需等待風水師“尋得一處能帶來好運的風水寶地”,論批這一習俗是“繁瑣的、交織著各種迷信的儀式”[7]。在傳教士的話語邏輯下,將死者葬于農(nóng)田的習俗嚴重侵占了山東民眾的生存空間,導致“成千上萬勤勞的農(nóng)民被迫移民到富饒的平原黑龍江”,并充滿文明教化意味地痛陳中國禮俗的力量是“壓倒一切的”,“傳道與勸誠皆不能與之抗衡”。
2.2 祭祖拜偶:“虛假神性”與“神權(quán)僭越”
山東布道區(qū)傳教士昆祚(Adolf Kunze)在《中國的黑暗力量將被光明成功戰(zhàn)勝》(Die Macht der Finsternis in China wird durch die Macht des Lichtes siegreich überwunden,1906)中頗具諷刺意味地將“迷信和偶像崇拜”論述為“異教徒的重要文化支柱”[8],稱其為“轄制中國”的“黑暗力量”。在傳教士的眼中,祭祀祖先與敬拜偶像“充溢”著具有原始宗教特征的迷信行為,與真正實現(xiàn)“靈魂得救”的基督教一神論格格不入,是傳教士群體極力抗爭的對象。中國的祖先祭祀是德國傳教士不斷反對的形式,但是他們又對祭祖習俗中敬拜父母、感懷先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表示肯定。
2.3 禮節(jié)傳統(tǒng):“形式化的表面客套”
禮節(jié)亦是儀式的一種。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習慣性行為,禮節(jié)是一種潛意識的“應(yīng)有行為”和“禮貌的形式化”[9],是社會各階層人物的身份表征。在數(shù)千年文明與文化洗禮下,“禮”經(jīng)過歷代統(tǒng)治者的改造與規(guī)制,從最初的宗教、政治領(lǐng)域逐步擴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擁有儀式、政法制度、行為規(guī)范與等級標識的多重意涵[10]。德國傳教士對中國之“禮”的察看與觀識,主要圍繞“禮”在日常生活中作為“行為規(guī)范”的表現(xiàn)形式,認為了解中國民眾的禮節(jié)是獲取信任與賞識的重要一環(huán)。弗里德里希·威廉·來施那(Friedrich Wilhelm Leuschner )在《中國的形形色色》認為,中國人雖然極其重視禮節(jié),然而大多只是流于淺表的形式化客套,實則“口不對心”,論批這種形式化的禮節(jié)實為民眾生活的一種制約和束縛。
2.4 中國婚禮:“娶來的妻,買來的馬”
婚禮被稱為“紅事”。迎妻過程是一件嚴肅重大的事情,官吏也要為婚禮隊伍讓路,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干擾,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婚禮是一項非常莊嚴、隆重的禮儀傳功,德國傳教士盧國祥(Rudolph Pieper)在《中華苗蔓花》一書中僅就其感興趣或者對感覺不可思議的部分進行了介紹。其中一部分篇幅著重介紹婚禮前及婚禮儀式過程中“婚帖”,而且對“新娘啟程”和“新娘進新郎家”的過程中的禁忌及習俗進行了書寫。其中,盧國祥描述妻子嫁到婆家后,必須遵守“出嫁從夫”的習俗,照顧好公婆,如果公婆不滿意自己的兒媳婦可以選擇休妻,女性完全失去人身的自由,成為丈夫的附屬物。對此,盧國祥認為,“異教恐怖如此,連最基本的廉恥觀都已經(jīng)被摒棄了。”其實,對于基督徒而言,婚姻是神賜的禮物,人們不能因為各種原因褻瀆婚姻。
在傳教手冊中,為凸顯中國昏昧無知、愚妄頑腐、暴戾原始的異教國度形象,傳教士慣于在買賣女嬰為童妻、將妻女作為資產(chǎn)售賣等話題上著墨較多。傳教士筆下的婚禮習俗以傳宗接代為目標,稱其是女性婚姻后的“最重要的義務(wù)”。反之,沒有子嗣便是女性“最大的不幸”,“丈夫被迫納妾”“被所有女性鄙視”“無法祭祀祖先”,生命了無希望。苦難和操勞與中國女性的前半生時刻相隨,在跨越生育子嗣的界限之后,搖身一變成為兒媳前半生的苦難施動者,而“當婆婆不再活著,兒媳便立刻以令人欽佩的技巧奪取家庭的統(tǒng)治權(quán)。”傳教士基于對中國家庭關(guān)系的表層觀察,將女性苦難的緣由之一歸因于女性成員對家庭權(quán)力的爭奪,忽視了當時父權(quán)家長制的社會背景,弱化了男性所代表的強勢話語權(quán)及其對女性的深層鉗制和宰制。雖然為了進行傳教,行文有所夸大,但是也揭示了舊社會婚姻對女性的殘害。
德國傳教士認為,中國女性是真正尋求“靈魂救贖”和“靈魂安寧”的人,她們是婚姻的受難者和精神貧乏者,又因與佛教、民間宗教的接觸更早地了解到罪、重生、贖罪等與基督教相通的宗教概念,在這一意義上來講,她們是理想的、更易獲得信仰“入門”的宣教對象。在傳教手冊中,多是逆來順受、任勞任怨的中國女性形象,她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對自身處境和命運缺乏思考和反抗。誠然,女性群體也是傳教士較難觸及和“爭取”的福音受眾。由此可見,德國傳教士對中國舊時代女性的同情更多是建立在宗教意義上,認為她們是可以接受“福音”的對象,而非出于對男權(quán)社會下婚姻制度的批判。
3 民俗研究的價值
通過以上關(guān)于德國傳教士對中國民俗的研究可以認識到:民俗是在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大背景下產(chǎn)生和衍變的,研究一個國家的民俗(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夠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由此可見,民俗是文化的載體,民俗的研究對于文化的研究有著重要價值。
此研究能充分解讀中國近代民俗學在傳教士眼中的形式,對我國民俗學研究發(fā)展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民俗學的價值對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意義,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趨勢下越來越值得關(guān)注。
4 對中德兩國未來民俗的研究的借鑒意義
19至20世紀,隨著中國國門被迫打開,大量西方新教傳教士接踵入華,傳教士所撰寫的傳教文學無疑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shù)價值。作為流通廣泛的大眾讀物,傳教文學無疑成為西方讀者尤其是基督徒社群瞭望遙遠東方古國的重要窗口。傳教士作為中西方交流史上最為重要的溝通橋梁,其撰寫的傳教文本承載了大量中國社會文化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構(gòu)筑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原初認知,并在此后很長時間內(nèi)持續(xù)發(fā)揮著影響。在中國同世界的聯(lián)系空前密切的當下,回溯清末民初德國傳教士與中國人對話的歷史語境,分析德國傳教士中國書寫背后的認知符碼,揭示基督教文化影響下德國人認知他者的民族心理與思維范式,有助于推動中德異質(zhì)文化間的對話與理解,具有深切的現(xiàn)實關(guān)照意義。■
引用
[1] 楊樹喆.中外民俗學發(fā)展述略[J].百色學院學報,2006(5):1-7.
[2] 彭瑞紅.他者鏡像中的中國近代民間禮俗——法國傳教士祿是遒對中國婚喪、歲時風俗的書寫與研究[J].民俗研究,2018(4):62-70+158.
[3] Gottfried Endemann.Wie aus einem Knecht des Teufels ein Gotteskind wurde.[M].Berlin: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913:58.
[4] Carl Johannes Voskamp:Im Schatten des Todes[M].Amerika: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1925:167.
[5] 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J].民俗研究,2016(6):14-24+157.
[6] 葉春生,施愛東.廣東民俗大典(第二版)[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29.
[7] Carl Johannes Voskamp:Im Schatten des Todes.[M].Amerika: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1925:15.
[8] Adolf Kunze:Die Macht der Finsternis in China wird durch die Macht des Lichtes siegreich überwunden.[M].Berlin:Buchhandlung der Berliner evangel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913:5.
[9] 羅納德爾·格萊姆斯.儀式的分類[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1.
[10] 楊汝福.中國禮儀史話[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