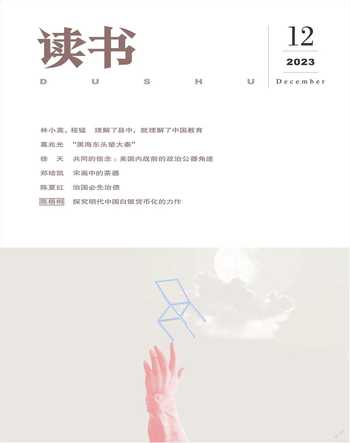宋畫中的茶器
鄭培凱
長期以來,人們研究唐宋茶器,主要靠的是文獻,如陸羽《茶經》、蔡襄《茶錄》、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審安老人《茶具圖贊》等。一般討論陸羽創制茶器,是說陸羽創制了二十四種茶具,但是,《茶經·四之器》卻共列二十五器:風爐(灰承)、筥、炭撾、火、、交床、夾、紙囊、碾(拂末)、羅合、則、水方、漉水囊、瓢、竹、鹺簋(揭)、碗、熟盂、畚(紙帊)、札、滌方、滓方、巾、具列、都籃。或許古人是為了方便,以十二的倍數,泛說“二十四”,形容創制的茶器既多又規整。還有一個說法是,都籃是盛放容納茶具的器具,所以不算在二十四器之中。其實,陸羽創制的茶具當中,有許多不是通常說的“茶具”,而是煮茶煎茶使用的水火器。到了宋代點茶的器皿,蔡襄《茶錄》列有茶焙、茶籠、砧、椎、茶鈐、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十器,省略了水火器。趙佶《大觀茶論》列了羅、碾、盞、筅、瓶、杓,幾乎只剩下了瀹茶器與飲茶器。南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則列有十二器,相對較為完備,但也跟《茶錄》一樣省略了水火器。
近幾十年來,因為考古文物的出土與發現,如法門寺地宮的茶器、呂大臨家族墓的茶器,都呈現了實物佐證,對唐宋茶器因此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特別是茶器的材質與瓷器燒造和施釉的技術。同時,我們也發現不同瓷窯燒制的精品,可以在同一批埋藏的窖藏或墓葬中出現,顯示古代茶人對茶飲瓷器有著多元多樣的喜好。
浙江大學出版社的《宋畫全集》,又利用高清影像技術,在全世界收集宋畫數據,為宋畫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材料。黃晨整理《宋畫全集》中與茶飲相關的圖像,撰寫了一本《宋畫茶韻》,聯系文獻資料與文物茶器,盡量解析唐宋茶飲如何使用茶器,讓我們進入唐宋飲茶的情景。用他的說法,就是:“將茶文化中原本霧里看花的一些節點,做了祛魅和還原,俾使畫里畫外,茶味雋永。” 他對宋畫做了極其仔細的梳理,對畫中涉及茶事的圖像分析入微,認為茶事入畫,大致有三種類型,一種是茶具的描繪,一種是茶事的渲染,再有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茶。這些圖畫中最可關注者為雅集與游園,其次則是人物圖,其中往往有對茶事的細節描繪。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局部)
為了顯示宋畫中的茶事,這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講述宋畫中所表現的宋人生活,展示宋人對生活美學的關注。文人雅士的琴棋書畫詩酒風流之外,一般士民也講究插花、燒香、點茶、掛畫。第二章梳理唐宋茶書文獻,分析當時茶儀、茶器和典故。第三章以傳世宋畫中的茶事描繪對應文本敘述,還原唐煎宋點的儀軌,以及茶器形狀與色調。第四章以宋畫為據,講述宋人茶生活的細節,以及喝茶的場景。第五章從茶藝到茶道,探究“茶禪一味”的原委,還原“吃茶去”的初心。
仔細觀察《宋畫全集》的高清圖像,可以發現許多文獻沒有提供的場景與茶器的實物形象。如《商山四皓會昌九老》(遼寧博物館藏)這樣的長卷中,觀測點從草堂論書畫的場景,移到側廂的茶房,就會發現,茶房中有書僮扇風煮水,旁邊的茶桌上整齊疊放著茶碗茶盞。茶房外面,另有一僮蹺腳休憩,顯然是來回行走、提瓶點茶的茶僮,隨時為賞畫論道的雅士提供茶飲之樂。從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飲茶圖》中,更可推想大戶人家室內飲茶的場景,窺知僮婢煮茶與上茶的情況,反映茶飲從茶爐煎煮到呈進內室,以供主人飲茶的流程。畫中的青衣小鬟托著茶盤一路行來,進到內室,主婦正在室內靜立候茶,形成宋人生活中閑雅的畫面。
宋畫中常見的茶器,有茶爐(風爐/ 燎爐)、(銚子/ 鐺)、湯瓶、茶碗(盞/ 杯)、盞托、茶碾、茶匙和茶筅,經常出現在宋畫之中。黃晨在書中指出:
首先可以拿來觀瞻的是《蕭翼賺蘭亭圖》,此題畫作在《宋畫全集》中有三件,一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一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另有一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前兩件都有關于煎茶的場景描繪,北京的較為清晰而簡略,遼博的略有漫漶但陳列更為完備。《賺蘭亭》的圖像上,可以看到白色的茶碗與黑色的盞托,《茶經》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畫中的白色茶碗是否為邢窯不好說,但一定不是《茶經》所推崇的越窯。而唐人煎茶不用的盞托是宋代點茶必需之物,出現在表現唐人故事的畫面中也算是畫家無意流露的時代特征吧。
黃晨讀畫十分仔細,也為我們指出,宋人想象中的唐人飲茶,選用茶碗,并不一定是陸羽極力推崇的越窯青瓷。宋畫是宋人所畫,畫唐朝飲茶,當然是出于后代對唐人生活場景的想象,有臆想的成分,不見得忠實呈現了唐代實況。但是,唐人飲茶也不可能人人都遵循陸羽所說的“邢不如越”法則,非得用越窯青瓷作為茶具不可。陸羽推崇越窯茶碗為最,也就是陸龜蒙贊嘆的“秘色瓷”茶盞:“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是皇家宮廷使用的貢器。秘色茶碗等級雖高,并不能排除有人愛好精美純白的邢窯茶器。從唐到宋,邢窯到定窯的白瓷,如銀如雪,風格精美細致,一直傳承有序,近年來定窯考古發現的瓷器可以作為明證。同樣的情況,我們還可從呂大臨家族墓的發掘,同時出土了珍藏的建窯兔毫茶盞與定窯白瓷茶盞與盞托,看到北宋人雖然最為崇尚建窯黑瓷,但也不排斥精美大方的白瓷茶碗。
黃晨書中,繼續探討《蕭翼賺蘭亭圖》所提供的飲茶圖像數據:
遼博所藏圖畫可見的茶器有:風爐、茶銚、竹、茶盞、茶托、具列、鹺簋、熟盂、水方、瓢、火,比故宮所藏多出了火、水方等物。畫中有一個木制承案,之上的三足風爐足間開窗與《茶經》相類,爐頸兩耳置環,通體也是光素無有文字藻飾,跡近故宮藏畫中的三足泥爐。承案上尚放有鹺簋,其中斜伸出來的就是用來舀鹽花的“揭”了,而鹺簋的合蓋就放在具列上靠近風爐的地方,已經模糊了。司茶人的腳邊斜躺著火,最前方的瓦盆應是水方,《茶經》說“水方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里并外縫漆之,受一斗”。畫中的看起來更像是瓦制,宋代的一斗合今天的 6.7 升,按體量看應該不差,且其中還漾著一把瓢。與北京所藏比較,這些多出的器物增加了細節,更加準確地還原了煎茶的場面。兩畫相同的白碗黑托,展示的是宋人的飲茶習慣與審美。
這樣細致的探討,對比兩幅《蕭翼賺蘭亭圖》繪畫的茶器,以圖像對照陸羽《茶經》的文獻數據,為我們提供了唐宋飲茶的形象細節。特別是指出茶器的安放與彼此之間的關系,對煮茶的流程,有了清晰的視覺展示,鞭辟入里,實在難能可貴。
宋人喝茶成風,不分貴賤,雅俗共賞。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論及當時的飲茶風尚,認為是太平盛世景象,得意萬分。在《大觀茶論》中,他大談飲茶反映了人民安居樂業,有余暇品嘗茶趣,更盛贊龍團鳳餅,激賞玉毫條達的建窯黑釉碗,還親自教導擊拂拉花的點茶技巧:“妙于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須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筅重,指繞腕旋,上下透徹,如酵蘗之起面。疏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之根本立矣。”宋徽宗的點茶技藝已經達到化境,要求茶人精益求精,制作完美的一碗茶湯,前前后后,要經過專心致意的七個步驟,才能達到點茶咬盞的境界:“乳霧洶涌,溢盞而起,周回旋而不動。” 宋代李邦彥的史料筆記《延福宮曲宴記》中也曾記載宋徽宗親手擊拂點茶:“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烹茶。飲畢,皆頓首謝。”記載的是,宋徽宗在延福宮設宴,令近侍取來茶具,親自注湯擊拂。經過他妙手擊拂拉花,湯花浮于盞面,呈疏星淡月之狀,接著,徽宗給諸臣分茶,說:“這是我親手施予的茶。”諸臣接過御茶品飲,一一頓首謝恩。宋徽宗精于茶藝,顯然認為烹茶也是藝術展現,不是侍臣童仆的賤役,親身為群臣點茶、分茶,是為了炫技,展現點茶藝術的最高本領。
宋徽宗創作的《文會圖》,是絹本設色的一幅大畫,畫面聚焦于一張寬大的茶桌,八九位文士圍坐其間,綸巾儒服,意態優雅閑適,無明顯的尊卑之分,有如好友之間的雅集。這幅畫的布局比較典雅方正,有宋徽宗親筆題詩及蔡京和詩,涉及唐代十八學士的典故,顯然是典型的皇家院畫,或許還有徽宗本人指點潤色。因為要表現皇帝澤被天下的威儀,朝廷上下熙和的景象,與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相比,缺少了詩酒風流的瀟灑隨意,而對宋代宮苑茶席的場景,做出真實的描繪。此圖呈現朝士飲茶,歡聚在園林美景之中,其樂融融,有意呈現統治階級的精英人士,在處理國家大事余暇,意態舒和,從事風雅活動,顯示徽宗時代國泰民安的景象。畫中人物喝茶論道、談詩賞畫,可謂文人雅士向往的清雅境界,所用茶器當然也是精致美觀的典范。《文會圖》最引人注目的是,桌上擺著成套的茶具和豐盛的時鮮水果,從中可以看到宋代茶具的擺放方式,以及茶席進行中賓客與童仆侍者互動的關系。畫面下方的侍從們也正不緊不慢地準備著茶席,茶床上陳列著茶盞、盞托、茶甌等物,一童子手持長柄茶杓,正在從茶罐中取茶粉放入茶壺。床旁設有茶爐、茶箱等物,爐上放置茶瓶,爐火正熾,顯然正在煎水。有意思的是,左下角坐著一名青衣小童,左手端碗,右手扶膝,似乎正在品飲,倒也悠閑自得。文人雅集當然少不了音樂,無論是抱琴起身的綠衣者,還是遠處石案上的古琴,都給整幅畫面增添了幾分雅致。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絹本設色的劉松年《攆茶圖》,不但布局巧妙,人物栩栩如生,還提供了飲茶場景,讓我們了解唐宋飲茶的用具與煎點的程序。這幅畫分左右兩部分,右邊顯示文人雅士寫字作畫的風雅,左邊則描繪童仆碾茶與制作茶湯的勞碌。畫的是唐大歷年間懷素揮毫作書,詩人錢起、戴叔倫凝神圍觀。左側畫仆役在旁為點茶做準備,本來是作為雅聚陪襯的,卻成了整幅畫最引人注目的場景,成為觀畫的聚焦之處,精心呈現了唐宋時期飲茶的煎點方式。一個仆人騎坐在長條矮幾上,右手轉動茶磨;另一名仆役正佇立桌邊,右手提湯瓶,左手執茶盞,正要注湯點茶。黑色方桌上陳列著篩茶的茶羅、貯茶的茶盒、白色茶盞、紅色盞托、茶匙、茶筅等,一應俱全。桌旁有一風爐,上置提梁(釜),燒煮沸水。右手旁邊是貯水甕,上覆荷葉。這幅畫展示了唐宋飲茶特色的研末煎煮,詳細繪出從研磨茶粉,到注湯點茶的器具及場面,再現了仆從勞動侍茶,文人雅士詩畫風流的場景。不過,這幅南宋畫家劉松年(活動于一二二〇年前后)圖繪唐人飲茶的實況,時間相隔四五百年,反映的究竟是唐代茶飲煎煮,還是宋代點茶擊拂的情景呢?
當然,畫家繪畫,主要畫的是胸中丘壑,追求心中想象的神思美感,與歷史實景出現捍格,也無足為怪,并不絲毫有損畫作的藝術成就。但是,作為歷史圖像學的研究對象,畫中出現的器物與具體情景,卻是判斷歷史時代與當時風尚的指標。比如說,劉松年想要呈現唐代飲茶的風貌,但畫中出現宋代以后才有的茶磨、茶筅、盞托,則只能說是宋人想象唐代飲茶情景,其中雜入了畫家熟悉的宋代飲茶風尚。《攆茶圖》中可見的茶具有:石轉運(磨)、宗從事(拂末)、風爐、茶銚(即《茶經》的)、茶匙、茶筅、杓、茶碗、盞托、水方。其中值得玩味的是,畫面中同時出現茶銚和湯瓶,還有茶匙與茶筅。揚之水《兩宋茶事》討論點茶與煎茶之別,認為石銚是唐代煎茶用具,而銀瓶則是宋代點茶的器具,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異,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因此劉松年《攆茶圖》所繪飲茶情景,忠實呈現了唐代煎茶的場景。研究宋畫的黃晨則指出,揚之水判斷的依據主要是唐代以茶銚煮水,但是茶桌上明明橫放著宋代點茶工具茶筅,該作何解?
黃晨還指出,《攆茶圖》里的茶銚描摹細致,與宋摹唐閻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的區別,是沒有長柄,代之以提梁,又加了一個蓋子。唐代煎茶的銚子基本無蓋,因為要觀察初沸、二沸、三沸。銚子加了蓋,主要功能就是煮水,蓋子既防灰,且提高熱效率,與陸羽形容的唐代茶銚功能不同。《攆茶圖》中有仆從專事推磨,畫出了石磨下鼓蕩的粉塵,動感逼真。陸羽《茶經》有“碾”,南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則著錄有金法曹與石轉運,表明宋代茶事碾與磨并存。碾與磨的分別,可能在于磨能使茶粉更細,更適宜點茶的擊拂拉花。《茶經》原注:“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又說“碧粉縹塵,非末也”。可見,按陸羽的標準,唐人煎茶的茶末以極細微之顆粒為佳,但不可為粉塵狀,所以《茶經》講茶具,只有碾而不用磨。到了宋代,點茶需要的調膏末茶,則是以粉塵為佳,所以,隨著點茶興起,磨成為茶事的要務,可以碾磨并用,也可以單用磨,但是只用碾就不能達到點茶“乳霧洶涌,溢盞而起”的效用了。因此,《攆茶圖》繪寫的情景,雜用了唐宋茶器,不是揚之水認為的唐代煎茶,而是呈現了宋代點茶風貌。
宋畫的司茶構圖中,十分常見童仆準備茶湯的圖景,經常會有三個人物,一人手托茶盤,一人跪地司爐,一人手持竹攪動釜中茶湯,比如劉松年《十八學士圖》、李公麟《山莊圖》、燕肅《邃谷仙儔圖》等等,通常都是有人煎茶有人奉茶,各司其職。上海博物館藏的《蓮社圖》就呈現了這樣的司茶組合,畫面中的風爐則值得注意。火爐下承仰蓮與覆荷,置于圓形的蓮花托座之上,其形象與《茶經》所述的風爐頗有出入。黃晨指出,這可能是唐宋時真正常見的樣式,像“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人《人物圖》中即有著一模一樣的蓮花風爐,而宣化遼墓壁畫中更是多處出現。黃晨觀察到宋畫中蓮花風爐的形狀,與陸羽描述的風爐,出現相當大的差別,是十分有趣的現象,有可能是陸羽風爐的制作有意凸顯個人名聲,明示“此爐為我造,此爐顯我名”,要在爐身呈現五行八卦,在爐窗突出古文書六字“伊公羹陸氏爐”,而與一般實際制作的風爐有異。
此書還記載了私人收藏的一幅傳為蘇漢臣的《羅漢》,畫中羅漢趺坐禪椅,神態安詳,前景兩個童子,一人碾茶,一人煮水,左邊另有一僮雙手托盤,上面放著將將洗凈的茶盞趨步而來。畫面雖略有漫漶,但童子碾茶的磨具(石轉運)以及長凳頭上的拂末(宗從事)和羅合(羅樞密),依然清楚可見。手執芭蕉扇的童子對著風爐,上面長流的湯瓶(湯提點),也可以清晰辨識。此圖也是三人司茶,配合上述的幾幅宋畫,應該是宋人飲茶的常規。此圖所繪的風爐,帶有考究的寶頂,由兩根連接在灰承上的連接桿,支撐著懸于湯瓶之上,既是裝飾,又是一種便于拎提攜帶的裝置,類似的爐子在野外茶飲的圖像中十分常見。比如李公麟的《山莊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就有這樣的手提風爐,雖然比《羅漢》圖里的簡陋得多,但顯然是同一個樣式。而日常居家使用不需要手提移動的話,可以在李嵩《貨郎圖》的擔子里看到一個更簡單的爐式。
仔細觀察宋畫的茶事,黃晨提出幾點值得思考的現象,破除了過去一味依賴文獻所做出的論斷。第一,蓮花風爐和三足泥爐可能才是常用的煮茶爐具,而陸羽描述的鼎形爐只是他自創的形制,并沒有普遍流行,他在爐身標榜的“尹公羹陸氏茶”恐怕也沒有得到時人太大的認同。第二,許多學者以為“唐煎宋點”是區別唐宋飲茶習慣的關鍵,以為是唐宋茶飲的重大變化,但是觀之宋畫卻不盡然。很多畫面是煎點并作,比如前述《山莊圖》的幾個局部茶事的場景,就是既有以鐺煎茶,又有湯瓶點茶的情況。宋畫中往往同時描繪了煎茶器和點茶器,如劉松年的《攆茶圖》,而使觀者難以判斷畫中的茶事,甚而認為是畫師不懂茶而信手涂抹,其實不然。這情形正如我們今天熱衷于恢復宋代的點茶和唐代的煎茶,并且以點茶為文人雅集之一種游藝。所以,有宋一代應該是煎點并行,無有偏廢的。從李公麟《山莊圖》、佚名的《人物圖》都可以看出來,在聚會中可以同時有煎茶和點茶,甚至在茶事中,二者的茶具也是可以混用的。
不過,書中誤引揚之水的論斷證據,解釋宋代持續唐式煎茶,是因為宋代士大夫追慕古風而更傾向于煎茶。所舉的蘇東坡詩句“銀瓶瀉湯夸第二”,作為論據的文獻證據,以為蘇軾將點茶置于煎茶之下,寓有茶品清濁之分,卻是錯誤的。因為蘇軾的這句詩,出自他在杭州通判時寫的《試院煎茶》,說的“夸第二”,一是夸贊天下第二的惠山泉,或如趙次公注:“此乃是尋常點茶時,先略傾瓶中湯,方點,謂之第二湯也。”從蘇軾寫《試院煎茶》之前寫的《求焦千之惠山泉詩》,懇求無錫知州焦千之致送惠山泉水,作為煎點新茶的精品,以及蘇軾多次親訪惠山泉,可以看出蘇軾對天下第二泉的傾倒。再看《試院煎茶》這句詩的前后文:“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銀瓶瀉湯夸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可知蘇軾夸贊的是點茶的程序與美感享受,與唐代煎煮茶飲不同,絲毫沒有“將點茶置于煎茶之下,寓有茶品清濁之分”的意思。然而此書征引不慎,并不妨礙全書最重要的觀點:唐宋飲茶的場景與茶器的使用,只有大體上的規約,沒有一成不變的律法。茶書中茶器及其用法的規劃與設計,在實際運作中,主要是作為參考的依據,不是天經地義不能變動。大量宋畫的圖像數據,提供了茶飲與茶器多元多樣的使用形態,也顯示了茶飲之趣的靈動性。
(《宋畫茶韻》,黃晨著,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