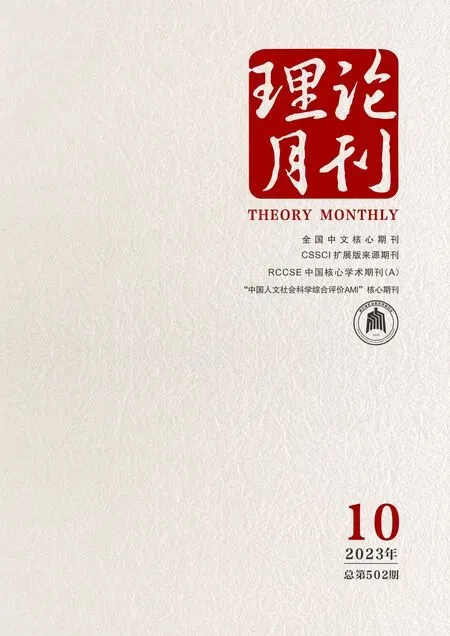社會主義的澄明與圖景重塑
——基于“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視角
□馮旺舟
圍繞探尋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的復興,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兩條路徑:一條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以霍克海默爾、阿多諾等開創的批判理論為特色的路徑。這條路徑聚焦于當代西方社會的科技、文化、消費、生態等領域,提出文化工業、單向度社會、大拒絕、機械復制時代等概念,試圖從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展開對資本主義的大批判。但是,這條路徑過多地運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觀點來改造馬克思主義,消解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最終走向了審美救世、文化大拒絕等悲觀主義,無法找到一條科學的革命道路。另外一條路徑由以齊澤克、巴迪歐、朗西埃、奈格里、哈特等為代表的當代西方激進左翼提出。這條路徑雖然也激烈批判當代資本主義,試圖復興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觀念,但是越來越脫離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斗爭的實際,最終走向了激進民主的話語政治。
面對西方右翼勢力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詆毀,以及部分左翼對社會主義的悲觀失望,“政治馬克思主義”依然堅信21世紀社會主義必然會在西方復興,并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性分析。“政治馬克思主義”(Political Marxism)形成于20 世紀70 年代,是諸多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等)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相互碰撞、融合和競爭的產物。截至目前,“政治馬克思主義”已經走過了數十年的發展歷程,形成了三代學術共同體:第一代包括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艾倫·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尼爾·伍德(Neal Wood)、喬治·科米奈爾(George Comninel)、查爾斯·波斯特(Charles Post)、哈維·凱伊(Harvey Kaye)等;第二代包括漢內斯·拉切爾(Hannes Lacher)、貝諾·塔斯卡(Benno Teschke)、邁克爾·A.茲莫萊克(Michael A.Zmolek)、塞繆爾·科納弗(Samuel Knafo)、杰夫·肯尼迪(Geoff Kennedy);第三代包括薩維埃·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埃倫·迪茲金(Eren Duzgun)等。“政治馬克思主義”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當代發展形態,歷史特殊性、階級關系和階級分析構成了其核心范疇和方法,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政治維度作出了重要發展。以艾倫·伍德、布倫納、科米奈爾等為代表的“政治馬克思主義”學者圍繞“批判資本主義,重建社會主義”的理論主題,構建了新的社會主義觀,重塑了社會主義圖景,并試圖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和對傳統社會主義的反思,實現科學社會主義在21 世紀的西方的復興。
一、社會主義的多重意蘊
1991 年的蘇聯解體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消極影響,甚至很多人認為,蘇聯的解體預示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和消亡。但是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指出,“那種認為蘇東共產主義的解體代表著馬克思主義最終危機的假說多少讓人感到有些奇怪”[1](p1)。伍德堅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能夠在西方實現,并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頗為新穎的解讀,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內涵。
(一)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整體超越
“典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將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將社會主義作為對立的階級斗爭,直接與資本主義聯系起來。”[2](p165)馬克思早已揭示了資本主義內在生產體系的不可持續性,認為只有構建一個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統治體系的超越;列寧在馬克思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是建立共產主義的基礎和第一階段,社會主義要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技術、管理經驗等,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因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深刻的聯系,這種聯系深刻體現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處于某種生產體系和社會關系體系之中。伍德指出:“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的需要;我們可以設法應對非常分散的、無法確定的民主概念,這些概念并不明確反對任何可以確認的社會關系體系。”[1](p258)因此,在伍德看來,資本主義將自身同自由民主簡單等同起來,這就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的矛盾: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財產關系基礎上,通過財產權而運行,并且被資產階級所操縱的;而自由民主在形式上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獨立于財產所有權。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以資本邏輯為主導,而社會關系體系卻又受制于具體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體系,這就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離傾向和不斷“內爆”。由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的分離傾向和統治體系的“內爆”特點,它必將被有著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社會主義所代替。社會主義的最大作用就是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統治體系,徹底改變了其運行法則,并在此基礎上扭轉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通過他對黑格爾和法國大革命激進政治的批判,以及他對爭取社會正義的民眾斗爭的支持,馬克思甚至在開始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前就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馬克思通過同資本主義指導原則對抗所構想的社會主義改造,與以前構想的任何改造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這種社會主義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階級斗爭的產物,最終別無選擇,只有結束整個階級社會的歷史,才能結束通過勞動力商品化展開的剝削,保證大多數工人階級的利益。”[2](p178)
(二)社會主義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剝削和矛盾普遍化的消解基礎上
伍德認為,資本主義對勞動群眾的剝削是永恒和特殊的:“資本主義對其所剝削的人民的社會認同,罕見地不感興趣。它不同于此前的生產方式,其剝削方式并不是非要與經濟外的法律的或政治的認同、不平等、差異糾纏在一起。”[3]資本主義的剝削深刻體現在勞資關系中,體現在資本主義企業生產過程中的競爭和利潤最大化的強制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透過市場作為媒介來展開的,資本主義使工人為了商品工資而出賣勞動力,“可以肯定的是,當出賣勞動力以換取工資成為獲得生存條件,甚至是獲得勞動機會的唯一手段時,無產的工人幾乎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是這種強制是非人格化的。這里實施強制的,或顯得如此的,不是人,而是市場”[4](p2)。但這恰恰證明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隱蔽的,因為工人是按出賣勞動力的時間而獲得工資,而不是按他在那段時間內實際能生產多少商品來獲得工資的。無論工人生產多少,被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屬于資本家的,資本家以利潤的形式占有了工人所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后,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的分離更加明顯,這也意味著其政治的相關功能和作用轉向相應的經濟領域,使經濟強制和資本邏輯擴展到更大范圍。正是在這種分離的基礎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被模糊化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更加隱秘與全面化。拉切爾指出:“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性質使得所有將資本主義的總體化解釋為一種完全進步的通往完美政治共同體(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全球層面)的嘗試的做法都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可能性;總體化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矛盾的總體化。最后,它也是開放式的,因為盡管資本主義的矛盾以及圍繞其再生產而進行的斗爭,允許我們窺見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生活秩序的內在可能性,但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實現并不是資本主義總體化的必然結果。歷史沒有終極目的,即使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如此,資本的總體動力并沒有遵循一條不可改變的道路,用自己的概念來認同真正存在的資本主義。”[5](p108)資本主義正是因為其矛盾導致其不斷進行著創造性的破壞運動,而這種運動的終點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張中,雖然其矛盾在擴大和激化,但是這又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社會主義正是在資本主義的矛盾和經濟強制中打開了缺口。隨著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加,對勞資矛盾和資本主義剝削的消除得以實現,從而為構建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正如伍德所指出的,“如果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廢除階級剝削,并代之以一種由直接生產者所組成的無階級性的生產組織,且更直接地廢除資本主義剝削,那么大抵上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心便與特定階級的解放相關,而這個階級受到的剝削則界定了資本主義”[3]。
(三)社會主義是對“普遍人類之善”的超越
伍德指出,很多人將社會主義同“普遍人類之善”結合起來,這種“普遍人類之善”在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那里主要指一種抽象的道德的善和抽象的人類的普遍利益。威廉姆斯指出:西方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的改善,特別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相對優越的特權階層的形成,使得對這種普遍的人類利益的追求遭受了嚴重挫折,而資本主義天然反對普遍利益;傳統上認為的工人運動同普遍利益自然聯系的觀點已經受到質疑,因為現實中工人階級也是會為了其個體的利益而進行某種反抗,但是這種反抗并不被認為是反資本主義的斗爭,并且社會主義作為普遍利益的代表在當前也隨著勞工運動的衰落而陷入困境。盡管如此,伍德認為,只要存在著某種局部和具體的斗爭和反抗,對于“普遍人類之善”的追求便不會因為勞工運動的暫時曲折而喪失。“在社會主義計劃中,‘主要的人類需要’或者‘統一的善’的定位問題是比較關鍵的,也是比較困難的。社會主義計劃,作為一種解放計劃,如果它想有任何可信性的話,就必須拓寬它關于人類解放與生活質量的構思。但是, 即使擴大社會主義的目標,以至把所有的人類目標都包括進來(這必定是真實的解放視野中的一部分),但就其自身而言,并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構成或者是社會主義斗爭的本質,及其組織形式與具體目標問題。”[6](p205)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追求全人類的普遍福祉,這當然既包括對工人等個體利益的保障,也包括對諸如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高質量生活的追求。這就使我們能夠將與之相關的“普遍人類之善”同工人階級的解放和人類解放結合起來,而且這種結合超越了威廉姆斯所說的抽象的道德的善和抽象的人類普遍利益。社會主義應當超越抽象的道德的善,將工人階級的意識轉化為社會主義意識,將工人階級具體的政治目標同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結合起來,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的利益、統治體系和權力結構,實現人類真正的自由解放。
(四)社會主義是以民主為原則的社會組織形式
傳統上,人們將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模式,強調的是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實現工人等群眾的政治解放。伍德從民主的角度對社會主義的組成結構進行了分析。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會把我們大部分的生活置于民主負責制之外,普通公民的民主權利無從談起。民主概念的社會內容已被抽空,積極公民被消極公民所取代,資本主義所謂的公民社會其實也是資本主義消解真實民主、實施形式民主的重要場域。資本主義與“真正的民主”是極端不兼容的,如果真的把民主擴展至它現在不能觸及的范圍,那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末日。在伍德看來,社會主義是唯一能夠實現最普遍和最真實民主的制度,因為它是有別于以國家強制或利潤最大化強制為核心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經濟體的唯一替代方案。正如伍德所指出的,“直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是社會主義的精髓,也會是民主的基礎”[7]。社會主義建立在以民主為原則的生產和社會組織的基礎上,實現了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民主,從而也實現了人民的解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直接的生產者及其自由聯合是精髓,并操控著整個社會的運行發展,社會的每個部分——工廠、社區、學校、社團、國家等都高度貫徹民主原則。作為社會組織形式的社會主義真正把握到了民主的精髓和價值, 民主也成為一切社會成員的根本規范。在伍德看來,民主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恰恰就是人民的力量,甚至是普通的百姓或窮人的權力。資本主義已經掏空了作為普通人民權力的民主的內涵,令勞動者遭受市場力量的折磨而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社會主義能夠讓人民掙脫市場的支配而重獲自由的民主,并對生產和分配實行民主的控制,從而彰顯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因此,伍德認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內涵是:“在不放棄以公民權、保護人權免受國家的侵害等形式體現出來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成果之下,要求恢復民主的原來意義,不過這種恢復自然要適應現代的條件。因為資本主義根本無法恢復民主原有的社會內容及積極的群眾權力,無法把民主權利伸延到那些被資本主義割斷的領域而不毀滅資本主義本身。我認為,在現代世界,民主必須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詞。”[8]因此,社會主義與民主具有同一性,社會主義既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的簡單擴展,也并非簡單地將民主擴展到社會組織的特定基礎之上。社會主義的民主不是抽象和孤立的,而是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的,要滿足人民群眾對更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重建社會主義的路徑
“政治馬克思主義”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在西方的復興,在東歐劇變后需要探索重建社會主義的路徑,這包括要重建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和階級斗爭動力、工人階級同其他社會群體的聯盟、革命政黨、工人同市場的關系等。
(一)重建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和階級斗爭動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階級,能承擔起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消滅剝削的歷史責任。“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益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9](p410-411)作為革命的主力軍,無產階級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而且是未來新社會的創建者。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的確立不僅涉及自身的解放,也關系著全人類的解放。因此,發展工人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而行事的能力至關重要。“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階級政治概念脫穎而出,可以看出它與改革派、起義派、無政府主義者……的政治概念有著內在的不同。馬克思準備作出巨大犧牲,來幫助工人階級在斗爭中前進。然而,這始終是工人們的自我組織。工人們不得不集體地使自己成為代理人,結束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角色,并將他們一生的勞動從使少數人致富的手段轉變為集體實現和享受人類潛能的手段。沒有一個單一的機構、領導人或意識形態概念能夠充分或不可替代地實現這一目標。”[2](p273)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重建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聚焦于勞資矛盾,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進行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生產方式仍然具有剝削性,而且這種剝削全面和深入地影響著社會秩序和生產體系。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中,工人階級受到資本的全面宰制。因此,工人階級要做的并不是對資本讓步,而是要徹底地消滅資本及其邏輯,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然而,我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做的不僅僅是迫使資本讓步。社會主義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比人道的資本主義更具可行性。但是,即使缺少社會主義或作為實現社會主義斗爭中的一部分,為了實現資本讓步而進行的斗爭不同于擺脫資本控制的斗爭;為資本主義制度‘安全網’的斗爭不同于使生活條件擺脫資本主義邏輯的斗爭。也就是說,追求某種難以捉摸且短期的階級契約與向階級關系發起挑戰之間存在不同之處。”[10]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的統治體系和勞資關系中確立起來的。當代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沒有消除,其遭受的剝削和異化更加全面且嚴重。因此,工人階級作為政治共同體是反抗資本主義最重要的集體力量,要重建社會主義必須首先重建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及其階級斗爭動力。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藏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9](p400)。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斗爭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以更全面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在醫療、教育、環境、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斗爭異常尖銳。伍德指出,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是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有力武器,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刻洞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狀況和轉型特點,并通過階級斗爭消除勞資矛盾、工人階級的異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實現工人階級等勞動群眾對國家機器的掌控,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為實現政治解放、勞動解放和社會解放創造條件。
(二)重建工人階級同其他社會群體的革命聯盟
“政治馬克思主義”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工人階級受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有被資本操控、被資本主義統治體系整合的危險,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剝削和異化,無論工人階級如何分化組合,其主體部分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足以構成對資本主義的威脅。“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也需要我們團結所有利益相關者和力量,聯合一致(而不是分頭出擊)進行反資本主義的斗爭。首先是階級這一利益相關者和力量:階級是能夠聯合各方謀求解放的斗爭最有影響的力量;而歸根到底我們所討論的則是我們這些普通人的利益和希望……而資本主義是難以滿足這些需求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做到。”[11](p15)在現階段,資本邏輯深度嵌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機體中,使各個階級內部以及階級之間高度分化,呈現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明確、利益分化嚴重、反資本主義斗爭力量不強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除了要進一步樹立革命主力軍的意識,開展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之外,還要團結其他進行反資本主義斗爭的各個階級和群體,特別是各類新社會運動的成員,比如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女權運動等。這些新社會運動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些邊緣人群和弱勢群眾在資本的統治和壓迫之下的反抗形式,雖然不具有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性,但仍然是反抗資本主義統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重建革命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認為,要建設一個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革命政黨。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運動中,會有少數人,特別是覬覦領袖地位而未能如愿的人堅持錯誤, 忽視甚至反對組建革命政黨,“但是一旦時機成熟,工人群眾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并且把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黨,組成一個能夠實行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黨”[12](p88)。這種革命政黨就是共產黨,它不僅要自覺地領導無產階級群眾,也要善于運用各種方式宣傳、組織和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群眾和被剝削的群眾。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觀點的基礎上,伍德認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真正的革命政黨超越了狹隘的經濟利益和政黨利益,既是指引革命主體進行革命斗爭的強有力保障,也是整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支撐。革命政黨能夠激發革命主體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突破資產階級的選舉機器的束縛,引導廣大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而斗爭。“如果一個政黨或運動不僅是一種選舉機器,而且是動員、斗爭以及在服務于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意識形態變化的工具,那么,它就不能基于一種短促的社會認同與膚淺的權宜之計,而必須在原則上關注更為根本和持久的社會聯合;而且,它必須以追求更接近于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的、與其社會主義目標相對應的利益作為動力。換句話說,如果一個政黨或運動打算從事權力的斗爭,同時充當群眾動員和意識形態改造的工具,如果它打算追求當下的目標, 同時又能推進了社會主義的斗爭,那么,這個政黨或者運動只能首先是一個圍繞工人階級的利益組織起來的‘階級黨’,并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導引。”[6](p235)因此,這種政黨是真正從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出發的革命政黨,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而為人類解放提供條件,同包括資產階級政黨在內的一切其他政黨有著根本區別。而這種革命的政黨其實就是共產黨,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9](p413)。
(四)重建工人同市場的關系
伍德堅持和發展了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關于市場依賴關系的論斷。她指出,布倫納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資本主義首先是由市場依賴和服從競爭界定的,在資本之間的關系中存在著一種無法緩和的矛盾,這種矛盾與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無關。他在分析資本主義戰后長期的經濟衰退過程中,明確反對將資本主義的經濟衰退歸咎于對勞工過于有利的條件所造成的利潤擠壓。“他探討了資本之間關系中不可減少的矛盾,這種矛盾與勞工關系無關。總而言之,這一論點解釋了資本主義競爭如何不可避免地導致產能過剩,最后導致經濟衰退,不論資本和勞動力間的關系如何。在固定資本方面的投資使生產者即使在低成本競爭者參與競爭時也能夠留在市場上,而且他們也可以以較低的利潤率留在市場上。”[13](p275)這是因為,制造商或生產者必須為了收回成本甚至繼續生產剩余價值而留在市場上,而不是選擇退出。這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的總利潤下降,對整個經濟的良性發展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據此,布倫納認為,造成資本主義衰退的根源在于資本之間的“橫向”競爭關系,這與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縱向”階級關系不同。資本之間的競爭直接導致勞動力的商品化,催生了無產階級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意味著勞動力的完全商品化,它會向市場施加一種新興的、影響更深遠的強制力,其具體方式是制造一種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必須完全依賴市場,且沒有任何可供替換的資源而完全受制于市場紀律的勞動大軍。”[14](p118)資本通過市場的強制對勞動力進行操控和剝削,催生了階級斗爭的新領域。而且即使在沒有資本剝削勞動力的情況下,在資本和勞動之間沒有階級劃分的情況下,即便生產資料被歸還給直接生產者,市場依賴和競爭也會帶來積累和競爭的強制,這些強制將優先于社會需要和福祉。而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剝削都不會產生這種影響。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市場強制迫使工人和經濟執行者都遵循其積累和競爭的規則,使所謂的無競爭力的企業和工人破產。一方面,資本依賴勞動力,由勞動力產生;另一方面,市場強制的普遍化也依賴于勞動力的普遍商品化。因此,要重建社會主義,必須要消除工人對市場的依賴,讓他們擺脫商品化的命運,免受資本的束縛和剝削。
三、重塑社會主義的圖景
在探索重建社會主義路徑的基礎上,“政治馬克思主義”描繪了新社會主義的圖景。這幅圖景包括緊密聯系的三個方面:作為政治與經濟統一的社會主義、作為真正民主與平等的社會主義、作為超越話語政治的革命的和有希望的社會主義。
(一)作為政治與經濟統一的社會主義
伍德認為,資本主義從形成之始就存在經濟與政治相互分離的趨勢,這種分離造就了資本主義獨特的統治模式,形成了其統治的意識形態,遮蔽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模糊了勞資矛盾。“經濟與政治的嚴格分離,當然也會模糊由國家所維持的資本主義剝奪方式,既然在政治與剝削力量之間不再有任何明顯的統一性,所以尤為真實的是,由于資本主義能夠把正式的法律平等和政治權力擴展到生產階級中去,甚至是擴展為全民選舉,所以就沒有直接對資本主義的占有與剝削的權力形成挑戰。”[6](p132)資本主義的統治之所以到現在還如此牢固,就算是激烈的罷工和相關群體的反抗都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的統治體系和政治經濟霸權,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是全新的獨特的社會制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高度統一,統治者直接通過行政、司法、軍事等超經濟手段實施統治和壓榨。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實現其更加全面和隱蔽的統治,資產階級通過宣揚政治領域的普選權和所謂的自由民主,使大眾誤認為其基本的權利已經實現,卻忽略了資本主義在經濟領域通過經濟法則(資本邏輯)進行強制的剩余價值榨取。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都沒有獲得真正的權利,也無法操控資本主義統治體系。這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一方面將政治領域的剝削和壓榨轉移到經濟領域,而另一方面這種剝削又要依賴超經濟領域的支持。從經濟領域中分化出來的政治領域只是為了適應資本邏輯或經濟法則,維持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從而構建新型的權力關系。簡而言之,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本來就是資本主義實施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要超越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徹底揭示資本主義統治的意識形態和霸權邏輯,就必須實現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統一。正如保羅·布萊克里奇(Paul Blackledg)所指出的,“伍德反對的一個關鍵的綱領性政策是教條主義的選舉主義:這種戰略無視過去一個世紀左右剝奪社會的民主內容的進程。由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和政治是分開的,社會主義政治對選舉舞臺的自我限制將確保社會主義者仍然被排除在真正的決策場所之外。相比之下,基于工人階級斗爭的社會主義戰略觀,可能有望克服經濟和政治領域之間的分離”[15]。雖然在社會主義階段并不能廢除一切異化和分離形式,但是社會主義能夠廢除掉一切壓迫形式, 實現政治與經濟等領域的統一。
(二)作為真正民主與平等的社會主義
伍德指出:在后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右翼學者那里,民主成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謂的民主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以選舉和議會制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還認為,民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不涉及任何社會制度和生產體系的制約,資本主義的民主能夠自然擴展為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自然發展的過程。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民主只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簡單擴張,通常只是從量上增加,不涉及民主的內涵及其權力來源的變更,也不關注民主背后的階級和國家性質。按照這種看法,從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到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擴展不存在某種歷史的斷裂,而僅僅是一個自然的和非對抗性的過程。這就混淆了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他們甚至認為,民主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但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領域事實上的分離,資本主義對于剩余價值的占有似乎沒有任何政治基礎,對于民主與平等的追求也似乎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剝削無關。對此,伍德指出,“資本主義下真正發生的是政治形式的分離,有些是在國家中分離,有些則留在生產環節中(對財產的控制、對勞動過程的權威等)。在真實的意義上,資本主義隱藏了剝削的政治性質以及它的權力基礎,并(借由讓國家看似與經濟分離)隱藏了國家這個支持剝削的關鍵角色”[16]。因此,資本主義中充斥著的是虛假的民主與平等。而社會主義的民主是從根本上廢除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民主,也完全消除了民主與經濟的非相關性和不確定性,體現了人民的利益與需求,是最真實和最廣泛的民主。“去除‘民主’與特定社會利益的關聯,它在NTS①NTS 是伍德《從階級退卻——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一書中的概念,是指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主義”,實質上是將階級與階級斗爭從社會主義方案中剝離出去,其最明確的特征是使意識形態與政治脫離任何社會基礎,特別是任何的階級基礎。那里就變成了一種抽象的理想。如果說作為一個政治目標,它反映了任何現實存在著的‘社會存在’,而且不僅僅是一種沒有力量去維持集體化社會行動的抽象的善的話,那么,似乎我們就必須假定在人本質深處存在著某種獨立的‘民主化’之動力。”[6](p164)任何類型的民主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同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階級基礎、文化形態緊密聯系的,從根本上來說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資本主義所采取的主要解決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無助于人類的進步事業。而社會主義能夠消除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根本對立,是對資本主義的完全超越,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與民主。
(三)作為超越話語政治的革命的和有希望的社會主義
伍德指出,從人的自由解放角度,社會主義也是人類解放的一個階段,而且這個階段主要實現的是工人階級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至于勞動解放、人的解放還要等到共產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作為一種集體力量,通過階級斗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的解放本身就是人類總體解放的基礎和一部分。“左派不再想當然地認為人類解放的決定性戰役將發生在‘經濟’領域,發生在階級斗爭的有效領域。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重點已經轉到了為超經濟產品(性別解放、種族平等、和平、生態衛生、民主的公民權)而斗爭。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應當致力于這些目標,事實上,階級解放的社會主義事業通常是或者說應當是實現人類解放這一更大目標的一種手段。”[1](p261)這些領域的異化其實質是資本主義擴展其霸權,實施全面統治帶來的必然結果。面對種族和性別壓迫、生態災難、民主的異化等一系列問題,資本主義不僅無法解決,反而通過其超經濟的手段強化了這種壓迫和異化。據此,伍德指出,某些左派只重視這些超經濟領域的斗爭,而忽視了決定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和統治的階級斗爭,從而陷入了資產階級右翼學者預設的話語或權利斗爭之中,喪失了批判性和革命性。因此,伍德主張必須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將話語政治轉化為階級政治,將被弱化的工人階級意識轉化為強大的革命意識,實現工人階級利益和普遍人類利益的結合,最終實現人類的自由解放。伍德對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雖然其理論有某種烏托邦色彩,但是畢竟已經指出了某種總體性的方向,能夠給人帶來勝利的希望。
四、評價與啟示
(一)“政治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觀的特點
“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具有鮮明的特點和重要的啟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正確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系。“政治馬克思主義”指出了在現代資本主義民主中,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和剝削同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共存, 直接生產者屈從并獨立于其政治地位之外的經濟強制,這是由工人不占有財產的狀況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公民地位和階級狀況的分離就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公民權不是由社會經濟地位決定的——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能夠與形式民主共存;另一方面,公民平等不會直接影響階級不平等,形式民主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剝削。”[1](p198)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通過經濟與政治的分離對工人階級等廣大勞動群眾進行了總體性的宰制,既加深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也使得民主的形式與內容相分離。伍德認為,在根本意義上,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底色和基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的全面統治和普遍化的歷史條件下,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分離導致資本主義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迷惑性,使民主幾乎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詞。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形式民主和虛假民主,其通過所謂的選舉和投票,遮蔽了普通勞動者的政治權利被削弱的問題。就算近代資本主義實現了普遍的民主制度,給予了工人階級一定的政治權利,但是這些政治權利也是廣大工人階級經過長期的反資本主義斗爭才實現的,而非來自資本主義本身。因此,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才是真實的,才能夠充分保障勞動群眾的政治權利,增強人的民主意識、法律意識等,從而推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第二,堅持從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和矛盾出發,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革命斗爭的重要性。“政治馬克思主義”既認識到了當前資本主義的總體統治所導致的階級斗爭的弱化,也認識到了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家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必然導致勞資矛盾加劇。資本主義從其誕生時起,就是由市場來支配的,而資本只有在市場中才能對勞動力進行剝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剝削者與生產者雙方對市場的依賴性意味著他們要受制于競爭、資本積累和不斷提高的勞動生產率等法則的強制;以競爭性生產為生存基本條件的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正是受這些強制性法則的驅動。”[4](p1)受制于資本邏輯,資本主義永遠處于擴張之中,其全球擴張也使其矛盾和危機擴張到全球,而這必將造成空間層面的世界非均衡發展和全面危機。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和危機的總爆發必然會使全世界的人們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反人類、反社會、反自然的本質,促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
第三,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不是追求純粹的經濟利益和抽象的善,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平和正義,旨在實現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全人類的自由解放。社會主義是在同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競爭和斗爭的環境下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永遠在和資本主義爭奪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導權,從而也使社會主義永遠處于憂患意識之中。社會主義要實現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生產正義和分配正義,以及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統一。社會主義并不純粹地追求抽象的善,而是始終將對道德層面的追求同現實的人的生存處境結合起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正是社會主義的這一實踐本性以及對人類終極價值的追求,使其永遠具有活力。
第四,具有后社會主義的特點。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在不斷地進行政治經濟領域的變革。恩格斯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17](p601)這說明社會主義就是在不斷變革中實現發展的,同時這種發展必須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從而保證社會財產關系不發生轉變。伴隨著東歐劇變,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被納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之中,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都不斷進行著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這種轉型不是徹底地變成資本主義的體系的一部分,而是具有某種德里克意義上的后社會主義特點。“后社會主義也必然是后資本主義的,但不是作為資本主義之后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表現為既利用資本主義的經驗又試圖克服資本主義發展缺陷這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18](p27)在“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中,社會主義有兩個方面的意義:其一,時代的意義,指在東歐社會主義解體之后的時代,我們要反思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其二,社會主義涉及在人類文明史中如何吸收和改造資本主義問題。“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當代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全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將長期共存,這就必然涉及對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鑒的問題。
(二)“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缺陷
“政治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主義社會也進行了診斷,試圖構建社會主義的理想模式,但是“政治馬克思主義”對一些問題的闡釋還不夠充分和準確。
第一,沒有澄清增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有效整合反資本主義力量的措施。“政治馬克思主義”批判了左派當中對于社會主義的悲觀主義傾向,也提出了反資本主義的力量整合問題,但是伍德對這個方面的闡釋存在著一些缺陷:其一,伍德更多地強調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以及革命主力軍的身份,但是并沒有對當代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以及這種分化造成的階級意識薄弱、階級力量分散等問題作出詳細的論述,從而削弱了其理論的說服力,不利于我們全面把握當代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總體統治體系中的生存境遇。其二,伍德雖然對除工人階級以外的反資本主義力量也有所論述,但是并沒有具體闡述這些反資本主義力量同工人階級的實際聯系以及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貢獻,也沒有提出對這些反資本主義力量進行有效整合的路徑與措施。其三,伍德對重建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有所論述,但是對于現存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強、斗爭不力的問題的分析還不夠全面和透徹。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受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消費模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要增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提升其階級斗爭的力量,就必須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有針對性的改變。一方面,在宏觀上,要徹底改變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讓工人階級更加明確自身的階級地位;另一方面,在微觀上,要關心工人階級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加強對工人階級的宣傳教育,讓他們能夠以先進的思想武裝頭腦,自覺維護自身合法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益,從而提升階級斗爭的力量。
第二,沒有清晰闡釋革命政黨的主要功能及其同國家之間的關系。“政治馬克思主義”在闡述重建革命政黨的過程中,雖然指出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但是并沒有論述革命政黨如何有效地領導反資本主義的力量,也沒有闡釋在進行革命斗爭的過程中,革命政黨同國家之間的關系。革命政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碎舊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機器,并帶領人民進行生產建設、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但伍德對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及之后革命政黨的功能和作用闡釋不清。實際上,革命政黨的功能包括政治引導、思想引領、宣傳教育等,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后,革命政黨更要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斷掙脫思想、體制、文化等方面的束縛,不斷地進行革命,鞏固社會主義政權。
第三,對政治與經濟的分離,以及民主的作用等方面的論述有待完善。“政治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應該是政治與經濟的高度統一,但是忽視了這種分離是資本主義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具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政治與經濟的分離雖然遮蔽了資本家的剝削,但是也促進了工人勞動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既要實現政治與經濟的統一,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政治和經濟利益,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也要防止政治過度干涉經濟運行,使二者保持持久的張力。比如,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下,政治過度干預經濟恰恰就是一個問題,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停滯。我們還要認識到,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是統一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本質,但也是現代國家的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體現。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指出:“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 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19](p40)列寧是從民主的本質來說的,即只要階級社會沒有被消滅,具有暴力機關的國家機器沒有被消除,就算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制仍然具有某種局限性。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實現了自由全面發展,才能實現完全意義的民主(消除了階級屬性的民主),而這是伍德沒有認識到的。
總之,伍德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診斷,構建了其“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這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有一定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