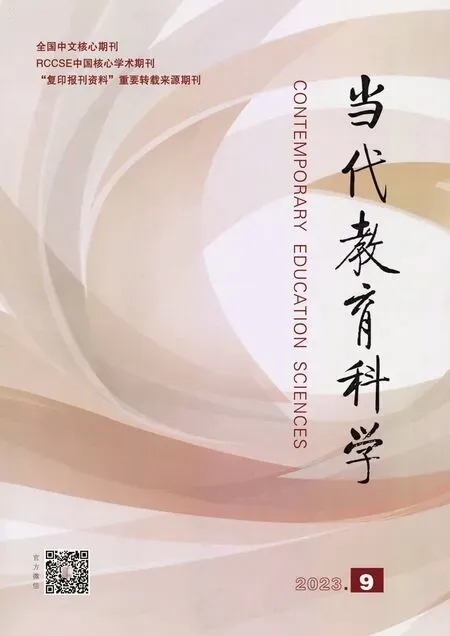從“割裂性評價”走向“融合性評價”
——學校德育評價改革的基本路向探析
● 葉 飛
德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重要基礎。德育評價在整個德育工作中又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它可以引領和促進學生道德品格的健全發展。2020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該方案明確強調要把立德樹人成效作為教育評價改革的根本指向,并強調“要堅決克服重智育輕德育、重分數輕素質等片面辦學行為”[1]。伴隨著這種評價改革理念的穩步落實,德育評價改革也在不斷推進過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過度的考試化、賦值化、數量化的德育評價模式的弊端。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當前德育評價體系也依然存在著顯著的問題與不足。這集中表現為德育評價依然沒有完全擺脫割裂性、切片性的評價模式的不良影響。這種評價模式沒有真正把學生道德品質的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全面、系統的評價,從而也就“沒有真正回歸于人、回歸于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根本價值”[2]。新時代的德育評價改革應當進一步破除這種“割裂性評價”的弊病,堅持以整體性、系統性的方式來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從而形成一種“融合性評價”的新范式。這種新范式能夠充分發揮出德育評價的引導和促進功能,更好地落實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的要求。
一、當前德育評價的“割裂性”困境
人的道德品質的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分離的、靜態的過程,“而是一個有機的、動態的、系統的生成過程”[3]。正如哲學家康德所言,教育(包括德育)是為了“均衡且合目的地發展人之一切稟賦”[4],從而實現人之為人的根本屬性。德育評價也應當始終把學生當作一個不斷生成、全面發展的道德人格整體來看待,從而更合理地理解和評價兒童的道德發展的整個過程。但是,當前德育評價體系依然存在著從分裂的、靜態的視角來看待學生道德發展的不良傾向,沒有真正把學生當作不斷生成的、全面發展的道德主體來看待,這事實上也帶來了德育評價的“割裂性”困境。這種“割裂性”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德育評價理念的主客體關系的割裂,導致了對學生的客體化、對象化乃至于物化。正如雅斯貝斯(Karl Jaspers)、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學者曾指出的,教師與學生是教育活動中的平等的主體,主體之間所形成的是一種“我與你”的主體間關系[5]。這種主體間的關系在教育理論研究及實踐領域已經為大家所熟知,但是,它在教育評價(包括德育評價)領域中還沒有被充分認同。在當前的德育評價中,學生往往仍然被視為客體對象,其道德主體人格及主體精神在評價過程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這也就在事實上造成了德育評價中的主客體割裂。這種割裂一方面表現為對學生的客體化和對象化。德育評價似乎只是成了教師的“獨角戲”,教師是評價過程中的唯一主體,而學生僅僅是被動接受教師評價的客體對象。這就難免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構筑起了一道“隔離墻”;學生成了“隔離墻”之外的客體,缺乏參與德育評價的資格和權利。這事實上不利于學生的道德主體人格的發展,也不利于德育評價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的實現。另一方面,這種主客體關系的割裂還體現為德育評價內含了一種物化的思維,傾向于把學生當作“可測量的物”來對待。這種思維導致了德育評價中的科學主義傾向,即評價者把人當作動物、植物或者化石一樣,運用科學主義的評價方式(比如,閉卷考試、問卷統計或者量化測評等)來對學生進行評價,并得出學生道德發展的“數值”。這種評價方式看似科學,但事實上卻是不科學、不合理的。人的道德、精神、心靈的發展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整體,是無法加以數量化的,是不能進行割裂式的、手術刀式的分解、測量的,“人的心智、心靈品質無法被數據估算,人的生命價值也不應當被估算”[6]。這種割裂式的、數量化的評價理念滲透了一種物化的思維。它沒有真正把學生視為具有精神、心靈的道德人格來對待,而是把學生當作可物化、可量化的客體來對待。因此,這種評價理念也就很難實現以學生為本,很難真正客觀、公正地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
其次,德育評價的內容指標體系的割裂,導致了品德各要素之間的割裂以及學生品德發展與道德生活的割裂。當前,德育研究領域對于德育評價的內容指標體系大體已形成了知情意行、知情行等主要派別,其中,以知、情、行三個品德指標要素的派別最為大家所認可和接受[7]。比如,美國學者托馬斯·里克納(Thomas Lickona)就主張把“Moral Cognition”(道德認知)、“Moral Emotion”(道德情感)和“Moral Behavior”(道德行為)作為人的品德發展的三大核心要素[8],德育評價應該對這些核心要素進行綜合性評價,而不能對這些要素進行割裂。但是,在當前的德育評價體系中,品德各要素之間卻往往是割裂的。這首先集中體現為德育評價的重點是指向于道德認知,而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往往遭受忽略,導致了道德的認知、情感與行為的割裂。德育評價往往習慣于采用知識性、理論性的考試或考察來評估學生的道德發展,這事實上主要是一種認知性的評價,評價的對象主要是學生的道德認知,而非學生的道德情感、道德行為以及作為整體的道德人格。這事實上導致了德育評價中的認知與情感、認知與行為等要素的割裂,使我們無法從整體的、全面的角度來評價學生的道德成長。另一方面,這種割裂也體現為品德發展指標與道德生活之間的割裂。學生品德發展的各項內容指標,不論是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還是道德行為,所構成的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且是完全融于生活的,是不能脫離生活的。但是,當前的德育評價還沒有真正能夠融入真實生活場景之中,不論是閉卷考試、問卷測量還是考察、觀察等,仍然主要是以脫離生活的方式來開展評價。這可以說是一種“抽離性”“抽象性”的評價。這種評價無法真正客觀、全面地評價學生在真實生活中的道德素養及道德能力,這對于全面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再次,德育評價在評價方法維度上也存在著單一性、割裂性的特征。它割裂了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的辯證關系,難以有效地評價學生道德成長的全過程。如果說定量評價是強調基于抽象的“量”來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那么定性評價則更加關注學生的“質”的發展,后者主張全面了解、掌握和描述學生道德成長的動態生成的整個過程。顯然,對于當前的德育評價而言,定性評價應該占據主導地位,而定量評價應該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兩者在一定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是,當前的德育評價在方法維度上依然呈現出顯著的、單一的定量化特征。根據筆者對一些學校的調查發現,目前,小學階段的很多學校仍然主要是采用考試評價或者操行評定的方式進行德育評價,而中學階段很多學校則采用單一的考試方式來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這種單一化的、以定量為主的德育評價方法,事實上沒有把學生當作一個整體的、生成的、發展的道德人格來對待。它既無法全面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也無法準確地描述學生道德發展的過程。因而,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面臨著很大的問題。這事實上也要求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定性評價,充分運用好定性評價方法去考察和評價學生道德發展的整個動態的、生成的過程。德育評價需要更加關注學生的“質”的發展,而不只是“量”的測算,從而避免德育評價方法上的單一性和割裂性,推進德育評價方法的革新。
最后,德育評價在評價渠道上也存在著割裂性的風險。這集中體現為德育評價渠道線上線下的割裂以及家庭、學校和社會之間的割裂。一方面,不論我們承認與否,我們已逐漸進入了以虛擬信息技術運用為主要特征的數字化社會(Digital Society)。在這樣的社會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教育活動以及評價活動中得以廣泛運用。這事實上也要求我們探索德育評價的新渠道、新途徑。德育評價既要充運用實體空間中的線下評價,在實體生活中評價學生的道德人格發展;同時,伴隨著數字化、智能化等新技術、新工具的使用,德育評價也應當充分運用大數據測評、數字肖像刻畫、AI 輔助等來全面了解、記錄和評估學生道德發展的動態、生成的整個過程,從而形成線上線下一體化的評價渠道,實現對學生的道德發展狀況的更加全面的、更加智能化的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當前我們的德育評價體系仍然主要是以學校和教師為主體,評價的是學生在學校生活中的道德表現,以學校為主渠道或者唯一渠道來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這在事實上已然割裂了學校、家庭和社會的有機融合關系,使得我們無法全面了解學生在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中的道德發展狀況。這種割裂性也會進一步導致學生的學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割裂,這對于學生的道德人格的健全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融合性評價”及其必要性
如前所述,當前的德育評價存在著主客體關系、內容指標體系、評價方法以及評價渠道等方面的“割裂性”困境,它導致德育評價疏離于人的道德發展的整體性、生成性和動態性等基本特性,從而難以全面、客觀而公正地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為了改變此種狀況,我們應當促進德育評價從“割裂性評價”逐漸走向“融合性評價”。這種“融合性評價”的核心要旨,就是以德育評價的主體間關系融合、內容指標體系的融合、方法的融合以及渠道的融合等為基礎,使德育評價真正回歸于學生以及學生道德發展的整體性、生成性和過程性,促進學生道德人格的整全發展。這種“融合性評價”在當前德育評價改革中已經愈來愈凸顯出了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融合性評價”是落實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理念的重要基礎。《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已明確指出,我們要“完善立德樹人體制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9]。在以往的德育評價中,我們依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唯分數、唯考試的誤區,這種做法割裂了學生的知識與道德、理智與情感等的緊密聯系,形成一種割裂性的評價范式。融合性的評價正是基于這種“破五唯”的評價新理念,試圖重建人的知識與道德、理智與情感、肉體與心靈等的有機融合關系,從而不斷地提高德育評價的系統性和全面性,扭轉不科學、不合理的德育評價導向。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融合性評價”是推動德育評價理念革新、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要基礎。立德樹人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學生的道德人格發展也是一個全面的、系統的發展過程。德育評價改革需要更好地發揮出自身在立德樹人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把學生當作一個整全的道德主體來加以對待、加以評價,以形成對學生道德品格發展的全面、系統的診斷。顯然,“融合性評價”可以推動建立更加系統、全面的立德樹人成效指標及評價標準,并且可以引導德育更好地圍繞這些成效指標和標準來評估學生的道德品格發展狀況,以發現學生道德品格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從而充分發揮出德育評價的反饋、矯正、導向和激勵等功能,更好地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使命。這會使德育評價更好地服務于培養全面發展的時代新人的目標。這是融合性評價在新時代德育改革中所能發揮出的重要作用,同時這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其次,“融合性評價”也是推動學校德育工作不斷創新發展、推動學生道德人格整全發展的迫切需要。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我們的學校德育工作面臨著不斷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學校德育工作不能只是在理論性和原則性的層面上重視學生的道德人格的全面發展,而是也要在實踐性的層面上真正去滿足學生的這種全面發展的需要。應該說,目前的德育工作仍然沒有完全做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評價指揮棒依然是割裂性的,而非融合性、系統性的。因此,不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的角度出發,推動這種以“融合性評價”為核心的評價改革,對于促進學校德育工作的探索創新、促進學生道德人格的整全發展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這種“融合性評價”的理念要求學校和教師真正去認識到學生的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等要素的有機融合關系,它們之間不是割裂的關系;德育評價必須注重這些品德要素之間的融合性、系統性,把學生的道德人格視為一個不斷生成和發展的整體,從而推動評價本身從“割裂性評價”走向“融合性評價”。惟有如此,學校德育工作也才能從根本上把學生作為一個“整全的”道德主體來對待,同時也才能更好地促進學生的道德人格的全面發展。
最后,這種“融合性評價”不僅注重學生的內在品德各要素之間的融合性和系統性,同時也注重外在德育環境要素之間的融合性和系統性,這包括德育的學校環境、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等環境要素。“融合性評價”不僅強調學校和教師的評價主體作用,同時也主張充分融入家庭評價、社會評價等,從而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融合性評價”來全方位地了解和把握學生的道德發展狀況,更加客觀而全面地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這最終也可以更好地發揮出評價的引領作用,為學校德育工作提供堅實、科學的評價基礎,促進學生道德人格的全面發展。
三、走向“融合性評價”:德育評價改革的基本路徑
德育評價改革事關德育發展的方向,它在德育工作中發揮出著重要的導向、反饋和促進等功能。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德育評價應堅定落實“破五唯”的評價改革精神,遵循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從“割裂性評價”逐漸走向新型的“融合性評價”,促進德育評價中的主體間關系、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方法、評價渠道等的融合性發展,真正回歸于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本真目標,促進學生的健全的道德品格的培育。
首先,建構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本的德育評價理念,形成一種以人本性、生成性和整體性為主要特征的融合性評價新理念。這種“融合性評價”的新理念,是把人作為全面發展的道德主體來進行評價,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本,回歸于人、回歸于人的整全人格,推動實現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這種本質規定性,事實上蘊含了人作為道德自主建構的主體人格的根本屬性。這一方面意味著,德育評價在基本理念層面上不是主客體二元對立的,而是堅持一種主體間的交融理念。人并不是被決定的客體對象,而是處于不斷地生成和自主建構過程中的道德主體。融合性的評價理念強調了學生的道德主體人格的全面性、系統性和自主性,德育評價因而要全面關注學生的道德發展及品格自主建構。學校在評價過程中應當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使評價成為一種主體間的交融性評價,而不是教師的單向度評價。另一方面,這種評價理念要求把學生視為整全的道德人格,拒絕以物化的方式來測量學生、分析學生,拒絕對學生的道德人格進行切片式、割裂式的數據測評。因此,這種評價理念反對以科學主義的評價范式來測量學生,拒絕評價的實證化、數量化等不良傾向,主張關注兒童道德發展的整體表現。它強調評價不是為了給學生道德發展一個最終的測評數值或者道德分數,而是逐步以過程性評價來取代終結性評價,全面觀察和評估兒童的道德生命發展的整個過程。在這種評價理念的革新過程中,學生不再只是一個被測量、被分析的物化的客體,而是真正成了具有整全人格的道德主體。這是一種擺脫了被物化、被異化的評價狀態。惟有如此,德育評價才能回歸于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本,發揮出德育評價對學生道德發展的引導和促進功能。
其次,發展綜合性的德育評價指標體系,以促進各項內容指標的有機融合和整體評價。由于遭受唯考試、唯分數等不良傾向的影響,以往的德育評價習慣于采用科學主義范式、考試評價機制對學生的道德發展進行評價。但是,這種評價往往只能測評學生的道德認知,而無法有效地測評學生的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等。因此,這種評價是割裂性的評價,而非有機融合的整體性評價。這些年來,我們雖然已經在理論層面上認識到了綜合性的評價指標體系的重要性,但是在實踐層面上依然主要是以割裂的方式來評價學生的各項道德指標要素的發展。因此,從融合性評價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僅應當在理論層面上,而且應當在實踐層面上構筑起綜合性的內容指標體系,真正從整體的、系統的角度來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一方面,應構筑更加全面的內容指標體系,全方位地評價學生的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等核心指標。我們可以通過認知性問卷、訪談觀察等來測評學生對道德概念、道德知識、道德觀念等方面的認知水平及理性思考能力;通過道德情感量表、體驗式評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情感觀察等,來了解學生的道德情感意識以及道德情感能力的發展;通過真實生活中的道德行為觀察來評價學生的道德行為意愿以及行為能力,等等。通過整體運用這些認知性評價、情感性評價以及行為性評價等方式,我們可以更全面地評估學生在道德認知、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為等方面的綜合發展。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結合具體的生活場景來展開融合性的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是與真實生活融合為一的,它們與生活是無法相脫離的。因此,我們在評價學生的各項道德指標的發展水平時,就不能采用與生活相脫離的“抽象性評價”,應當運用與真實生活有機融合的“融合性評價”,不然就很容易導致評價指標的“抽離化”風險。也正因為如此,德育評價不僅要通過問卷、觀察等方式來展開,更為重要的是要在真實的生活中來全面了解學生的道德認知、道德情感以及基于認知、情感而產生的道德行為的真實發展情況。只有把這些德育評價的內容指標(道德認知、情感以及行為等)真正“嵌入”真實的生活場景中,方能實現與真實生活的融合,德育評價所得出的評價結果才是客觀而全面的。基于這種真實的、客觀的德育評價,我們也才能更好地了解學生的道德發展狀況,最終促進學生的道德人格的健全發展。
再次,構筑多樣性的德育評價方法,破除德育評價方法的單一性弊端。在以往的德育評價中,我們的德育方法往往是比較單一的:單一的評價主體(教師)、單一的評價機制(考試)以及單一的評價結果(分數或者等級)。這顯然不符合新時代德育評價改革的需要。我們需要構筑更加多樣性的德育評價方法,以良好的德育評價方法來引領學生的道德發展。一是構筑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方法。德育是關乎人的道德、心靈和精神的,它們關乎人的發展的“質”,而不只是“量”,這些都是無法用單純的定量方式來加以評定的。為此,德育評價在方法層面上應該更加注重定性的方法,始終堅持以定性評價為主要方式,來全面了解、掌握和描述學生道德發展中的“質”。例如,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觀察、面對面的訪談、小組座談或者班級座談等方式,來深度了解學生的內心世界,全面評估學生在道德的認知、情感、態度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發展水平,從而形成對學生道德發展的一種深度理解和全面評價。當然,在定性評價之外,“在指標可靠、數據可靠、模型可靠的基礎上”[10],我們也可以進行一定的定量評價(比如,認知性測驗、情感測驗、問卷統計等)。但是,定量評價只能起輔助作用,定性評價應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從而實現定性與定量的有機融合。二是構筑多主體的協同評價。教師、學生、學生群體等都可以、同時也應當成為德育評價的主體。德育評價要打破單一的教師評價,推動學生評價、學生互評、群體評價等多樣性的評價方法的運用,從而促進教師、學生以及學生群體、教師群體之間的協同評價,以充分發揮出多主體的評價主體性。這可以使德育評價擺脫單一性評價的弊端,提升評價本身的科學性、合理性。三是探索道德銀行、道德積分卡等既具有趣味性又具有生活實踐性的評價新方法。道德銀行是“把學生的良好道德行為轉換成道德幣的形式并存入‘銀行’的一種評價方法”[11],道德幣的多少也就意味著學生所做的道德善事的多少。道德積分卡,則是給學生設立一個積分記錄卡,此卡可以記錄下學生的所有道德行為。不論是道德銀行還是道德積分卡,都可以對學生在學校生活、社會生活中的良好道德行為表現予以觀察、記錄和評價。這種評價方法帶有比較顯著的生活性、趣味性的特點,可以對學生的道德行為產生激勵和導向的作用,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鼓勵學生選擇道德上的良善行為,最終對學生的道德成長起到正向的推動作用。這些新型的德育評價方法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探索和實踐的,它們有助于多樣性的德育評價方法的建構和創新。
最后,形成開放性的德育評價渠道,構筑線上線下、家校社的一體化融合評價。伴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當前的德育評價改革也應當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工具、新技術來加強線上與線下的一體化評價,促進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實體評價與虛擬評價的融合。例如,學校和教師可以充分運用大數據的技術平臺來全面記錄、保存和分析學生的道德生活及道德行為,并以視頻、圖片或者文字等方式來形成道德成長的“線上檔案袋”[12],對學生的道德發展狀況進行全過程的跟蹤和評價。我們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觀測學生的認知、情感以及態度等方面的變化。這些數據使教師能夠及時掌握學生的發展情況,對學生道德發展中的問題予以及時解決。通過這種線上與線下相融合的評價渠道的創建,可以全面地評價學生道德品格的生成和發展的過程,實現過程性評價和發展性評價。這些是傳統德育評價所不具備的優勢。另一方面,還應不斷向外拓展德育評價渠道,加強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協同合作,推進教師評價、家長評價和社區評價等的有機融合。德育評價不僅要充分發揮學校和教師的評價主渠道作用,也不能忽略了家庭和社區的作用。因為,學生不僅是學校的一分子,同時也是家庭和社區的成員。以往的德育評價模式往往只注重學校的評價,忽略了家長和社區的評價。這事實上不利于德育評價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的提升。因此,對于當前的德育評價改革而言,我們還需要不斷加強學校和家庭之間的聯系,推進德育評價中的家校合作,使家長的評價也成為德育評價的重要部分;同時,不斷加強學校和社區的合作,通過社區把學生在道德上的良好表現及時反饋給學校和教師,使學生在社區活動中的道德行為表現成為評價的重要內容,從而更加全面地考察和評估學生的整體道德發展。總之,通過這種線上線下、家校社的一體融合評價的建構,可以更全面客觀地評價學生的道德發展,增強德育評價的質量和效果,最終更好地促進學生的道德人格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