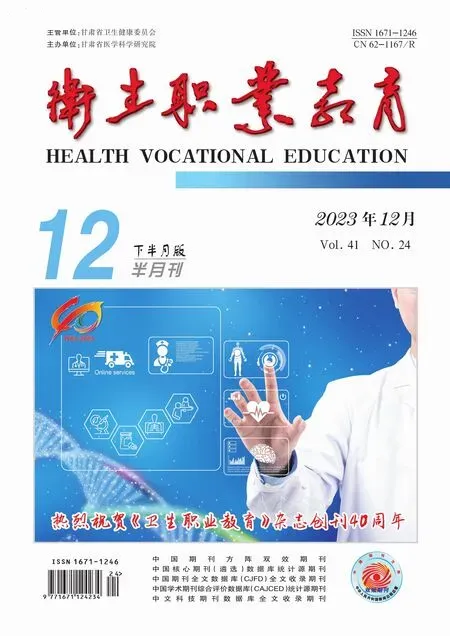2011-2020 年醫學生職業認同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
梁紅霞,王哲
(1.湖北醫藥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院,湖北 十堰 442000;2.湖北醫藥學院體育課部,湖北 十堰 442000)
加強醫藥人才隊伍和人力資源建設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的重要內容和政策實施的保障機制。隨著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和“健康中國”建設的全面實施,醫療人才隊伍的穩定和高質量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醫療衛生行業帶來巨大沖擊。在此背景下,醫學生能否堅定選擇從事醫學職業關系到我國醫療人才隊伍的穩定和醫療衛生事業的可持續發展。職業認同是指個體對于所從事職業的目標、社會價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與社會對該職業的評價及期望一致[1]。高水平職業認同的人能在從業過程中體驗到意義感和使命感,更容易獲得客觀的職業成功。相關研究指出,我國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2-3],但也有研究認為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偏低[4]。我國醫學生職業認同情況很難有一個統一的定論。同時,國內醫學生職業認同研究多以橫斷面研究為主,而橫斷面研究無法考察社會變遷條件下醫學生職業認同的發展趨勢。針對以上問題,橫斷歷史元分析(也叫橫斷歷史研究,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CTMA)是較為有效的研究方法。橫斷歷史元分析是由美國心理學家Twenge 于2000 年提出的一種定量研究方法,國內學者辛自強等[5]對其系統總結和應用。它采用“事后追認”的橫斷研究設計(即將孤立的已有研究按照時間順序加以連貫,從而使這些研究成為關于歷史發展的橫斷取樣)對大跨度時間內的心理變量進行研究,從宏觀上揭示心理變量隨年代的變化趨勢。此外,該方法還可以將社會變遷層面的宏觀變量(社會指標)與心理發展層面的微觀變量(心理指標)連接起來,考察某個心理變量隨年代的變化趨勢,通過與經濟社會指標的相關分析來推測心理變量變動的經濟社會原因[6]。本研究采用橫斷歷史研究法分析過去10 年間我國醫學生職業認同發展變化的基本趨勢和規律,并探討其變化的經濟社會原因。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使用華東師范大學張麗莉[7]編制的“醫學生職業認同量表”為測量工具的文獻作為分析對象。該量表包括職業認知、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期望、職業價值觀6個維度,共38 個條目。采用Likert 5 級計分法進行評分,認可度從低到高依次賦值1~5 分,得分越高,表示認可度越高。
1.2 文獻搜集方法
1.2.1 文獻搜集標準參照辛自強等[8]橫斷歷史研究方法。文獻納入標準:(1)以張麗莉《醫學生職業認同量表》為測量工具,對量表進行修訂后研究的結果不予采用。(2)調查對象為在校醫學專業大學生,具有同質性和代表性。(3)研究明確報告了一個群體的統計結果,包括總體或子研究的樣本量(n)、平均值(M)和標準差(sd)。排除標準:(1)同一數據重復發表的文獻,以最早發表的文獻為準;(2)特殊群體對比實驗的文獻;(3)數據缺失,且無法推算的文獻。
1.2.2 文獻搜集流程采用Konrath 等[9]2010 年所使用的引證文獻搜索方法,借助文獻數據庫平臺對種子文獻的引證文獻進行檢索,獲得所有引用種子文獻的文章。本研究以張麗莉碩士論文《醫學生職業認同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為種子文獻,在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平臺進行引文檢索,共檢索到文獻139 篇。其中期刊論文96 篇,碩士論文42 篇,博士論文1 篇,檢索日期為2022 年5 月1 日。沿用以往研究采用的年代記錄方法,對于已報告數據調查年份的文獻,以作者所述的取樣年份記錄,對于未報告數據取樣年份的文獻,以文獻發表年份減去2 年記錄。根據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最終納入28 篇文獻,文獻搜集年份為2011-2020 年,樣本量15 162 人。
1.2.3 建立數據庫職業認同及各維度以均值為變量值,年份以自然年為變量值,對納入文獻的數據進行整理并建立數據庫。共有3 篇文獻未報告總體均數和標準差,其總體均數依據各維度數據推算:μ=ΣXini/Σni(μ、Xi、ni依次為總體均數、維度均數、子維度條目數)。由于總體標準差σ 沒有參與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因此僅在計算總體效應量時將其排除。醫學生職業認同文獻信息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醫學生職業認同文獻信息統計結果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on medical students'vocational identity
1.3 統計分析方法
運用SPSS26.0 軟件對醫學生職業認同及各維度均值進行t檢驗、相關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采用橫斷歷史研究公式計算效應量[10]。
2 結果
2.1 醫學生職業認同與年份的關系
分別提取醫學生職業認同總均分及6 個維度得分均值與年份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醫學生職業認同及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價值觀與年份有關(P<0.05),而職業認知和職業期望與年份無關(P>0.05),見表2。職業認同總均分及各維度均分與年份的線性回歸模型顯示,醫學生職業認同與年份線性模型擬合較好(P=0.029<0.05)。在控制樣本量后(見表3),年份仍能顯著預測職業認同(P=0.049<0.05),變異解釋率為14.1%。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價值觀與年份有線性關系(P<0.05),變異解釋率分別為38.0%、30.1%、34.9%、20.1%。

表2 醫學生職業認同與年代的相關性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age

表3 醫學生職業認同及各維度一元線性回歸分析aTable 3 Medical students' vocational identity and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a
為排除統計數據中期刊來源(0=一般期刊,1=核心期刊,2=學位論文)、學歷(0=專科,1=本科,2=綜合)、專業(0=非臨床,1=臨床,2=綜合)、區域(1=東北地區,2=西部地區,3=中部地區,4=東部地區)等因素的干擾,以職業認同總均分為因變量,以“年份”“期刊來源”“學歷”“專業”“區域”為自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份是唯一進入回歸模型的變量(R2=0.141,F=4.27,P=0.049<0.05),進一步證實年份對醫學生職業認同的預測效應。
2.2 醫學生職業認同的變化趨勢
文獻數據涉及調查對象共15 162 名學生,醫學生職業認同總均分根據樣本量加權后的總均值為3.517,平均標準差為0.55。以中間值3 為檢驗值[11]進行單樣本t 檢驗,結果顯示,有統計學意義(t=285.142,P<0.01)。職業認知、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期望、職業價值觀6 個維度樣本量加權后的平均值分別為3.18、3.51、3.52、3.66、3.58、3.63。單樣本t 檢驗結果顯示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表明醫學生職業認同及各維度屬于中等偏上水平。
在控制樣本量后對職業認同各維度指標進行線性回歸并繪制曲線圖(見圖1)。結果表明,各維度線性回歸的未標準化系數(B 值)均為正值(見表3)。說明職業認同的6 個維度指標隨著年份整體都有上升趨勢。線性回歸及散點圖顯示,2011-2020 年間醫學生職業認同總均分隨年份增長有逐步上升趨勢,見圖2。

圖1 醫學生職業認同各維度得分隨年份的變化趨勢Figure 1 The trend of changes of scor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medical students' vocational identity over years

圖2 醫學生職業認同均值散點圖Figure 2 Scatter plot of the mean medical students' vocational identity
2.3 醫學生職業認同變化的年份效應量
為進一步揭示醫學生職業認同及各維度隨年份的變化幅度,采用已有橫斷歷史元分析計算效果量d 的方法,以年代為自變量,分別以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價值觀和職業認同為因變量,建立回歸方程:y= Bx+C(B 為未標準化系數,x 為年份,C 為常量)。效果量計算方法:d=(M2020-M2011)/Msd。結果顯示,醫學生職業認同均值從2011 年至2020 年上升了0.25 分,平均標準差為0.55,效果量達到了0.45 個標準差(d),見表4。Cohen[12]認為,效果量在0.2 至0.5(含)之間為小效應,0.5(不含)至0.8 為中效應,大于0.8 即為大效應。根據這一認定標準,醫學生職業認同在10 年間出現了較小程度的變化,職業行為和職業價值觀具有中等程度的變化,而職業情感和職業承諾則表現出了較大的變化。綜合以上數據,研究認為,除職業認知和職業期望外,醫學生職業認同及其余維度在10 年間都呈現不同程度的上升趨勢。

表4 醫學生職業認同隨年份變化的效應量Table 4 The effect quantity of vocat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over years
2.4 醫學生職業認同變化的結構性因素分析
根據量表開發者張麗莉[7]的研究,醫學生職業認同包含了職業認知、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期望、職業價值觀6 個維度,各維度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為了排除各維度間的干擾因素,在控制樣本量后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職業承諾、職業期望、職業認知3 個維度回歸模型擬合度較好(調整后R2=0.888,F=72.044,P=0.000<0.01),該模型能解釋職業認同88.8%的變異(見表5)。這說明職業承諾、職業期望和職業認知可能是影響醫學生職業認同結局的主要結構因素,其中職業承諾的影響最大(Beta=0.541)。

表5 醫學生職業認同的內部結構因素回歸分析a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nal structural factors of medical students' vocational identitya
2.5 宏觀政策及社會公共事件對醫學生職業認同的影響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和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產生重要和深遠影響的政策和社會因素。研究以事件發生的時間為節點,分別將2011-2015 年、2016-2019 年和2020 年醫學生職業認同均分兩兩進行比較。結果顯示,2011-2015 年和2016-2019 年職業情感、職業行為有統計學意義(P1<0.05)。2011-2015 年和2020 年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價值觀和職業認同總均分有統計學意義(P2<0.05)。2016-2019 年和2020 年職業認同及其各維度對比無統計學差異(P3>0.05)。從各維度平均值來看,除職業認知和職業期望外,醫學生職業認同及其余維度得分2020 年>2016-2019 年>2011-2015 年,見表6。

表6 不同年段醫學生職業認同各維度對比Table 6 Comparison of vocational identity dimension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of different period of years groups
2.6 醫學生職業認同變化與經濟社會學指標的關系
研究從2011-2020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13]中選取反映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的“年衛生技術人員數”“年平均工資”“年衛生總費用”“年衛生總費用占GDP 比重” 作為影響醫學生職業認同的經濟社會指標。結果顯示,醫學生職業認同與年衛生技術人員數(r=0.414)、年平均工資(r=0.404)、年衛生總費用(r=0.414)、年衛生總費用占GDP 比重(r=0.429)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P<0.05)。對相關指標和職業認同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發現,除“年平均工資”的預測為邊緣顯著外,其他經濟社會指標均能顯著預測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P<0.05),見表7。

表7 醫學生職業認同的外部環境因素一元線性回歸分析Table 7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medical students' vocational identity
為排除指標間的相互影響,在控制樣本量后對相關指標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年衛生總費用占GDP 比重”是醫學生職業認同影響因素回歸模型的唯一變量(R2=0.153,F=4.686,P=0.04<0.05),該模型能解釋醫學生職業認同15.3%的變異。
3 討論
3.1 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隨年份逐步上升
國內關于醫學生職業認同的研究自2000 年以來持續增長,至2021 年達到高位(305 篇,萬方數據,2022 年)。相關研究指出,我國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2-3],但也有研究認為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偏低[4]。研究結果存在差異甚至有相反結論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對于職業認同的概念界定和內涵解讀不同,研究的角度差異或側重點也不同,從而導致建立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二是調查對象不同,比如不同專業、不同學歷層次,或是不同群體(定向醫學生、鄉村醫生等);三是研究方法不同,比如采用不同的測量工具(量表)和調查手段。因此,單個研究無法準確概括我國醫學生職業認同的整體水平。同時,由于國內醫學生職業認同多以橫斷面研究為主,而橫斷面研究無法考察社會變遷條件下醫學生職業認同發展的一般概況。橫斷歷史元分析是以綜合已有的發現為目的,是對眾多單個研究結果進行綜合的研究方法,它通過對諸多文獻的定量再分析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本研究通過橫斷歷史研究方法發現,我國醫學生職業認同整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這與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縱向研究結果表明,年份能顯著預測醫學生職業認同的變化,2011-2020 年間醫學生職業認同水平整體呈緩慢上升趨勢。
3.2 醫學生職業認同各維度呈現不同程度變化
研究結果表明,醫學生職業認同各維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各維度間相比,職業行為>職業價值觀>職業期望>職業承諾>職業情感>職業認知。職業情感、職業承諾、職業行為、職業價值觀與年份有正相關關系(P<0.05),而職業認知和職業期望與年份關系不顯著(P>0.05)。在變化趨勢上,職業行為和職業價值觀具有中等程度提高,而職業情感和職業承諾則具有較大程度的提升。研究還發現,職業承諾、職業期望和職業認知是醫學生職業認同主要的結構性影響因素(P<0.05),其中,職業承諾對職業認同的影響最大。層次結構說認為職業認同可能由多項次認同組成,一些廣泛聯合在一起的次認同構成職業認同的核心,越是靠近核心,它們變化或消失付出的代價越大[14]。職業承諾一般是指由于個人對職業的認同和情感依賴,對職業的投入和對社會規范的內化而導致的不愿變更職業或專業的程度[15]。相對于在職人員,在校醫學生的職業承諾更多的是對專業的認同和情感依賴以及對未來職業的理想與期望。職業承諾能顯著增強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和職業決策能力[16-17]。研究結果證實了職業承諾對醫學生職業認同的重要影響作用,提示對職業承諾進行積極干預有助于提高醫學生的職業認同水平。
3.3 醫學生職業認同上升的經濟社會原因
相關研究表明,外部環境因素對職業認同的形成和變化起著重要的孵化作用。在微觀層面,外部環境因素干擾對醫學生職業認同具有顯著作用,如醫院暴力[18]、死亡凸顯[19]等。從中觀層面講,家庭環境、執業環境[20]、醫學人文教育等都是影響醫學生職業認同的重要因素。但在宏觀層面,諸如經濟、社會和政策變化對醫學生職業認同影響的實證研究尚不多見。橫斷歷史研究將社會變遷層面的宏觀變量與個體心理發展層面的微觀變量連接起來,通過分析有代表性的社會指標與心理健康狀況間的相關性,以解釋“社會”對心理健康的影響[8]。研究顯示,“年衛生技術人員數”“年平均工資”“年衛生總費用”“年衛生總費用占GDP 比重”與職業認同具有正相關關系(P<0.05)。除“年平均工資”外,其余均能顯著預測醫學生職業認同的年份變化趨勢(P<0.05)。其中,“年衛生總費用占GDP 比重”對醫學生職業認同的影響最大。分析認為,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度改革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社會變化對醫學生職業認同具有一定影響作用。200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拉開了我國新醫改的序幕。2016 年“健康中國”戰略逐步實施,我國衛生發展模式從“以治病為中心”轉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聚焦疾病預防與綜合健康管理的新階段。新醫改和“健康中國”戰略的實施拉大了國家對醫學生的需求量和衛生事業的投入經費[21],制度性改革的同步推進改善了醫療行業的執業環境,醫務人員的正向價值得到不斷提升。同時,國家對醫療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長還有利于緩解醫學生就業壓力,提高醫學生的職業期望。在此背景下,廣泛的社會支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醫學生專業學習的信心,使其職業認同度得到提高。本研究結果從經驗層面證實了國家宏觀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對醫學生職業認同提升的影響作用。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橫斷歷史研究要求納入文獻需采用同一測量工具,本研究文獻收集的是以張麗莉[7]編制的“醫學生職業認同量表”作為檢索篩選文獻的唯一依據,沒有收錄和分析使用其他量表測量醫學生職業認同的情況,因此,本研究結果不能代表所有相關研究。同時,由于本研究執行較為嚴格的文獻排除標準,使最后納入研究的文獻量相對較少,可能會使個案數據對于研究結果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