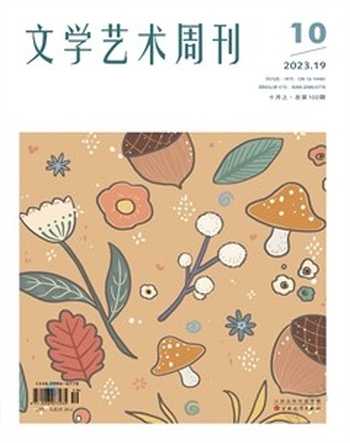“新工筆”圖像隱喻性的觀念表達
圖像中隱喻性的觀念表達受時代變化和社 會經歷的影響,不同圖像的交錯呈現,圖像符 號通過寫實或模仿來表征和反映客觀現實。作 品中隱喻性表達是在挖掘繪畫深處的功能表現,喚起作品中所指、概念以及藝術家的愿望。藝 術家所描繪的圖像都多少與其時代背景、生活 環境、兒時經歷或個人情感追求有聯系。這就 決定了藝術家對物體種類的選擇和圖像形式的 不同表達是承載著藝術家審美意趣和價值內涵 的特殊物象,標志著藝術家個人獨特繪畫語言 風格。藝術家將隱喻性的表達轉化為視覺圖式 語言,通過對原有現實關系的重塑建立新的連 接性關系,通過隱喻的方式來認知現實,反映 出新工筆藝術家們潛意識賦予繪畫的藝術想象,因而,觀者需要不斷審視這些作品深處的功能 表現和與之相對應的關系,在畫面視覺表現和 社會意義間,解讀藝術家對社會意識隱喻意義 的本質情感表達。
一、潛意識的自我感知
藝術創作是一種本能的宣泄,潛意識是創作靈感的基礎。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識分為潛意識、前意識和顯意識三個部分。人的顯意識表達的每一種觀念,背后都具有龐大和深刻的根 源。而這個根源的一部分是可以推測的,那就是前意識區域。另一部分難以推測的,就是深邃的潛意識海底。所以潛意識理論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心理活動都有一定的因果關系,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發生的,夢也不例外。意識的愿望只有在得到潛意識中相似的意愿加強后,才能產生夢。弗洛伊德也注重靈感和夢中的創造性成就,認為夢中的“智力成就屬于在白日引起同樣成就的同一種精神力量”。夢是了解精神領域中潛意識活動的一種最重要的途徑。夢不是偶然形成的聯想,而 是被壓抑的愿望偽裝的滿足。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里談道:“夢,并不是沒有緣由的, 不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荒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識昏睡,而是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產物。它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是一種愿望的達成。它可以算是一種清醒狀態精神活動的延續……”
弗洛伊德還曾經將作家的世界說成是“白日夢”,是實現自己無法實現的愿望的途徑。畫家跟作家的世界有著共通性,夢都是對清醒時被壓抑的潛意識中的一種欲望的委婉表達, 通過對夢的分析可以窺視人的內在心理活動,探究其潛意識中的本能和欲望。因為對藝術家來說,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意識與非意識之間的區別是不存在的。人類要接受外部世界的意象,要將外部意象賦予形狀并對此做出解釋,就必須調動所有的意識能力與非意識能力。而非意識世界中的內容,如果不借助某種可以知覺到的繪畫形式,是不能成為我們的知覺經驗的。對于新工筆畫家們來說,他們的創作過程也是嘗試將現實觀念與本能、潛意識以及夢的經驗相糅合,關于圖像隱喻性的觀念表達,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傳統對美好事物的描繪,而是把圖像作為依托以抒發藝術家的情感。這種潛意識的情感宣泄,一種是放棄理性意識和意志,僅憑本能的自動行為或無意識行為進行創作;另一種是拒絕日常思維和經驗,不拘于邏輯地處理作品的夢幻結構的形式。它就像是一個沖洗膠片的暗房,外在的生活狀態,都是從這個地方沖洗出來的。賴希指出,只有當我們懂得了“情感表達”的時候,才能夠讀懂潛意識。
畫家高茜認為危機與夢幻是同一存在的。《白日夢》是高茜2007年的作品,畫面中心是一盞古老的燈,幽幽地發著光,可是玻璃燈罩里卻留下一只飛不出去的蝴蝶,可能它是向著光而來,卻沒想到在這個理想而透明的逼仄空間里危機四伏。這表達的正是被籠罩在玻璃燈罩下內心焦急的蝴蝶,去往自由天空的憧憬注 定只能是一個白日夢。隱喻人生際遇,如同圍城,在一不小心的美好憧憬里,飛蛾撲火。白日夢的存在是令人無奈嗟嘆卻又不可或缺的存在。藝術家借鑒西方超現實主義繪畫的處理方式,強調不合理事物和夢境之間存在的合理性,藝術家通過物象代替現實中的人以訴說的口吻傳達對生活的思考。當代新工筆畫中以圖像隱喻形式暗示著潛意識的某種觀念,為圖像隱喻性的觀念表達提供了載體意義,擴寬了藝術表達的思維方式,以其成為反映客觀現實的重要手段。
潛意識是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開始從潛意識出發尋 找自我本能,以圖像的隱喻暗示人性的最初欲 望。新工筆圖像中隱喻性的觀念表達與西方超 現實主義繪畫思想觀念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藝 術家追求夢幻與現實的統一,提倡知覺和潛意 識的自然流露,強調本能和欲望。利用圖像表 現違背自然常態的不合理現實,在圖像的隨意 性拼貼和重組等多維度空間交錯的視覺效果中,盡可能地表現自我的抽象情感和潛意識,藝術 家將個人無法言說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通過圖像 呈現的角度去訴說,在不受規律、邏輯和道德 約束的環境中,展現出藝術家在面對現實生活 壓力時,通過對作品創作給予內心以慰藉。
新工筆藝術家以圖像為依托直面人類潛意識里的夢境、現實生活的反映和欲望的隱喻,潛意識是藝術作品形而上的重要途徑,藝術家通過直視自己顯意識之下的潛意識,最后通過自己的藝術表達方式展現在畫紙上。以隱喻內心欲望的表達,達到自我宣泄的作用,讓藝術 家直面現實。
二、“物我同化”的心境映射
“物我”是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關系的一對范疇。《莊子·齊物論》云:“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易傳》主張物我和諧,以達到“盡人之性”與“盡物之性”的目的。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中有“故神思為妙,神與物游”。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寫“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曾借“物我”這對范疇來探究藝術意境的問題。而同化的客觀前提是對象審美特征同主體審美心理結構具有同形同構或異質同構的關系,適應主體的審美經驗和 需要。“物我同化”的隱喻作為隱喻手法中的 互喻形式,是將藝術家當作畫中的某個物件, 畫中的某個物件也轉化為藝術家,二者形成一 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喻形式。當代工筆 畫中的隱喻性在很多方面都有運用,比如風景、動物、靜物。當下社會經濟迅猛發展,人們受 到多元化環境的影響,在物質上得到極大滿足 的同時,更加渴望對精神文化的滿足。人們因 社會環境造就的對人際交往和語言表達的缺失,因缺乏對他人的信任而無法袒露心聲。因此, 更多的藝術家通過對靜物的多角度描繪,達到 自說自話、以物傳情、“物我同化”的心境映 射,以滿足藝術家借物抒發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也借此讓觀者在畫面中找到心靈的共鳴。
姜吉安尤為關注“物”與繪畫的關系,以修辭和光影邏輯再現物。他的現成品繪畫善于從物出發,以物化物,以物移物。他以絹本做顏料,以絹畫絹,通過剪下絹本的邊緣,將絹本燒成顏料,罩染絹本,再用剩下的絹渣,捏成雕塑質感的枝條置于絹本一側。仿佛世間萬物不過是相同元素間的不同組合與形態。
姜吉安的作品讓我們關注物性與人文詩性的內在關聯,他把日常的飲茶行為轉變為當代 的現成品繪畫,這是異常婉轉詩意的轉化:喝過的一片片茶葉被拼貼在茶色染過的絹本上,宛若一首古人以古詩詞寫就的信箋,讓物性與圖像相互印證,又再次塑造出日常的詩意與文人生活的場景,這是水墨性的現成品繪畫最為當代的轉化。這就讓自然材質獲得了詩意的呼吸與當代的趣味,讓現代人再次品味到古色古香的“余味”。
三、傳統符號化的再認識
符號學是解讀當代藝術最重要的理論,關聯著當代藝術的形式分析和傳播模式,在具體的語境中,話語、文字、圖像等符號所傳達的 意義超越了這些符號本來的意義而又與其有著 密切的聯系,這種符號意義轉移的現象即對符 號的再認識。修辭學關系到圖像自身的符號特 征,傳統工筆花鳥畫中以看得見的符號、視覺 形象來表征看不見的人物品質,如梅蘭竹菊被 轉喻成四君子,這些逐漸程式化的文化符號已經逐漸形成對人物品質表現的文化符號。新工 筆作品神奇之處就在于,它們總能以一種新的 展示方式來看待我們周圍的普通事物。一旦它 們以新的媒介被放置在一個特定的場景空間里,它們就充滿了超乎尋常的生活和情緒。新工筆 藝術家通過對傳統美術作品中圖像的挪移借鑒,實際上是將這些物象作為一種文化符號通過作 品的視覺藝術再現,借不同文化符號抒發內心 對社會變化的思考和情感表達的需要。
符號學作為一種文化哲學,使得作品中的 一切物象都是有意義的。也正因此,貢布里希 建議,應該把圖像作為“自然符號”的思想與 圖像作為對自然的“模仿”的思想對立起來。更有利于增進對圖像符號的相似性的認識。這 些圖像符號可以被看作是象征,通過其比例及 相互關系而與他們所代表的事物、思想以及事 件表現出相似性。所以,藝術的創作并不只是 創造本身,同時也是審美觀念的表現。由此可見,即使是畫作中挪用來的符號,也必然存在一定 的隱喻性表達,藝術家對傳統符號的再認識,明確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認識,有別于盲目效仿外來的藝術形式。藝術家通過借助某一特 定文化符號給觀者傳達內在的精神取向,作品中特定的物體符號可以充當給觀者的安慰劑, 借圖像的功能性,給人以精神慰藉,從作品中尋找撫慰心靈的良藥。在社會變革和人們視覺 審美需求的轉化下,對于傳統文化的隱喻意義 逐漸被淡化,藝術家對傳統作品思維意識的轉 變,對傳統符號借鑒引用, 再認識符號的內涵,傳達出符合當代人審美意志的新觀念。也借此思考當下藝術創作與傳統繪畫藝術觀念的區別,從而賦予作品中的物象符號新的隱喻內涵。
高茜作品《李迪的餐桌》是對傳統圖像的 直接借用,試圖傳遞出新的意圖和語言。畫家 通過對人們所熟知的傳統繪畫圖像符號的改造,借此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雛雞站在鋪著蕾絲的 桌面上,在這樣一個非自然的空間里,藝術家 賦予作品某種文化含義。這種截取傳統文化符 號進行嫁接的手法體現其對當代社會環境的思 考。在將古人作品中的元素挪移到自己畫面中時,構建與并置了新的思維觀念,傳達出作品 的詩性傳統和浪漫色彩。高茜作品中還有很多 符號,如高跟鞋、蝴蝶、花等,都跟她的童年 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是童年虛假和真實記 憶的反映。這些符號更像是女性主義的象征, 符號化的背景豐富工筆畫的場景性。
喬治·布拉克建議藝術家們從那些看起來 根本不同的事物中尋找它們的共同點,并將這些共同點表現出來。高茜作品中表現出的現代生活物品的典雅和生動,把現實中無生命的物品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將魚蟲以擬人化的符號表達暗示內心的情感。通過比喻、隱喻的暗示,可以使觀者超越客觀事物的慣有表象,對那些很少有共同點的不同物體做出描述,同時將相 同的物質聯系起來。
新工筆藝術家逐漸意識到內心的情感表達和個人化的色彩表現對畫面的重要性。他們從對符號的借用出發,把現實場景和內心情感緊密結合起來。徐累畫中有很多的視覺符號,馬和帷幔是最為常見的。很多作品中都用帷幔做分隔,使畫面中物象間產生一種似近又似遠,但遙不可及的幻覺。而帷幔就像是對時間的隱喻。帷幔之外是客觀真實存在的,帷幔里面是虛無的幻象,徐累把帷幔做符號,以此分隔出 真實和虛幻,隱喻現在與過去之間的無法打破的界限。在這些無聲的戲劇舞臺上,表現出動態的時間感,讓觀者產生追憶,想直探出帷幔背后所指。新工筆畫家通過對傳統文化中符號的“借用”和對圖像新的解讀,超越其本身存 在的意義。通過對符號的再認識,突破對傳統工筆繪畫的束縛。在各種“借用”的作品中,也是需要實驗精神的實踐和探索,通過圖式、程式、符號元素的文化價值屬性的借鑒,融入當代審美觀念、思維語言和表現形式。
四、結語
新工筆繪畫以獨特的繪畫語言和表現豐富了當代繪畫創作的隱喻觀念,打開了藝術家對身邊事物觀看的角度,新工筆較傳統花鳥畫而言,發揮了更多的想象力和創造空間,使得圖像隱喻觀念的表達更加豐富,為當下新工筆藝術家提供了新的展示和表達空間。當下新工筆繪畫更多的是從人物意緒、城市環境和社會狀況反映繪畫,從圖像的立場出發,以物象做情 感傳達的依托,讓更多的藝術家關注當下,從微小的物體中觀察社會的奧妙,從中得到思考和啟迪。繪畫隱喻作品結合修辭手法中的比喻、象征、比擬、轉喻等,達到文學和藝術表現手法綜合運用的結果,體現了當今社會人們對文化、歷史、社會和個體生存狀態的思考,以圖像之名代替處于焦慮社會中的人們傾訴釋放。
[ 作者簡介 ] 葉可,女,漢族,安徽宿州人,畢業于上海大學,碩士, 研究方向為中國工筆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