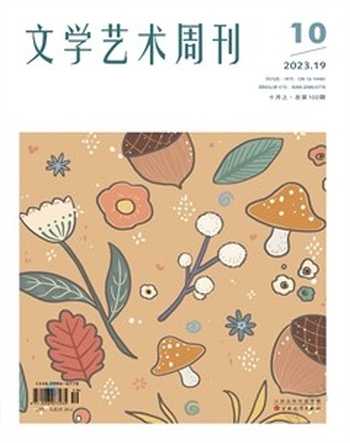吟游詩人王家衛(wèi)
著名導(dǎo)演、編劇王家衛(wèi)1958年出生于上海,5歲時隨父母移居中國香港。1980年,王家衛(wèi) 進(jìn)入無線導(dǎo)演訓(xùn)練班,并擔(dān)任制作助理。1982年投身電影圈,任編劇,迄今為止由他擔(dān)任導(dǎo) 演和編劇的影片共有10余部,其擔(dān)任監(jiān)制、制片人的電影則有70余部。他的每部作品都品位 獨特,值得細(xì)細(xì)品味。1997年,王家衛(wèi)憑借《春 光乍泄》獲得第50屆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導(dǎo)演獎, 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導(dǎo)演。
王家衛(wèi)是少數(shù)在華語地區(qū)之外被廣泛認(rèn)同的中國電影導(dǎo)演。王家衛(wèi)出身于中國香港電影工業(yè)化體系,卻摒棄傳統(tǒng)中國香港電影“生產(chǎn)線”式的快速攝制方式,以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感受進(jìn)行創(chuàng)作,一部電影往往要耗費一到兩年的制作時間。大部分出品人不喜歡王家衛(wèi),覺得他的項目制作周期長,主題、風(fēng)格沒有照顧觀眾的認(rèn)知水準(zhǔn),有的影片票房不佳。制作人員覺得王家衛(wèi)的電影沒有劇本,拍攝效率太低,沒法多賺錢。王家衛(wèi)的嚴(yán)苛緩慢、超出預(yù)算的制作方式似乎與當(dāng)時的大環(huán)境格格不入,一快一慢,彰顯了對待電影創(chuàng)作的不同初心。王家衛(wèi)的電影是復(fù)雜的、精密的。影片中有大量關(guān)于時間、回憶的主題,非線性的情節(jié)、跳躍式剪輯、大段的獨白,都源自王家衛(wèi)認(rèn)為東方人的世界是精致細(xì)膩的,并且通過電影向外界傳遞這種觀念,打破了世人對于中國香港電影“膚淺”的印象。在當(dāng)時商業(yè)電影大行其道的時代顯得特立獨行,一雅一俗,昭示創(chuàng)作者的電影創(chuàng)作訴求與藝術(shù)追求。
不喜歡王家衛(wèi)電影的觀眾覺得他的影片冗長、晦澀、深奧,直呼“看不懂”“不知道在說什么”。但能通過影片的各種元素去解讀王家衛(wèi)電影深義的觀眾,往往看完影片之后大呼“過癮”。這種兩極分化的鮮明對比不禁讓人深思,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從電影的外在形式來看,電影的類型化是原因之一。類型是一個成熟的電影觀眾在看電影時默認(rèn)、熟知的概念,是連接電影生產(chǎn)者所想和電影觀眾所需的可靠紐帶。你喜歡看什么,我就生產(chǎn)什么,在我可控的成本范圍 之內(nèi),讓觀眾隨自己的口味、偏好選擇并體驗。類型化電影實際上就像一套電影制作守則,觀 眾點什么菜,導(dǎo)演這個“廚子”照著菜譜做就是。可是,還有兩個概念是我們常常容易混淆的, 即題材和類型。王家衛(wèi)的電影往往是借愛情題 材講述時間、回憶、孤獨等大主題,表面上看是愛情片,實則是文藝片,因此,觀眾會用愛情片的觀影習(xí)慣、預(yù)期去審視王家衛(wèi)的作品, 看不懂也就不足為奇。
其次,從電影內(nèi)在來看,時間與記憶是王 家衛(wèi)電影的重要母題。在王家衛(wèi)的電影中,我 們常常會看到列車、時鐘、水滴、腳步、背影這些意象出現(xiàn)。有人說王家衛(wèi)的電影屬于20世 紀(jì)60年代,這種感覺源自電影故事的時代背景,又或者是作品呈現(xiàn)的時代氛圍,《阿飛正傳》《花樣年華》《手》都有類似的情調(diào)。也有人說王 家衛(wèi)的電影屬于20世紀(jì)90年代,這種感覺源 自搖晃的鏡頭、碎片化的敘事、拼貼和半隨意 的創(chuàng)作方式、大量的罐頭音樂的使用、自我封 閉式的獨白,仿佛那時流行的音樂電視。王家 衛(wèi)生于20世紀(jì)50年代,成長于60年代,起步 于80年代,打拼于90年代,作品中存在導(dǎo)演 鮮明的個人烙印。在20世紀(jì)90年代回望60年 代,進(jìn)行時間的重構(gòu),令作品呈現(xiàn)出歷史抽離感,仿佛在給觀眾講一個沒有具體時代卻真實存在 過的故事。《花樣年華》的片尾字幕充分說明了這一切:那些消逝了的歲月,仿佛隔著一塊 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 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沖破那塊積著灰 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記憶和忘卻也是王家衛(wèi)電影的重要主題, 人物往往通過忘記去消解不能處理的傷痛。在 《旺角卡門》《墮落天使》里我們都可以窺見一斑。而《一代宗師》卻是在追憶、記住一個逝去的武林。“我記不記得她, 其實并不重要。
對她來說,不過是一個過程。”《墮落天使》中莫文蔚飾演的女孩在與黎明飾演的殺手離別時,狠狠咬了他一口,要他記住自己,殺手答 應(yīng)了女孩的要求,同時響起了這句獨白。
王家衛(wèi)的視覺風(fēng)格源自他對文學(xué)的偏好和 對人文關(guān)懷的響應(yīng)。20世紀(jì)90年代,中國香港即將回歸祖國,文化認(rèn)同、身份認(rèn)同加上政治、經(jīng)濟(jì)等因素造成的焦慮、矛盾成為那個時代中國香港人民的集體經(jīng)驗。而王家衛(wèi)的影像用稍縱即逝、躊躇不定和曖昧不明的內(nèi)含特征回應(yīng)了人民想要擁抱歷史轉(zhuǎn)折和文化改變的欲望。慢動作、跳幀、重疊剪輯等都是王家衛(wèi)的慣用手法。運用這些技術(shù),王家衛(wèi)的電影經(jīng)常呈現(xiàn)出一種夢游般的狀態(tài),讓觀影者在一系列令人 陶醉、夢境般的圖像引誘下解讀導(dǎo)演訴諸影像的創(chuàng)作初衷,整個觀影過程仿佛做了一場夢, 而電影本身也平添幾分“催眠”特質(zhì)。而這也要求電影的觀眾具備高度的審美自覺,因為這種視覺風(fēng)格就是憂郁內(nèi)斂之美,看得見,摸不著。觀眾仿佛稀里糊涂,但導(dǎo)演卻高度清醒。觀眾與電影角色之間既親近又疏離,像是見到最熟悉的東西出現(xiàn)在夢中。在王家衛(wèi)的電影中,觀眾總能在光影享受中觀照現(xiàn)實,將生活中的事情看得更清楚,讓真實與虛構(gòu)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從《阿飛正傳》開始,到后來的《重慶森林》《墮落天使》《春光乍泄》,王家衛(wèi)的視覺風(fēng)格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但以發(fā)展的眼光來看, 從《花樣年華》開始,他的視覺風(fēng)格更趨向于在平穩(wěn)中尋找跳動的返璞歸真, 而到《一代宗師》時,這種特征已經(jīng)發(fā)展到極致狀態(tài)。
王家衛(wèi)的制作方法奉行“機緣”和實驗性質(zhì),隨機性比較大。他偏愛圖解的故事大綱勝過詳 盡的劇本。實驗性質(zhì)的情境、人物描繪與隱喻,取代了細(xì)致的腳本構(gòu)建,并在這些粗略未完成 的“劇本”中重新塑造情節(jié)。在制作前期,王 家衛(wèi)告知演員他們的角色和故事情節(jié),每一個 拍攝日都致力于發(fā)展并拍攝兩到三處場景,而王家衛(wèi)只在數(shù)天甚至數(shù)小時前完成戲份的設(shè)計、對白的編寫。經(jīng)常擔(dān)任王家衛(wèi)電影美術(shù)指導(dǎo)的張叔平則需要對場景構(gòu)建的連貫全面負(fù)責(zé),因此,張叔平往往還要擔(dān)任剪輯指導(dǎo)的工作,在影片后期制作時與王家衛(wèi)一道用各種方式整合影片,直至情節(jié)順暢完整。張叔平證實,他們經(jīng)常花更多時間討論究竟最后一場是否應(yīng)該作為開場,或者終場是否真的作為終場,而非決定哪一個特定的場景該被剪輯或再次剪輯。這種由不設(shè)限制的創(chuàng)作行為帶來的情節(jié)編排的后置和中國古代詩人在創(chuàng)作詩歌時斟酌字句的“推敲”相似,雖然看似影響了電影的制作進(jìn)度,但使得影片的基本敘事成為焦點。這種“倒敘中的倒敘”的觀點,在《東邪西毒》《2046》《藍(lán)莓之夜》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最精彩的當(dāng)數(shù)《花樣年華》,情節(jié)止于高潮處, 讓觀眾對“是我, ?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和我一起走啊”的中國式含蓄表白念念不忘,這一切也正是王家衛(wèi)電影背后的中華文化傳承。
作為一個沉浸在聲音與影像中的導(dǎo)演,王家衛(wèi)觸及觀影者的雙重感官以達(dá)到戲劇和表達(dá)的效果。除去影像之外,他賦予音樂特殊的重要性,只要考慮到王家衛(wèi)是一名電影題材的名作家,就不該忽略這一點。音樂是人類共同的語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溝通方式,它超越地域、語種,具有最大的兼容性。陳勛奇、梅林茂等作曲家曾為王家衛(wèi)的《東邪西毒》《一代宗師》《花樣年華》等作品進(jìn)行原創(chuàng)配樂。如果在王家衛(wèi)的電影里聽到了與影片時代、環(huán)境不符的音樂也不足為奇,這是王家衛(wèi)通過自己的音樂鑒賞能力,精挑細(xì)選地為電影找到合適的曲目來充當(dāng)配樂。如《花樣年華》里的上海老歌,以及《一代宗師》里的意大利歌劇。這種雜糅的音樂風(fēng)格調(diào)配像極了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通感”修辭方式。音樂為影片剪輯提供了更多調(diào)整節(jié)奏的可能性,擴(kuò)展了影片的 敘事空間,讓觀眾沒有脫離所處的時代,使得王家衛(wèi)的電影呈現(xiàn)出濃厚的后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使得影片在文化上、風(fēng)格上呈現(xiàn)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和多樣性。所以說,王家衛(wèi)能夠受到中外觀眾的喜愛不是沒有原因的。
說到王家衛(wèi)影片風(fēng)格的另一個重要層面, 就是那些出演過王家衛(wèi)電影的演員。人是各種感官的集合體,既接收信息,又傳遞信息,通過感官刺激的方式進(jìn)行影像信息的傳播,這便是演員需要做的工作。王家衛(wèi)的電影似乎有一 種啟發(fā)演員表演天賦、讓演員表演能力得到精進(jìn)的神奇魔力,比如演過《春光乍泄》之后的梁朝偉、演過《重慶森林》之后的金城武以及演過《阿飛正傳》之后的張曼玉,他們在影片中是那般迷人,表演是那般從容不迫、不動聲色、極具張力。要討論這一群人,一定繞不開梁朝偉。從《阿飛正傳》開始,梁朝偉幾乎參與了王家衛(wèi)的每部電影,除去他的演員合約簽在王家衛(wèi)的澤東電影有限公司這個原因之外,就是梁朝偉在王家衛(wèi)的特殊調(diào)教下,終于從明星變成了演員。《阿飛正傳》中,觀眾只在最后一場戲 看到了梁朝偉的表現(xiàn),而實際上整部影片中,梁朝偉承載的是另外一條線索的敘事。拍攝了很多素材,甚至于一個鏡頭重復(fù)拍攝27次。而 ?且王家衛(wèi)并沒有給出具體的理由,說明哪里的表演不對,只是讓梁朝偉通過不斷揣摩去進(jìn)入角色,這種不計時間成本的拍攝方式,旁人看來是一種“折磨”,但作為一個演員,有機會去慢慢演、慢慢體會,是非常難得的,如同有一個平臺,一直允許你犯錯,一直替你承擔(dān)試 錯成本。所以, 王家衛(wèi)的這種做法對演員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從海量的素材里挑選出來的,一定是最好的,這是對演員負(fù)責(zé)、對作品負(fù)責(zé)的典范。看似浪費,實則成就了演員,成就了自己。
放眼王家衛(wèi)高產(chǎn)的那些年,正是中國香港電影工業(yè)化的鼎盛時期,他的身上集合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商業(yè)營銷的矛盾,以及多種藝術(shù)種類相互兼容的矛盾。所以,如果說中國香港電影是一片產(chǎn)量巨大、類型繁多的電影城市森林,那么王家衛(wèi)就是在這片城市森林里流浪的吟游詩人。
王家衛(wèi)電影呈現(xiàn)出的文藝詩學(xué)和孤獨憂郁讓他的電影具備了獨特的美感。表面上看,這種美感表現(xiàn)為搖晃的畫面、濃郁的色彩、強烈的對比度以及精美的臺詞,實際上這些都源自創(chuàng)作者深邃的思考和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為每一部作品所做的工作讓王家衛(wèi)獲得了國際認(rèn)可,《花樣年華》《2046》《春光乍泄》《東邪西毒》蜚聲海外,王家衛(wèi)的作品成為得獎大戶。
王家衛(wèi)電影母題強于主題、情調(diào)勝于情節(jié)的特色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類型化電影概念所能界定的。他不滿足于講述男女之間的情愛故事,而是將時間、回憶、孤獨這些龐大的母題加在故事之上,借助這些來表達(dá)自己內(nèi)心的想法,所以,一般人看他只看表面,只會用愛情片來定義他的作品,但實際上這種根植于類型或類型的變異對影片風(fēng)格和結(jié)構(gòu)塑造產(chǎn)生的影響正是得益于王家衛(wèi)在文學(xué)方面的造詣,他將文學(xué)和電影高度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如果一定要給王家衛(wèi)的電影打上標(biāo)簽,他的電影 完全可以歸為作者型電影、感官型電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明的高度發(fā)達(dá)除了需要發(fā)達(dá)的經(jīng)濟(jì)作為強有力支撐外,更需要有高水準(zhǔn)、高價值的藝術(shù)作品來引領(lǐng)市場、教育市場。作為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需要有更高的藝術(shù)追求,把創(chuàng)作的眼光置于市場需求之上,由此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才能夠卓爾不群,獨領(lǐng)風(fēng)騷。王家衛(wèi)深諳電影之道,一直恪守自己的拍片原則,他從未拍過一部“爛片”或者純粹的商業(yè)影片,他像一個流浪在類型片這片森林里的吟游詩人,持匠人之心,借電影之實,傳遞人文精神。
當(dāng)今時代,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工業(yè)化發(fā)展日趨完善,在國際電影市場走出了屬于中國電影自己的發(fā)展道路。回望來路,我們發(fā)現(xiàn)王家衛(wèi)其實早就邁開了腳步,用全球化的思維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妙溝通世界。王家衛(wèi)沒有停下創(chuàng)作的腳步,近年依舊在拍攝新作,而他也遠(yuǎn)未到達(dá)自己職業(yè)生涯的終點,因此,我們依然可以借鑒他的作品風(fēng)格和創(chuàng)作理念,在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向著更高的目標(biāo)前進(jìn)。
[ 作者簡介 ] 吳治國,男,漢族,浙江人,供職于江西瑞可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畢業(yè)于江西師范大學(xué),本科,研究方向為影視編導(dǎ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