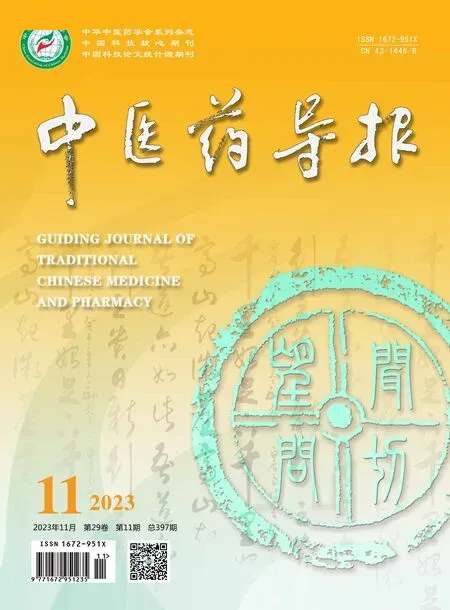認知翻譯學視角下《金匱要略》英譯的四維度識解研究*
王 薇,周艷紅,薛雙雙
(1.陜西中醫藥大學外語學院,陜西 咸陽 712046;2.陜西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陜西 咸陽 712046;3.陜西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陜西 咸陽 712046)
隨著“哲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神經科學、人工智能”等學科融合的譯學跨學科研究發展,“認知科學”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熟[1-2]。翻譯不僅是簡單語言形式的轉換,更是一種認知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是復雜且多維度的[3]。認知翻譯學是一門將認知領域和翻譯領域相結合的新興交叉學科。它是以認知心理學、認知語言學、神經分支學科為主要理論基礎的翻譯跨學科研究,研究對象多為譯者認知能力、心理活動及認知行為等[4]。因此,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適合解釋翻譯過程背后的動因和認知規律。從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認知語言學的日益發展,學界翻譯研究也越來越凸顯認知傾向,認知翻譯學的興起為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徑。認知翻譯學通過使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重點探索認知與翻譯之間的互動關系[5]。近年來認知翻譯學研究對象、內容、方法漸趨清晰,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表明認知翻譯學已發展穩定成熟[6]。目前認知翻譯領域中研究對象集中在文學翻譯,中醫典籍翻譯的研究仍然處于邊緣地位[7]。中醫學具有深刻的哲學與文化根基,這一點在中醫典籍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中醫典籍中的中醫術語反映了人與世界的不同體驗,是人與自然及疾病之間的理解和認知[8]。這與認知語言學中提倡人與世界的互動體驗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從認知翻譯學角度來研究中醫典籍的英譯(本文以《金匱要略》英譯為例),可以彌補中醫翻譯理論研究方面的不足。
1 識解理論與翻譯
翻譯是不同語言或語言變體之間基于符號轉換的文化活動。在翻譯的置換語境(displaced situation)中主體與主體、客體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所以翻譯之間是語言的轉換,是一種高層次的認知活動,即從一種識解方式到另一種識解方式[9]。因此從識解的角度看待轉換,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轉換的認知過程。美國語言學家LANGACKER R W 1991年在認知語法中提出識解(construal)的概念,指出人們具有用不同能力解釋同一場景的能力[10]。語言表達的內容不僅是概念相關的,也是人們識解內容的特定途徑[11]。不同的識解方式解釋一個特殊場景時,可編碼不同的場景方式構成概念化[12]。這也是識解最明顯的作用,即同一場景提供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對于相同的認知概念和內容,如果識解方式不同,就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語義[13]。王寅[14]提出識解不僅可以分析人類的主觀性語言層面表達,也適用于翻譯認知過程的研究。張艷等[15]運用識解理論對唐詩的翻譯過程進行認知研究,對不同英譯背后的認知機制進行了深度分析,提出從認知翻譯視角充分考慮漢語主觀性動詞,可以選用三義一體的動結式或結果義的英譯策略,從而有效避免唐詩譯文中意境的流失。
綜上所述,識解與翻譯的關系較為密切,認知識解的分析視角有助于描述翻譯語言轉換和意義構建這一過程。識解能夠為翻譯過程中采用的增譯、減譯和轉換等變譯策略和方法提供統一的解釋,從而有助于揭示翻譯過程背后的動因和認知規律。LANGACKER R W將識解的構成因素分為轄域、背景、視角、突顯和詳略度5個部分。王寅[16]認為可以將轄域和背景這2個因素合為一類,總結為4個維度。受到這4個不同維度的影響,不同譯者有著有不同的理解和認知,從而產出不同的譯文,而識解理論也可用于對其差異進行解釋。
2 《金匱要略》英譯研究的意義
中醫藥文化是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瑰寶,提升中醫藥文化軟實力迫在眉睫。在中醫藥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中醫典籍英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金匱要略》作為中醫四大經典之一,是我國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論述雜病診治的專著。雖然該書成書于東漢,但其所蘊含的理法方藥,在當今的醫療實踐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和臨床實用價值。原著載方共205首,臨床應用廣泛,為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清代尤在涇概括其為“醫方之祖,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17]。作為極具臨床應用價值的中醫典籍,《金匱要略》中記載了大量病證術語,涉及內科、外科、婦科等,對后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18]。由于該典籍中提及的中醫術語晦澀難懂,缺乏概念的共識性,英譯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阻礙[19],因此對該典籍英譯的跨學科、多角度研究有助于提高中醫典籍英譯事業的發展,提高對外傳播的質量[20]。
3 《金匱要略》兩個英譯本認知識解對比分析
本研究選取了《金匱要略》的兩個英譯版本,不同版本的譯本是由不同的“識解”因素構成的,但都遵循一個原則:準確傳達原文含義,最大程度上傳遞原文信息。本研究從識解的4個維度對羅希文《金匱要略》英譯本[21](簡稱“羅本”)和李照國《金匱要略》英譯本[22](簡稱“李本”)進行分析。
3.1 轄域與背景 轄域(scope)與背景(background)是指人們在理解某一事物或表達論述的過程中,激發出來的其他相關領域的概念或知識,以此來達到使文章被充分“識解”的目的。翻譯是對概念的復述,應當考慮概念所依存的背景和知識[23]。由于受知識儲備和文化因素等影響,各譯者在識解過程中,轄域與背景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沒有特意考慮,這一因素在無形中也影響著人們的識解,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理解為譯者在不同的轄域中激活了不同的概念域[24]。概念域由多個方面構成,在中醫術語翻譯過程中,可分為病因域、癥狀域、證型域、功能域等。在不同轄域下激活不同的概念域,即可產生不同的識解結果。譯者對原文背景和轄域的最大程度了解,有利于對認知對象的準確認識。
例1 問曰:血痹病從何得之?
羅本 Qusetion: What is the cause of arthralgia due to stagnation of Blood?
李本 Question: How is blood impediment disease caused?
對于中醫病證名的翻譯,譯者不僅要理解中醫病名的含義,還要有全局的觀點,理解整個中醫學理論體系[25]。“血痹”是以肢體局部麻木不仁為主癥,由于患者自身氣血不足,又外感風邪所引起的一種疾病。其基本病理變化為血行澀滯,痹于肌膚。對于“血痹”的翻譯,在翻譯時激活癥狀域、病因域和病理域,有利于更好識解這一中醫病名。羅本將“血痹”譯為“arthralgia due to stagnation of Blood”,選用了現代醫學的“arthralgia”關節痛,同時增譯了病因,在激活病因域的同時激活了癥狀域,有助于讀者更深層次理解血痹這一疾病;李本直譯為“blood impediment”,譯出了疾病最主要的含義,即血液流通障礙,與原文氣血運行不暢的解釋一致。
在全局觀指導下進行翻譯,譯者自身所儲備的轄域和背景具有重要作用。翻譯的重點在于能否通過譯文喚醒讀者的轄域,從而進一步對中醫病名進行充分認知。2位譯者都有著豐富的中醫學知識儲備,在理解血痹這一核心癥狀術語時,兩位譯者在概念域激活上都較為準確。
3.2 視角 視角(perspective),即譯者的翻譯角度。譯者對源語認知的角度不同,翻譯的結果也會有差別。選擇不同的視角,其實就是選擇不同的認知參照點。認知參照點的不同會導致識解結果不同[11]。“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人們觀察或者描述一件事物時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觀點或結論也會有很大差別。在翻譯中醫典籍時,譯者對于視角的選擇大多體現在譯語主語的選擇上。
例2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羅本 When the doctor palpates the patient in the epigastrium, he feels distention and pain. This indicates an excessive syndrome. A purgative such as Decoction of Greater Radix Bupleuri can be adopted.
李本 [Abdominal] fullness and pain under pressure indicates excess syndrome/pattern and should be treated by purgation. Da Chaihu Decoction(大柴胡湯,major bupleurum decoction) is the appropriate [formula for treating it].
此例選自《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并治》。羅本選擇了第三人稱“he”作主語,指代“the patient”,且在狀語從句中增譯了主語“doctor”;李本將癥狀作為主語,對應原文漢語表達省略主語的特點,從而避開選擇視角的問題。兩種譯法有各自的優勢,羅本選擇醫生的視角,符合原文張仲景“辨證論治”代表作的特點,增強了譯者與原作者、原作者和讀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性,也展現了醫學專著的特征。李本的譯文更加忠實原文,與典籍原文的中文表達習慣一致,讓讀者可以更準確地將原文中的表達和譯文對應。視角的轉換,可以滿足讀者的思維習慣和閱讀期待[24]。譯者在識解時考慮譯語讀者或遵循原文等因素,選擇不同的翻譯視角,可以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獲得不同的醫學信息。
3.3 突顯 突顯(prominence)就是適當地將某些事物的特點進行突出,以此達到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目的,即人們根據語言與客觀世界的關系來處理語言的一種方式。認知主體在面對同一情景時,會突顯不同要素,形成不同的描述方式和選擇方式[26]。在認知翻譯學研究中,突顯即指譯者在翻譯時,選取不同的翻譯方法,翻譯出源語重要的部分或者譯者想突出的部分。突顯可以讓譯語更加接近源語的認知參照點。要突顯的東西也是譯者認為重要的東西。好的譯本與譯者突顯的部分息息相關。譯者突顯的部分與原文重合度越高,譯文的真實性和可讀性就越高。
例3 風濕相搏,骨節疼痛,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未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羅本 Conflicting Wind and Humidity factors cause acute pain in joints, which impairs movement of joints due to serious referred pain. The pain is aggravated if pressure is applied. The patient is short of breath, perspires,avoids wind, is reluctant to remove clothing, and suffers from dysuria and a slight swelling of the body. Decoction of Radix Glycyr rhizae and Radix Aconiti Praeparata can be prescribed.
李本[When] wind and dampness contend with each other, [there will be symptoms and signs of] pain of joints with vexation, inability to stretch [the joints due to] spasmatic pain, acute pain when touched, sweating, shortness of breath, aversion to cold ,disinhibited urination, no desire to remove clothes, or slight swelling of the body. Gancao Fuzi Decoction(甘草附子湯,licorice and aconite decoction)[can be used] to treat it.
《金匱要略》作為學習中醫必讀的經典著作,既有中醫基礎理論的內容,也具有臨床學科的性質。其條文有方有癥,方與癥具有同等重要臨床指導意義。譯者在識解過程中側重于某一方面,就會產生突顯。該文本描述的是風濕的癥狀,羅本通過which定語從句來解釋風濕相搏所帶來的身體癥狀,增譯了主語(the pain和the patient)。同時其運用了轉譯的方法,將癥狀中的名詞短語“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轉譯動詞“The patient is short of breath, perspires,avoids wind,is reluctant to remove clothing and suffers from dysuria”,突顯了患者受風濕后癥狀的表現,將病與癥的關系敘述完整。李本則多用名詞短語的形式(sweating, shortness of breath,aversion to cold ,disinhibited urination, no desire to remove clothes),突顯了譯語與源語語言形式的對應,傳遞原文癥狀信息的同時強調源語中的語言形式。羅本在“識解”過程中強調《金匱要略》醫書的特點,能夠詳細準確地表達原文中的醫學信息;而李本則更加突顯術語在原文結構中的適配度,以及保留《金匱要略》中醫術語的語言特點,更利于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的完善。
例4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羅本 Skin-edema with the following symptoms and signs can be treated with Decoction of Radix Stephaniae Tetrandrae and Poria: edema in the extremities, edema under the skin and slight twitching in the extremities.
李本 Skin water disease, [marked by] swelling of the four limbs, [retention of] water qi in the skin and quivering of the four limbs, [can be] treated by Fangji Fuling Decoction (防己茯苓湯,the root of stephania tetrandra and poria decoction).
在翻譯皮水病這一病證時,羅本將譯語的語序進行了轉變,以with介詞短語作定語的句式,將方藥提前,將癥狀放在句尾,將這一條文中“皮水”的癥狀作為重點;為了突出皮水病水腫的表現,羅本在翻譯水氣時省譯了氣,直接用了“edema”替代,對應了西醫中的水腫癥狀,傳遞的醫學信息十分清晰。李本則偏向于遵循原文語序,未改變原文的句式,沒有進行突顯處理;而在處理中醫術語時,李本將水氣對應翻譯為“water qi”,突顯了中醫術語的譯者的話語權。突顯內容不同,讀者的閱讀體驗就不同,而且接收到的信息也不同。但翻譯時的突顯應遵循重合性原則,即突顯和原文的重合度越高,傳遞給讀者的信息就越準確。
3.4 詳略度 詳略度(specificity)也稱精度,指作者描寫某一事物或場景時的詳細程度。在翻譯中詳略度的選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翻譯過程中不僅要遵循原文,還要保證譯文通俗易懂、不贅余。關于詳略度的表達方式,語言可以用粗顆粒度(coarse-grained)和細顆粒度(fine-grained)兩種方式進行觀察[27]。觀察方式不同,語義強度也就不同。
例5 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之里,轂食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
羅本 Pathogenic factors of a clear and light nature will invade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dy, pathogenic factors of a turbid nature will invade the middle part of the body. The six climatic pathogenic factors will invade Exterior and seven emotional factors will invade the interior. Intemperance in eating will cause indigestion.
李本 Clear pathogenic factor (fog and haze) are in the upper and turbicd pathogenic factors (water and dampness)are in the lower. Major pathogenic factors attack the external while the minor pathogenic factors attack the internal.Cereal pathogenic factors that has entered (internal) from the mouth (causes) the retention of the food.
病邪各有特征,作用于人體后引起的疾病表現不同。此條文中的語言晦澀,很難直譯出來。兩位譯者都選取了細顆粒度的解析方式,通過增譯的翻譯策略,以高解析度重現場景。羅本將原文中的大邪、小邪識解為外感六淫和七情,所以英譯為“six climatic pathogenic factors”和“seven emotional factors”,翻譯得精確而細致;而清邪和濁邪分別指霧邪和濕邪,李本通過括號加注的形式[“(fog and haze)”“(water and dampness)”]詳細地闡釋了此概念的內涵語義,可以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病邪的特征。在處理穀飪之邪時,2位譯者采取了不同的解析模式。羅本選擇了粗顆粒形式,省譯了穀飪之邪及從口入的翻譯,整體意譯為“intemperance in eating”,同時宿食也直接用西醫中的“indigestion”消化不良的癥狀來譯,使譯文簡潔清晰;而李本則選擇了細顆粒的解9析形式,穀飪之邪直譯“cereal pathogenic factors”,同時宿食譯為“retention of undigested food”,并將穀飪之邪產生的場景進行細致重現,更加重視中醫文化層面的忠實表達。中醫典籍中有許多這樣文學化語言的名詞術語和語句,翻譯時考慮英漢語言和文化差異,遵循翻譯創造性的原則,合理選擇粗顆粒度和細顆粒度的方式,表達有詳有略,提高譯文接受度,可以實現譯文信息等值。
4 結語
翻譯是意義建構或概念化。意義建構或概念化是識解的結果,是識解化。因此某種程度上翻譯也是識解化[11]。譯者不同的識解方式,造成了不同譯文產生的結果。中醫語言醫哲交融,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交織,有些語言深奧玄虛、晦澀難懂,故譯者如何加工處理譯文需要研究其背后的認知過程。這是中醫典籍英譯研究中的重要發展。譯者的不同翻譯策略又體現了翻譯的不同原則。羅希文和李照國根據對中醫典籍的不同認知,激活了各自認知不同的轄域,從不同的視角,突顯強調的內容也有異同。受4個維度的影響,羅本更加偏向傳遞醫學信息,忽略了譯文形式與原文的對應,更符合英文表達習慣;而李本更加突顯了源語的語言特色,忽略了英文的句法結構,在最大限度地重構源語的語言結構、保留源語文化的同時準確傳遞了中醫典籍中所涵蓋的概念、術語等信息。譯者的識解因素造成了譯文的差異,且譯者的知識決定了其識解的能力,從而影響譯文的質量。因此譯者的中醫學知識儲備越豐富,對原文的識解就越準確、越透徹。譯者才能最大程度將中醫經典所包含的醫學知識和文化內容傳達給目的語讀者,促進中醫藥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
本研究僅通過文獻法進行分析對比,結論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后續應采用更加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探討,以期得出更為全面客觀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