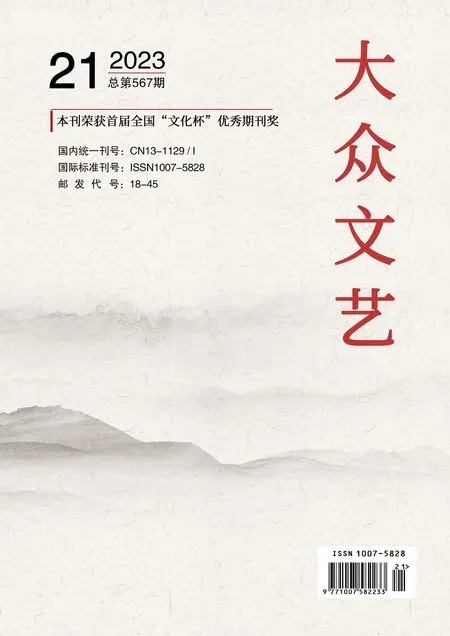淺析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宗教與非宗教意蘊
劉俊辰
(延邊大學,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133000)
狄更斯的《雙城記》一直是一個深受中外學者關注的研究熱點話題。然而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從現實主義的單一角度入手的。將狄更斯在這部作品中共同體現出的現實主義批判與人道主義關懷視為一種作家無法調和的內心矛盾,并且結合了狄更斯的生平將這種矛盾解釋為“他對生活困苦的社會底層人民的同情與憐憫;本人對上層階級的向往與憧憬”[1]之間的矛盾。然而如果從宗教與非宗教的多角度切入,作者所體現出的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就是不矛盾的。宗教的部分表現為作品洋溢的救贖意識及諸人物體現出的《圣經》母題。而非宗教的部分表現為作品獨特的“血描繪”和對暴力反抗階層壓迫的批判。而作者厚植文本的人道主義情懷則可以看成這兩部分的重合區域,充當二者的紐帶,既有宗教意蘊,又有非宗教意蘊,賦予了作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一、基督的救贖——拯救與被拯救
古希伯來文化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精神養分之一。《圣經》是這種文化的載體。相比于其他宗教著述,《圣經》最突出的特點是拯救意識。《舊約》中,耶和華第一次在世人面前顯露他的名時,就告訴世人:“我是耶和華,我要……救贖你們脫離他的重擔”①。《新約》中,耶穌在山上的寶訓里有“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②。《圣經?舊約》與《圣經?新約》的成書年代不同,作家群體也不同,但拯救意識是一以貫之的。狄更斯深受基督影響且諳熟《圣經》內容,在雙城記的宗教意蘊中,拯救意識處于核心地位。
作者為這部作品中的人物安排了若干對多向度的拯救關系,構成了作品的救贖關系譜。在這張關系譜中,露西小姐處于中心位置。露西小姐的形象切合《圣經》中“圣母”這一母題,正像許多中世紀圣母題材的油畫作品一樣,她是整個陰暗基調的《雙城記》中的一束光。金黃的頭發,潔白的皮膚,絕美的容顏,令世人為之傾倒。同時她又善良寬容而博愛,周身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她用女兒對父親的親情的愛拯救了年老而精神受到重創的馬內特醫生,令他重新恢復神智。又用愛人之間愛情的愛拯救了侯爵侄兒達奈先生,令他找尋到了真正的幸福。她用傾慕與被傾慕者之間復雜的情感拯救了卡頓先生,令他在無盡的頹廢與墮落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同時她又是被拯救的。忠實的銀行辦事員洛里先生和達奈先生幫助她找到了自己的父親馬內特醫生,實現了一次拯救。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后,恢復神智的馬內特醫生以其十八年巴士底獄牢獄之災的經歷在反抗軍中獲得了崇高的聲望,多次挽救了眾人,這是二次拯救。卡頓犧牲了自己救出了身陷絕境的達奈,間接地拯救了露西,這是三次拯救。其中卡頓與達奈之間的拯救關系又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二者本是情敵關系,而且卡頓在初識達奈的時候就表示“我很不喜歡你”。他覺得二人唯一的相似處可能就在于長相。一方面卡頓是“老貝利”當紅律師斯特萊福的助手,是一條被隱藏在“老虎”背后的“豺狗”。他雖然才華橫溢但總在幕后工作。長期的抑郁不得志使他總是通過酒精麻痹自己,“散亂的頭發”成了標配。另一方面達奈是隱姓埋名來到倫敦的法蘭西貴族后裔,做法文教師謀生。俊朗的容顏和優雅的風度受到了馬內特父女的一致認可,同時也是一眾追求者中露西小姐唯一青睞的。二人構成了文本的“雙城”隱喻。就像是硬幣的兩個面一樣相貌神似,然而一光一暗;一個朝氣蓬勃,一個暮氣沉沉;一個嚴謹正派,一個玩世不恭的特質卻又迥然相異。但是在深層價值觀念上兩個人又有驚人的一致性——拯救意識。達奈為了救昔日的老管家拋下倫敦的安樂窩重回動蕩的法蘭西結果身陷囹圄。卡頓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做一件比我所做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毅然替換下達奈,做了斷頭臺上的“第二十三個”。在拯救達奈的同時,也實現了自救。
此外,體現在馬內特醫生、達奈、卡頓等人身上的“復活”意識也極具宗教色彩。一次救贖代表著一次“復活”。復活在《圣經》中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指向。上帝之子耶穌為救世人被釘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復活代表著新生。馬內特醫生坐了十八年監獄神志恍惚,只會在昔日仆人德發日的閣樓上做鞋,經女兒的拯救后得以重獲新生。達奈與卡頓之間的拯救也代表著二人的“復活”。卡頓先生在赴死前不住地重復耶穌的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也直接揭示了這一行為的宗教意蘊。這樣的復活又暗合《圣經》中耶穌受難這一母題,為作品增添了神圣的光輝。
二、現實的殘酷——壓迫與被壓迫
《雙城記》的非宗教意蘊主要體現在作者為我們構筑的法國大革命的醞釀及爆發這一歷史藍圖上,是飽含現實主義批判意識的。在這一歷史藍圖中,作者又格外偏愛對鮮血的描繪,這股鮮血有貴族壓迫平民時平民流下的血,也有大革命發動后貴族流下的血。是壓迫者的血同時也是被壓迫者的血。作品一開始寫到德發日夫婦的酒館打翻了一桶葡萄酒,引得圣安東的貧民們哄搶的場景,首次將鮮紅的葡萄酒和鮮血聯系到了一起。底層人因為長期的貧困根本喝不起酒,在哄搶葡萄酒的時候“就好像發狂的野獸”一般,營造了一副人間煉獄的景象。同時也為下文埋下了伏筆,因為在大革命爆發后,憤怒的底層人民真的將鮮艷的紅酒變成了鮮血,讓它從貴族的脖頸上噴涌而出。血的象征意味也就更加明顯了。
大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間爆發的,作者用了冗長的篇幅為大革命的爆發做了鋪墊。我們可以看到侯爵為了滿足片刻的淫欲殺害了佃農女孩一家,女孩的哥哥反抗后被刺身亡在他們看來也只不過是“一條普通的小瘋狗!一個農奴!他逼我弟弟拔出劍來,我弟弟就一劍把他刺倒了——像一個紳士那樣”。貴族的車馬在城鎮里壓死了一個孩子,也只不過是付一個金幣了事。“你們不是天天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嗎?”巨大的階層矛盾使得民間蓄積了一股可怕的復仇力量。德發日太太每天都坐在她的椅子上編織,她織的每一個花紋都代表一個她想殺掉的貴族,德發日太太是民間復仇力量的具象化人格化。這股復仇力量在憤怒的貧民攻占巴士底獄以后達到了頂點,“四處都在起火”,法蘭西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街上的革命軍甚至可以因為一個路人衣著華麗些就把他送上斷頭臺,革命后的共和國完全浸泡在了鮮血里。
不同于一般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并沒有完全站在所謂“人民立場”上對革命進行歌頌,對貴族進行毫不留情的否定,而是站在了一個冷靜的“第三者”立場上描繪了這場血腥沖突中的雙方。雖然他以犀利的筆觸控訴了貴族對平民犯下的罪行,“我從未見過這種受壓迫的意識,像火似的噴發出來……我見到它潛伏在這個快死的孩子心里的時候,才見到它爆發出來。”但當平民起義以后,他又以同樣犀利的筆觸控訴了“革命”的人民,“自由、平等、博愛,要么死亡”的法蘭西犯下的罪行。我們在狄更斯的筆下看到了失去理智的、憤怒的、扭曲的、像野獸一般的人群,院子里的磨刀石會一直工作到拂曉,每一個革命軍身上都沾滿鮮血。“他們,由于長期受到那可怕魔法的迷惑,已變成了野獸,在紅旗下,在宣布了他們的國家處于危急之中后,動亂不已”。與之相對的是被關押的貴族顯得優雅、從容、冷靜。被復仇烈焰吞噬最深的德發日太太最后也因復仇而死,保留了一絲人的理智的德發日先生得以存活,這種藝術處理也非常耐人尋味。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雙城記》中的現實主義意蘊并不是教唆人們去“革命”,而是揭示了一個“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樣一個公理。作者極度憎惡掌權者對弱勢群體的壓迫剝削,但也不推崇被壓迫者的暴力式革命。《雙城記》寫了倫敦與巴黎兩座城市,作者極力渲染巴黎發生大革命以后的慘狀也隱隱地規勸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統治者不能再繼續盤剝人民,否則也會迎來法蘭西貴族同樣的結果。同時也告誡英國人民暴力革命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處境,因此不可以暴力革命。這種崇尚非暴力仁愛思想的底層邏輯就是作者所秉持的人道主義原則。這種原則也充當了《雙城記》宗教與非宗教意蘊之間的橋梁。同樣的原則我們也可以在與狄更斯同時期稍晚一些的另一位大師——列夫?托爾斯泰身上見到。
三、人道的光輝——憐憫與被憐憫
人道主義指一種強調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的思想體系。在《雙城記》中,這種肯定體現為作者超階級的憐憫。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種“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惻隱之心。而這種憐憫就接近我們所說的“惻隱之心”。
弱者與受苦難折磨者是值得同情的,這一點與基督教義中的拯救意識接近,然而卻并不一致。基督教講求“因信稱義”。只有虔誠地篤信上帝才能成為義人,成為義人是得救的前提。當審判日降臨之時,經過天使的揀選,一切義人將升上天國,而不義之人將墮入地獄。所以不義之人也是不值得拯救的。然而在《雙城記》中,狄更斯的憐憫卻無私地施與了所有人。他對處于壓迫之下艱難的平民保有深切的同情,但這并不妨礙他同情一個馬上要被處死的貴族稅務官:“如果這個七十多歲的不幸的罪孽深重的人,還不明白這個理由,只要他能聽見這回答的喊聲,就會打心眼里明白過來”。盡管他曾經視人民為牛馬,在憤怒而扭曲的人潮面前,這個貴族稅務官也只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兒。在狄更斯看來任何剝奪他人生命的做法都是不可容忍的,包括革命者以革命的名義剝奪這位貴族的生命。
這種人道主義的二律背反也集中體現在德發日太太身上。德發日太太是一個頗具現實主義悲劇性的人物形象,同時也是在作者筆下完全喪失了憐憫心的形象。她全家被侯爵屠戮殆盡,以遺孤的身份在圣安東隱姓埋名數十載,她存在的全部意義似乎就在于向貴族復仇。作者對這個可憐的女人依舊施與了同情,然而德發日太太的復仇卻在大革命開始后一發不可收,逐漸走向失控,她本人也走向瘋狂,甚至不斷地牽連無辜。她完全不念及馬內特醫生昔日救人的情分起訴了達奈,使得本來已經脫險的達奈又一次墜入絕望的險境。甚至在得知露西一行人可能會逃走之后,決定背著德發日先生處決掉這些人。德發日太太的冷酷甚至讓自己人感到害怕。同為革命軍的雅克三號“出于極度的畏懼,才對她那樣尊敬。”丈夫德發日先生也覺得她做得太過火,然而她卻認為“德發日無疑是一位好同志,然而他卻不可原諒的同情一個貴族!”在作者第三人稱的敘述中,“她絕對沒有憐憫心。即使她曾經有這種美德,也蕩然無存。”這樣一個完全沒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革命領袖最終死在了追擊露西一行人的路上,而且是被自己的配槍打死的。這樣的結局無疑蘊含著作者的個人情感,反向論證了《雙城記》的人道主義立場。
四、結語
我們可以看到,僅僅從某一個視角來審視《雙城記》都是片面的。這部作品由宗教成分、非宗教成分以及人道主義底色三個部分構成。這同時也解釋了作者在若干對人物關系中表現出的看似矛盾的立場。
然而我們還是要明確一點,《雙城記》蘊含的這種復雜意蘊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作者看來,只要每個人都秉持著仁愛之心,世間就不會有苦痛不會有壓迫,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幼稚的觀念。作者“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對貧民表示同情,對貴族表示痛恨。但是在革命勝利之后,狄更斯又對貴族表示同情,并反對農民階級的武裝反抗。”[2]每一場暴力的社會變革都是舊社會積重難返的產物,是階層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的集中爆發,這種血腥的沖突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一路走來,有權勢有地位者不會良心發現地停止剝削下層民眾,即使偶發善心也只是在不觸及自身利益的范疇之內。下層民眾也不會停止怨恨當權者的剝削,如果民眾沒有反抗,不代表民眾不怨恨,只代表民眾的怨恨還沒有積蓄到暴力反抗的程度。從這一點來看圣安東區人民的暴動是必然的,巴士底獄的淪陷也是必然的,這是封建法國蛻變成現代法國不可避免的過程之一,田園牧歌式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繼而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屬于工業的時代。但這并不代表狄更斯的觀念就毫無可取之處,心懷仁慈,博愛地處事,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是值得贊揚的。
注釋:
①引自《圣經?出埃及記》.
②引自《圣經?馬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