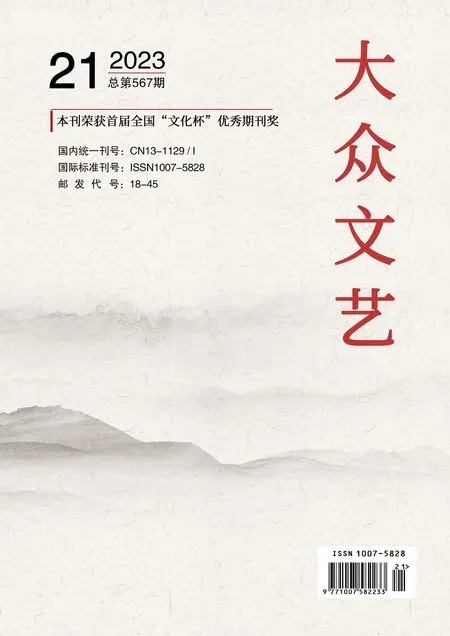新時代內地詩歌題材紀錄電影的鄉村想象
黃心怡
(首都師范大學科德學院,北京 102602)
長期以來,我國電影創作以持續的鄉村想象,呼應著鄉土中國的城鎮化變遷。雖然鄉村題材仍然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但是近年來中國銀幕上仍然建構起了各具特色的鄉村景觀。在濃厚的商業化語境下,中國銀幕的“返鄉書寫”發出“鄉關何處”的感嘆,抒發著中國不同階層的鄉愁與鄉怨,成為世界獨具特色的中國“鄉村電影”類型。更加重要的是,當鄉村題材和詩歌題材在紀錄電影中交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此類紀錄片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景觀。
中國是詩歌大國。近年來,中國創作出大量的詩歌題材的紀實類影視作品,對于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積極作用。具體到鄉村來說,中國擁有龐大的農村人口,城鄉發展不均衡,城鎮化程度不高,處于城鄉裂縫中的農民詩人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和現實,《我的詩篇》(2015年)和《搖搖晃晃的人間》(2017年)等紀錄電影給出了開創性的回應。
出于論述的需要,本文主要選擇《我的詩篇》和《搖搖晃晃的人間》兩部院線紀錄片作為研究對象。它們率先聚焦在當代中國農民詩人的群體之上,采用現實主義藝術手法,揭示城鄉新型的權力空間關系,抒發當前農村“田園水鄉不再,城市無處為家”的家園失落之痛;同時,突出農民詩人主體性,讓農民通過詩歌表達社會變革之下自身的情感和思想;但是,隱藏在影片語言結構中的過度商業化和精英主義視角也頗值得探討。
一、異鄉人:無處為家的痛感
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城市在經濟上的優勢導致各種資源向城市集聚,城鎮化本質上演變為社會資源重組與社會秩序重構的動態過程。“農村不再是歡欣鼓舞的農村,而是動蕩不安的農村、易于失衡的農村。”②因此,城鄉之間的文化裂痕日益加劇,“農民逐漸淪為經濟和文化方面雙重弱勢的群體”,③城鄉之間的空間關系成為權力斗爭和文化碰撞的重要表征。
在空間政治學的視野中,城鄉空間不再是山水與高樓的自然場所之別,而是政治、經濟與文化觀念之間文化權力對抗的場域。城鄉之間“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單面的政治(強者壓迫弱者,弱者爭取自身的地位),而是延展到對于人的豐富性和人的權力的多面性的強調”。④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鄉村題材影視作品對中國當代城鄉中的空間政治進行了深入展現。其中電影作品既有《血色清晨》(1992年)刻畫的鄉村“死地”,也有《暴裂無聲》(2018年)呈現的西北“灰土”,還有綜藝節目《向往的生活》和李子柒自媒體營造的田園鄉村。而本文論述的詩歌題材紀錄電影刻畫的鄉村不再是兇險與田園的兩極劃分,而成為農民心靈的異托邦。對于農民詩人來說,他們面臨的是尷尬的現實處境:一面是牧歌式鄉村的崩壞,回不去的故鄉;一面是無處為家的心靈漂泊的陌生都市。
這種尖銳的現實沖突在電影《我的詩篇》中表現得尤其強烈。本片結構于城鄉空間對比的基礎之上,空間成為承載人物情感和心靈的心理場域。影片注重展示城鄉空間的差異,在緩慢的影像中對于空間進行描繪。對于城市空間,影片著力刻畫城市的冷漠、疏離和遙遠。影片開場就是都市的摩天大樓的遠景,飛機劃過天空,一個普通的小院內一場詩歌朗誦會正在舉行,在烏鳥鳥登場朗誦之后,影片剪輯進大雪紛飛的城市寒冬的冷冽景象。在片名“我的詩篇”之后,工人的勞動空間通過黑白畫面、缺乏生氣的流水線和產品的長鏡頭與許鴻志的朗誦交叉剪輯在一起。陳年喜幽暗的工地、朝陽門地下通道玩滑板的都市少年與討債民工的對比、鄔霞住了十幾年“一朵花都沒有”的翠景花園以及她攜家人遠觀彼岸的香港、烏鳥鳥在求職未果之后躑躅而行在地鐵里不知向何處去以及富士康員工宿舍的鐵網圍欄等都在進一步強化詩人眼中的都市空間。
對于鄉村空間,詩人們既無法找尋自然意義上的田園山水,又處于代際隔膜之中,面對丟失的傳統文化無處安放鄉愁。影片的首次鄉村空間出現在彝族充絨工吉克阿優打工七年首次回四川老家過彝族年的路上。遠山寂寥,橋下河水干涸,簡陋的木屋是他的老家,這些空間均非傳統文藝描繪的田園水鄉的烏托邦。吉克阿優對兒子用普通話說,“你是一個彝族人”,他在用最后的堅持無力地挽留慢慢丟失的族群意識。許立志頂著壓力瞞著家人,詩人的理想并不被父親理解。父親在悲傷之余說,寫詩沒有用處,技術才是掙錢的路子。正如烏鳥鳥的《家園狂想曲》所言:牛徹底退出了耕耘史,靜靜地為餐桌養育牛肉。祖傳的游戲,正在孩子們中間消失。
而另一部電影《搖搖晃晃的人間》雖然聚焦在詩人余秀華的自我和成長上,但是城鄉空間的對比仍然醒目可見。余秀華初到北京,車窗外高聳的寫字樓、在香港接受采訪之余她面對都市繁華夜色的“惶恐”、在星級酒店躺在沙發上孤獨睡去、離婚之后獨自坐在酒店的玻璃窗前望向窗外高樓……,這些影像無不是在揭示情感困頓中的余秀華的孤獨,也在揭示農民身份的她對于突然面對的陌生都市的緊張與未知。所以,影片中余秀華面對大海說“害怕”而不敢前行,也在隱喻余秀華對于未來的人生的不確定性。
影片通過余秀華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搖晃”來表現她在兩種異質空間中掙扎。可以說,城市空間中的新書簽售會、詩歌研討會、媒體錄制節目等空間在表達他的緊張和惶恐的心理;而在農村空間,她洗衣吃飯飼養兔子、和父母斗嘴、發脾氣、吵架、夜里聽廣播、奔走于鄉間小路、安靜地寫詩則是余秀華真實的鄉村生活狀態,傳達著鄉村生活的自由、真實和回歸。城鄉兩個異質空間的并置,傳達出詩人真實的內心世界、一種詩人獨有的對于世俗的超越性。
頗耐人尋味的是,影片對于余秀華家庭之外的村莊只有自然場景的展示,對于村民鄰里關系沒有直接涉及。父母只是擔憂村民對于余離婚的非議,“這個(離婚)不好辦”。農村是“熟人社會”⑤是一個不爭的社會現實,余秀華的離婚在村子里產生的效應可想而知,她對于殘存在鄉村中文化偏見的態度也不言自明。余秀華雖然自幼生活在農村,但是,精神上和行動上都是文化偏見的強者和反抗者。所以,余秀華對于鄉村的感情是復雜的,無法把她放在“田園鄉村”的簡單想象中。
總之,兩部影片通過城鄉空間對比,捕捉了城鄉關系的裂變。詩人在故鄉與異鄉之間掙扎而心靈無處安放,既無法做到山水原鄉,也做不到精神還鄉。異鄉人的身份承受著新時期以來城鎮化進程中無處為家的痛感。
二、詩人的主體性
千百年來,詩歌主要掌握在知識分子手中,普通勞動者只能被詩歌表達,而不能表達自己。因此,農民詩人本身即帶有沖破語言霸權和對抗現實的雙重意義。如同美國漢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認為的那樣,中國工人詩歌有為“沉默的大多數”證詞的意義,她認為工人詩歌具有揭示社會現實、時代精神和個人思想的能力,是一種生動的創造。⑥
新時代以來,《我和我的家鄉》等新主流電影開始變革城鄉之間的“富有和落后”的單純從經濟元素來判定的二元對立思維,開始關注新時代下農民采取切實行動,振興鄉村回饋土地的新風尚。同樣,《生活萬歲》(2018年)、《出山記》(2018年)和《人間世》(2022年)等紀錄片開始關注農民的精神、情感和生命觀,形成“有聲音”的農民堅韌精神的影像志。
與以上作品不同的是,《我的詩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主人公既是農民,也是詩人。“詩言志”是我國詩歌的本質特征。影片中,詩歌成為電影表達的既有文本,成為人物情感和思想的載體,可以直接發聲表達底層生活。在城鄉關系裂變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多重交織下,農民詩人被賦予太多預期:詩歌是家園失落的見證,又因其高度精神性構成對資本邏輯和城鄉差距的無言抵抗,進而促進階層之間和諧對話的樂觀前景。
詩人的主體性首先表現為詩人鄔霞對于“農民工”命名合法性的質疑。在深圳安家生子的鄔霞說道,“我們是農民,我們來到這個城市又叫農民工,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鄔霞對其身份歸屬產生了思考。這種身份撕裂在彝族青年吉克阿優身上更加強烈。年幼的兒子已經不會彝族語。雖然他在返家祭祀中再穿彝族服飾,但是面對七年未見的父親,父子間只能長時間的沉默。銀幕上印出他的詩句:我謊稱自己仍然是彝人,謊稱晚輩都已到齊,但愿先祖還在,還認得我們穿過的舊衣。
詩人的主體性還表現在女詩人面對鏡頭大膽表達自己的女性情感。鄔霞說“翠景花園一朵花都沒有,我們住了十幾年”“工裝顯示不出身材”“我最喜歡吊帶裙”“陌生的姑娘,我愛你”“夜里到洗手間穿著裙子轉一轉,幾分鐘感受穿裙子的快樂”。鄔霞的堅強和希望在詩歌《爬山虎》中如此體現:就算是有一塊石頭壓著我,我也要像花啊草啊,倔強地推開那塊石頭,昂起我的腦袋,向著陽光生長。她還寫道:我不會訴說我的苦難,就讓它爛在泥土里,培植愛的花朵。(《我不是沒有想到過死亡》)。
這些大膽的女性表達在《搖搖晃晃的人間》中達到激烈的程度。鄔霞在用詩歌表達對于家鄉、工作和情感的細膩感受,而余秀華卻在詩歌和生活上同時進行著一場語言和家庭的革命。余不僅用詩歌對抗庸常的生活,而且打破世俗的偏見,親自動手解放了自己。影片把故事主線放在余秀華離婚上,被觀眾戲稱為“余秀華離婚記”。這種處理雖然受制于內容的戲劇化而容易流于膚淺、很難深挖詩人背后的社會因素,但是也不失為揭示女性主體性的一種敘事策略。
以上兩部紀錄片鄉村和城市的交匯,讓沉默的農民發聲,叩問了農民在時代洪流中的生存窘境,賦予詩歌的現實對抗性和精神超越性。人民網如此評價《我的詩篇》,該片“以詩言志,為同命運的產業工人、農民工立言,為底層的生存作證,形成一部反映基層工人現狀的現實影像。”⑦
三、精英主義視角
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進入啟蒙時期,以《黃土地》為代表的鄉土電影總是把農民置于“被觀看”“被拯救”的位置。⑧誠然,《我的詩篇》等作品具有社會現實的揭示意義,但是我們無法忽視其中的城市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視角。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影片在深入揭示詩人個體和急劇變化的時代等方面,難免有美中不足之嫌。有時,詩人們在“他者”的目光下“被表達”,艱難的“詩歌發聲”成為略帶遺憾的“沉默的詩篇”。
(一)被抽離的現實
現實題材的紀錄片單純復制生活是不夠的,更應挖掘背后的社會深度。真正的藝術形象需要思想和形式的有機統一,缺少任何一方都會削弱藝術力量。所以,工農題材不僅要傳達工農的心聲,更要思考其中的社會根源。單就農民詩人來說,撕裂的身份對于詩人意味著什么,詩歌能否構成有效的抵抗等等都是有意義的視角。
《我的詩篇》以六位詩人為主人公,以詩歌朗誦與日常城鄉場景交叉剪輯,著意刻畫詩人群像,人物平均用力,貪多而雜亂,社會現實淺嘗輒止。離開了社會現實,人物難免被懸空;缺乏鮮活的人物形象,觀眾自然無從獲得同樣的情境與人物共情。同樣,《搖搖晃晃的人間》選擇了“離婚”的故事線,增強了故事性卻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詩人鄉村生活中的物質和心靈的雙重困境,忽視了更豐富的人物現實處境。
(二)抒情的尺度
羅丹認為:“藝術就是情感”,但是不要忽視:電影故事是抒情的基礎,要在“故事中追求抒情性”。⑨在人物懸空和現實抽離的情況下,失去基礎的抒情可能會演變為煽情。《我的詩篇》的六位詩人每人都有動人的故事,但是由于每個詩人都缺乏深入描繪而淺嘗輒止,影片只能求助抒情來助力。詩人的故事沒有深入即被切換到“詩意”的抒情畫面,難免使得抒情失去敘事的根基。
當紀錄片的抒情表達壓過現實觀察和思考的時候,拍攝對象就變成藝術家手中的提線木偶。農民詩人成為消費主義揉捏的悲情材料,事實上迎合了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感動。在這個抒情泛濫的時代,脫離現實的抒情會成為一種文化消費的商品而失去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他者的目光
“為底層發聲”是農民題材電影的社會責任和擔當,但是農民不是弱者,城鄉之間也絕非“拯救和被拯救”的關系。所以,放下精英主義的“他者”視角、拋去獵奇和刻板成見尤其重要。
《搖搖晃晃的人間》正如它的短片《一個女詩人的意外走紅》那樣,過于強調農民詩人的特殊標簽,無意中迎合資本對于“農村”和“殘疾網紅女詩人”的獵奇心理。其實,余秀華的婚姻固然不幸,但是余不是弱者,她才是生活的強者,并不需要影片中的“你不怕,我也不怕”的男性視角來獲得安慰。
可見,農民詩人在紀錄片中擁有了發聲的機會,但是往往依舊被資本、城市精英、男性視角和消費主義聯合鉗制,很難徹底改變“被表達”的命運,形成詩人話語、社會現實以及“故鄉”與“異鄉”多重分裂的特征。
四、結語
近年來,我國涌現出眾多農村題材的優秀文藝作品,探索著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文藝路徑,特別是農民借助新媒體短視頻的便利,雖然目前尚處于眾聲喧嘩狀態,畢竟農村由被表達的對象逐漸轉變為鄉村話語的主體。未來對于如何表達農民的真實聲音,讓農民“記得住鄉愁”,我國已經從國家層面進行了戰略性的頂層設計。如何消除城鄉隔膜和文化偏見,突破資本操控,如何增強“人民電影”屬性,農民詩人紀錄電影在城鄉空間、詩人主體性以及文化困境等方面做出摸索,為未來更加真實、豐富和平等的鄉村想象提供了改進空間和無限可能。
注釋:
①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6.
②孫寶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鄉土電影題材與形態略論[J].聲屏世界,2018(05):14-17.
③孫衛華,孫蕾.當代影視劇與農民審美形象的變遷[J].當代傳播,2009(04):74-76.
④劉子桐,陳祖君.空間的政治: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1) :71-74.97.
⑤賀雪峰.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J].政治學研究,2000(03):61-69.
⑥[美]賀蕭.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張赟,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⑦眾籌觀影:呼和浩特首映工人紀錄片《我的詩篇》[EB/OL].人民網(2016-08-14)[2022-11-03].
⑧戴錦華.不可見的女性: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與女性的電影[J].當代電影,1994(06):37-45.
⑨孟君.“志”與“辭”:中國小城鎮電影的抒情美學[J].民族藝術研究,2022,35(04):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