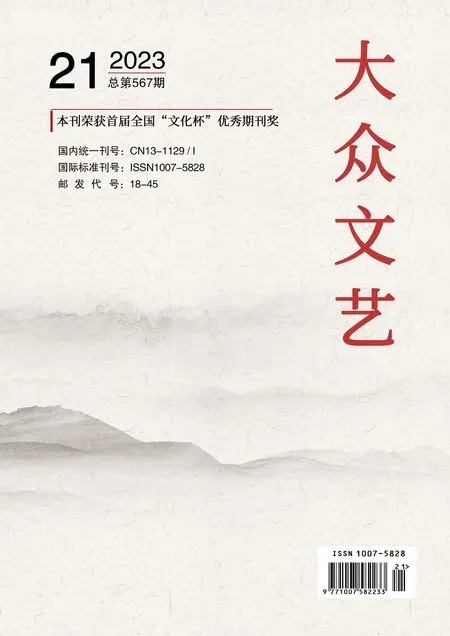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打破視域枷鎖”
——高校美術課堂寫生教學策略改革
單思穎
(淮陰師范學院,江蘇淮陰 223300)
赫伯特?里德曾說過:“整個藝術史是一部關于視覺方式的歷史,關于人類如何觀看世界所采用的不同方法的歷史。”[1]從學科概念的方面來說,“美術”門類豐富產生大量以觀看為欣賞方式的作品,所以更趨向是一種“視覺藝術”,此處的“視覺”不僅限于作為欣賞者的閱覽觀看,藝術創作者在進行例如繪畫等視覺藝術學科行為之前,同樣要對創作對象進行審視“觀看”,這是一個前置性的命題。通過對于一階段的高校基礎寫生課堂教學,筆者發現經歷美術高考的洗禮,大部分學生并不具備繪畫基本“觀看”的能力,甚至尚未產生“觀看”的意識與觀念,由此現象產生了一系列的分析,并結合寫生課堂實際教學策略進行討論。
一、視域的“枷鎖”
寫生課程開始之初,考慮學生們經歷美術高考的洗禮對于常規靜物已失去新鮮感甚至產生疲憊與厭惡感,我采用了學生自主選擇寫生對象的方式,讓學生在靜物室、校園、寢室等等生活場景中收集寫生對象,從而產生繪畫初始的興趣與欲望。然而通過一階段的課堂教學,我發現學生對于寫生的對象并不“感興趣”,大部分寧愿“埋頭苦畫”,也不愿多抬頭看一眼,甚至距靜物臺“千里之外”做個“角落工作者”,我將此現象稱為“盲畫”。藝術創作者如果不具備會觀察的眼睛,“眼不盲而心盲”,那么就無法賦予藝術作品以生命,是一種莫大的悲哀。對此現象我開始覺得好奇與詫異,覺得學生沒有參照怎么還能畫的“津津有味”,后來通過觀察發現有無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學生將寫生對象育下的習畫歷程,作畫步驟與思維習慣已然形成。“默寫”是美術高考許多院校的考題要求,從畫面的構圖布局到靜物或人物的形態結構、明暗關系、色彩冷暖甚至筆觸走向都依靠大量拍照后直接參照手機里的照片進行描繪,第二種是給寫生對象大致定形后直接揮揮灑灑自己“頭腦中的物象”。那么這種“物象”從何而來,思考下這顯然來自學生受以往應試教育反復的練習背誦影響,導致學生繪畫的思維方式形成了“名詞記憶”:所謂“蘋果”是什么色彩,“女青年”“男中年”是什么樣貌。
學生面對熟悉的寫生對象頭腦中產生已有固化的藝術圖像,這些描繪對象好像失去了個體差異性,蘋果永遠是那一個蘋果,桌布永遠是那一塊桌布,不會因為他是棉麻還是綢緞質地而有所改變,就好似大眾熟知的一種識別障礙癥“臉盲”映射在了我們的藝術創作之中。而對于不熟悉的寫生對象好一點的情況是學生由頭腦中這些固化的圖像碎片進行拼湊描繪,如在塑造靜物牛角時學生知道結構與明暗可以參考已熟悉的圓錐圓柱體,但卻忽略了觀察牛角本身的質地與紋理,有“形”而無“神”;同樣如寫生人物塑造手臂與腿部時造型與明暗根據固有經驗參照圓柱體而忽視了人體結構中一些微妙的骨點轉折,導致人物肢體呈現出僵硬怪異類似“石膏假人”的姿態;如無論寫生教室里光線如何、不同時間段光色冷暖如何變化、光源數量多少來自什么方向,塑造出的人物臉部永遠是一種明暗、一種色彩。壞一點的情況則是學生不知怎么表現,面對陌生的對象茫然無措“不會畫”,有些甚至“無視”“跳過”“干脆不畫”。寫生課程重在構建自我視覺體系,發展對于物象的直觀感受與自主體悟能力,諸如此類現象導致學生對于寫生對象缺乏觀察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從而對于寫生課程甚至繪畫創作失去興趣。藝術創作者如果對于描繪的對象沒有基本的創作欲望與熱情,那么可想而知藝術作品也如流水線上機械生產的批量產品,雖然技術水平過關,基本質量有保證,但早已失去了本身應有的鮮活與生命力。
所以高校在設置低年級美術課程時大多將寫生課程作為其中主要組成部分,目的就是重塑和建構學生繪畫時最基本的觀看方式,打破學生頭腦中受應試教育影響帶來的固化思維模式。
二、重塑寫生“觀看方式”
解決了“為什么要‘看’”的問題后,學生面臨著寫生中最困難的一個問題“不會‘看’”,即“怎么‘看’”與“‘看’什么”。
關于“怎么看”的問題,我們的傳統藝術理論其實早已給了答案。南朝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出“含道映物”“澄懷味象”的觀點,前者大意為在我們反映自然物象時,應遵循自己內心的道理與法度,有自身完整的主觀境界,后者大意為我們應澄清胸懷,蕩滌雜念,以純凈無瑕的目光去體味客觀物象。兩者意味一脈相承,都是對于我們作為藝術工作者在進行實踐創作前的基本要求,前者“含道”即可理解為創作者需要有自身明確的觀點與表現的目標,后者“澄懷”即可理解為創作者要用純粹的目光去審閱觀察創作對象。這兩個詞組顯然已明確解釋了“怎么看”的辦法:“目標”與“純粹”。
同樣“看什么”也就是最基本的觀看對象的問題,明確這一點學生首先要清楚自身的創作目的,即上文“目標”的繪畫具體涵義:畫面主要想表現什么?想要達成何種效果?實現什么目標?在寫生訓練中其實也就是寫生對象最打動、最吸引你、最抓緊你眼球的某一方面,是“造型體量”還是“層次節奏”,又或是“質感氛圍”。例如素描寫生中同一角度的同一組靜物,有些學生想表現構圖的平衡或動態,有些想塑造對比不同物體的質感,有些想營造靜物與周圍大環境空間的氛圍感,有些致力于追求一組靜物不同物體間的黑白節奏,有些甚至放大一組靜物的某一個角落單純刻畫一些有趣的細節,等等。同樣如人物色彩寫生,總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致力于刻畫打磨人物皮膚微妙的明暗光影、色彩冷暖,衣著的紋理與質感,也總有另一部分學生享受著將人物和背景轉為各種“大關系”“小關系”用大色塊鋪陳帶來的酣暢淋漓,不令自己陷于一些細枝末節的糾結之中。經過基礎寫生課程中的這種觀看訓練,學生觀看的主動性被激發,落筆的目標明確,這種思維習慣漸漸形成一種繪畫的視覺習慣,在后期的自身創作中無論是在圍繞創作主旨選取素材時的敏銳力還是選擇何種表現手法的明確度上,都有著極大的提升與飛躍。由于不同創作者的觀看點與角度不同,個體成長軌跡與境遇不同形成的思維建構、心理狀態不同,這種觀看訓練同樣也更加有利于學生自身繪畫風格語言的確立。
創作的過程其實就是先確立一個目標,然后調動一切手段去實現它,做到極致。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煥發視覺的主動性,不會陷入“同一個蘋果”“萬人同一臉”的怪圈。
而如何進行“純粹”的觀看呢?一方面我們可以從現象學的角度去理解,將我們的視覺做“減法”,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曾提出:“繪畫所要做的,不是去填滿一個空白的空間,而是去清理它、掃除它(原型與概念等)”。我們在引導學生進行實際觀看時,應強調學生打破清除腦中所有已知的繪畫固有程式與概念,以現象學的方式的去審閱觀看對象,即物象當下的形體、色彩、質感、空間等視覺元素層面,從而獲得直接而感性的視覺體驗。[2]只需放下應試美術教育下“主觀處理”的“魔咒”,大膽遵循自己的眼睛,不要一味追求風格與技法,回到自身豐富的個人觀看,因為現象即本質,本質已然通過表象自足的呈現,我們只需要去尊重與捕捉對象豐富而直觀的自然征貌。另一方面,除去物象表征的觀看,涉及了我們自身精神層面對于物象的感性體察與共顫,這種純粹的感性體驗是在情感、精神、觀念、意義上對世界進行獨立的關照與深層的解讀。
三、如何進行“深層觀看”
在實際寫生過程中,我們觀看的對象受不同時間段、不同天氣光色的影響色彩冷暖、明暗節奏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甚至被我們自身主觀的情緒心境所映射,而我們作為創作者想要表達的創作目標,其實通俗來說是一種想要達到某一方面某種程度的欲望,欲望作為人類本能釋放的一種形式,就無可避免地受主觀情感的催生與驅使,無法達到完全的理性與智性,所以說藝術創作的過程只能由人類完成,動物與人工智能無法做到,它們或許可以完成某些藝術性的行為,但還不能稱之為藝術創造。所以當學生掌握了怎么用眼睛與大腦去“看”的基本方法后,我們更需要用“心”去進行深層觀看。而心境的產生除去我們個人的性格特質、成長經歷與主觀情感,還由我們的知識體系與認知觀念所架構,經歷了高中三年心理與生理的磨礪成長,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與價值觀基本形成與穩定的這一時間段,除了大量有關自身專業的知識儲備還需要基本的人文素養以建構認知觀念,所以大量的閱讀與瀏覽是構成學生“深層觀看”的重要途徑。藝術史證明,畫家不能僅畫其所見,二維平面上有限的色彩與造型通過藝術家心理、情感的過濾與鍛造一步步地修正以逼近對象達到“真實的視覺錯覺”的效果,這是“藝術”與“科學”兩個人類獨特創造活動的寶貴結晶,所以藝術創作必須以知識為基礎,理性為依托。通過閱覽大量美術史論、藝術品評家文章專著、藝術家傳記訪談與畫冊等,學生對于藝術史的發展、風格流派的演進、藝術大家的手法語言與觀念表達等有了基本認知,逐步形成自身繪畫的理論體系與數據庫,藝術觀念架構也更加明晰。在此基礎上,文學、哲學社科類專著文章也需要納入閱讀范圍,在學生實際面對寫生創作時,想要表達的繪畫目標與主題才更加開闊,創作內容也不只停留于畫面的技法效果或手法形式,而將理性的觀看轉為感性的視覺現象與個人化的繪畫觀念、情感內涵進行關照與聯系,培養對世界萬事萬物升華與深化的審視閱讀能力。[3]
四、“觀看”訓練打開視域
寫生課堂無疑是學生觀看訓練的最好時機與場所。在實際進行低年級色彩寫生教學的過程中,我發現學生一開始很難從美術高考水粉畫的色彩處理觀念中跳脫出來,受“色彩需要主觀處理”這一宗旨的影響,學生在追求色彩表現時往往面臨兩個極端:一是思維走入扭曲的“為了主觀處理而處理”,最后畫面呈現的色彩和寫生對象本身風馬牛不相及,更別提“觀看”這一過程了,學生早已被賦予各個物象什么樣的色彩而想破了腦袋。二是學生直接轉為“復讀機”模式,參照以往臨摹與默寫的物象色彩,如“蘋果或襯布……是什么顏色加什么顏色”,一股腦“復制粘貼”在畫面中。這一問題首先要根本性的解決,學生才能真正得以打開色彩之門,特別對于后期油畫專業課程的學習影響也十分深遠,規避畫什么都透露著“水粉味”的問題。為了擺脫這種“洗腦式”觀念,在這里可以在寫生課堂開始前進行一個色彩調色力的基礎訓練:準備一組色階相差較大的基礎靜物,學生需要用眼睛認真觀看每個物品的色彩,并用顏料盡可能調出一模一樣的顏色涂在紙條上,并將紙條貼在靜物上進行對比調整,期間學生可以相互交流討論,彼此指出問題并分享調色體會。這一訓練的目的在于切實讓學生將目光完全置于寫生對象去“觀看”,去分析解構我們身邊有固有色、光源色、環境色的真實而微妙的色彩,在此訓練過程中,學生產生基本“觀看”的意識,色彩掌控能力、感知度、敏銳度也會得到極大提升。
此外,寫生課堂的準備也是打開學生視野的重要環節,這里以寫生靜物課堂為例。一方面,在選取寫生對象時,教師可組織學生在靜物室中自行挑選,鼓勵學生大膽選取未接觸過、感興趣的寫生物品,同時可以收集身邊觸手可及的各類物品如校園里道路兩旁的枯枝落葉、寢室里各類洗漱生活用品,甚至是車庫里廢棄的自行車,都可以作為寫生的對象,這一環節的目的一是在于打破學生對固有寫生對象的思維定式,增加繪畫的新鮮感與積極性,二是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學生的潛意識里物品與其個人的生活與情感經驗結合起來,從而展開對預期畫面的構思。
另一方面,實際寫生物品的擺放同樣可以以學生占主動、教師輔助的形式實現。在教師規定好靜物組數的前提下,學生將個人挑選的靜物進行合理的擺置,這就涉及了學生間交流討論與個人構思兩個方面的碰撞,在此環節中,不同物品位置的主次安排、色調的節奏層次、質感的強弱對比等等都變成了不可回避的問題,學生不得不主動性的考慮與討論畫面構圖、色調、氛圍與空間節奏,將腦海中的預期畫面效果進一步具體化,潛意識里寫生的表現目標從而漸漸凸顯。
那么學生在實際寫生中確定表現目標時,視覺收集的大量圖像信息與個人豐富感性體驗結合總會帶來多種構思的碰撞,小稿訓練就無外乎是一種最直接明了的目標選取方式,將最初的視覺體驗快速記錄下來。寫生這一概念最早由印象主義提出,此前藝術家基本采用畫室作畫,描繪的也都是室內較為昏暗的光線,而印象主義畫家走向了室外,追求描繪大自然明亮而變化豐富的光線,這就要求畫家們捕捉物象的瞬間色彩,也就是視覺的第一印象,而制作小稿無外乎是記錄這種第一印象的最好方式。
關于小稿作畫的具體步驟與方法相關專業書籍著作均有詳細說明,本篇文章在此不再多贅述,需要補充的有筆者認為制作小稿最側重的兩點,一是構圖,二是色調(或明暗)。構圖從觀察者的層面來說其實就是觀看角度,可把人眼比作單反相機鏡頭:有方位、有焦距,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可鼓勵引導學生從多個不同視角、不同遠近去觀看寫生對象,在這種思考、選擇、觀看、感受的過程中,學生會慢慢形成寫生表現目標的意識:“從這個視角會更好表現……這一方面”,通過大量繪制小稿的積累,形成明確創作目標的思維習慣。而色調或明暗以小稿的形式確定也正契合了上述印象主義的寫生觀念,受光色、環境、心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我們觀看到的景象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是繽彩紛呈的,一幅幅小稿作品就如我們用相機快速捕捉一張張照片,色彩的強弱冷暖與明暗的黑白節奏有如濾鏡處理般切實記錄下即刻想要表達的意圖與心境。創作小稿的目的故在于此:盡可能將學生的所有表達欲望以大量的形式平鋪在我們面前。在此還需補充小稿訓練的一大要旨,就是“鋪大感覺,忌小細節”,即切勿刻畫小細節以丟失觀看到的瞬間知覺,這種瞬間知覺就是我們潛意識中最受物象吸引的部分,也是我們想要表達的創作目標。同樣,在后期創作正稿的過程中,我們也要秉持緊扣創作目標而不被其他吸引點混淆主題、細枝末節拘泥的宗旨。
經過上文幾個方面對于寫生創作基本觀看方式的討論與梳理,希望學生在藝術實踐中能夠擺脫腦中已有的應試程式與模板,顯現高等美術教育基礎素質培養的專業性與優質性,打破藝術創作視域的枷鎖,學會“觀看”的方法、享受“觀看”的過程、體味“觀看”的成果,以一種真實而純粹的視角去觀照與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