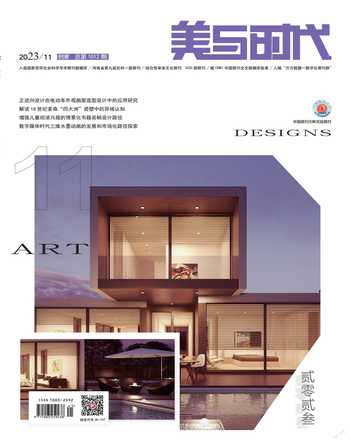文化記憶視角下鹽城海鹽文化譜系構(gòu)建及設(shè)計(jì)傳播
摘? 要:以鹽城海鹽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首先從文化記憶的視角分析鹽城海鹽文化的組成,根據(jù)鹽業(yè)相關(guān)活動(dòng)中人、事、場(chǎng)的相互關(guān)系將其分為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形成的海鹽文化、鹽俗活動(dòng)中形成的海鹽文化及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dòng)中形成的海鹽文化三部分,構(gòu)建海鹽文化構(gòu)成譜系。其次從文字和圖像、地點(diǎn)和空間、儀式和節(jié)日等方面分析海鹽文化媒介,建立鹽城海鹽文化過去和現(xiàn)在的聯(lián)系。最后從形象、結(jié)構(gòu)、意義、載體幾個(gè)角度進(jìn)一步分析海鹽文化設(shè)計(jì)傳播方法,以推動(dòng)海鹽文化的現(xiàn)代傳播。
關(guān)鍵詞:文化記憶;鹽城海鹽文化;構(gòu)成;媒介;傳播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2023年度鹽城市政府社科基金項(xiàng)目“鹽城傳統(tǒng)鹽俗信息圖譜構(gòu)建和文化傳播研究”(23skC57)研究成果。
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gè)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個(gè)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1],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不僅生動(dòng)述說著過去,也深刻影響著當(dāng)下和未來。豐厚的海鹽文化即鹽城人民集體記憶中的重要部分。鹽城地處黃海之濱,有兩千余年的鹽業(yè)發(fā)展歷史,在“煮海為鹽”的年代,對(duì)于鹽業(yè)生產(chǎn)具有先天的地理優(yōu)勢(shì),因遍地皆鹽場(chǎng)而得名,是我國唯一一個(gè)以鹽命名的地級(jí)城市,眾多鄉(xiāng)鎮(zhèn)均與鹽文化有內(nèi)在的深厚淵源,至今仍有許多包含“場(chǎng)”“團(tuán)”“灶”“總”“丿”“倉”等鹽業(yè)詞匯的村鎮(zhèn)名稱。從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設(shè)置鹽瀆縣至清末民初“廢灶興墾”,一直是一種大范圍、集體性的勞作生產(chǎn),主要為自身生存和政治服務(wù),這和一般性的傳統(tǒng)手工藝的小范圍活動(dòng)是有所區(qū)別的。在這一漫長(zhǎng)階段的文化傳承中,是以連續(xù)性的集體記憶形式繼承和發(fā)展,文化傳播的環(huán)境、形式?jīng)]有根本性變化;到清末民初“廢灶興墾”之后現(xiàn)代化鹽業(yè)生產(chǎn)方式的施行,傳統(tǒng)制鹽逐漸退出歷史舞臺(tái),古鹽業(yè)城鎮(zhèn)村落也紛紛轉(zhuǎn)型;時(shí)至今日,原本植根于人們血液中的海鹽文化已逐漸被稀釋、遺忘。在地域文化生態(tài)建設(shè)的背景下從文化記憶的視角重新審視海鹽文化過去和現(xiàn)在的關(guān)系,夯實(shí)鹽城本土文化之根,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尤為必要。
一、文化記憶的概念
文化記憶的概念由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有關(guān)集體記憶的研究中首次提出[2]。阿斯曼夫婦從媒介研究和文化史出發(fā),提出文化記憶是一個(gè)將傳統(tǒng)、歷史意識(shí)、“神話的動(dòng)能”和自我定義結(jié)合到一起的文化范疇,它受制于紛繁多樣的歷史變遷。由此可見,文化記憶具有持續(xù)動(dòng)態(tài)演變的特征,由媒介技術(shù)手段決定其革新進(jìn)程。目前學(xué)術(shù)界暫且將其界定為“社會(huì)文化語境中現(xiàn)在和過去的互動(dòng)”[3],以強(qiáng)調(diào)其研究范圍既有記憶的聯(lián)系,也有社會(huì)、文化的語境,核心是過去和現(xiàn)在的互動(dòng)。在社會(huì)快速發(fā)展進(jìn)程中,一些地區(qū)由于文化基礎(chǔ)的破壞,集體的、跨代際的交往基礎(chǔ)和理解能力的消失,出現(xiàn)了現(xiàn)在和過去的脫節(jié),一些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逐漸被淡忘和消失。文化記憶正是要在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建立一種非共時(shí)性的存在,以保存歷史記憶,并構(gòu)建其現(xiàn)代意義。文化記憶理論展示了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實(shí)現(xiàn)融通與契合的方式,為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及文化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提供了一個(gè)具有啟發(fā)性的研究視角。
二、文化記憶視角下鹽城海鹽文化構(gòu)成譜系
在中國古代社會(huì),兩淮鹽業(yè)因其重要的經(jīng)濟(jì)地位而被歷代王朝所重視,海鹽文化也在和鹽業(yè)相關(guān)的一系列活動(dòng)中孕育產(chǎn)生。依據(jù)文化記憶理論中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契合的各個(gè)方面,可把傳統(tǒng)海鹽文化按照活動(dòng)主體、活動(dòng)方式、活動(dòng)場(chǎng)域的不同分為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形成的海鹽文化、鹽俗活動(dòng)中形成的海鹽文化及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dòng)中形成的海鹽文化。
(一)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的海鹽文化
鹽業(yè)生產(chǎn)活動(dòng)的主體包括鹽官、鹽商、鹽民及其他相關(guān)勞動(dòng)者。鹽官為管理者,按照等級(jí)和職責(zé)有不同劃分,各朝各代亦有所差別,以明代為例兩淮鹽業(yè)設(shè)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分司—鹽課司三級(jí)管理機(jī)構(gòu)[4]。鹽城境內(nèi)13個(gè)鹽場(chǎng)分屬泰州、淮安分司,是兩淮鹽區(qū)鹽場(chǎng)最為集中、鹽產(chǎn)最為豐碩之地,為當(dāng)朝政權(quán)貢獻(xiàn)了重要的鹽產(chǎn)資源和鹽稅收入[5]。鹽課司是明代鹽業(yè)的基層管理單位,通過灶戶中的團(tuán)灶組織,對(duì)沿海分散的鹽業(yè)生產(chǎn)者(灶戶)實(shí)施管制,形成以鹽官為主體的鹽政文化。在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鹽民無疑是鹽文化創(chuàng)造的最主要群體,主要體現(xiàn)在生產(chǎn)工具、制鹽工藝及制鹽遺跡等方面,伴隨生產(chǎn)工藝的不斷改善,鹽文化內(nèi)容也不斷豐富,如鹽城地區(qū)古法制鹽技術(shù)經(jīng)歷了煎熬成鹽—磚池曬鹽—泥地曬鹽三個(gè)階段,技術(shù)的升級(jí)使組織結(jié)構(gòu)、工具材料等也發(fā)生相應(yīng)變化。同時(shí)鹽商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生產(chǎn)領(lǐng)域也會(huì)進(jìn)行資本投入,設(shè)立新灶、雇用鹽民擴(kuò)大生產(chǎn)。其他相關(guān)勞動(dòng)者則包括運(yùn)鹽的河工、臨時(shí)雇傭的腳力、從事鹽業(yè)工具制造的工匠等。這四類人群在各自場(chǎng)域的行為方式共同形成了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的海鹽文化。
(二)鹽俗活動(dòng)中的海鹽文化
鹽俗是在鹽業(yè)發(fā)展歷史進(jìn)程中逐漸形成的鹽文化民俗,鹽城地區(qū)鹽俗歷時(shí)悠久、豐富多維。傳統(tǒng)鹽俗活動(dòng)是海鹽文化基因的本質(zhì)體現(xiàn),具有豐富的地域性文化場(chǎng)域,是喚醒和呈現(xiàn)海鹽文化記憶的重要源泉,包括節(jié)日、飲食、服飾、俗語等。節(jié)日中祭鹽宗是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其多維性體現(xiàn)在祭祀活動(dòng)參與主體不同,祈求內(nèi)容和形式也會(huì)有所差別。如鹽官一般祭拜管鹽之宗管仲,鹽商祭拜經(jīng)鹽之宗膠鬲,鹽民祭拜產(chǎn)鹽之宗夙沙氏或鹽盤大圣、鹽婆娘娘。祭祀規(guī)模則根據(jù)組織機(jī)構(gòu)排場(chǎng)大小不同,一般鹽場(chǎng)組織排場(chǎng)大,團(tuán)灶組織排場(chǎng)小;飲食和服飾主要體現(xiàn)在鹽民和鹽商兩個(gè)不同群體的差別,如鹽幫菜可分為鹽工菜和鹽商菜,服飾包括鹽民工服、鹽商華服及儀式服飾。其中明清鹽商奢華之下的極致要求對(duì)淮揚(yáng)菜、服飾的發(fā)展均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俗語則包括方言、諺語、歇后語、鹽業(yè)術(shù)語、鹽味地名等。
(三)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dòng)中的海鹽文化
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dòng)主要是為滿足人們精神需求而產(chǎn)生,生活是其重要素材來源,鹽城地區(qū)相關(guān)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的主體為歷史文化名人和人民群眾,包括傳說、詩文、戲劇等。通過人民群眾的代際傳播、演繹發(fā)展,原本的鹽工號(hào)子、“門嘆詞”已演變成經(jīng)典的淮劇;張士誠“十八扁擔(dān)起義”、卞元亨打虎等眾多歷史事跡也被施耐庵所借鑒,融入到《水滸傳》中;清朝鹽民詩人吳嘉紀(jì)的“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讓人穿越歷史時(shí)空,至今能清晰地體會(huì)到鹽民的辛勞。
三、鹽城海鹽文化記憶媒介
文化記憶作為一種過去和現(xiàn)在的互動(dòng),需要不同的媒介來支撐,不同的形式去組織[6],海鹽文化記憶媒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文字和圖像
文字自誕生起,就成為記錄歷史的重要媒介,且具有永生的性質(zhì),人類依靠文字支撐起厚重的歷史記憶。其特點(diǎn)一是記錄歷史的真實(shí),雖然這種真實(shí)可能會(huì)被書寫者的個(gè)人情感或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志所“渲染”,但不妨礙架構(gòu)起過去和現(xiàn)在的聯(lián)系,使現(xiàn)在的人們對(duì)過去有所了解、認(rèn)知。如《鹽城縣志》《淮南中十場(chǎng)志》《兩淮鹽法志》等方志史料,對(duì)鹽政管理、生產(chǎn)關(guān)系、風(fēng)俗文化都有記錄;二是文字的思想性,文字能夠跨越時(shí)代進(jìn)行引導(dǎo),具有積極的象征作用。如施耐庵的《水滸傳》、李汝珍的《鏡花緣》等在鹽城地區(qū)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均有海鹽文化的豐富體現(xiàn)。圖像也是文化記憶的重要媒介,包括圖畫、建筑、雕像、器具等,隨著物質(zhì)性的圖像在時(shí)間流逝中不斷被毀壞,愈發(fā)體現(xiàn)出保留下來圖像的彌足珍貴。文獻(xiàn)中的圖例、建筑中的壁畫、鹽宗祠中的雕塑、遺存下來的盤鐵、鍋丿等制鹽器具,這些圖像都與整個(gè)海鹽文化不可分離地編結(jié)在一起,以一種視覺凝固的姿態(tài)承載著海鹽歷史記憶,并被賦予強(qiáng)烈的情感加以強(qiáng)化。
(二)地點(diǎn)和空間
地點(diǎn)是用來整理文化記憶的順序,方便這些記憶被重新找到的是回憶的載體,其對(duì)于文化的保留、挖掘及其回憶空間的建構(gòu)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因?yàn)樗鼈兡軌蛲ㄟ^把回憶固定在某一地點(diǎn)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證實(shí),還體現(xiàn)了一種持久的延續(xù)[7]。如安豐、新興、小海、便倉等村鎮(zhèn),都是古代鹽場(chǎng)或鹽倉所在地;大豐草堰古鹽運(yùn)集散地保護(hù)區(qū)是現(xiàn)存國內(nèi)最大、海鹽文化遺跡最為豐富的區(qū)域;西溪古鎮(zhèn)曾是歷史上鹽稅的主要征集地,北宋時(shí)期呂夷簡(jiǎn)、晏殊和范仲淹早期都曾在此做過鹽稅官員,有“西溪三相”之稱;以及阻擋海潮的范公堤,運(yùn)鹽的串場(chǎng)河等。這些地點(diǎn)和地點(diǎn)之上建筑的空間都體現(xiàn)著文化的傳承和記憶的隱喻,而出于人們對(duì)范仲淹的感激敬仰,對(duì)鹽宗的敬畏崇拜,范公祠、鹽宗祠這類建筑空間會(huì)升華成為一種紀(jì)念性的文化記憶。
(三)儀式和節(jié)日
一般文化記憶的維系是專職傳承人員的任務(wù),如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相關(guān)機(jī)構(gòu)的研究人員等,而廣泛的集體人員對(duì)于文化記憶的獲取,則以集會(huì)式在場(chǎng)參與完成,儀式和節(jié)日是其中首要的組織形式。通過定期重復(fù),強(qiáng)化集體認(rèn)同,保持文化一致性和傳承發(fā)展,這也是文化傳播在傳統(tǒng)風(fēng)俗中的一種體現(xiàn)。影響較大的有鹽婆生日、祭鹽宗、曬龍鹽、烘缸會(huì)等。如每年農(nóng)歷正月初六為鹽婆生日,鹽民到灘頭或風(fēng)車頭貼鹽婆畫像,點(diǎn)燭、焚香、放鞭炮,燒紙磕頭,燒紙名為“燒鹽婆紙”或“燒灘頭紙”,通過祭祀祈禱以求產(chǎn)鹽又好又多;農(nóng)歷三月初三是開曬日,鹽民生火燒鹽之前,要先祭鹽宗,供三牲,燒香燭,行三跪九叩之禮。秋后滅火休煎,也要祭之,感謝鹽宗保佑當(dāng)年鹽產(chǎn)豐收[8]。特定的儀式和節(jié)日體現(xiàn)了鹽業(yè)風(fēng)俗中人們的追求和信仰,是海鹽文化集體記憶傳承的重要媒介。
四、鹽城海鹽文化設(shè)計(jì)傳播
海鹽文化包含生產(chǎn)、生活、藝術(shù)創(chuàng)造多個(gè)方面,其文化記憶的多種場(chǎng)域具有不同的意義和象征,在時(shí)空?qǐng)鲇蚓艳D(zhuǎn)變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下,可根據(jù)不同記憶媒介和文化載體,對(duì)其進(jìn)行現(xiàn)代性設(shè)計(jì)轉(zhuǎn)譯,建立古今的文化關(guān)聯(lián)性。
(一)構(gòu)建海鹽文化形象符號(hào)
文化記憶不是歷史,其發(fā)展演變的特征決定了在現(xiàn)代文化傳播時(shí)形象符號(hào)也要跟進(jìn)切合人們的生活方式,形成文化自覺。代際更迭,社會(huì)語境的變化,原本的紀(jì)念之地逐漸變?yōu)榛貞浿厣踔吝z忘。因此在海鹽文化形象構(gòu)建時(shí),不僅包括文化載體的物質(zhì)形象,還包含其所蘊(yùn)含的精神形象,即符號(hào)所傳達(dá)的隱喻和象征[9],以加強(qiáng)海鹽文化形象符號(hào)的認(rèn)知。首先可通過IP設(shè)計(jì)的方法建立海鹽文化產(chǎn)品的整體傳播形象,如“鹽之有禮”“鹽之有物”之類品牌形象通過文字的力量給人以代入感;再根據(jù)媒介和文化載體的不同進(jìn)一步挖掘形象特征,構(gòu)建文化符號(hào),如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的制鹽工藝、器具、場(chǎng)所等本體形象和其所蘊(yùn)含的象征意義。
(二)解構(gòu)代表性器物、建筑的結(jié)構(gòu)形式
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中,一些代表性的器物、建筑的形式和結(jié)構(gòu)特征是設(shè)計(jì)研究的重要對(duì)象。傳統(tǒng)器物、建筑本身就是歷史、文化的載體,其結(jié)構(gòu)形式特征即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功能、審美的普遍性認(rèn)知印象,如范公堤、三賢祠、海春軒塔等古建遺存,不僅具有物質(zhì)化遺產(chǎn)的功能特征,還鐫刻著千百年來人們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傳承。對(duì)其結(jié)構(gòu)形式進(jìn)行解構(gòu)即突出重要特征以形成對(duì)海鹽文化的快速感知和認(rèn)同,解構(gòu)具有明顯特征的海鹽文化載體的方法可以在海鹽歷史記憶傳承過程中,擴(kuò)展其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形成一種更利于現(xiàn)代性傳播的文化認(rèn)知。
(三)功能意義的轉(zhuǎn)變和映射
文化傳承不是單一通過有意識(shí)地建立傳統(tǒng)而連續(xù)進(jìn)行,還需跟隨時(shí)代變遷,研究社會(huì)語境和應(yīng)用場(chǎng)景,使之服務(wù)于當(dāng)下的社會(huì)活動(dòng)。正如文化傳承不僅包含歷史記憶的存儲(chǔ),還包括功能性的轉(zhuǎn)變。因此,為使其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可以進(jìn)行合乎邏輯的意義轉(zhuǎn)變和映射,使文化載體的功能意義契合當(dāng)下所應(yīng)用的情境。在“煮海為鹽”的時(shí)代,鹽民的生活是異常艱苦的,屬于封建等級(jí)制度下被剝削的底層人民,整日辛勤勞作又無可奈何,但也體現(xiàn)了鹽民吃苦耐勞的優(yōu)秀品質(zhì)。當(dāng)然也有反抗精神,如張士誠等人的“十八扁擔(dān)起義”。其中吃苦耐勞的品質(zhì)是寶貴和值得傳承的,可通過設(shè)計(jì)轉(zhuǎn)譯使其映射到使用者的心理感受中。
(四)拓展海鹽文化傳播形式
隨著技術(shù)的進(jìn)步,文化記憶的存儲(chǔ)媒介在不斷演變,其表現(xiàn)載體也呈現(xiàn)多元的特征。若要建立過去和現(xiàn)在更好的互動(dòng)交流,必須準(zhǔn)確把握信息智能時(shí)代載體的形式演變,用更適合的載體輸出價(jià)值意義,在時(shí)空、場(chǎng)景、情境等方面探索更多可能性。尤其是對(duì)于代際較遠(yuǎn)的年輕一代的文化輸入,由于生活方式的完全斷裂,想讓其接受和理解,在場(chǎng)式的體驗(yàn)尤為重要。如“擔(dān)灰灘曬”“上鹵煎鹽”“撈灑撩鹽”等制鹽工序,完全還原場(chǎng)景會(huì)受到地理位置、空間、氣候、安全等多方面限制,可采用VR虛擬現(xiàn)時(shí)技術(shù)讓人們得到沉浸式體驗(yàn)。
五、結(jié)語
鹽城海鹽文化記憶具有多維的組成和多樣的媒介、載體,時(shí)代變遷下的表現(xiàn)形式已發(fā)生改變。在設(shè)計(jì)領(lǐng)域?qū)ζ鋫鞑ィ墒乖竟潭ǖ娜绻沤ㄟz跡等“動(dòng)”起來;可使原本已消失在人們記憶中的如先民生活方式、制鹽方法等“再現(xiàn)”出來,即通過設(shè)計(jì)轉(zhuǎn)譯使海鹽文化記憶產(chǎn)生“回聲”,重新回到人們的思想當(dāng)中,形成認(rèn)知、認(rèn)同,鞏固城市文脈。在文化多元發(fā)展的今天,傳承和發(fā)揚(yáng)優(yōu)秀民族文化需要更多樣的形式去實(shí)施。文化記憶的視角打破了傳統(tǒng)文化構(gòu)成物質(zhì)與非物質(zhì)的分類方法,更關(guān)注文化活動(dòng)主體、行為方式和活動(dòng)場(chǎng)域的聯(lián)系,使我們更清晰地認(rèn)識(shí)傳統(tǒng)文化在當(dāng)下的構(gòu)成形式和存儲(chǔ)媒介,認(rèn)識(shí)其形式變遷和演變的規(guī)律,重新審視時(shí)空轉(zhuǎn)換、代際更迭下文化傳播的方法和意義,形成文化自覺和復(fù)興。
參考文獻(xiàn):
[1]習(xí)近平.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dòng)人類文明進(jìn)步和世界和平發(fā)展的重要?jiǎng)恿J].當(dāng)代黨員,2019(11):4-6.
[2]楊福川.基于文化記憶理論視角的新時(shí)代改革開放精神弘揚(yáng)研究[D].西安:西安交通大學(xué),2020:35-38.
[3]埃爾,紐寧.文化記憶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2.
[4]郭正忠.中國鹽業(yè)史:古代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4.
[5]李傳江.明清兩淮鹽業(yè)經(jīng)濟(jì)影響下的區(qū)域文藝創(chuàng)作與消費(fèi)[J].求是學(xué)刊,2017(1):113-120.
[6]郭琳,張凌浩.經(jīng)典國貨文化記憶在當(dāng)代設(shè)計(jì)中的價(jià)值與延續(xù)[J].包裝工程,2012(10):110-113,117.
[7]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德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344.
[8]陳紅紅.鹽城海鹽文化[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95-97.
[9]米歇爾.圖像學(xué):形象,文本,意識(shí)形態(tài)[M].陳永國,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88-90.
作者簡(jiǎn)介:戚鳳國,碩士,鹽城工學(xué)院設(shè)計(jì)藝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工藝文化與產(chǎn)品設(shè)計(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