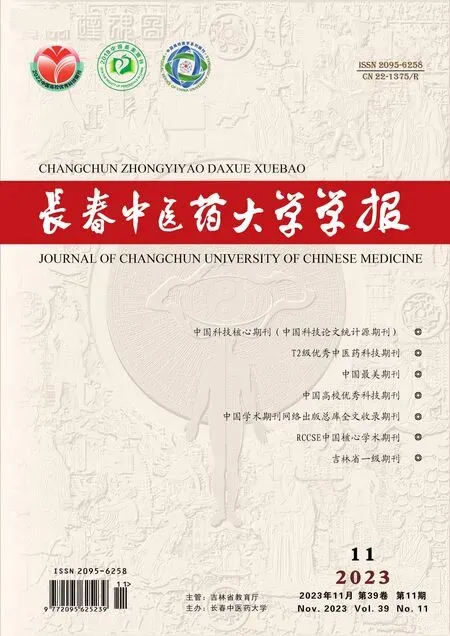“態靶辨治”體系下常用理化指標的標靶方藥初步整理
孫士鵬,楊忖卿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生物樣本庫,北京 100053)
中醫藥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面對復雜病因、不明病因的慢性病及重大突發傳染病時,具有獨特優勢。現代診療技術進步和健康體檢的普及,許多理化指標異常往往在無明顯的癥狀感知時便可檢測到。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更新迭代,多組學技術、時空轉錄組學、表型組學以及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現代醫學進入了精準醫學、整合醫學時代,中西醫匯通融合的新型醫療模式成為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必然需求。在此醫學變革的大趨勢下,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守正創新地提出了中西醫融合的“態靶辨治”體系,覆蓋中醫的“診斷、用藥、劑量”三個核心環節,融匯了病證結合、宏觀與微觀結合、中藥量效關系研究等新穎思路,使中西醫的特色優勢得以互補[1-2]。經長期臨床實踐證明,在“態靶辨治”體系指導下,疾病診斷的準確率、治療的及時性和有效性提升顯著,是中醫未來創新發展之路。
1 態靶辨治體系
《黃帝內經》曰:“生之本,本于陰陽”。健康人屬于“陰陽平衡”的“常”態,《黃帝內經》對常態的描述的原文為“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致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谷,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當人體外感六淫、內傷七情及飲食起居等出現影響健康的因素時,人體內環境平衡被打破,陰陽失衡,產生“偏態”。《注解傷寒論》言:“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仝小林院士依據《黃帝內經》“陰平陽秘、陰陽平衡”等基礎理論,按照中醫思維,借鑒現代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審視疾病全過程,厘清疾病發展各階段,歸納核心病機,以確定理法方藥量,并大力尋找治病的靶方靶藥,關注疾病之前的“因態”和疾病預后的 “果態”,提出了“態靶辨治”體系暨“態靶因果”的臨床辨治方略[3-5],實現對疾病的全方位辨知和治療。“態靶辨治”體系的內涵有二,一是 “分類-分期-分證”的“病證結合”模式;二是“宏觀調態與微觀打靶相結合”的“態靶結合”模式。“態靶辨治”體系蘊含并拓展了“因機證治”中辨其病因、病機、病證、態靶并治及治未病、防惡果的全病程診療體系。
“態靶辨治”的“態”有兩層內涵,廣義上“態”指人體陰陽運行之狀態,包括了常態(陰陽平衡)和偏態(陰陽失衡)。人體健康的常態又可依據人體生、長、壯、老的不同階段按陰陽(氣血)變化之規律細分。狹義上的“態”特指疾病的“偏態”,即疾病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態勢,是疾病某階段的整體概括,具有“狀態、動態、態勢”三層含義[3-4]。治療上的“調態”即是糾正“偏態”,使機體回歸“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的穩態。同時,也要考慮引發疾病的因素(即“因”),以及疾病可能造成的并發癥或預后轉歸(即“果”)。
“靶”借用了現代醫學“靶點”的概念,特指中藥在宏觀、微觀兩個層面上的作用點,包括三個方面,即病靶(對疾病具有特定療效的靶方靶藥)、癥靶(對臨床癥狀具有特定緩解效果的靶方靶藥)和標靶(對理化指標、影像學檢查等具有特殊效應的靶方靶藥)[4]。“病靶”指直接針對疾病本身的治療,病靶就是疾病的根,找到根就能從本質上解決疾病,中醫應用中藥也無需辨證論治,比如說用青蒿素治療瘧疾、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但是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找到疾病的“病靶”目前都是一個難題。“癥靶”指針對癥狀或體征的治療,中醫傳統文獻、現代名老中醫經驗,都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內容,這是傳統中醫的特色優勢。“標靶”是指現代醫學中常規檢驗、病理和影像學檢查出來的異常指標。仝小林指出現代中醫必須重視理化指標的調控,把理化指標的改善作為臨床療效判定的重要標準之一[6]。標靶方藥應用的原則為:態靶一致為首選,平性藥物不受限;倘若藥態兩相背,適當反佐以求安[1]。
2 仝小林院士常用理化指標的標靶方藥初步整理
2.1 血糖及糖化血紅蛋白
血液葡萄糖臨床上簡稱血糖。葡萄糖是細胞的主要能量來源,葡萄糖代謝產生的ATP是支持細胞多種生命活動(包括酶生物合成、細胞內運輸和細胞擴散)的能量物質。血糖的來源主要是食物、機體內儲存的糖原分解、糖異生作用以及其他糖原的轉化。血糖的去路主要是組織細胞對葡萄糖的攝取和利用,包括氧化供能、合成糖原、轉化成甘油、脂肪酸、氨基酸等非糖物質、轉化為其他糖或糖類衍生物。血糖濃度的動態平衡受到激素(胰島素、胰高血糖素、腎上腺素、生長激素、皮質醇、甲狀腺素、生長抑素)、體液調節因子(葡萄糖轉運因子和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的精細調控[7]。血糖升高常見于糖尿病、內分泌疾病、應激性高血糖、肝源性高血糖等疾病[7]。糖化血紅蛋白(HbA1c)是紅細胞中的血紅蛋白與血清中的糖類(主要指葡萄糖)通過非酶反應相結合的產物,其形成的非酶反應具有持續、緩慢、不可逆的特點,一旦形成即可存在于紅細胞。正常健康成年人紅細胞壽命約為70~140天,臨床上認為HbA1c一般可反應2~3個月血糖的平均水平。《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明確指出:在有嚴格質量控制的實驗室,采用標準化檢測方法測定的HbA1c≥6.5%作為基本點,來輔助2型糖尿病的診斷可以作為糖尿病的補充診斷標準。現代藥理學研究結果表明,黃連、桑葉、桑枝、桑白皮、知母、赤芍、天花粉等中藥具有降糖功效[8-10],這些藥物是仝院士最為常用的降血糖和HbA1c的靶藥。
黃連性苦味寒,歸心、脾、胃、肝、膽、大腸經,清熱燥濕,瀉火解毒。藥典劑量為2~5 g。依據“態靶辨治”體系,糖尿病早期-中期-中后期-后期的病程發展可分為郁、熱、虛、損四態。大劑量黃連降糖迅捷,糖尿病早、中期的“郁”態和“熱”態階段黃連是態靶同調藥物,既可以清火泄熱,又能降糖,此時劑量宜大,一般用9~30 g;對于血糖極高,甚至出現糖尿病酮癥者,用量可達60~120 g,1~2 劑即可迅速降糖[9-10]。大劑量使用黃連時,常與干姜、生姜相配伍以制約其苦寒傷胃[10]。糖尿病后期“虛”態、“損”態,黃連劑量不宜過大,一般用 9~15 g[9]。血糖控制達標后,痰熱、火毒等病理基礎基本已清除,可以小劑量黃連(1~3 g)長期調理。
桑葉性寒味甘、苦,歸肺、肝經,疏散風熱,清肺潤燥,清肝明目。用于風熱感冒,肺熱燥咳,頭暈頭痛,目赤昏花。《中國藥典》2020版桑葉臨床用量范圍為5~10 g。作為糖尿病的靶藥,桑葉可散中焦及上焦郁火,臨床常用劑量為15~60 g。現代研究證明桑葉多糖、黃酮等有效成分可能通過減輕糖尿病小鼠體內氧化損傷,修復受損胰島細胞、改善機體胰島素效應細胞的抵抗作用,達到協同降血糖效應[11]。桑葉中的多糖類和生物堿類成分具有抑制小腸黏膜對葡萄糖的吸收和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12]。桑枝性平味微苦,歸肝經,祛風濕,利關節。用于風濕痹病,肩臂、關節酸痛麻木。《中國藥典》2020版桑枝臨床用量范圍為9~15 g。桑枝散四旁經絡、皮腠之郁火,糖尿病末梢神經病變兼有血糖高者尤宜,臨床常用劑量為15~30 g[13]。桑白皮性寒味甘,歸肺經,瀉肺平喘,利水消腫。用于肺熱喘咳,水腫脹滿尿少,面目肌膚浮腫。《中國藥典》2020版桑白皮臨床用量范圍為6~12 g。桑白皮清肺胃之熱,有”小白虎湯”之美譽,臨床常用劑量為15~30 g。桑葉常與桑白皮、桑枝合用作為“郁”態的態靶同調藥物中的代表[13]。桑葉、桑枝、桑白皮各30 g,其降糖力度大約相當于阿卡波糖50~75 mg,每日3次的效果[13]。
知母性寒味甘、苦,歸肺、胃、腎經,清熱瀉火,滋陰潤燥。用于外感熱病,高熱煩渴,肺熱燥咳,骨蒸潮熱,內熱消渴,腸燥便秘。《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6~12 g。仝小林把知母多作為糖尿病“熱”態清胃熱的態靶同調的靶藥。作為糖尿病的靶藥臨床用量為10~90 g,平均劑量36 g[14],糖尿病酮癥酸中毒時,為 30 ~90 g,若要發揮較好的降糖功效,須達 30~60 g[15]。知母中皂苷、多糖、雙苯吡酮類化合物等通過減弱α-葡萄糖苷酶活性、降低肝糖元的活性、增強外周組織對的胰島素敏感性等機制降低血糖[16]。
赤芍性微寒,味苦,歸肝經,清熱涼血,散瘀止痛。用于熱入營血,溫毒發斑,吐血衄血,目赤腫痛,肝郁脅痛,經閉痛經,癥瘕腹痛,跌撲損傷,癰腫瘡瘍。《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6~12 g。仝小林把赤芍作為糖尿病“熱”態清血熱的態靶同調的靶藥[8],作為糖尿病的靶藥臨床用量為15~30 g[17]。赤芍提取物體外降低 α-葡萄糖苷酶活性和抗氧化活性,其提取物能夠增加肝糖原含量,不同提取部位均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能夠明顯的緩解小鼠糖尿病癥狀[18]。
天花粉性微寒,味甘、微苦,歸肺、胃經,清熱瀉火,生津止渴,消腫排膿。用于熱病煩渴,肺熱燥咳,內熱消渴,瘡瘍腫毒。《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10~15 g。仝小林把天花粉作為糖尿病的靶藥常用劑量為15~30 g[8]。天花粉及其乙酸乙酯提取物和凝集素粗品具有較強的降糖作用[19]。知母、天花粉、葛根是仝小林臨床常用的清熱養陰生津小方,三味藥合稱“滋膵飲”,見熱盛陰傷均可配伍使用[8]。
除上述最常用的降血糖的靶藥外,仝小林也多使用苦瓜、生地黃、葛根、黃芩、梔子、山藥、山茱萸、苦參等中藥降血糖靶藥[20]。
1.2 血脂
血漿脂質簡稱血脂,包括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磷脂(phospholipid,PL)和游離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三酰甘油、總膽固醇必須與親水性的脂蛋白(特殊蛋白質和磷脂等)形成親水性大分子才能在血漿中運輸。依據顆粒大小和密度的差異,血漿脂蛋白可以分為乳糜微粒(chylomicron,CM)、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VLDL)、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TC、TG、HDL-C、LDL-C和LP(a)是臨床生化檢驗的常規血脂檢測項目,主要用于發現與診斷高脂蛋白血癥,協助診斷動脈粥樣硬化癥,評價動脈粥樣硬化疾患如冠心病和腦梗死等危險程度,檢測評價飲食與藥物治療效果[7]。臨床上,仝小林針對血脂異常用的靶藥有紅曲、山楂、決明子等,多用紅曲、神曲、半夏曲三味小方作為降血脂的靶方[20]。
紅曲味甘,性溫,入肝、脾、大腸經。《本草衍義補遺》言其能“活血消食,健脾暖胃,赤白痢下水谷”。紅曲可顯著降低體內膽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且其降血脂具有高效性、耐受性和安全性,可作為他汀不耐癥患者治療高脂血癥的替代品[21]。神曲又名六神曲,最早收載于《藥性論》,為面粉、麥麩、苦杏仁、赤小豆、青蒿、辣蓼及蒼耳草混合后經發酵而成的曲劑,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復合體、消化酶、揮發油等多種成分,具有健脾和胃、消食調中等功效[22]。半夏曲性溫,味辛,歸脾、胃、肺經。其具有消食化積,化痰止咳的功效,為通利上焦和中焦之藥。現代藥理研究表明,以上三味藥可促進胃腸動力,調節腸道菌群,降低總膽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膽固醇[21]。仝小林三藥配合使用時,神曲常用9~15 g 以健脾和胃,消導調中,半夏曲常用9~15 g以通泄消導,燥濕化痰而協助病理產物排除體外,紅曲作為降血脂的靶藥,其臨床用量范圍為3~15 g以健脾燥濕,消膏降濁[21]。
山楂味酸、甘,性微溫,歸脾、胃、肝經,消食健胃,行氣散瘀,化濁降脂。《中國藥典》2020版記載其主治用于肉食積滯,胃脘脹滿,瀉痢腹痛,瘀血經閉,產后瘀阻,心腹刺痛,胸痹心痛,疝氣疼痛,高脂血癥,臨床用量范圍為9~12 g。仝小林把山楂作為高脂血癥的靶藥臨床用量為 9~90 g,三酰甘油含量大于4 mmol·L-1時,生山楂的用量為40 g以上。山楂降血脂活性物質主要有黃酮類化合物如表兒茶素、花青素、金絲桃苷、蘆丁、槲皮素等,三萜酸如熊果酸、齊墩果酸、山楂酸等,植物甾醇有谷甾醇、胡蘿卜苷、豆甾醇等,還有果膠等物質[24]。山楂通過提高膽固醇7α-羥化酶的表達水平,抑制3-羥基-3-甲基戊二酸單酰輔酶A還原酶、酰基輔酶A:膽固醇酰基轉移酶的活性,增加低密度脂蛋白受體水平及通過調控多種脂肪代謝酶的機制調節血脂[23]。決明子味甘、苦、咸,性微寒,歸肝、大腸經。能清熱明目,潤腸通便。用于目赤澀痛,羞明多淚,頭痛眩暈,目暗不明,大便秘結。《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9~15 g。仝小林把決明子作為高脂血癥的靶藥臨床用量為15~60 g[24]。決明子正丁醇提取物具有明顯的降血脂作用,能顯著降低高脂血癥小鼠血清總膽固醇(TC)和三酰甘油(TG)[25],決明子蛋白質、蒽醌苷皆可降低高脂血癥大鼠的TC,TG和LDL-C[26]。因決明子具有確切的降血脂作用,決明子及其復方制劑在臨床上已廣泛運用于高脂血癥的治療[26]。
除了上述常用的降血脂靶方靶藥外,仝院士也多使用五谷蟲、大黃、淫羊藿、水蛭粉、制何首烏、女貞子等中藥作為降血脂的靶藥[27]。
1.3 血尿酸
尿酸是嘌呤核苷酸代謝的終產物,水溶性較差。嘌呤代謝紊亂,體內尿酸增加會出現高尿酸血癥,尿酸鹽晶體可沉積于關節、軟組織、軟骨及腎等處,導致關節炎、尿路結石、腎疾病或痛風等疾病。測定尿酸主要用于尿酸代謝異常的評價、痛風診斷、關節炎鑒別和腎功能評價。“濕濁態”為高尿酸血癥的常見態勢,土茯苓、威靈仙、萆薢是仝小林院士臨床常用的治療高尿酸血癥的態靶同調小方[28]。
土茯苓甘淡,平,歸肝、胃經。功能解毒,除濕,通利關節。用于梅毒及汞中毒所致的肢體拘攣,筋骨疼痛;濕熱淋濁,帶下,癰腫,瘰疬,疥癬。《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15~60 g。仝小林把土茯苓作為濕濁態高尿酸血癥的態靶同調的靶藥臨床用量為15~60 g[28]。現代醫學研究發現土茯苓可以促進腎臟對尿酸的排出,而且其根莖中含有的多種化學成分能抑制血尿酸的生成、利尿,并可改善腎功能[29]。
威靈仙味辛、咸,性溫,歸膀胱經,祛風濕,通經絡。用于風濕痹痛,肢體麻木,筋脈拘攣,屈伸不利。《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6~10 g。威靈仙為仝小林臨床常單用的降尿酸要藥,常用劑量為9~30 g。藥理學研究表明,威靈仙制劑除了能顯著降低血尿酸,還能強效抗炎、有效保護腎臟,治療高尿酸引起的腎病[30]。
萆薢可分為粉萆薢與綿萆薢,均味苦,性平,歸腎、胃經,利濕去濁,祛風除痹。用于膏淋,白濁,白帶過多,風濕痹痛,關節不利,腰膝疼痛。《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9~15 g。仝小林把萆薢作為濕濁態高尿酸血癥的態靶同調的靶藥的常用劑量為15~30 g[28]。
除了上述常用的降血脂靶方靶藥外,仝小林也多使用秦皮、馬鞭草、澤瀉、豨薟草、秦艽等中藥作為降尿酸的靶藥[27]。
1.4 膽紅素、轉氨酶和堿性磷酸酶
膽紅素是膽汁的重要成分之一,是血色素的降解產物,非結合膽紅素在循環血中與清蛋白結合,轉運至肝臟,在肝細胞一系列酶的作用下與葡萄糖醛酸結合形成水溶性強的葡萄糖醛酸膽紅素即結合膽紅素,隨膽汁進入腸腔后大部分被微生物分解為膽素原,然后氧化成膽素隨糞便排出,少部分經腸肝循環隨尿排出或再排入腸腔[7]。膽紅素的檢測主要用于診斷和治療肝臟疾病、溶血性疾病、血液學的疾病和代謝紊亂,包括肝炎和膽囊梗阻。雖然很多組織都含有轉氨酶,但是肝臟損傷是血清轉氨酶升高的最常見原因[7]。仝小林針對膽汁淤滯引起的高膽紅素血癥、肝或膽道酶(堿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轉肽酶、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常用靶方為茵陳蒿、赤芍、金錢草[31]。
茵陳蒿味苦、辛,微寒。歸脾、胃、肝、膽經。清利濕熱,利膽退黃。用于黃疸尿少,濕溫暑濕,濕瘡瘙癢。《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6~15 g。仝小林根據臨床黃疸嚴重程度使用茵陳蒿用量:輕度黃疸15 g,中度黃疸30 g,重度黃疸30~120 g[32]。現代藥理及相關研究證明茵陳蒿及其成分可增強肝細胞功能、促進肝臟對膽紅素代謝、顯著降低血清和肝組織中的轉氨酶水平[31-32]。
赤芍味苦,微寒,歸肝經。仝小林視患者肝熱程度,赤芍用量為15~ 60 g[31]。現代藥理及相關研究證明赤芍可改善肝臟微循環,加強膽紅素攝取、結合、轉運、彌散及排泄的作用,促進黃疽消退和肝細胞炎癥消失[33]。
金錢草味甘、咸,微寒。歸肝、膽、腎、膀胱經。利濕退黃,利尿通淋,解毒消腫。用于濕熱黃疸,膽脹脅痛,石淋,熱淋,小便澀痛,癰腫疔瘡,蛇蟲咬傷。《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15~60 g。仝小林視患者膽道淤阻情況金錢草用量為15~90 g,用于排石用量則為45~90 g[31]。現代藥理及相關研究證明金錢草能可以影響結石結構,促進結石溶解、縮小,同時可松弛膽道括約肌促進膽汁分泌和排泄、加強平滑肌運動加速排石,對降低膽紅素及ALP、γ-GT 有良效[31,34]。
1.5 抑制自身免疫反應的靶藥
現代藥理學表明,雷公藤和穿山龍均具有類似甾體樣激素的作用,是仝小林常用的抑制自身免疫反應的靶藥[35],在成人隱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2型、IgA腎病、系統性紅斑狼瘡、橋本甲狀腺炎等多種臨床疑難病的治療中,對改善臨床癥狀,優化疾病特異性指標,延緩及阻斷疾病進程有明顯療效[36-37]。
雷公藤味苦、辛,性溫,有大毒,歸肝、腎經,具有祛風除濕、活血通絡、消腫止痛、殺蟲解毒的功效,對肝腎、心臟、生殖、消化、血液、免疫系統等都有一定的毒性[37]。仝小林使用雷公藤作為自身免疫反應抑制劑,臨床用量范圍為9~ 15 g,并配伍解毒保肝的中藥五味子,對于生育期及肝腎功能不全者應慎用或不用[37]。雷公藤是全方位多靶點的抑制免疫反應的中藥,對抗原呈遞細胞、T細胞和 B 細胞均有作用。
穿山龍味甘、苦,性溫,歸肝、腎、肺經。功能祛風除濕,舒筋通絡,活血止痛,止咳平喘。用于風濕痹病,關節腫脹,疼痛麻木,跌撲損傷,閃腰岔氣,咳嗽氣喘。《中國藥典》2020版臨床用量范圍為9~15 g。仝小林認為穿山龍藥性平和,大劑使用,力專功捷,常用劑量30~90 g。對于雷公藤使用受限的患者,選擇穿山龍具有較大的優勢[36]。穿山龍無激素的不良反應,亦無生殖系統影響,臨床使用安全。
1.6 尿蛋白
由于正常人腎小球毛細血管的屏障功能和腎小管的重吸收功能,正常人尿中有微量蛋白,正常范圍內定性為陰性。當尿中蛋白質含量增加,普通尿常規檢查即可測出,稱蛋白尿。在高蛋白飲食及精神激動、劇烈運動、長時間受寒、妊娠等情況下會出現生理性蛋白尿。當腎小球、腎小管發生病變時,可出現病理性蛋白尿。
黃芪為仝小林治療腎性蛋白尿的常用靶藥[38]。黃芪味甘,微溫。歸肺、脾經,補氣升陽,固表止汗,利水消腫,生津養血,行滯通痹,托毒排膿,斂瘡生肌。用于氣虛乏力,食少便溏,中氣下陷,久瀉脫肛,便血崩漏,表虛自汗,氣虛水腫,內熱消渴,血虛萎黃,半身不遂,痹痛麻木,癰疽難潰,久潰不斂。《中國藥典》2020版中黃芪的臨床用量范圍為9~30 g。現黃芪作為腎性蛋白尿的常用靶藥,仝小林用量范圍是30~120 g。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黃芪富含微量元素硒,對腎小球基底膜的電荷屏障和機械屏障均有保護作用,減輕通透性蛋白尿[39]。
仝小林治療腎性蛋白尿的常用靶方為菟絲子、女貞子、金櫻子[42]。《中國藥典》2020版菟絲子、女貞子、金櫻子臨床用量范圍均為6~12 g。作為腎性蛋白尿的靶方,仝小林根據臨床蛋白漏出的量決定藥物用量,用量范圍菟絲子、女貞子為9~15 g,金櫻子為9~30 g[40]。菟絲子辛、甘,平,歸肝、腎、脾經,補益肝腎,固精縮尿,安胎,明目,止瀉;外用消風祛斑。用于肝腎不足,腰膝酸軟,陽痿遺精,遺尿尿頻,腎虛胎漏,胎動不安,目昏耳鳴,脾腎虛瀉;外治白癜風。女貞子甘、苦,涼,歸肝、腎經。功能滋補肝腎,明目烏發。用于肝腎陰虛,眩暈耳鳴,腰膝酸軟,須發早白,目暗不明,內熱消渴,骨蒸潮熱。金櫻子酸、甘、澀,平。歸腎、膀胱、大腸經。功能固精縮尿,固崩止帶,澀腸止瀉。用于遺精滑精,遺尿尿頻,崩漏帶下,久瀉久痢。
1.7 血肌酐、尿素氮
血肌酐來源于食物攝取的外源性肌酐和體內生成的內源性肌酐兩部分,幾乎全部經腎小球濾過進入原尿,且不被腎小管重吸收。機體內源性肌酐每日生成量幾乎保持恒定,嚴格控制外源性肌酐攝入則能維持血肌酐值的恒定。血肌酐是臨床反映腎小球濾過率的較好指標。肌酐產量與肌肉量平,故又作為肌肉量的評價指標。尿素氮又稱尿素,因一個尿素含有兩個氮,尿素和尿素氮的換算是尿素等于尿素氮乘以2.14[7]。尿素是機體內蛋白質代謝的終末產物,分子量小且不與血漿蛋白結合,可自由濾過腎小球。但是,進入原尿的尿素約50%隨后被腎小管和集合管重吸收。尿素是腎功能以及腎前狀態和腎后狀態的度量標準,腎前因素引起的尿素氮的升高包括心臟代償失調,缺水或增加的蛋白質分解代謝。任何類型的泌尿道的梗塞受阻是尿素氮水平升高的腎后因素。
仝小林降肌酐、尿素氮常用靶藥為生大黃[38]。大黃苦,寒,歸脾、胃、大腸、肝、心包經,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涼血解毒,逐瘀通經,利濕退黃。用于實熱積滯便秘,血熱吐衄,目赤咽腫,癰腫疔瘡,腸癰腹痛,瘀血經閉,產后瘀阻,跌打損傷,濕熱痢疾,黃疸尿赤,淋證,水腫。《中國藥典》2020版記載生大黃用量為3~15 g。作為血肌酐、尿素氮的靶方,仝小林大黃用量范圍為3~15 g,以患者大便每日不超過2次為度。大黃的活性成分大黃素能顯著降低5/6腎切除大鼠肌酐、尿素氮水平,改善腎功能;同時通過提高大鼠腎組織E-cad的表達水平,抑制上皮-間質轉化及纖維連接蛋白的表達,干預腎纖維化,從而起到腎臟保護作用[41]。大黃經腸道干預對慢性腎功能衰竭大鼠可減輕腎臟病理損傷,可降低大鼠血清肌酐、尿素氮水平,對殘余腎臟組織的腎間質纖維化及炎癥浸潤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可能與腸上皮細胞Claudin-1、Occludin和ZO-1的mRNA及蛋白表達增加有關[42]。
2 結語
“態靶辨治”體系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中醫的“辨態、調態”之長與現代西醫的“精準打靶”之長,覆蓋中醫的診斷、用藥、劑量3個核心環節,為疾病診治提供真正有效的中西醫結合之路。仝小林院士在臨床實踐中非常重視現代理化指標和影像學指標,標靶方藥是“態靶辨治”體系在中醫理論指導下又充分借鑒現代中藥藥理成果,將現代中藥藥理研究成果回歸于臨床,用中醫藥裝置了一套現代化標靶精準打擊系統,是“態靶辨治”體系獨特優勢內涵之一。本文對仝小林院士針對理化指標的“標靶”,包括血糖、血脂、血尿酸、膽紅素、轉氨酶、尿蛋白、血肌酐、尿素氮及抑制自身免疫反應的靶方靶藥進行了初步整理,從藥物的藥性、相關的現代藥理學機制、臨床常用劑量范圍進行了簡要的概述,在臨床使用時當根據患者具體情況選擇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