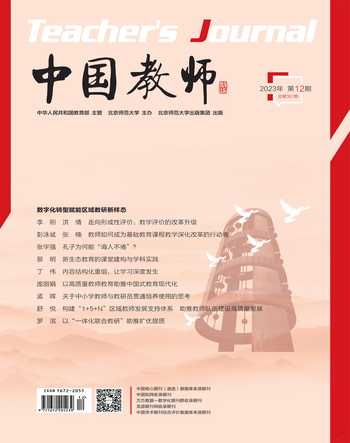因愛赴滇,無悔支邊
張璐瑤 高榮嬡藝


訪談張璐瑤 高榮嬡藝
整理高榮嬡藝 張璐瑤
一、我的家庭與教育經歷
1. 重視教育的家庭氛圍
1966年,我出生于重慶永川,有一個哥哥、兩個妹妹。父親是重慶江北縣(今渝北區)人,讀書讀得很好,一直在機關工作。母親是重慶江津人,她不愿匆匆嫁人,通過讀書走出農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我見過父母上學時的優秀證書,因為他們,我覺得讀書是天經地義的事,能夠讓我看到更大的世界。
2. 我的教育經歷(1972—1990年)
(1)基礎教育階段
1972年,我開始上學,在勝利小學讀書。1977年,我升入永川東方紅小學的戴帽中學(后改名十一中)讀初中。初一時的班主任叫吳修讓,他鼓勵學生,也很包容學生。在他的影響之下,我的性格開始變得開朗,膽子變大,自信心更強。
也是初一那年,高考恢復了。我們很興奮,想著趕緊長大,長大后就可以參加高考,可以上大學了。上大學是一代人的夢想,也是整個國家所有人的夢想。
1980年,我考入我們當地最好的中學—永川中學,還進了尖子班。老師們都很優秀,數學老師要求每做一道題必須找出幾種解法,地理老師講四姑娘山、峨眉山、貢嘎山、九寨溝……滔滔不絕,令人向往。1983年我參加高考,以永川文科最高分519分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校教育專業。
(2)我的大學生活
學校的學習氛圍很濃厚。進校以后,我讀了大量人文類書籍,在閱讀過程中個人思維方式逐漸形成。王策三、黃濟、厲以賢、王炳照、趙敏成等老師都給我們上過課,師生關系很好。那時上課沒有教材,也沒有錄音機,我們都是自己動手記筆記,老師上課每一句話都不重復,所以我們記筆記的水平特別高。
大三上學期,我們開始上樸永馨老師的特殊教育學選修課。樸老師經常帶我們去北太平莊后面的一所聾校參觀,我們還去過盲校、工讀學校、前門的培智班、清河福利院。看到殘疾兒童的樣貌以及老師教學的艱辛,我覺得做特殊教育真是不容易。
大學時藝術活動特別豐富。中央歌劇院的指揮鄭小瑛帶著歌手和樂隊,到學校里講《卡門》序曲。到了周末,我們還會聽各種各樣的講座,啟功、張維迎、楊煉、顧城等名人作過講座。同學們還經常一起春游、秋游。夏天的晚上,大家就在天文樓后面的草地上圍坐成一圈,彈琴唱歌。
1985年年底,我和我先生馬林認識了。他在歷史系,是個典型的文藝青年,會唱歌、會寫詩,知識面廣,思想也比較深刻。他對我很好,一直把我放在第一位。1987年,他本科畢業,回到了家鄉云南,在昆明師專歷史系工作,我留在北京讀碩士。碩士三年,我一直都在思考:去云南還是不去云南?最終還是決定去云南,但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準備:我不是為了誰而去昆明的,無論如何都要選擇一個城市生活,或者北京,或者重慶,或者昆明……只不過,昆明有一個自己喜歡的人。為自己做選擇,不要覺得是因為誰而去,后面的路才好走一些。
1989年,我們領了結婚證。畢業前,我向學校申請去昆明。許多老師覺得很遺憾,但我的導師沈適涵老師說:“李里啊,你記住,你走到哪都記住,不要給母校丟臉。”我說:“好,我保證不給母校丟臉!”
二、我的支邊經歷(1990年至今)
1. 進入教育學科教研室(1990—1999年)
(1)開展調研,了解基層教育情況
1990年我到了昆明師專,一進校就被分到教育學科教研室。教研室一共有10名教師,主要負責心理學、教育學和班主任工作技能課三門必修課的教學工作,教研科研風氣很好,工作氛圍也好。
同年,我參與了一項大型調查—昆明師專“畢業生就業質量調查”和“未來五年的教師需求調查”。我們去昆明所有初中學校和一線校長交流,了解教師的自然減員①情況、畢業生的工作情況,調查學校需要什么樣的教師、什么學科的教師。基于我們的調研報告,校長提出,昆明師專的人才培養定位是培養“農初師”—培養農村的初中教師。
(2)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
1991年7月,我開始從事教學工作。剛開始我一學期只上一門課,教育學或心理學。1996年起,學校開始重視心理學,要求在公共選修課中開設相關輔修課程。于是,授課量就比較大了,最多的時候我要上四門課,教育學、比較教育學、大學生心理健康,還有中小學心理咨詢理論與實踐。
我在上課、備課方面花的功夫比較多。我會提前到圖書館借閱資料,自己買書看,手寫教案,聽別的教師上課,還會主動跟著學生去中學聽課,了解一線教學情況。我逐漸對好的課堂有了自己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風格。第一,教學應該把教育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理論學習結合豐富的實際案例,教學實踐則要回歸理論基礎。第二,需要把書本知識和社會現實、歷史背景結合起來。第三,好的課堂要能夠激發學生的思考,拓展學生的視野和心胸,把做學生、做人、做事結合起來。
2. 參與云南省教師培訓項目(1999—2011年)
1999年開始,我利用假期,參與云南省中小學教師履職晉級培訓、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培訓等教師培訓任務。我見證了許多變化。首先,根據國家政策的變化和培訓階段的深入,省里會不斷調整培訓的目標和內容,如新課程改革開始了,就大規模地做新課程改革的培訓;強調師德,就增加提高師德的培訓內容。其次,教師培訓的理念也在逐漸提升,從國家政策的介紹和推廣,慢慢地到教師素質的拓展、教學能力和教學質量的提高,再到教師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的提升。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教師們在教學理念和學習觀念上的變化,慢慢地他們能夠接受新課改的理念,落實新課改的要求,參與培訓的學習熱情也日益提高。這對云南的教育有促進和提高作用。
3. 推動特殊教育事業發展(2012年至今)
(1)建立并發展特殊教育專業(2012年至今)
云南省原本是沒有特殊教育的。2011年,為了承擔起為社會服務的責任,學校領導決定開設特殊教育專業。2012年,我開始設計人才培養方案。2013年,特殊教育專業終于建成,由我擔任負責人。
經過反復咨詢和論證,我們把特殊教育專業的目標定為:培養適應時代要求和基礎教育改革需要,具有較高的職業道德和健全的身心素質,具備扎實的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知識技能與較強的教學實踐能力,能在特殊教育學校以及相關機構從事特殊教育教學、康復訓練等實踐,以及理論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復合型人才。
特殊教育類課程由理論課程和康復類課程構成,整個人才培養方案是一個等邊三角形的“三足鼎立”結構—底邊是教師基本功,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需要具備教師的基本功,能夠實施個別化教學,對應特殊教育理論課程;左右兩邊是言語康復和動作康復,對應康復類課程。此外,還開設了教師教育類課程、教學技能課程,培養學生的基本教師素養。
為了建立師資隊伍,我們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重組,對現有教師隊伍進行再培養;二是引進,引進特殊教育專業或相關專業的博士或碩士,同時鼓勵年輕教師攻讀博士學位;三是外聘,聘請優秀的一線特殊教育教師作為本專業技能方面的兼職教師;四是對外交流與合作,與國內外高校同行建立合作關系,聘請國內著名特教專家作為特聘教授,或邀請其來校開展講座和教學。
除了要讓本科生學習基礎知識,還要讓他們樹立從事特殊教育的信念。第一年,學校會定期組織學生到特殊教育學校參觀,請教師和校長作主題講座。第二年見習,目的是了解特殊教育及特殊學生,參與教學活動,進行課堂觀摩。第三年為體驗性實習,持續一學期,一周去一次或者兩周去一次。學生分成四組—言語康復組、動作康復組、情緒組(心理疏導組)和孤獨癥組進入班級,模擬教學及康復活動。第四年是畢業實習,為期一學期,學生需完成“三個一”,即教學(不少于10節課)、班主任工作和一個學生的個訓(含評估與個訓方案)。經過這樣的培養,我們的畢業生因工作認真踏實、熱愛特殊教育而受到特殊教育學校的歡迎,許多學生成為骨干。
2013年,特殊教育專業獲得學校設備費支持,2014年又獲得了云南省教育廳和中央財政的支持。有了經費,我就帶著隊伍前往全國各高校進行溝通、交流、參觀,了解特殊教育設施建設的情況,學習設備類型、技術參數等。
特殊教育專業對特殊兒童的分類很細致,很難按照障礙類型分別建設實驗室,于是我將思路轉化到特殊兒童的共性問題上:無論是哪種障別的孩子都可能會有語言問題、動作問題、心理問題。
因此,我們搭建起由言語康復評估與訓練、動作康復與訓練、心理康復與訓練和教師教學技能四個板塊共同組成的綜合實驗平臺,每個板塊都包括多個實驗室。這樣的綜合實驗平臺既能包含各種障別,又能把學前教育和心理實驗室資源整合起來,同時未來可在此基礎上擴展更多板塊,也可以在現有架構內下設更有針對性的實驗室。
為了更好地服務社會,我們的特殊教育實驗室面向公眾免費開放,家長可以帶孩子到校做康復治療。我們會給孩子建檔評估,由言語康復和動作康復專業的教師帶著學生,分組陪伴孩子,進行針對性的游戲和教學活動。這個公益活動已經開展了六七年,我們的特殊教育專業因此在社會上很有名氣,口碑很好。
(2)建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2015年)
2015年3月,云南省打算建設一個集管理、服務、科研支持、教研支持等職能于一體的特殊教育資源中心,面向高校招標。因為當時我們的實驗室建設初具規模,且提出的設想比較豐富,能夠充分考慮到政府、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使用需求,所以成功爭取到了機會,設立了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我們學校的是省級資源中心,下設培智、孤獨癥、職業、聾盲、學前和融合教育六個分中心。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150多個資源中心,每個市(州)、每個縣的資源中心的建設都在有序推進中。
(3)推動融合教育發展(2016—2019年)
2015年,我受救助兒童會云南辦事處的邀請,作為顧問專家參與項目推進,前往開展隨班就讀的學校,深入班級和課堂,觀察學生的成長、教師的教學。救助兒童會十分信任我,把云南的政策推進調研項目交給我做。這個項目在云南開展了兩期,第一期從2016年到2018年,在巍山和景東;第二期從2017年到2019年,在五華區。
項目期間,我每年向教育局、民政局、殘聯和衛計局就項目調研情況和政策推進情況進行一次匯報,督促部門間加強合作,做到信息共享。項目還包括教師培訓工作。2017年,我幫助五華區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團隊開展針對普通教師的融合教育培訓,也稱為“種子培訓”,目的是建設一支能開展融合教育的一線教師培訓者隊伍。經過三年的系統培訓,我們在第一批種子教師中篩選優秀教師,由他們繼續為五華區和昭通等五六個縣區的普通小學教師開展培訓,為云南培養一支能開展融合教育的種子教師團隊。
三、回看支邊生涯
概括我的支邊經歷,我覺得一共有三句話。第一句話是:“選一個人,就接受一座城。”我選擇了我的愛情,離開了家鄉重慶和承載青春歲月的北京,來到昆明。我見證了昆明的變化,認同感也越來越強,我覺得我的選擇是值得的。
第二句話是:“不給母校丟臉。”這個信念一直鼓勵著我在工作中不斷努力。既然到了這里,我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盡力,不能給母校丟臉。
第三句話就是:“本著良心工作,愿意為特殊人群奉獻。” “做特殊教育的老師要有慈悲之心。”這是樸永馨老師1986年在特殊教育課上曾經對我們說的一句話。特殊教育在許多地方還未被納入主流教育,但特殊兒童的數量并不少,孩子們等不得,這項工作需要有人去推動。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從事特殊教育,我覺得為這樣的人群做多少工作都是值得的,我愿意為他們多奉獻一點。
訪談后記
與男性偏向宏大敘事、以名利和榮譽為主線的敘述方式不同,女性的敘述,有屬于自己的語言、色彩和氣息。李里老師是一位講故事的好手,她的敘述不停留于粗略的時間、地點、人物和基本事件,而是充滿了溫暖清晰的細節—有穿著未干的衣服跑去上學、用讀書抵抗嫁人命運的母親;有對學生無限包容,在家訪時明確地表達喜愛和認可的初中班主任;有愛人寫的信、唱的歌、在看電影時望過來的帶笑的眼神;有春游時和同學們在郊外看過的一夜晚星;有讀書期間各位恩師的句句教誨;有偏遠農村地區的學校里搖搖欲墜的教室、土的操場、學生自己做飯用的小小的灶……正是這些生動具體的細微之處,帶領著我們跨越經年,輕而易舉地抵達老師記憶中從未蒙塵的閃光歲月,讓我們一度潸然淚下,一時又笑作一團。
從李里老師身上,我們能感受到愛的魅力。她愛自己的愛人,在更好的發展機會和愛情之間,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后者。她愛教育事業,在校內,她認真鉆研教學科研,設計人才培養方案、建設師資隊伍、建設綜合實驗平臺,投身特殊教育專業的建設事業;在校外,她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建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促進政府間多部門合作,開展種子教師培訓,為云南省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發展貢獻力量。對特殊兒童與特教事業的情懷與責任感,讓她敢于從零開始,一路耕耘,直至今日碩果累累,桃李滿蹊。
在李里老師身上,我們能看到女性力量的傳遞。至今難忘,李里老師提起母親時柔軟而自豪的神情。不愿初中畢業就嫁人而拼命抗爭的母親,勤奮學習、依靠讀書走出農村改變命運的母親,是她一生的榜樣。因為母親的成長經歷,她覺得讀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母親的養育方式,她事事獨立自主,不依靠任何人,在工作中努力進取。在李里老師身上,我們感受到了一種生機勃勃的女性力量,這種力量,由她的母親傳遞給她,又由她傳遞給我們,讓我們尤其振奮,深受鼓舞。
感謝李里老師,這段訪談經歷對我們而言十分珍貴,而訪談過程又十分幸福。感謝導師胡艷教授,讓我們有機會向一位優秀的支邊教師、一位閃光的女性前輩學習,也感謝導師在訪談和整理過程中給予耐心點撥和指導。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師口述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胡玉敏
李里
1966年出生,漢族,重慶永川人。1983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1990年研究生畢業后進入昆明師范專科學校(現昆明學院,以下簡稱“昆明師專”)工作至今。曾任昆明學院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教授、副院長,云南省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副主任,云南省心理學會理事,云南省殘聯兼職副理事長。曾獲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校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2014年獲昆明學院教學名師稱號,主編教材《班主任工作技能》獲2014年云南省精品教材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