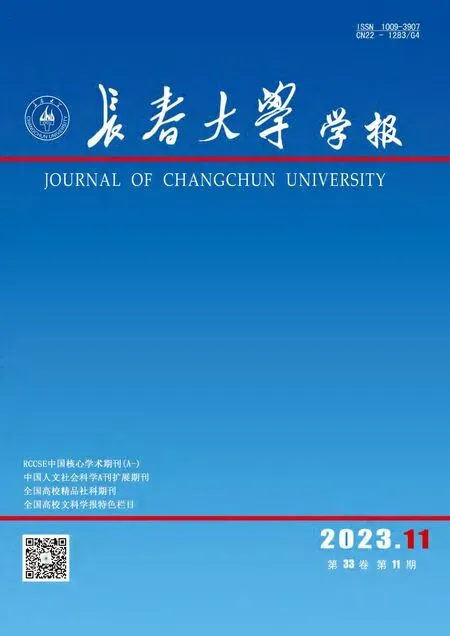七夕節形成再探
段湘懷
(湘潭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文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
七夕節傳承久遠,是我國的傳統節日,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根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的記錄,“七夕”指的是農歷七月七日夜晚,七夕節又叫“乞巧節”或者“女兒節”。在長期的民間傳承中,形成了諸如祈拜牛郎織女、乞巧、種生、接露水等民間風俗。可見,這一節日和我國民眾的生產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是我國傳統農耕社會里人們精神信仰的生動反映。對其進行探源研究,有利于呈現傳統社會人們的精神、思維特點和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揭示我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內涵。
關于七夕節的形成,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圍繞七夕節形成的時間及原因展開探討。
關于七夕節形成的時間主要有四種看法。一是戰國說。張君認為七夕節源于“漢之游女”神話,產生于戰國時期的楚國,而且當時僅在楚國流傳[1]。因楚人重漢水祠祀,他們所祭祀的“漢之游女”即織女,他們祭祀的婚姻愛情女神、兒童庇護神、執掌生育的處女神少司命身上都有織女的影子。但戰國時期并無記載織女同時執掌婚姻愛情、生育、庇護兒童神職的文獻,作者也沒有論證,故其說法不足為信。二是西漢說。陳連山主要以《西京雜記》所記載的賈佩蘭所言戚夫人事及漢彩女穿七孔針事為據,推斷西漢時期七夕作為表達愛情、祈求子嗣和乞巧的節日已經出現[2]127。不過,關于七夕節產生時間若以東晉葛洪所撰的《西京雜記》為據,則缺乏說服力,劉宗迪已經指出這是后人的想象和杜撰之辭[3]61。三是東漢說。楊琳根據崔寔《四民月令》記載的曝曬習俗以及周處《風土記》記載的七月七日飲食的不同,認為七夕節是東漢以來逐漸流行起來的,無論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情節還是乞巧風俗,都是產生于七夕節之后[4]268。劉宗迪也以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曝經書及衣裳,習俗然也”的記載為據,認為七夕節在東漢時期已經形成[3]63。但七夕指的是七月七日晚上,而這些文獻并未明確記載是晚上,也沒有與七夕祈拜儀式相關聯的記載。因此,只能說明七月七日是一個有特殊時令意義的日子,不能證明七夕節已經形成。趙逵夫認為“乞巧的風俗,最早見于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5],認為這一天民間設酒、脯、時果,祈請于河鼓織女,言牽牛織女二星神相會,從而認定這是關于乞巧節的最早記載。很多學者對于七夕節、乞巧節也都如此認為。但事實上,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并無相關說法,是后人誤傳所致,故結論自然缺乏說服力。四是晉代說。臺灣學者洪淑苓認為七夕風俗形成于晉代,內容包括觀星和乞愿兩項,但乞富、乞壽、乞子等和牽牛織女并無直接關系。至南朝宋,始有“穿針”習俗,至梁才有“乞巧”之說。“穿針”和“乞巧”才與牽牛織女建立起直接的關系[6]。其關于七夕風俗形成于晉代、至梁始有“乞巧”之名目的觀點是客觀中肯的。
關于七夕節形成原因的探討也有三個切入角度:一是從“七”特殊含義的角度展開探討。楊琳認為七夕節形成的民俗依據是“七”為人的生日及七夕為乞子之日,意思是“七”在民間為人日,它與乞子習俗促成了七夕節的形成[4]269-272。陳連山也認為七夕節的形成在于“七”這個數字與人類的創造繁衍有關[2]125-127。不過,以上研究只能解釋七月七日成為一個有著特殊民俗意義的日子的原因,而無法解釋七月七日晚上舉行相關儀式的七夕節的形成原因。二是從夏人歷法的角度進行探析。吳天明認為七夕的形成與原始夏歷的紀日方法有關,“七”是夏人心中的圣數,主要源于將宗教信仰、感情、月亮盈虧規律、女人行經規律調和起來的“一月四分之術”[7]134-135,又因為牽牛織女是夏人的先祖、先妣神,故夏人選擇在七月七日祭祀他們[7]150。這個觀點具有啟發意義,但并未論證牽牛織女是夏人先祖、先妣神的原因;既然如此,為何直到魏晉時期才形成當日夜晚專門祭祀牽牛織女的七夕節?作者并沒有闡明這個問題。因此,其結論略顯潦草,缺乏說服力。三是從牛郎織女的原型角度探析。王孝廉根據《荊楚歲時記》所記錄的乞巧儀式推測七夕乞巧的民俗源于古代織女桑神的原始信仰[8],這種信仰基于牛郎織女神話傳說而形成。洪淑苓在分析七夕節形成的原因時即持此觀點。這個結論成立的前提之一是乞巧節與七夕節是同一節日。然而,乞巧民俗的產生要晚于七夕節的形成,七夕節又叫乞巧節是后來的事情,故其從桑神原始信仰的角度來解釋七夕節的形成就不可信了。日本學者小南一郎認為,七夕節和牛郎織女神話傳說出自一個共同的母體:西王母。他認為牛郎、織女最初是由西王母所分化出來的一組具有陰陽交會意義的對偶神;七夕節的產生則與古時人們把西王母當作愛情守護神、商媒神有關。由于牛郎織女與人們日常生活關聯緊密,因此逐漸演變成了戀愛故事,形成了節日習俗[9]。這個研究思路頗有新意,但必須要證明西王母信仰早于牽牛織女星神信仰,這明顯與文獻的相關記載不相符,故結論不足為信。
本文認為,七夕節最遲于魏晉時期已經形成,最早的文字記載見諸時人周處的《風土記》,節日的主要內容是人們祈拜牽牛織女,向其乞富、乞壽、乞子。乞巧習俗是七夕節形成后才興起,東晉時已經出現,但最早的記錄文獻是南朝宗懔的《荊楚歲時記》。七夕節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具有獨特民俗意義的七月七日信俗與牽牛織女神話傳說的融合;二是牽牛織女傳說的獨特內涵契合了當時民眾的內心需求和愿望,即長壽、富貴、乞子。
一、七夕節形成的時間
作為一個節日,在探討其形成的時間時必須考慮構成節日的核心要素。“歲時節日,主要是指與天時、物候的周期性轉換相適應,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具有某種風俗活動內容的特定時日。”[10]從這個定義可以概括出構成節日的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有相對固定的特定時日,一是有相應的民俗活動內容。要確定七夕節的形成時間,必須重視這兩個核心要素。首先,民間舉行儀式的具體時間必須是七月七日夜晚,而不能是籠統的七月七日。因為“七夕”即七月七日夜晚,跟七月七日有顯著區別。古人記載相關事項時,往往都有明確、具體的時間。如崔寔《四民月令》就是按月分別介紹各種民風民俗,其中“七月”條又具體到日,一一介紹各種民間行事。其次,七月七日夜晚民間確實有各種相應的儀式活動。如果只有時間而沒有相關儀式的記載,就不能作為七夕節已經形成的證據。如東漢末應劭的《風俗通》雖有“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的記載,提到了“七夕”,但只提到時間而沒有具體的信俗內容,因此不能作為“七夕”已經產生的依據。我們現在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記載是魏晉時周處的《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幾宴,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愿,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耀五色,以此為征應,見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11]據此可以斷定:七夕節就是在七月七日夜晚舉行祈拜牽牛織女星神的節日。在最初的節日習俗里,人們主要向牽牛織女乞富、乞壽、乞子,七夕節最遲在魏晉時期已經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七夕祈拜牽牛織女星神儀式中,民眾只是乞富、乞壽、乞子,并無乞巧的風俗。直到托名西漢劉歆、實為東晉葛洪所輯抄的《西京雜記》出現,才有關于七月七日乞巧的說法:“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俱以習之。”[12]12不過,目前所見最早明確著錄民間乞巧風俗的文獻卻是南梁宗懔的《荊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婦人結彩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符應。”[13]而在文人詩歌里,整個魏晉時期詠七夕的詩歌很多,但均無與乞巧有關的詩句。一直到南北朝,始見宋人劉駿《七夕詩》描寫了乞巧風俗:“開庭鏡天路,馀光不可臨。沿風披弱縷,迎輝貫玄針。”到南梁時期,文人才比較頻繁地在詩歌中描寫乞巧節[3]75。當時,學者宗懔把民間的乞巧風俗載入了其專門記錄楚地歲時節令風物故事的筆記體文集《荊楚歲時記》。無論是詩歌還是筆記里的乞巧風俗,自然都是來自民間,從中可以清晰看到乞巧風俗由產生到逐漸流行的過程。可見,乞巧風俗形成于七夕節之后,是七夕節發展過程中新生的民間風俗。因此,如果認為自古以來七夕節就等同于乞巧節,從乞巧來追溯七夕節的相關風俗及成因是行不通的。劉宗迪根據崔寔《四民月令》記載的曝曬習俗認為七夕節在東漢已經產生,并且認為乞巧、祭拜織女的習俗也已形成。《四民月令》之所以沒有這些習俗的相關記載,是因為該書“主要著眼于與民生日用、田園經營息息相關的各項農事,歲時祭典則非措意,或者是因為年節風俗,早成慣習,為百姓所周知,因此無須在書中諄諄教導。”[3]62這明顯與《四民月令》所涉及的內容不符。如《四民月令·正月》就記載了正月擇吉日為滿十九歲的男孩舉行成人禮的習俗:“是月也,擇元日,可以冠子。”[14]6還記載了在上旬天干逢“丁”的一天祭祀道神、在上旬“亥”日祭祀善神和先祖的習俗:“乃以上丁,祀祖于門,道陽出滯,祈福祥焉。又以上亥,祠先穡及祖禰,以祈豐年。”[14]7而關于周處的《風土記》也沒有提及乞巧的問題,他解釋為“雖未明言穿針乞巧,但他在說到世人向河鼓、織女二星‘乞富、乞壽、乞子’的祈愿活動時,已暗暗道及乞巧活動了。”[3]67這樣的解釋略顯牽強。所以,七夕節最遲在魏晉時期便已形成,而七夕乞巧風俗則形成于東晉,南梁時開始廣為流行。
二、七夕節形成的動因
七夕節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在七月七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人們向二位星神乞富、乞壽、乞子。如果要追根溯源,就要圍繞這一核心內容展開。可從以下兩個角度入手:一是人們選擇七月七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的原因;二是人們選擇牽牛織女向其乞富、乞壽、乞子的原因。
(一)人們選擇七月七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的原因
古人在七月七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主要因為這天是一個有著特殊民俗意義的日子,而牽牛織女也是在這一天相會。
“七”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頻繁出現的非常神圣的數字,《詩經·大東》里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周易》說“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佛教有“七寶”之說,古代典籍的命名更是經常使用“七”字,如劉歆《七略》、枚乘《七發》、傅毅《七激》,等等。葉舒憲解釋,因為數字“七”具有宇宙象征的意義,不僅象征著無限的時間,也象征著無限的空間:“由于現實的三維空間只有六個具體方位,加上中間為七,已經到了極限,無以復加了,所以七就成了宇宙數,表示無限大的循環基數,并因此而產生了法術和禁忌的神秘意義。”[15]83而七月七日又是兩個“七”的重復,在人們的認知中無疑更加神秘。如《太平御覽》引《淮南子》的記載:“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靨,即當滅矣。”[16]149崔寔《四民月令》“七月”條記載:“七日遂作麹。及磨。是日也,可合藥丸及蜀漆丸;曝經書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也。”[14]55這些記載說明七月七日在時人心中有一種神秘力量,因此,人們利用各種儀式活動紀念、祈福。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王室式微特別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原始的天道信仰逐漸受到懷疑。人們不再盲目崇信天地神祇,人事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這就導致了傳統的歲時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的信仰由上古的天道自然崇拜逐漸轉向以人為核心的祖先崇拜。因此,“秦漢以后,歲時信仰與上古歲時信仰比較已經出現性質的局部改變。時令祭祀雖然依舊是節俗的主要內容,但已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出服務于民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質,歲時中的人文因素多于自然宗教因素。歲時信仰呈現出多元混合的形態。”[17]40-41正因為這種轉變,當時的七月七日信俗活動,如曝曬、作干糗、采葸耳等往往都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系密切。
東漢晚期,鵲橋之說已經成型,牛郎織女七月七日鵲橋相會已在民間廣為流傳,體現了民眾對這一神話傳說的關注。因此,當帶有原始宗教信仰性質的歲時信仰逐漸向服務于民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質轉變時,體現民眾美好愿望的牛郎織女神話傳說終于和古已有之的七月七日民俗信仰慢慢結合起來了,形成了穩定的節日儀式內容,且逐漸推廣、影響日大,到魏晉時期終于被諸多文獻記載。有研究指出:“歲時生活與民間傳說的結合大概開始于兩漢時期,傳說依托一定的講述時間,有利于它本身的傳承;歲時節俗有了傳說作為其符合時世的新解釋,從而增強了歲時節日在民眾生活中的精神地位。”[17]62牛郎織女神話傳說的主題精神本來并不符合重視孝道的漢代社會倫理觀念,正是因為與七月七日民間信仰的融合才獲得了傳承發展的空間,并具有了蓬勃的生命力。而七月七日的民間信仰最終能發展成七夕節,信仰內容不斷豐富,影響日漸深遠,也正是因為有了牛郎織女神話傳說的融入而擁有了新的活力。
七夕節的時間定于七月七日夜晚,還與人們觀星、禳星的實踐活動有關。“上古歲時主要是以時令祭禮的形式出現,那些從日常生活中凸顯出來的時日其首要的意義在于它們與天時的對應。人們將與天時相對應的時間點視為神秘的節點,采取種種祭祀活動以愉悅天神,襄助人事。”[17]16人們要祭祀牽牛織女星,必須且只能在夜晚,因為此時才能看得清天上的星星。杜牧的“天街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寫的就是失意的宮女晚上看牽牛織女星的情形。《管子·侈靡》言:“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熺,有時而熰,有時而朐。”[18]講的就是古時的祭祀必須嚴格遵循時令。
綜上,正是牛郎織女神話傳說和七月七日信俗的融合,出現了人們在當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星神的風俗,從而為七夕節的最終形成提供了可能。
(二)人們選擇牽牛織女向其乞富、乞壽、乞子的原因
七夕節最晚在魏晉時期已經形成,周處《風土記》中的相關記載即為佐證。關于七夕節具體信俗形成的社會動因可以結合兩漢魏晉時期的社會特點展開探討。
1.兩漢魏晉時期世風尚富,而織女主珍寶
物質條件決定生活水平,追求財富是人的普遍心態,故司馬遷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19]2834漢初實行休養生息的惠民政策,孝惠高后時放松了對商賈的律令。商人活動范圍擴大,商業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漢興,海內為一,無關梁,張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19]2826社會現實激發了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到漢文帝時,甚至實行貴粟政策,“使民以粟為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20]161,意味著財富可以買官或抵罪,進一步刺激了社會對財富的追求。賈誼曾上書文帝說:“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番,釋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谷不為多。”[20]166指出了人們追求財富、棄捐農事的社會現實。東漢王符在《潛夫論·浮侈》中記載,“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21]148,“富者竟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21]148,生動地描繪出漢代世人追求物質享受、競相攀比的不良現象。魏晉時期,大一統格局破裂,商業發展受挫。總體情況是南方商業活動盛于北方,豪門氏族官僚資財勢力強大,掌握了商業重權。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乘機鉆營謀利。“入晉以后,地主世族佃客部曲的階級形式漸成,王公世族軍將官僚,保有逾量之田宅,逾量之生產品,并擁有多數之部曲奴隸,供其驅使;于是興生求利,殖貨聚斂,成為王公世族通常之活動。”[22]而普通人也想盡辦法謀求財富,一時出現了很多巨富之人,如趙掇、丁妃、鄒甕等,他們家業千金,車服堪比王侯。據《南齊·郁林王紀》記載,郁林王曾對豫章王妃庾氏說道:“今日見作天王,……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23]郁林王居然羨慕市邊屠酤兒之富,可見當時人們對財富的渴望。漢魏時期的墓穴石棺中大量關于人們的起居出行、宴飲行酒、樂舞百戲、田獵習射等畫像就是時人追求財富的真實寫照。研究者指出:這些表現墓主生前富貴生活的畫像之所以在墓葬中出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墓主“祈望能將生前的財富和榮華富貴的生活帶入另一個仙境”[24]。
可見,兩漢魏晉時期,世風尚富。而織女作為古老的星神,在世人的觀念里本就與財富有關。《開元占經·織女占十二》引《春秋合成圖》言:“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寶。”[25]625《史記正義》也記載:“織女三星,在河北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26]1233顯然,兩條記載中的瓜果、收藏、珍寶、絲帛等都與財富有關,織女星神主富的神職非常明確。因此,人們在祈拜牽牛織女時自然會向其求取富貴了。
2.兩漢魏晉時期人們追求長生,而牽牛織女主通天之關梁
兩漢時期,鬼神術數、圖讖星占、神仙之說十分盛行,追求長生不老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現象。漢代“神仙信仰和追求長生不死的風氣不斷擴散,逐漸成為一股社會潮流,一種普遍的精神追求”[27]。而魏晉時期,玄學勃興,形成于東漢的道教因玄學的影響而流傳日廣。而且,經葛洪等人改造后的道教更加契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與封建政權的聯系日趨緊密。葛洪對神仙之說深信不疑,其《抱樸子·內篇》和《神仙傳》在內容上相呼應,其中心思想就是“神仙實有、仙學可致”[28]。道教以其長生成仙的華麗謊言一時在封建統治階層吸納了大批信眾。“魏晉以來,……人們提倡修身養性,追求長生不老,希冀得道成仙。”[29]273煉丹吃藥、服食養生蔚然成風,這時期已有了自成體系的具體修煉成仙之法。
《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張守節《史記正義》解釋為:“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26]1222河鼓儼然成為主管天關、威儀無比的大將軍。據學者們考證,河鼓三星中間的河鼓星才是最初的牽牛星。隨著天文學的發展,為了便于觀察天象,遂將距赤道較近的一組星命名為牽牛,而之前的牽牛則改名為河鼓。但在具體的使用中,人們往往習慣將牽牛、河鼓混用。如《太平御覽》引《日緯書》文“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主關梁”[16]149,直接把牽牛當成了河鼓,但仍強調了其主管天梁的地位。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解釋《史記·天官書》中“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時,引西漢末年讖緯之士所著的《春秋元命包》言:“潢主河梁,所以度神,通四方。”又引東漢名臣宋均言:“天潢,天津也。津,湊也,故主計度也。”[26]1221可見“天津”就是跨越天河的橋梁或者津渡,通過“天津”可以讓神仙渡過天河,通達四方。而河鼓也就是真正的牽牛,正是主管這一通道的神,可見其位置的重要性。凡人欲順利成仙的需借助牽牛星的力量,王熠就曾詳細論證過牽牛主天關、天梁[30]。《開元占經》曾引東漢天文學家、星占家郗萌言“織女一名東橋”[25]625,織女星神這一別名中的“橋”也有通關之梁的意思。可見,在漢人眼里,織女和牽牛一樣,同樣都擁有主管通天關梁的神職。漢代墓室畫像上出現牽牛織女圖像,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人們在七月七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時,向二星神求壽,希望二星神能庇佑他們長生不死,成仙通天。
3.兩漢魏晉時期乞子之風盛行,而織女主婚嫁
生育是關系到人類繁衍、血脈傳承的大事,一直以來備受人們的重視。如上古的高禖神信仰,《禮記·月令》記載:“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講的是仲春之月,天子帶領妻妾祭祀生育女神高禖之事[31]。《孟子·離婁上》甚至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32]隨著封建集權國家的建立,父權中心的禮法倫理制度逐漸完備,傳宗接代、生子廣嗣的現實要求使社會的求子之風變得愈加頻繁。《大戴禮記·本命》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33]女人無子就是一大罪狀,需要承擔被休的后果。因此,漢時人們不僅祭祀高禖求子,而且求助于巫祝。《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就記載了皇后衛子夫剛懷孕時,漢武帝即為其立禖求子之事:“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20]623林富士也通過對漢代巫者的研究,指出其具有左右生育的職能:“雖然生育是一種自然的生理現象,可是漢人卻相信生育會受到鬼神力量的影響,并且認為可利用祭祀、祝詛的手段,為自己求子或使他人無法孕育子女。”[34]到魏晉時期,因連年戰亂人口銳減,“要安定社會,恢復殘破的經濟,就必須盡快地增殖人口,這已成為當時人們的共識,生兒育女也就成為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全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29]212。這一時期,雖然社會動蕩、經濟蕭條、扶養困難,可人們還是想方設法求子:“向各種神靈求子是這一時期求子活動中最常見的做法。”[29]215
《漢書·天文志》記載:“婺女,其北織女。”[20]200《史記正義》記載:“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26]1223“織女三星,在河北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26]1223《開元占經》又引《甘石星經》言:“須女動,則嫁娶。將有嫁娶,占于須女。”[25]585從這些記載可知,織女有三星(中間最亮的那顆就是傳說里的織女星),主果蓏絲帛珍寶;須女即婺女,有四星,主嫁娶。織女三星在須女(婺女)四星北,距離并不遠。因兩者名字僅一字之差,故容易被混淆。夏鼐曾指出:“婺女宿原為4星,但是唐代的二十八宿竟有做3星的。”[35]南陽白灘漢墓出土的東漢時期的牽牛織女畫像石(圖1)中的織女星象也畫了四顆。可見,人們確實容易把織女和婺女相混淆。周處《風土記》記載的七月七日夜晚祈拜牽牛織女時,人們向二位星神乞子的行為,很可能把主嫁娶的婺女的神職錯置到了織女身上。

圖1 牽牛織女畫像石(源自王建中的南陽兩漢畫像石)
此外,當時人們認為七月七日非常神秘,一直有著許多特殊的信俗。葉舒憲曾指出正月“七日為人日”是中國創世神話在節俗禮儀中的重構[15]90。而根據列維-布留爾的研究,原始人的思維是不同于今人的原邏輯思維和神秘思維,“構成這個思維的集體表象及其相互的關聯是受互滲律支配的”,并不考慮邏輯矛盾律[36]。故包含了兩個“七”的農歷七月七日在原始思維中很可能早就具有了生命創造、新生等義。如《漢武故事》載漢武帝生于七月七日:“帝又夢高祖謂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于猗蘭殿。”[12]93《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言宮中樂事》記載了戚夫人侍兒賈佩蘭所言之事:“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12]26這兩則記載都蘊含了生命創造、新生的意象。古語言“禮失求諸野”,后世人們在七月七日向織女星神舉行的乞子儀式里,或許就蘊含著遠古七月七日創生意識的“活化石”。
由于七月七日蘊含了生命創造、新生的獨特意義,織女身上又移置了本屬婺女的主婚嫁的神職,故人們在晚上祈拜牽牛織女時,自然會向其乞子了。
三、余 論
歲時節日是人們努力適應自然及社會現實的產物。探討節日形成的原因時需注意幾個要點:一是先要確定其產生的時間,進而探究節日產生的自然社會動因。二是要根據具體的節日儀式、活動等進行溯源分析。因為這是節日的核心內容,該內容必然與節日產生的時間存在內在的邏輯關系。離開內容探源分析等于緣木求魚,無法得出有價值的結論。目前,學界關于七夕節形成的研究在這兩點上明顯關注不夠,特別是對七夕節形成之初的乞富、乞壽、乞子行為缺少關注,甚至直接把七夕節等同于乞巧節,過于簡單武斷,導致了很多不實之論。本研究在這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歷七月七日已成為一個充滿情感色彩的特殊節日,承載著世人最虔誠的期盼。在這一天,人們不但延續了結彩縷、上高臺、穿針乞巧之俗,還增加了一些似與牽牛織女星神并無明顯關系的諸如兜售摩睺羅、水上浮、谷板及種生、祝七娘、拜魁星等習俗,且遍及全國,輻射海外。關于這些習俗產生的緣故,雖已有學者展開了研究,如楊琳分析了乞巧行為背后的文化意義,劉宗迪等學者探討了摩睺羅的來源問題,但還不夠深入。因為七夕節實在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寶庫,其深厚的文化內涵有待學界更深入地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