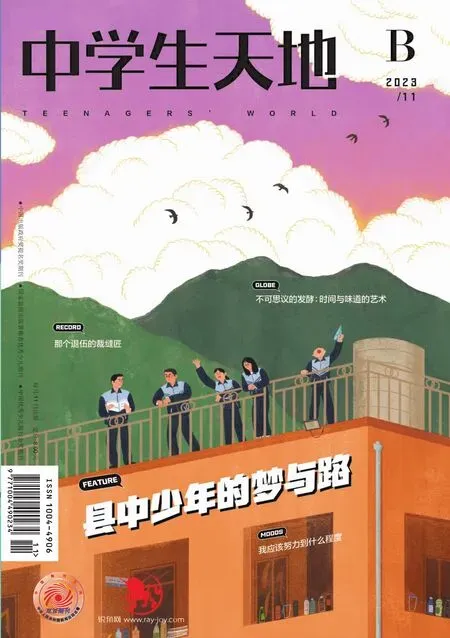縣中觀察手記:人生應是曠野,不是軌道
這里有一群不是中學老師卻長期與縣中學生相處的年輕人, 他們來自 “PEER 毅恒摯友”。 這是一個致力于促進城鄉教育公平的教育公益組織,自2015 年起,它在湖南、廣西、貴州的10 所合作中學設立了自主設計的PEER空間, 每個空間每學期都會駐扎1~2 位長期志愿者,和中學生們共同打造縣中里的“學習空間、生活空間和公共空間”。
他們稱呼自己為“摯行者”,可理解為“觀察者、陪伴者、改變者”之意。 他們為縣中學生打造空間,進行朋輩輔導,組織活動,開發興趣課程,讓更多學生能夠被看見、被聽見、被理解。 他們希望通過微小的行動,讓縣中學生擁有曠野人生。
讓穩固的搖晃,讓搖晃的穩固
摯行者:鄧鵬卓
駐扎學校:湖南省懷化市溆浦縣第一中學

如果你問我“摯行者”是一個怎樣的角色,我會回答是和一群十五六歲的孩子一起同行的人,我們一起更好地認識自己、改變世界,這也是“PEER”這個教育類非營利組織存在的意義。
PEER 空間是校園里另類的存在,在按部就班的學校系統下面,其實有很多沒有被看見的東西,可能是情緒,也可能是更多的屬于人的可能性,而PEER 空間就是要讓這個原本穩固的系統有一絲縫隙,讓它更具彈性。
和大家分享一個學生的故事。曾經有個女生跟我說想要報名參加“友毅思”,那是“PEER”支持學生在校園內外開展的且與可持續問題相關的公共行動項目,但對于選題她卻面露難色,之后我才知道,去年她也參加了“友毅思”,但因為沒有在跨校比賽中拿到獎,所以很沮喪,那次比賽也給她留下了心理陰影。
這種情形很常見,經常會有學生來找摯行者傾訴煩惱。“打碎”他們的可能是同學的排擠、師長的批評、成績的下滑等,但問題是往往等不及他們開始思考,下一次“打碎”可能就來了,因為他們的生活被填得太滿了。在一個充斥著外部評價且評價標準單一的環境里,人就會想通過獲得外界認可來找到一點點自己存在的價值,當這種認可沒有及時出現時,他們就很容易懷疑自己。
擺在我面前的難題是如何幫助他們重建信心。
所以當那個女生之后來PEER 空間找我聊選題時,我就跟她說:“現在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先做,喜歡什么主題就做什么,大不了咱們再換。”她點點頭,很快就坐到電腦前開始查資料、做展板。她選擇了“延續自然”主題,組織了和世界地球日有關的活動,但沒什么人參與,中途她還經歷了班主任和家長反對、小組成員幾乎全員退出等狀況……這些按理說足以構成“打碎”她的理由,但都沒有影響她的干勁,不過月考還是絆住了她的行動,她為此退出了一段時間。
最后她還是回來了,而且找到了靠譜的新組員。她們開始做“女性主義”主題,成立了“我們(women)編輯部”。她們在校園內外組織開展了與反性侵相關的書影音推薦和詩文征集活動,創建了與美麗羞恥相關的問答墻及母親節當天的真人圖書館等。由此可知,即便是在縣城,關于“女性主義”,學生能想、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作為摯行者,我覺得我們能做的事情其實只有一件,那就是:看見并且理解學生,讓他們看到學校這個系統之外更多的可能性。
在PEER 空間里,我看到了從我上學那個年代起到現在這么多年來沒有改變的一些東西,也許來自系統,也許來自個體,也許來自其他地方。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堅定地相信,在學校里,我們要更多地去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而這也是我們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Q:你在文中反復提到了“系統”一詞,可以聊一聊在“PEER”做志愿者的過程中,你對于縣中學校系統的看法嗎?
鄧鵬卓:說實話,我覺得自己還不具備回答這個問題的能力。 我在文中所提到的“系統”指代的是任何一種忽視人的個體多樣性的環境。 縣中的學校系統如果僅從我的觀察出發, 我覺得一個最明顯的特征是評價標準單一,這就導致除了學習成績之外,很多東西會被掩蓋和壓抑,比如心理健康、社會情感等。同時,為了更高效地達到目的, 這個系統也會給身處其中的人鋪設好一條看似合理的路,讓人逐漸失去選擇的自由。在這種不適又熟悉的環境里生長, 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力氣成為“幸存者”。
縣中停電的晚上,我們舉辦了一場生命故事會
摯行者:索大川
駐扎學校:湖南省邵陽市城步苗族自治縣第一民族中學
我不知道怎么就把“停電”和“講故事”聯系到了一起。在學校一個停電的夜晚,在小小的PEER 空間,我們舉辦了一場生命故事會。
小杰是第一個抽問題回答的學生,他是我在城步縣中遇到的最有想法的學生之一,他會和我討論民主到底是什么、游戲和現實中的快樂到底有沒有區別……面對“童年時你最喜歡的人是誰”這個問題,他只是癱坐在沙發里,聊起他的二姨。二姨是他小時候調皮吵鬧被揍時的避風港,是經常給他買好吃的、帶他玩耍的大伙伴。他笑著,眼睛瞇成一條縫。“現在我來一中讀書了,一個月也不能回老家一次,能見到二姨的時間也少了。但我最喜歡的人還是我的二姨。”
阿亮選擇主動分享自己的理想。他談到自己以后想搞創作,想成為up 主,錄制吉他視頻和自己的原創音樂。可之后,他的神情突然嚴肅起來,說自己現在還是想考一所好的專業學校,如果是重點的最好,但這不太容易……講完他便無言了,只是回過神后,又露出了他招牌式的笑容。
那天晚上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座僅有的兩名女孩。其中一個女孩抽到的問題是“你最好的朋友是誰”,她和我們談起了“香菇”。女孩講故事的時候一直在玩紙條,偶爾和我進行眼神交流。她說“香菇”和她很像,她們都是經常轉學的學生,所以不約而同地關注起對方,但“香菇”從來不吃學校食堂的飯,于是自己經常給她帶零食吃。“她為什么從來不吃食堂的飯呢?她好瘦啊……”說著說著,女孩的眼角泛起了淚光,我也有些不安了起來。我當時很想問,那個女孩現在在哪里,她們還有沒有聯系,但我忍住了,我只是請同學們一起感謝她分享的故事,這或許是那個夜晚我們能給她的最合適的禮物。
另一名女孩沒有講出她的故事,至少,沒有講完全。她抽到的問題是:“最能給你安全感的地方是哪里,在那里發生過什么”我當初設置問題時,想的是有時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釋放也不一定是件壞事,可女孩的眼眶有些閃亮的光點。“最安全的地方,應該是在我媽媽身邊吧……”她已經有點回答不下去了,我只能盡力溫柔地對她表示感謝和安慰。
事實上,在讀者看到這篇文章時,我就違反了一開始自己定下的約定,把故事帶離了那個空間。但我相信,這些故事是真實而有力量的,把故事講出去,能讓更多的人看見那些被忽視的主體的另一面。
最后,我送給他們每個人一只千紙鶴,感謝他們帶來的故事。他們可能不知道,我在每一只千紙鶴里都寫上了一句話:你很棒,要相信自己呀,加油!

Q:學生們愿意來參加這樣一個“生命故事會”,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對摯行者有足夠的信任,那在PEER 空間,摯行者是如何與學生們建立信任和朋友關系的呢?
索大川:PEER 空間的項目官員和摯行者們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和思考,我只能分享我個人的想法。 我當時所在的學校,行政樓3 樓的PEER 空間和教學樓內的教室,兩者天然地呈現出不同的功能,劃分出特別的場域。 PEER空間的志愿者就是會被同學們無條件地信任。 當時有個同學說,TA 每個學期都會來看一眼, 如果和某個志愿者投緣的話,這個學期TA就會積極地來到空間。所以,這種信任的建立有一部分緣于PEER 空間散發的 “特質”,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源于私人關系。
隱藏的“小鎮大玩家”
摯行者:王熹妍
駐扎學校:湖南省懷化市中方縣第一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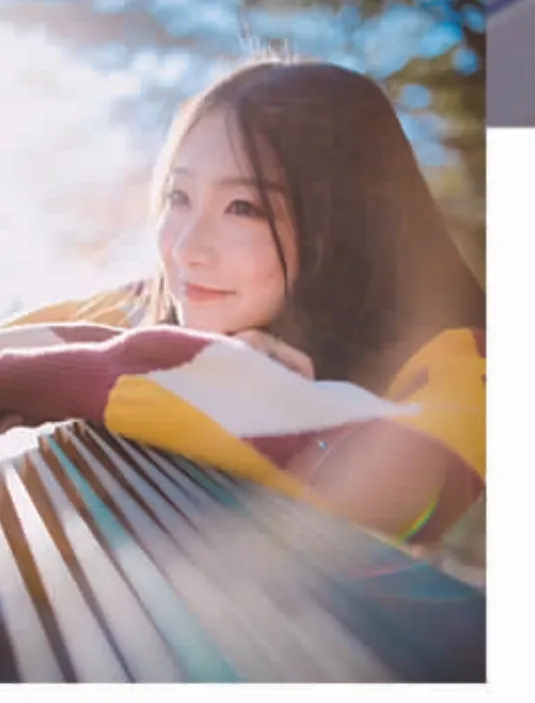
“小鎮做題家”似乎漸漸成了縣中學生的代名詞。在真正駐扎于一所縣中前,我也持有相同的觀點:囿于地域和原生家庭,縣中學生是只會做題、認為只有做題才能改變命運的群體。但當我駐扎縣中兩個多月后,我改變了原來的觀點。他們有太多超脫于“做題家”身份的東西值得我去講,比起“小鎮做題家”,很多學生給我的印象更接近于“小鎮大玩家”。
他們可以是“漢文化迷”“B 站大亨”的手作玩家。
學生小L 有足足兩大盒自制手作首飾,而且每個首飾都不一樣。他會把這些手作首飾拿到漫展上售賣,他還有自己的B 站賬號,會更新有關漢文化和手作的內容,粉絲不少。小L 也做過學校漢文化知識競賽的策劃者,活動的策劃案撰寫、號碼牌制作和主持都由他負責。晚休時,他會來PEER 空間做活動PPT、出題,邊出題還邊考我,比如漢服的形制有哪些,采用漢服作為學位服的是哪所大學,漢服復興運動興起的標志是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反倒是學生給我的啟發更多。
他們可以是“財務自由”的繪畫玩家。
學校的一個美術特長生已經能靠接別人的約畫委托基本實現財務自由。我對此很感慨,就詢問類似情況的學生,他們哪來時間做這些。他們大部分對此輕描淡寫:喜歡做的事擠擠時間總能做;晚自習太無聊了,偷偷做;能賺錢的差事誰不做……我和朋友開玩笑,如果自己再晚幾年出生,那完全不是現在這些學生的“對手”。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娛樂方式和愛好特長,哪怕那可能是高壓催生的產物。在這個網絡時代,縣中學生的信息并不閉塞。
他們還可以是“吃書”的閱讀玩家。
我剛來沒多久,有個同學塞了一本《呼蘭河傳》給我,說:“讀完這本書有一種吞了一把鈍刀的感覺。”我特別相信,能主動給我薦書,又能把閱讀感受描述得如此簡潔而貼切的學生,一定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還有幾個學生已經把大家耳熟能詳的熱門書都讀完了,還經常會因為書荒來找我推書,我驚訝于有些學生的閱讀量不比我少。“是在‘吃書’嗎?”聽到小Z 同學說她用兩天時間讀完了《胭脂扣》,我如此驚嘆道。
他們不是“小鎮做題家”,或者說不都是。他們的視野早就飛出了課本。要真正讀懂他們,需要一個“周旋”的過程。通過這些新的、零碎的觀察,我會說,為群體貼標簽,真的會淹沒這些在思考、在發光的具體靈魂。Q:你是否想過,文中提到的學生僅僅是縣中學生中的少數群體,正是因為有“大玩家”屬性,他們才愿意去PEER 空間和你相遇。 你對于更大范圍的學生群體和學生生活有過觀察和總結嗎?
王熹妍:我有時會覺得PEER 空間是“被學生選擇的”——雖然我們以開放的姿態歡迎每一個學生參與各種活動,但學生在繁忙的課業中有自己的價值排序。 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本身就喜歡“玩”的學生更傾向于主動與我們相遇。 也有很多學生,本來是老師和摯行者眼中相對意義上的“做題家”,但因為看到活動宣傳海報、偶然與摯行者進行過溝通……他們突然就對空間產生了興趣, 展現了一直沒有被發現的潛質。 比如我在PEER空間里添置了一架古箏,有個從未來過的學生偶然經過進來彈了彈,彈得很好,她的朋友都在一旁評價說:“我第一次見到你這樣的一面誒, 彈琴的樣子。 ” 我覺得PEER 空間就是一個給人提供“豁然開朗”契機的平臺,也是給人“重新認識自己、認識身邊人”機會的平臺。 沒有人天生是“做題家”,也沒有人天生是“大玩家”,跳出空間觀察整個縣中生態也會得出同樣的答案——他們缺的不是天賦和興趣,而是機會和平臺。
- 中學生天地(B版)的其它文章
- 錦灰堆:抱殘守缺的綺麗之美
- 問題不大
- 縣中少年的夢與路
- 印記
- 生長,在文字照亮的世界
- 文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