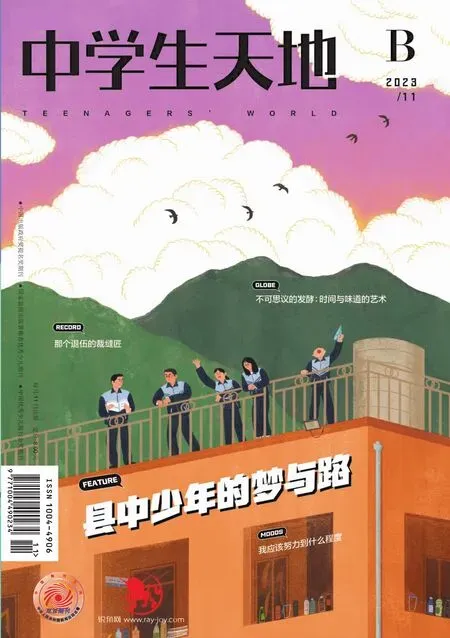打開電影,看“小鎮青年”
文/楊 毅(天津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講師)
一
在中國,小鎮正在快速崛起。2020 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3.89%,僅用了30 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鎮化歷程。短短10 年間,中國新增了2000 座小鎮。如今的中國小鎮,生活著逾3.6 億中國人,而在未來10 年,這個數字將可能超過5 億。
當我們聊到小鎮時,不可避免地會聊到“小鎮青年”,根據媒體發布的《相信不起眼的改變:2018 年中國小鎮青年發展現狀白皮書》的定義,“小鎮青年”指出生在三四線城市及以下的縣城、鄉鎮,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會周邊城市打拼的青年。快手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走向更好的自己:2019 小鎮青年報告》顯示,我國2.3 億小鎮青年正在用他們積極的進取心和創造力,打造著一個燦爛奪目的未來世界。
“小鎮青年”這一稱呼并非最近才出現,而是伴隨著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出現的獨特現象。比如電影《人生》中的農村青年高加林,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將大城市看作他們的理想乃至夢想之地,于是毅然前往上海實現人生價值。“小鎮青年”之所以在近10 年成為熱議話題,是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下沉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商業配套日益完善,生活在鄉鎮或縣城的年輕人群的規模不斷增長,這使得“小鎮青年”逐漸成為消費市場的主力軍和新勢力。
事實上,對“小鎮青年”話題的熱議始終伴隨著新聞媒體的渲染,都市青年利用網絡媒介等優勢資源,建構出獨特的文化品質,同時,“小鎮青年”也被建構成與都市文藝青年具有不同審美趣味的群體。

二
早在“小鎮青年”這個概念被媒體曝光之前,已經有很多導演通過電影來聚焦這類人群。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章明、賈樟柯等第六代導演對小鎮的刻畫與以往電影產生了明顯的不同。他們將小鎮作為電影敘事的地域空間,并且聚焦“小鎮青年”作為電影著力表現的主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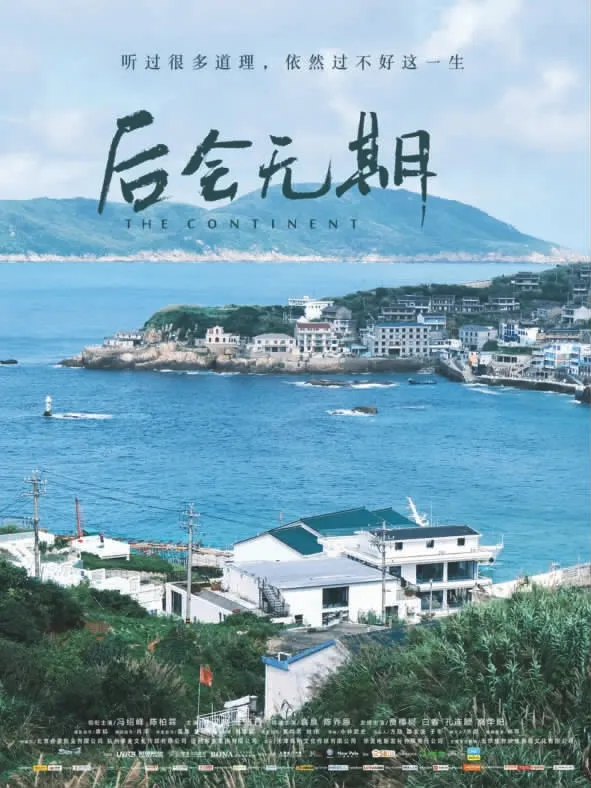
比如,賈樟柯電影中的山西汾陽是他的家鄉,也是電影《小武》的拍攝地,社會的變革給那里的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他說拍攝《小武》的契機正是目睹了整個縣城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小武這個邊緣人物巧妙地展現出縣城青年的處境,他們渴望獲得友情、愛情和親情卻得不到,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失落。隨后,帶有自傳色彩的《站臺》則通過突出20 世紀80 年代外在世界對汾陽縣城的沖擊,展現了以崔明亮為代表的縣城青年從革命理想主義到渴望融入世界但最終失落的精神裂變。不難發現,賈樟柯電影中的縣城/小鎮青年正處于多重意義上的傳統與現代社會的轉折點上,他們既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和迷戀,又無法真正融入其中,留下的是前路未知的無盡迷茫。
有趣的是,成長在改革開放后的韓寒雖然以“叛逆者”的形象出道,但他的電影具有明顯的商業化特征。韓寒從不避諱自己“小鎮青年”的標簽,反映在作品中就是熱衷于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小地方,例如其成名作《三重門》的主角林雨翔來自小鎮;電影《后會無期》的主角從東極島出發;電影《乘風破浪》發生在小鎮上;電影《四海》同樣延續了韓寒的“小鎮情結”,故事被設定在南澳島上。韓寒電影中的“小鎮青年”雖然保留了某種“非主流”的特點,但重心卻已置換為外在的“廢柴”。他們既向往大城市現代化的物質生活,又對現有的日常生活表示不滿,并想要有所偏離。這些“小鎮青年”不斷地與世界對抗,或失敗被拋下,或拍拍灰站起來一笑了之,繼續前行。
三
大體來說,影視作品中的“小鎮青年”形象,既有積極努力打拼、實現自我價值的新時代青年主體,也有像韓寒電影中那樣充滿調侃和消解的文藝青年,還有那些純真浪漫、率性而為的青年形象。這些形象或許未必能用某種明確固定的標簽概括,甚至連“小鎮青年”這一概念本身也難免大而無當。
但觀眾,特別是同樣出生在小鎮或縣城的年輕觀眾,會從電影中找到與現實或心靈的聯結,進而形成某種自我投射,在屏幕內外達成共鳴。
雖然很多人提到“小鎮青年”,總會勾勒出“小鎮做題家”等深陷內卷或躺平的形象,然而實際上,如今生活在中小城市的“小鎮青年”,早已不是媒體渲染的帶有負面含義的無名者,而是生活穩定甚至安逸舒適的青年群體,以至于他們反過來被深陷內卷的城市青年向往。
“小鎮青年”不僅是介于城市與鄉村中間地帶的群體,更有可能成為建構新型城鄉關系的紐帶。特別是在當前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回到家鄉,投身鄉村建設,體現出新一代年輕人更加理性自主的選擇和肩負責任的使命感。不妨說,新世紀走過20 年,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我們更能直面自我與內心的需求。
- 中學生天地(B版)的其它文章
- 錦灰堆:抱殘守缺的綺麗之美
- 問題不大
- 縣中少年的夢與路
- 印記
- 生長,在文字照亮的世界
- 文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