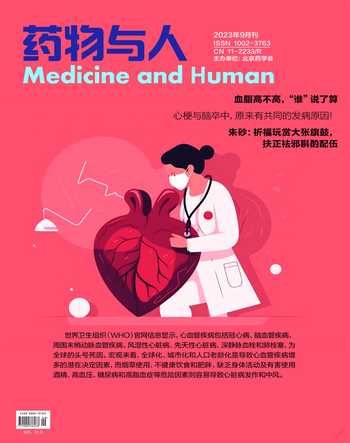關于抗菌藥物的8個爭議問題及新觀點
杜博冉 馮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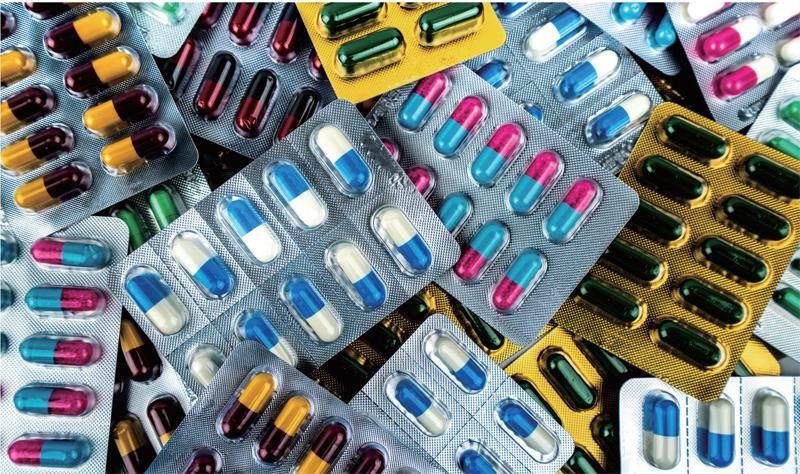
抗菌藥物是臨床常用的治療藥物,但關于抗菌藥物的使用更多的是基于既往的實踐經驗—比如,很多常規操作會在沒有循證研究基礎的情況下建立,所以往往也存在爭議。而只有當新的特殊病例或循證證據出現后,很多先前存在爭議的常規操作才會被修正,典型的如:后期修正了對青霉素過敏的患者避免使用所有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的誤區。
近期,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及杜克大學醫學中心針對8個抗菌藥物相關的常見爭議問題達成共識,對抗菌藥物的使用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同時針對爭議的起源、現有循證證據及目前尚不明確的內容進行了闡述。下面,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這些問題進行轉述。
爭議問題1:中樞神經系統感染避免使用頭孢唑林
Uptodate(一種基于循證醫學原則的臨床決策支持系統)上有這樣的表述:由于頭孢唑林不能充分滲透至中樞神經系統,不應將其用于甲氧西林敏感型金黃色葡萄球菌(MSSA)所致腦膜炎。此意見源于1973年:考慮頭孢噻吩對于血腦屏障的低通透性,Mangi等不建議將頭孢噻吩用于治療中樞系統感染。
但是,Frame及Novak等發現:以“2 g,每8小時1次”的方式輸注頭孢唑林預防給藥,腦組織中頭孢唑林的濃度明顯更高。Gregoire及Le Turnier等發現:將6~12 g頭孢唑林連續輸注,所測得的濃度均高于金黃色葡萄球菌及腸桿菌的治療界值,同時高于歐洲藥敏試驗委員會(EUCAST)對于MSSA的治療切點值。
目前,關于抗菌藥物在腦脊液中的藥代動力學還不明確,因為藥物進入腦脊液后較其他隔室存在時間滯后性,腦脊液與血漿中的藥物濃度比也會逐漸增大。盡管如此,高劑量的頭孢類抗菌藥物(如頭孢曲松)仍是中樞系統感染的首選治療藥物。
總之,頭孢唑林是治療中樞系統感染的備選方案之一,可應用頭孢唑林每日8~10 g連續輸注治療脊髓硬膜外膿腫,以替代傳統頭孢唑林“2 g,每8小時1次”的給藥方案。另外,進一步的臨床研究還在繼續,將有助于推動頭孢唑林治療劑量不斷優化。
爭議問題2:使用SSRI類藥物的患者不得使用利奈唑胺
利奈唑胺是惡唑烷酮類抗菌藥物,對于多重耐藥的革蘭氏陽性菌具有較好的體外抗菌活性及藥代動力學優勢。然而,由于其對單胺氧化酶(MAO)具有可逆的非選擇性抑制作用,合用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類藥物的患者需謹慎用藥,以避免5-羥色胺綜合征(SS)發生。據此,美國FDA建議患者需有14天的洗脫期,以避免相互作用;如果是氟西汀(一種SSRI類藥物),洗脫期甚至變為5周,而這很容易延誤治療。
后來,在一項關于革蘭氏陽性菌感染患者的研究中發現,合用SSRI類藥物與利奈唑胺的患者,SS的發生風險并未顯著提高。而且,SS的發生風險與利奈唑胺的應用時間也并無明顯關聯—因為其發生率實在太低。Gatti等發現利奈唑胺與西酞普蘭合用發生SS的報告最多,推測利奈唑胺與西酞普蘭、艾司西酞普蘭、美沙酮合用時,SS的發生風險更高。
總之,利奈唑胺合用SSRI發生SS的風險相對較低。所以,對使用SSRI類藥物的患者權衡利弊后,利奈唑胺仍可作為備選;用藥時需嚴密監測。
爭議問題3:對于腎功能不全的患者,無須調整利奈唑胺劑量
利奈唑胺常規用法為“600 mg,每12小時1次”、靜脈或口服給藥;對于腎功能不全的患者,說明書中并未建議進行劑量調整。這在當時并沒有問題,因為在早期臨床試驗中,利奈唑胺血小板減少的發生率相對較低。然而,隨著臨床應用的擴大,越來越多骨髓抑制的不良反應被發現—對于腎功能不全的患者,血小板減少及嚴重血小板減少的發生率更高。
因此,研究建議:對于eGFR<60 mL/min/1.73m2的患者,可經驗性地降低利奈唑胺用量至“300 mg,每12小時1次”,以平衡安全性及治療有效性。
總之,盡管對于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是否需要調整利奈唑胺劑量并未載入藥品說明書,但過程中的治療監護及劑量調整工作仍需特別關注。同時,建議利奈唑胺的24小時的AUC/MIC維持于80~120為最佳,保持谷濃度<7 mg/L。
爭議問題4:對于青霉素過敏患者,克林霉素可作為一線手術預防藥物
克林霉素是50S亞基蛋白合成抑制劑,其不含β-內酰胺化學結構,臨床常作為青霉素過敏患者的手術預防首選藥物。
正常來說,頭孢唑林為患者手術預防的首選藥物。但是,由于其屬于β-內酰胺類藥物,傳統上認為青霉素過敏患者須避免使用。然而,進一步的研究卻對此觀點提出了質疑:研究發現,頭孢唑林的側鏈與其他β-內酰胺類藥物并不相同,對青霉素過敏的患者也對頭孢唑林過敏的情況極少。另一項關于青霉素過敏患者的研究中發現,應用頭孢唑林、克林霉素、萬古霉素的過敏發生率相近。
同時,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一種臨床上常見的毒性較強的細菌)對于克林霉素的耐藥性逐年增加,美國化膿性鏈球菌對于克林霉素的耐藥性也逐年上升,無乳鏈球菌的耐藥性亦是如此。有鑒于此,Joint Task Force on Practice Parameters工作組更新了相關指南,建議對于側鏈存在差異的頭孢類藥物,如頭孢唑林、頭孢曲松,仍可考慮對青霉素過敏的患者作為一線手術預防用藥。克林霉素的外科手術預防作用仍十分有限。
爭議問題5:甲氧芐啶-磺胺甲惡唑對于化膿鏈球菌無體外抗菌活性
臨床數據顯示,皮膚軟組織感染(SSSI)中非皮膚膿腫的蜂窩組織炎主要以化膿性鏈球菌為主。而隨著MRSA病例的不斷增加,替代頭孢類的藥物,如甲氧芐啶-磺胺甲惡唑開始被關注—自然而然地,其也被更多地與化膿性鏈球菌聯系到一起。過去,考慮到甲氧芐啶-磺胺甲惡唑對于化膿性鏈球菌較弱的體外活性,臨床上常與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聯合治療皮膚軟組織感染。
但是,后期的研究顯示:復方磺胺甲惡唑對化膿性鏈球菌作用的理解是錯誤的,這種錯誤主要由當時的實驗室檢測手段引起。在體內,復方磺胺甲惡唑通過阻斷胸腺嘧啶合成及細菌復制而發揮作用。但是,當內源性胸腺嘧啶被復方磺胺甲惡唑成功阻斷時,部分細菌仍可通過利用外源性胸腺嘧啶而繼續生長—比如化膿性鏈球菌。過去,用于培養鏈球菌的瓊脂中就常會添加外源性胸腺嘧啶,以分離上呼吸道樣本中的化膿性鏈球菌。所以,是外源性胸腺嘧啶的添加導致了理解上的錯誤。目前,去除胸腺嘧啶的培養基則消除了此類問題。
最近的臨床研究亦支持以上微生物學研究結論:2017年的系統綜述中認為,復方磺胺甲惡唑可以單藥用于葡萄球菌及鏈球菌引起的皮膚軟組織感染。
爭議問題6:口服磷霉素治療單純性膀胱炎效果顯著,推薦作為一線藥物
目前,關于使用磷霉素治療單純性膀胱炎有效性的研究數據尚存爭議:首先,單劑量磷霉素與7天療程呋喃妥因的療效相似;但是,在一項關于單純性膀胱炎患者的隨機對照試驗中,5天療程呋喃妥因相較磷霉素具有更優的臨床效果。
而且,隨著磷霉素用量的增加,對磷霉素耐藥及超廣譜β-內酰胺酶耐藥的大腸埃希菌數量也會大幅增加。同時,由于磷霉素需通過葡萄糖-6-磷酸酶(G6P)發揮抗菌作用,但人體尿中并無此酶,這也對以其治療單純性膀胱炎提出了疑問。
簡單來說,盡管單劑量磷霉素的治療方式對于單純性膀胱炎似乎頗具優勢,但目前的隨機對照試驗結果并不支持其替代呋喃妥因的治療地位,仍需進一步的評估。
爭議問題7:利福平和慶大霉素能用于治療葡萄球菌引起的人工瓣膜心內膜炎
臨床上,侵襲性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人工瓣膜心內膜炎(PVE)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及死亡率。美國傳染病學會(IDSA)指南推薦,利福平和慶大霉素可用于治療MRSA引起的人工瓣膜心內膜炎,從而使患者獲益。
但是,Cosgrove等并未在人工瓣膜心內膜炎的治療中發現加入慶大霉素對患者預后的益處。與之恰恰相反,慶大霉素的加入增加了患者急性腎損傷的風險。
其實,以利福平和慶大霉素治療MRSA引起的人工瓣膜心內膜炎的推薦來自一項感染隊列的事后分析。但是,該分析納入的樣本量很小,僅為觀察性的關聯。同時,另一項多中心觀察性研究顯示,利福平的加入對于相關醫療結局并無改善。
總之,利福平和慶大霉素對于心內膜炎的治療作用有待商榷。
爭議問題8:多西環素禁用于妊娠期女性及8歲以下兒童患者
妊娠期應用四環素類藥物會導致母體肝毒性;同時,對于孕期暴露的新生兒或兒童,則可能引起骨骼及牙齒發育異常,因此,對于妊娠期女性及8歲以下兒童禁用。不過,在這類藥物中,多西環素可能是個例外:目前,多西環素是立克次氏體感染的首選藥物;同時,相比其他四環素類藥物,其引起的不良反應也明顯更少。但是,受美國FDA在1970年所規定的“四環素效應”的影響,多西環素仍嚴格禁止用于8歲以下兒童。
然而,最新觀點認為:對于部分特殊情況,多西環素可以嘗試性地用于妊娠期女性及8歲以下兒童,棄用多西環素將對此類人群存在明顯風險——比如,當兒童確診落基山斑疹熱及立克次氏體感染時,棄用多西環素可能導致致死性風險顯著增加。
另外,研究顯示:對于8歲以下兒童及嬰幼兒,當出現多西環素暴露時,其牙齒變色及發育畸形相較非暴露者并無顯著差異。美國兒科學會認為,多西環素對于牙齒變色的影響較小,多西環素不超過21天的短期治療是可以接受的。美國FDA認為,盡管目前沒有對照研究評估妊娠期多西環素的安全性,但基于目前的致畸信息系統結果及專家意見,妊娠期多西環素的治療劑量不太可能對致畸風險造成影響。
以上數據顯示,當出現嚴重感染而沒有替代方案時,如立克次氏體感染,對于兒科患者應用多西環素治療利大于弊。另外,針對多西環素用于妊娠期女性及8歲以下兒童的安全性研究已在陸續開展,包括藥代動力學研究以及評估多西環素對于骨骼發育及牙齒脫色的長期縱向研究,對于其結果,我們拭目以待。
綜合上述8點可知:隨著循證學證據的不斷完善,臨床上對抗菌藥物的認識在不斷更新;同時,需要結合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個體化的抗菌藥物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