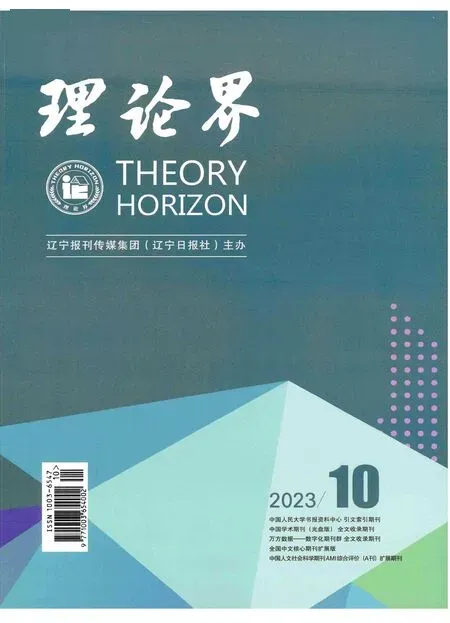主體認同的理論構想
——基于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的政治意識形態思想
酒海明
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的政治哲學思想中凝結著有關政治意識形態的論述,這一理論內容具有豐富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將著眼于阿爾都塞、普蘭查斯的政治意識形態思想,分析其中的結構系統特征,進而具體論述觀念性思想系統及其與主體認同之間的內在關系,最后梳理和分析制度性機制及其具體內容,從而探究這一機制與主體認同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結構系統性:阿爾都塞、普蘭查斯政治意識形態理論的抽象特征
在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那里,他們都將結構主義的理論特點注入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理論分析之中。意識形態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基礎,存在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制度性機制又內在于其中,那么就抽象特征而言,意識形態具有結構系統性,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關于意識形態的結構系統樣態,阿爾都塞作出這樣的規定:“意識形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1〕,“是社會的歷史生活的一種基本結構。”〔2〕在以上論述中,阿爾都塞借助結構主義的理論特點對意識形態進行解讀,其中具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意識形態表象體系作為一套由各種思想內容構成的規范系統,具有意識形態性的規約實踐效用,成為社會現實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結構,同時作用于主體化的生成過程,主體認同內在于這一過程之中。在阿爾都塞的高足朗西埃看來,其老師所理解的表象體系亦是一套規約系統,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幻覺系統存在。〔3〕另一方面,就實踐過程而言,意識形態具有“非強制”的無意識特征。借用盧卡奇有關物化意識的相關論述可以更好地理解。物化意識統攝下的主體認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誤認,即對物的神秘性的誤認,將由本質呈現的表象錯視為本質,存在一種認同的錯位,而且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發生。而主體之為象征界主體而不是處在想象界的個體,正是因為個體在意識形態結構系統之中得到了“注冊”,比如阿爾都塞所述的“體驗”關系就是“注冊”的一個方面。意識形態并非只有單向度的傳播路徑,以一種認識論層面的宣傳教化抑或是陳述句形式的強制性命令與要求,而是憑借其外化的“文化客體”進行傳播,即現實的、可感可知的客觀世界的結構系統。比如,盧卡奇所言的物化的社會結構亦是這一抽象性、結構性概念的具體體現。進一步來說,意識形態及其制度性機制具有了在社會歷史結構之中普遍性、系統性及永恒性存在的意味,人們又不得不生存在意識形態之中,正是阿爾都塞所言的“沒有意識形態的種種表象體系,人類社會就不能生存下去”〔4〕。人們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從事一系列的社會活動,在形式上具有非強制的無意識“體驗”“想象”關系。
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無歷史問題的論證展示出共時性的結構維度。阿爾都塞吸收弗洛伊德對無意識的永恒性—無歷史論斷,在結構主義的視角切入,認為意識形態“在整個歷史(=有各社會階級存在的社會形態的歷史)中具有永遠不變的形式”〔5〕,“這種結構和發揮功能的方式以同樣的、永遠不變的形式出現在我們所謂的整個歷史中。”〔6〕可以說,意識形態內化在組織機構及制度性機制之中,就意識形態運作的結構系統形式而言,具有相對無歷史的特征,進而可以成為國家制度系統得以良性運作的基本構成性因素。
普蘭查斯和其老師阿爾都塞一樣,在結構系統維度論述意識形態,延伸出對于機構和結構的基本理解,構成他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集中論述的理論先聲。普蘭查斯對占據主導地位意識形態的系統樣態進行了論述。即“占主導的意識形態不是社會形態中唯一的意識形態:有幾種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子系統,與斗爭中的各種階級有關。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只是它通過成功控制其他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子系統而形成的。”〔7〕普蘭查斯的這一表述意在說明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需要在各種意識形態及其系統的對抗之中占據領導權。而且,這里的意識形態子系統就是普蘭查斯所理解的意識形態部門,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將諸多子系統聯合起來的觀念性思想系統。此外,意識形態和社會中的各種機構及其結構系統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普蘭查斯指出,“結構概念包括了機構組織化了的矩陣。通過意識形態的運作,結構總是隱藏在它所建構的機構系統中,并被其組織。”〔8〕這一論述中具有兩個層面的理解向度。其一,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機構組織化為一套“矩陣”系統,機構系統之中具有內在的結構。各種機構就其形式而言是一個尚待占據的“空位”,這就需要將機構概念放置在權力維度進行分析,因此,“機構只能與掌握權力的社會階級有關。”〔9〕普蘭查斯又指出,盡管機構和統治階級相聯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各種機構完全受動地功能化為統治階級維護社會統治的工具,服從統治階級的組織原則,因為這些機構還有一定的自組織特點,即“自主性和結構層面的特殊性”。〔10〕其二,組織化的機構系統具有意識形態性的規約要義。這里的機構系統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含義較為接近,“機構是社會認可的規范或規則體系,因此,機構概念不能僅為一種司法—政治機構,因為公司、學校、教堂等也構成機構。”〔11〕各種具體的機構合目的性地按既定的規則,有機地組織成為一套復雜的結構系統,意識形態性的規約要求滲透在這套機構系統之中。普蘭查斯的這段論述已經展示出意識形態的系統化和規范性等特征,這點在普蘭查斯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論述中得以更加詳盡地闡述。
綜上所述,在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的理論闡發之中,意識形態亦是一套高度組織化、結構化的系統性構成,結構系統性就是其抽象特征。在阿爾都塞那里,意識形態表象體系作為價值規約的思想性內容,具有結構性的形式,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結構,亦是主體認同的核心中介。在普蘭查斯那里,意識形態具有系統性的形式,機構又與意識形態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通過制度性機制的運作,意識形態滲透在各種機構之中。需要注意的是,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看似存在一種宿命論式的悲觀論調,實際是展示普通大眾的無可奈何,即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建構情勢下保持主體認同之誤認關系,呈現資本主義條件下意識形態制度化的極端異化樣態。
二、觀念性思想系統:諸多意識形態部門間的鏈接與整合
普蘭查斯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論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中具有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就其中的意識形態部分而言,普蘭查斯對意識形態的階級性進行了明確,認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并且具有統一性、滲透性等特征。其中,普蘭查斯將意識形態理解為非嚴格意義上的“部門”,展示意識形態部門間的潛在鏈接關系,其整體就是一套宏觀意義上的觀念性思想系統。
普蘭查斯指出了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統治階級之間的內在關聯,這就是他對意識形態問題思考的一個基本立足點,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意識形態部門的批判性論述。普蘭查斯指出某種具體的意識形態在社會形態的總體結構中是被多元決定的,“在一種社會形態內,意識形態是受到各種表現、準則、意念和信仰等因素的總體支配的。”〔12〕這就是說,意識形態不是單一、自在的說教或理論構想,而是受到多種文化、價值等觀念性因素的影響,同時又反作用于社會形態。普蘭查斯更加具體地指出:“由于事實上意識形態(即一種既定的意識形態)是作為結構統一的一個部門環節而構成的,這種結構在某一階級中占有統治地位,因為它在階級斗爭領域中發揮其效用。”〔13〕這里的結構(統一體)就是一種總體性構成,不同的意識形態部門配合制度性機制在這套結構系統之中承擔建構幻想、協調維系、掩飾矛盾等規約功用。
就意識形態的諸多部門而言,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念等內容滲透其中,各部門間的有機聯合就是一套觀念性的思想系統。具體來看,意識形態可以按照性質劃分出不同的部門,比如“道德、法律、政治、美學、宗教、經濟和哲學意識形態”。〔14〕就諸多意識形態部門有機組合的基本線索而言,意識形態的價值性、規范性內容深深地嵌入意識形態“部門”之中,總體上構成了一套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影響和引導的觀念性思想系統。進一步看,意識形態配合制度性機制深入人心的過程,往往伴隨著觀念性思想系統的形成,正如米歇爾·佩肖所指出的,“‘思想領域’是以穩定點的形式在社會歷史上構成的,它產生了主體。”〔15〕比如,就具體的意識形態部門——道德而言,道德往往作為法的輔助出場,促進受道德教化影響的主體形成自反式的認同。
在普蘭查斯看來,盡管存在多種的意識形態部門,但總是會有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部門如同“普照的光”,主導并統攝其他意識形態部門。此類意識形態部門的核心特點就是能夠最好地實施“掩飾”工作,可以有效地掩蓋占據主導地位意識形態的客觀事實,促使受眾保持一無所知卻又勤勉為之的主體認同狀態。普蘭查斯以與封建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宗教意識形態為例,作為論述占據主導地位意識形態部門的例子。這點在經典作家的宗教批判思想中就可以得以體現。比如,恩格斯在功能解釋維度論述宗教意識形態,“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只把它當做使下層階級就范的統治手段。”〔16〕也就是說,宗教呈現意識形態性,成為群眾回避痛苦、聊以自慰并獲得虛幻自欺性滿足的精神靈藥,其中就形成了非理性的“情感”認同。回到普蘭查斯那里,他明確地指出宗教部門的意識形態功能,“宗教意識形態正是最適合于掩蓋意識形態本身統治作用。”〔17〕“它往往執行統治作用并且需要把自己的真正作用掩蓋起來。”〔18〕也就是說,宗教認同基礎上的群眾并未察覺到宗教所肩負的意識形態職能。
需要進一步拷問的是:宗教“掩飾”功能的實現何以可能?實際上就是因為幻象和制度性機制的強強聯合。一方面,宗教的“精神鴉片”功用就是為大眾提供意識形態性的幻象,為信徒提供一層由信仰所支撐的幻象,進而屏蔽苦難或創傷,形成了一層阿爾都塞意義上的想象性關系來鏈接主體對宗教以及統治制度的絕對認同。另一方面,意識形態性的“掩飾”還需要制度性機制,即教會、儀式、傳教士等要素的組合。在此基礎上,意識形態性的“掩飾”功能才能進一步展開。
顯然,在文化價值多元化和傳統思想領域不斷分化的當代,很難達到類似中世紀天主教在各思想領域之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諸多意識形態部門中,仍會有某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部門,絕非某些西方學者所給出的諸如“意識形態終結”一類的意識形態性論斷,在阿爾都塞看來,“只有意識形態的世界觀才能想象出無意識形態的社會。”〔19〕那么,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境遇之中,法律政治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部門,“法律政治意識形態最適于執行掩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形態中經濟占統治地位的作用。”〔20〕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部門這里,“分離”就是一重手段,普蘭查斯指出在封建時代意識形態宗教部門階段,主要是建立一種依附性的關系,“假‘自然’和‘神圣’之名推行”,〔21〕即“把神圣和宗教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22〕相較于此,資本主義階段下的法律政治意識形態部門則是追求形式上的分離,使得大眾在國家共同體中獲得形式上的自由以及平等的政治身份,即“使代理人從‘自然束縛’中分離和解脫開來”。〔23〕比如,具有法律保護的勞動者進行勞作,同時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工會組織之中獲得集體的認同感。也就是說,在制度性機制的分離、回溯、掩飾、調和的運作線索下,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意識形態部門完美隱藏了非正義的剝削行為,而且不以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面目直接呈現,不明所以的勞動者在法律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勞動的再生產,實際上也就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參與到意識形態再生產的閉環之中。與此同時,普蘭查斯還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幻想關系進行明確,即“政治共同體中的‘同樣的’、‘互不聯系的’和‘孤立的’個人一律‘平等’的幻想”。〔24〕這層幻想關系反映在主體認同和現實活動的無意識維度,不同類型的幻想有助于掩蓋階級統治的剝削行為,協調社會關系并撫平社會矛盾,而且內在于思想系統之中,亦是制度性機制的關鍵一環。
概而言之,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滲透在意識形態各部門之中,這些部門又分布在各個具體的思想領域,其中會有某些部門占據主導地位,諸多意識形態部門間的有機聯合就會形成一套觀念性思想系統,這套思想系統就是維護社會統治、維護制度運作的思想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這套思想系統將會聯合制度性機制,一同影響主體的認同。
三、制度性機制:具象化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并作用于主體認同
眾所周知,阿爾都塞討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受到了葛蘭西市民社會理論的啟發。阿爾都塞在理論層面論述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臣服”系統,實際上就是意識形態喚問個體的系統,和葛蘭西市民社會理論具有內容上的互補性。宏觀上看,這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其內部的制度性機制作為一套預先存在的系統,凌駕于主體之上喚問主體并促其在象征秩序之中進行注冊,使得“主體的各種觀念(好像碰巧!)就是從這些機器里產生出來的”,〔25〕而且成為在“我”之外的“他者”,如同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我”就是被“拋擲”到意識形態之中的個體,主體無法作為無負荷的個體存在于意識形態的真空之中自我決定,需要接受意識形態的喚問。由此,在特定歷史時期,看似人們發揮其主體性進行言說,操縱和規范意識形態,實際上早已被無形的意識形態力量所捕獲,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維護其認同關系再生產的思想根基。因此,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制度性機制與主體認同的內在關聯及其理論特點就需要從阿爾都塞的相關論述中進行理解。
在阿爾都塞那里,文化意識形態職能與暴力統治職能交相呼應,具有更加潛在的同一性塑造與規范功能。相較于在公共領域中行使直接統治職能的暴力機器,蟄居于日常空間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依附暴力機器及相關制度規范為其提供的“運行的一般政治條件”,〔26〕以文化意識形態的手段滿足意識形態—主體認同關系的再生產。由此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制度性機制,有助于常態化地維護、穩固國家制度及政權。
具體而言,阿爾都塞指出應該形成多個具有覆蓋不同思想領域、具有內在統一性并根據不同目標進行再生產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同時,一系列并存的機構組織,存在于私人領域而非以往的政治領域即公共領域,共同組合成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比如“宗教系統、教育系統、政治系統、等等”,〔27〕總體上構成一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歷時性地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歷史中具有相對不變的結構形式與制度性機制,作為國家制度系統得到良性運作的基本構成因素,而具有歷史性、階段性的國家政權則會產生不斷的更迭。
相較于封建時代教會機器的意識形態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學校機器就是促進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典型,這套機器將個體對于政治制度以及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同視作再生產的具體目的,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性機制之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因此,它已經成為“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生死攸關的結果的機制”。〔28〕學校作為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具有了完整的組織內涵、培養職能以及育人格局,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剝削階級的合法性進行維護與鞏固。統治階級通過學校機器,將意識形態通過教育的諸多環節,將富有規范性價值以及知識性等內容輸入個體,不斷強化意識形態性的“律令”,從而使個體被喚問(教化—引導)為具有思考能力的、能動的主體,進入由大他者所建構的一套面向主體的幻象。被喚問的主體可以在齊澤克對經典佳片《銀翼殺手》的解讀中進行形象化的理解,在對復制人及其質疑活動的主體性的論述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復制人產生在工廠的制度化操縱系統之中,它們無法脫離工廠對其的預先設定,比如記憶、意志、性格。但是,當復制人偶然踏出符號秩序,意外得知主體的不可能之后,明晰其主體性的空洞位置,他們才開始獲得具有批判反思性的主體意志,即“主體就出現于它在傳統體系中失去其支撐的時候”,〔29〕進而開始綜合其以往的記憶碎片。在這種情勢下,質疑行為就成為復制人反思、拷問制度化整體對其規訓的重要活動,復制人不再只是將自身視作客體,而是作為主體開始思考自己在象征界之中究竟處于何種位置,從而開始殊死反抗的路途。這樣的故事性內容也從側面反映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其制度性機制的極端異化和誤用,形象化地展示出這套機制作用于個體主體化及主體認同。
在普蘭查斯那里,他在1969 年的一篇論文中也曾提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盡管論述不多,但部分觀點和阿爾都塞的理解基本一致。他在論文中指出:“如果國家被界定為維持社會形態的一種凝聚力,而且通過維持階級統治來再現社會制度的生產條件,那么很明顯,有關機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發揮著完全相同的功用。”〔30〕這里就已經展示出普蘭查斯對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其制度性機制的基本理解,這些內容有助于維護社會制度的運作。不止于此,普蘭查斯指出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凝結在一個結構內部的機構和機器中,比如:教會—宗教機器、政黨—政治機器、工會—工會機器、學校和大學—教育機器等。〔31〕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具體分支和基本構成而言,普蘭查斯寫道:“政黨、工會或學校本身不是機器,而是政治、工會或教育機器等的分支。”〔32〕這點同阿爾都塞的觀點基本一致,意在說明某個政黨是歸屬于政黨機器范疇的,具有一層種屬關系。政黨是具體的,而政黨機器則是一種抽象的結構系統,這一內容又構成制度性機制的具體內容。在不同歷史階段,政黨機器這個結構系統基本不會發生改變,但是會有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政黨在制定具體的意識形態。普蘭查斯指出:“意識形態(規范和規則)和政治壓制(社會規訓)對這些機構或機器的運作進行干預。”〔33〕從這句表述中,我們便可以發現其中的兩重意蘊:第一,意識形態作為規則和規范,就是一種廣義的制度,其規約要義滲透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機構或機器之中。第二,機構或機器就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同義表達,都將受到政治制度的規范和意識形態的引導,都是制度性機制的具體內容。在普蘭查斯看來,葛蘭西已經建構了將意識形態機器從屬于國家制度的理論。可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需要服從國家制度的統一導向,而且意識形態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廣義的制度。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鎮壓性國家機器服務于一種社會制度,制度性機制內在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中,通過其文化功用作用于主體認同并維護社會制度的有序運作。
結語
上述對阿爾都塞、普蘭查斯政治意識形態思想中的結構系統特征、觀念性思想系統和制度性機制三大主題的揭示,突出了意識形態的結構系統之維,以在此維度下回視主體認同的核心問題,一方面是意識形態凝結在一套觀念性思想系統之中,從而作用于主體認同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是表明意識形態不僅是規范性、觀念性的內容,同時具有物質化發展的趨向,需要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中的制度性機制的協同與配合,從而來常態化地影響主體的認同。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革命性,論述了主體如何打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規訓的策略方案,因為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那里就已存在一個爭奪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主題,十分關注接下來要“怎么辦”的現實問題,比如盧卡奇認為需要加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以及葛蘭西強調要爭奪文化領導權。回到普蘭查斯這里,他認為,“只有革命組織和階級斗爭組織才能最終‘逃脫’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34〕阿爾都塞從階級斗爭視角指出:無產階級需要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其結構形式進行考察,并在描述性維度指出,“要懂得利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它的某些特定形式,包括它的意識形態的某些特定要素。”〔35〕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需要關注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制度性機制的爭奪和介入,究其結構形式而言具有中立性的特征,它作為一個開放的場域可以為不同階級所定位和使用。也就是說,對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政治意識形態理論的梳理分析,既需要明確他們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異化發展的批判,又需要關注觀念性思想系統、制度性機制的描述性。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對于政治意識形態的探討有助于為我國意識形態制度化建設提供積極的理論參考,對此研究能夠更進一步地推動和提升我們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析、鑒識能力,這種認知能力是鞏固和維護我國文化領導權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