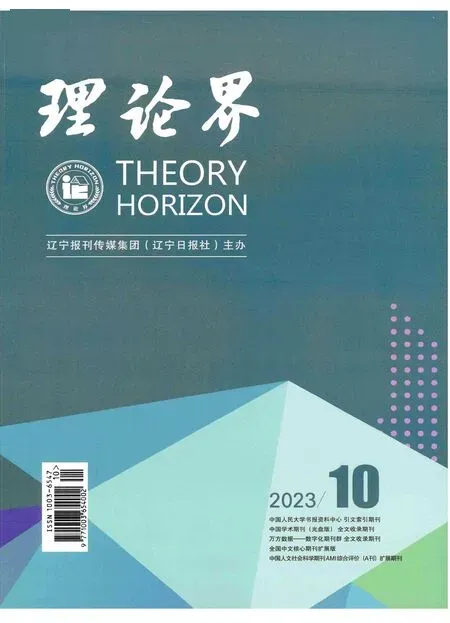新儒家構建中華文明新形態的奮勉:從現代性精神危機的應對看
邱龍虎
所謂新儒家是相對于原來以孔孟為代表的“舊”儒家即傳統儒家而言的。根據郭齊勇先生的考證,最早提出新儒家這一名稱的是馮友蘭,用來指宋元明時期的理學或道學。當然,學界對于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至今仍有不同的界定。本文所探討的新儒家指的是在西學東漸和民族危機雙重壓力之下,以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為使命的知識分子力求恢復傳統儒家文化主導的官方文化和民間文化,重建儒家倫理精神,以此來建構會通中西并繼往開來的文化思想體系,從而成為符合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獨特文化出路。新儒家所倡導的新儒學一度是與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鼎立的三大思潮之一,〔1〕曾經產生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一方面,在一些人看來,儒家文化在產生并需要它的歷史社會環境瓦解之后,“無所為地只在心底象古玩般地被珍愛著”,〔2〕或者如美國學者列文森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所言被保存到博物館,作為一種象征性存在著的死亡。另一方面,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以“學以成人”這一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設定學術主題,彰顯了全球哲學界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價值的重視與期許。面對人類現代社會的轉型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往的新趨勢,現代性問題于我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顯現。儒家文化在被“祛魅”的同時能否為精神困頓、道德危機和文化割裂等提供一些解答,為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參考?我們應該首先放下獨斷論的基調,從新儒家對現代性精神危機的應對中抽絲剝繭,也許能尋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
一、外來沖擊的回應與儒家文化精神的伸張
著名學者費正清提出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沖擊—回應論。新儒家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注是遭受文化沖擊后的回應,還是儒學內在精神的伸張?這必須從儒家文化的發展來看。雖然總體而言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在不同時期儒學的發展所面臨的社會場景各不相同,發展也有高潮與常態之分。學術界一般將儒學的發展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先秦儒學,第二期為宋明理學或道學,第三期為新儒學。先秦儒學作為一種文化學說,與西方同時期的哲學家所追求的路線不盡相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在倫理與世俗生活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如果說孔子的內“仁”外“禮”作為一種處世之道的君子人格,仁是君子的內在德行,禮則是君子的社會規范,那么孟子的性善論則是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理論,為孔子的君子人格學說辯護,并強調教化的重要性。與性善論截然相反,荀子性惡論以人性本惡為立足點來弘揚儒家的教化學說。作為“禮”處理利害關系法則的運用,儒家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將義與利對立,并取義舍利。作為一種普遍倡導的原則,其理論內在的自洽性自不待言。但是在先秦時期的社會環境下,儒家這一主張也在一定程度遭遇現實的困境,那就是君子必然會有生存的隱憂。這為墨家的顯出創造了條件,墨家以義利合一來修補儒家關于“利”的缺失。因此,墨學起源于儒學,與儒學并稱顯學;就連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漢武帝在董仲舒建議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百家爭鳴的私家學說正式登堂入室,成為官學的太學,并在此后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
到了宋元時期,經過儒道釋合流,以儒家文化精神為內核的道學或理學逐漸演化而成,在追尋現象世界之后的本體和人性認識之間尋找關聯。為重建儒學的形而上學,各種主張紛呈,如周敦頤和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在宋明理學或道學的理論體系中,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為典型代表。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主張“即物而窮理”,向外尋找本體的認識。在宋代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的基礎上,明代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通過內在良知將本體與本體的追尋融為一體,避免了朱熹的外在本體與內在良知的認識論難題。縱觀宋明理學或道學,其理論體系的構建更加成熟。雖然以西方哲學為參照標準來對比,不難發現其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的內容沒有那么透徹,但是我們以西方哲學為標準這一要求本身就不符合常理。正如賴爾所言,這是中西方思維的差異所在,中國思維側重指導如何做而西方思維側重于知道是什么。〔3〕而且,宋明理學的旨趣也不是哲學上對理智或認識的把握,而是在于社會倫理的正當性和規范性,從而為世俗生活提供個體自覺的指引,正所謂“理性為一”。
到了新儒家時期,這種傳統儒學的追求精神在外在的沖擊下更加煥發出活力。如果說利瑪竇來華傳教化身漢儒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從側面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儒家文化在官方和民間的主導地位。當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伴隨傳教士而東漸,中國先賢已經逐漸開始意識到西方文化的不同,有識之士也開始研究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這在中國科技史上并不鮮見。鴉片戰爭時期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分化成兩派:頑固派和洋務派。與頑固派堅守祖訓盲目排外不同,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中體西用”以開明的立場維護儒家文化的君主體制。與此同時,以嚴復為代表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子也極力宣傳西方文明以啟民智,科學、民主、自由等觀念逐漸被大眾所接受。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以梁啟超的“歐洲科學破產論”為代表,對西方文化引導人類文明進程的質疑以及東方文化的優勢發出強有力的呼喊,學衡派“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4〕表明了一批學人開放而堅守的傳統儒家文化心態。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即是西方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種思潮論戰的外溢,也是中國當時社會環境下全盤學習以科學為中心的西方文化與保留以儒學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紛爭。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新儒家努力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化轉型尋找方向。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寫道:“現在不是兩種文化對壘的激戰,實實在在是東方化存亡的問題。”〔5〕面對西方文化的傳入所展現的強勁態勢,梁漱溟擔心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否能夠存續的問題,所以梁漱溟試圖找出東西方文化差別的根本原因所在,回應文化上的問題,并由此避免中國人“蹈襲西方的淺薄”而讓人生問題無法安頓。
從儒學發展的三個高潮期的表現上看,新儒家對現代性精神危機的回應不能僅僅理解為沖擊—回應論。沖擊—回應論有其合理的一面,看到了西方文化在傳到我國的過程中對社會各個階層的沖擊,包括思想文化層面的深刻影響。但是,這一理論確實屬于西方中心論的基調,而且是一元論的視角,將文化視為相互沖突而不是在相互融合中發展,與世界文明發展的實際情況毫不相符。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觀點無視中國傳統儒學中一直存在的為尋找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所做的努力。從先秦儒學到宋明理學或道學,再到新儒學,儒家文化一直在融合其他各家文化中發展,包括外來的佛教文化,在不斷融合中演化出新的文化樣態。面對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文化交融,儒家文化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尋求新的探索路徑。
二、新儒家應對現代性精神危機的策略
無論是沖擊—回應論還是傳統儒家文化精神的伸張,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轉型,儒家文化必然需要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涅槃重生。重思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是新儒家的不二選擇。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就是對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進行一番綜合性的反思并與西方文化作對比,找出中國文化的特性和優勢,從而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儒家文化尋找新的出路,并由此出發為中國人的精神尋找寄托。在方法上,梁漱溟通過直覺體驗的方式來重建中國人的生命哲學,從而對中國文化精神予以維護和創新的發展。馮友蘭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諸多觀點深以為然,在美國用英文發表《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推介梁漱溟的思想。對于梁漱溟進行東西文化比較進而為中國人精神安頓所作的努力,張君勱也完全贊同,他在《新儒家哲學之基本范疇》中指出:“東方人之視其哲學,為道之寄托,可為擇善信守之資……而西方人之視其哲學僅為一種學說一種意見。”〔6〕
新儒家應對現代性精神危機的重點內容是生命哲學。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心性之學的倡導價值就是做好一名君子并通過努力而成為圣人。從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強調學習的功夫,再到孟子的“性本善”強調人有向善之心,再到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都是強調修性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中則表現為在紛繁復雜的時局和利益面前,如何追求內心的寧靜,通過自我修養以追求個人道德的完善,實現人生境界的提高。梁漱溟不僅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提出傳統儒家文化心性修煉的自覺,自身也言行一致并積極付諸實踐,在北京大學開設儒家哲學課程,探索從心靈深處尋找人生意義并進行宣教。生命哲學中的人生境界學說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貢獻。馮友蘭對傳統儒學的人生意義深入研究之后,以人生覺解程度的高低為標準,提出四境界說“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關于天地境界的劃分從中國哲學層面上將中國人的精神追求作了精辟的歸納,完全超越了西方哲學中的道德學說對人的要求。而方東美則從人生實踐的角度,依據所從事活動的價值類型高低將人生境界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形而下境界的自然人,包括“行能的人、創造行能的人、知識合理的人”,對應的人生境界又可細分為物質世界、生命世界和心靈世界;第二種是形而上境界的高貴的人或宗教境界,并在高貴的人之上還有宇宙精神的“皇矣上帝”。〔1〕必須指出的是,方東美一生致力于以人生哲學為基礎重建新哲學體系,曾深入研究中西方人生哲學思想,其關于人生境界的劃分在一定程度上將西方人生哲學思想引到儒家人生哲學中來,或者說,利用西方的語言體系來描述儒家哲學思想,必然留有西化的痕跡。港臺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對于人生境界的三層次劃分“覺他而非自覺”“自覺而非覺他”“由自覺而超自覺”體現了生命的自在、自為和超越三種形態。這些新儒家對于人生境界的研究豐富和拓展了新儒學的學術空間。
新儒家們開展的第三項重要工作是結合西方哲學關注的內容對儒家文化一致或近似的地方進行豐富和深化,以呈現中國哲學的近代哲學體系特征。以本體論為例,在這方面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等做了重要工作。盡管梁漱溟一再強調儒學屬于身心性命之學,不應納入哲學范疇并諷刺熊十力的努力是“癖好思想這把戲”,〔7〕但是熊十力則持哲學定義之界定的開放態度,認為哲學以本體論為論域,中西差別僅在于西方從知識論層面追求本體,而中國從修養層面追求本體,殊途同歸而已。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熊十力對本體—宇宙論孜孜以求。在熊十力看來,宇宙萬物的現象之中有本體的存在,這一本體就是實體,它既含物質性也含精神性,從現象上表現為物質,從功用上表現為精神,實體與宇宙萬物同一存在但又不隱藏于萬物之后,同時“體用不二”“翕辟成變”即相反相成。從終極目標而言,熊十力的努力并非僅是為了哲學而哲學,其實質是以現代西方哲學體系來重建儒學,從而完成對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思潮的超越。馬一浮以心本體為形而上學的基礎,必須指出的是,此心并非生理學的心臟,而是性、天、命、德;再通過“一心開二門”,對應形而下的功夫論和六藝論。馮友蘭以西方哲學的分析方法來重建中國哲學,以貞元六書為代表的“理本體”創造了程朱理學的新發展,在海內外影響深遠。對于港臺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在這方面的努力,杜維明作了高度評價:“承繼了熊十力的本體探究和梁漱溟的心性修煉,完成了數百萬言的有關儒家心體、性體和心靈境界的巨作,為儒家哲學注入了新理念、新范疇、新方法和新思路”。〔8〕
三、新儒家應對現代性精神危機問題的審思
以科學與民主為大旗的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民族文化進行了挑戰并大獲全勝。儒家文化似乎面臨著被消亡的境地,依筆者之見,新文化運動實際上使得儒家文化得以涅槃重生:新文化運動削減了俗儒文化的消極方面,儒家文化的積極方面反而獲得了重生或發展的機會。此后,以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為標志的西方近代理性主義精神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民族文化再次沖突,雖然論戰的最終結果是科學主義陣營勝利,但是以“玄學鬼”張君勱為代表的主張“科學不是萬能的,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也讓儒家文化在科學主義的碾壓下獲得了生存的空間。
新文化運動和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給新儒家提供了直接的學術主題:儒家文化對民主與科學的應答。在儒家文化對民主問題的應答中新儒家并沒有從西方的民主的實施形式方面著手去論證中國古代也有選票式民主,而是強調在儒家文化中存在著民主的文化基因和主張。在這方面觀點最為鮮明的是張君勱,他提出儒家文化中的選賢任能、關注民意、自由言論、孟子王政思想主張天下為公、宋明時期儒家主導下的鄉約都具有民主的種子,孟子的王政思想就是要服務于百姓。此外,賀麟力圖以仁為本體論重建中國哲學、方東美等肯定儒家文化從自然人到具有宇宙精神的全人的道德境界的追求、余英時對士的傳統和精神的歷史梳理等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證儒家文化中關于民主的主張。在儒家文化對科學問題的應答中新儒家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探究,其一是以馮友蘭為代表的新儒家對中國古代文化為什么沒有產生西方近代自然科學進行了追問。1921 年,馮友蘭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宣讀了自己的論文《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來的一種解釋》,并于第二年發表在《國際倫理學雜志》(32 卷3 號)上,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9〕其二是熊十力、馬一浮為代表的新儒家認證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能夠包容近代科學。熊十力用“體用不二”的哲學體系開出知識論與外王學,馬一浮以“一心開二門”的方式將科學歸為“六藝”之組成部分的本體之用。〔4〕
新儒家從直接的學術主題拓展開來,挖掘西方哲學中與現代性相適應之內容的思想為參照,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尋找類似思想之源頭,并結合時代要求做新的闡發。張君勱認為儒家哲學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如“理智的自主性,心的作用與思想,德性學說,宇宙的存在,現象與實體,或者道與氣”〔6〕在現代社會中都具有復興的價值,并身體力行以儒家哲學為基本,將之與西方哲學家的理論進行互相比較衡量或印證,從而使中國哲學的論證方法更加嚴謹,表述更加意義明確,分析更為透徹,更加適合現代生活的節奏需求,也在傳統與現代的反思中開辟了新的儒學論域,并進行中西哲學的會通,援佛入儒等,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
結語
發跡于軸心時代的儒家文化經幾千年而不消亡,這一現象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價值。面對現代性的精神危機,以梁漱溟為代表的學者以儒家文化為根本,尋找應對辦法,體現了幾代學人對于中華傳統儒家文化在新的歷史時空下傳承與發展的艱辛求索,其探索的路徑、方法和成果在現代學術史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于我國的文化強國建設以及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儒家文化精神的倫理情懷,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而調和持中的態度等,對于解決當今世界紛爭,消解極端民族主義和文化霸權,化解文明沖突并參與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待當代學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續寫儒家文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