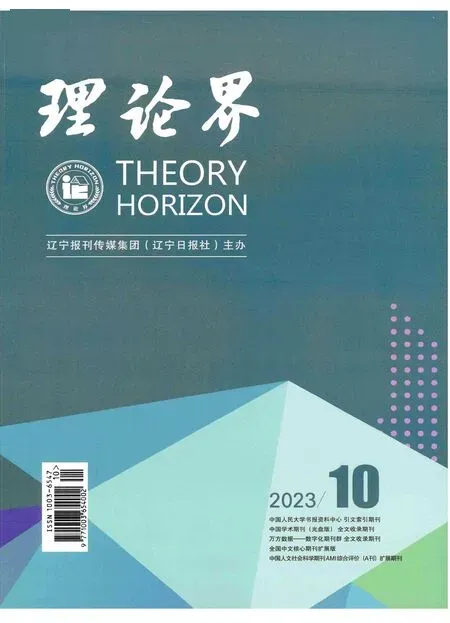從“兩端”到“中和”:王船山性情思想重構中的價值轉向
楊 超 李 萌
學界于蘇東坡、朱子兩派性情觀歧異,討論甚多,然于此二脈性情之辯互斥模式的化解之道,無有觸及。此外,已有研究,將王船山性情觀劃入道德寬松或道德嚴格主義陣營之中,亦有未盡之處。
一、問題指向:蘇東坡、朱子兩派內外偏執中的“性情之辯”
北宋以降,由于受到佛學、道學較為完備形上學說的挑戰,孔子所罕言的“性與天道”,成為諸多儒者無法回避的論題。在此情境下,“性”(天性)、“情”(人情)之關聯,作為“性與天道”學說中最為核心的議題,為學界爭訟不已。
以蘇東坡為代表的主情一派,以七情為性,重人之情。蘇東坡欲終止聚訟不止的性情論爭,在總結歷代學人性情思想的基礎之上,批判了孟子及荀子的性善、性惡論說,認“喜、怒、哀、樂”為性,并主張性、情無善亦無惡,但可為善為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于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1〕蘇東坡將紛繁復雜的人性之爭,歸咎于孟、荀,較之二者非此即彼的人性論,更青睞揚雄人性善惡相混之說。在蘇東坡這里,“仁義禮樂”與“喜怒哀樂”均為人之性,二者猶如白紙,無善無惡,可以給人以隨意創作的自由:“以為仁義禮樂皆出于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2〕“俗儒”所言的“仁義禮”之“性”,實際上亦出自“喜怒哀樂”之“情”。
在性情關系上,蘇東坡主張情可見性,情本性末。蘇東坡認為前人所言之性,均似性而非真性:“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3〕性不可見,可見之性非性,那我們應當如何見性?“方其(性)變化,各之于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4〕所以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見性以情。“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于其末,則以為圣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5〕圣人之道,實為情之道,不循可見之情,而尊不可見之性,則必然本末倒置。
蘇東坡持此性情觀,亦有現實考量。其一,在修身之法上真其性情。“飲酒,人情所不免。禁而絕之,雖圣人有所不能。”〔6〕孔子并不主張滅絕人情,《論語》有言:“惟酒無量”。蘇東坡認為,其“真性情”的主張并非憑空捏造:“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轉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7〕微生高向鄰居討醋轉借朋友,孔子謂其“不直”;陳仲子刻意壓抑自然欲望,近似迂腐,為孟子所不取;陶淵明光明灑落,或仕或隱,任性而為之,至今為人稱道,因此,性情以真為貴。
其二,在治理之則上賤禮貴情。蘇東坡強烈反對以刑法滅情的做法:與其以禮扼性制情,不若放任性情自流,物極必反,惡去則善來:“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于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8〕以情為惡,隆刑重法,壓制人自然的欲望與情感,終會自取滅亡。與刑法相比,禮教對人自然性情的戕害,有過之而無不及:“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于其末者之過也。”〔9〕喪葬之禮,將人不愿意持續的悲痛,延續至三年;婚嫁之禮,卻使得本應該享受持久的快樂,不得終日。所以,不宜以禮法強加于百姓,堵不如疏。
蘇東坡之門生秦觀,曾如此盛贊蘇東坡的道德性命之學:“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于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10〕秦觀認為,性命之學方為蘇東坡學說之精華,以文章稱頌蘇東坡,名尊而實卑。但在朱子那里,讓蘇東坡及其門人引以為傲的性命之學卻不名一文:“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11〕蘇東坡學說確有其可取之處,但天人性命之學卻不得要旨。
及朱子之世,胡五峰等人對蘇東坡以“情”為“性”之主張極為認同:“胡五峰說性多從東坡子由們見識說去。”〔12〕更有甚者主張失卻中道喜怒哀樂,亦是人之常性,朱子于此批判道:“如此,則性乃一個大人欲窠子!”〔13〕于朱子而言,胡五峰之輩沿襲蘇東坡之性情觀,以欲代性,不分善惡與是非。所以,打破不分性情,甚至以欲為性的局面,是朱子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首先,朱子判未發是性,已發是情;性為仁義禮智,情為四端、七情;性為理所賦,全善無惡,情因氣而成,有為善或為惡的可能。二程批判了以愛言仁之說,嚴格地區分了性、情之不同:“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14〕朱子承繼并發展二程之學說,認為性為未發,情為已發,依此而言,不僅喜怒哀樂愛惡欲是情,四端亦是性之動:“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個谷種相似,谷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知四者而已。”〔15〕仁義禮智為未發,無有不善,然而發出來卻有不善,是何故?“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16〕在朱子看來,四端之情雖由理而出,無有惡處,但七情卻是氣之所動,氣有渣滓,故有為惡的可能。
其次,在性情關系層面,朱子主張性本情末,心主性情。“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17〕因性之難見難言,與蘇東坡相類,朱子也主張以情見性:性為形,情為影,性發動為情,由四端“情”之善,可以看到性之善。與蘇東坡不同的是,在朱子這里,性情有本有末,性具有更為根本性的作用,情之于性,如影隨形。“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籠統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18〕朱子認為性為心之體,寂然不動;情為性之用,感而遂通;心管攝、分別性情,靜時主宰性,動時主宰情。
最后,在工夫論上,朱子認為“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心是做工夫處”,〔19〕故未發時須涵養人性,已發后省察人情,以此存善去惡。“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20〕依朱子之意,不論是存其善,還是去其惡,都需要在心上做工夫:心在靜時,思慮不起,需要持敬涵養,以此察覺天地之心,而存其善;心受到聲色貨利引誘而動,則需要克己省察,以去其已萌之惡。“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遍,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21〕心之本體萬理具足,靜時全其本體,動時發其功用,如此,便能做到天理流行,人欲盡去,不論是已發還是未發,始終保持在一個應然之善的狀態。
究其根本,蘇東坡、朱子性情之辯可以規約為內外之爭。蘇東坡重人之情:真其情,直其情:“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22〕通過情的自由外放,獲得身心的滿足。朱子重人之性:以至善之性為標的,涵養未發之性,省察已發之情,其批評東坡不屑于禮法,厭惡修身工夫之行徑:“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23〕朱子以性的內收,由性及情,由內達外,顯乎本然之善,消除人情為惡的可能性。
二、學理意涵:王船山內外交養的性情主張
王船山對蘇東坡與朱子的“性情之辯”,有較為直接的評議:“或人誤以情為性,故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今以怵惕惻隱為情,則又誤以性為情,知發皆中節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作者按: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節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善與?此孟子所以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征性也。”〔24〕王船山認為蘇東坡與朱子的“見性之方”均不可取:蘇東坡以仁義禮智為情,以情之有善有惡,而知性之可善可惡;朱子以四端為情,以四端之善,而知性之善。王船山批判性地繼承了二者對性情的界定,認為仁義禮智、四端均為性,而七情為情,性為善,情可善可惡。那么,作為宋學殿軍之一的王船山,當如何取二者性情觀之長,以去其短?
首先,王船山凸顯了情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性自行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動則化而為情也。”〔25〕情獨立于性之外,并非為性的附屬品。因此,我們要肯定情的釋放,以“達情者以養其性”。〔26〕朱子認為性已經是至善至美的,“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27〕故其著重未發時的涵養,與已發之時的省察,以情之善顯性之善,以保證道德實踐的至善境地。于王船山而言,性是日生日成的,而性的生成,離不開情的助力:“功罪一歸之情,則見性后亦須在情上用功。……既存養以盡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為功而免于罪。”〔28〕朱子與王船山有關情是否有能動性的差異,最為集中地顯現在二人對《論語》“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一章的詮解之上:“‘實’與‘本’確然不同。本者,枝葉之所自生;實者,華之所成也。《集注》謂‘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是大綱說道理,恐煞說二者是實,則嫌于以仁民、愛物、貴貴、尊賢等為虛花,故通諸有子之說,以證其有可推廣相生之義。”〔29〕朱子釋“本”為“仁性”之根基,其以孝悌為愛、為用、為情,在此視域下,守住內心的“仁性”之根基,才是第一要務,相比之下,尊賢、貴等之實事,只是“仁性”自然外顯而成的“虛花”。“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30〕而仁為體為用,涵養仁體之根基,向外擴充,則孝悌之情不請自來。王船山解“本”為“實”,如此愛之情為花,仁之性為實,花有其能動性與獨立性,有花方能有實。王船山肯定朱子由性生情之說,否定其以性顯情之論,以彰顯性之于情的能動性:“若情固由性生,乃已生則一合而一離。如竹根生筍,筍之與竹終各為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如父子,父實生子,而子之已長,則禁抑他舉動教一一肖吾不得。情之于性,亦若是也。”〔31〕情自有其能動性,情之于性相通相成,如竹之與筍、父之與子,交相成長,以此生生不息。
其次,王船山亦強調以性之善,對七情之惡適度地節制。蘇東坡的“以情為性”之說,與朱子的“以性為情”之論,均有其危害。“若盡其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熾然充塞也,其害又安可言哉!”〔32〕蘇東坡“以情為性”,盡其性情,則七情不加節制,人欲充塞。“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見,人之不以人心為吾俱生之本者鮮矣。……性有自質,情無自質,故釋氏以‘蕉心倚蘆’喻之;無自質則無恒體,故莊周以‘藏山’言之。無質無恒,則亦可云無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33〕在情上用力,隨其自然,放任人情,最終只會沉溺于物欲之中。已發之情,需要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性的節制,情方能保持中道,并助力性之實現。“夫情茍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從而生?乃以歸之于物欲,則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緒談。抑以歸之于氣,則誣一陰一陽之道以為不善之具,是將賤二殊,厭五實,其不流于釋氏‘海漚’‘陽焰’之說者幾何哉!”〔34〕朱子“以性為情”,盡四端之“善情”以顯性,將不善歸于物欲對人心的引誘,則容易陷入釋老的禁欲主義。所以,王船山主張情已發之后,亦可以“性”節“情”:“喜怒哀樂之情雖無自質,而其幾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節,則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敵靈,靜不勝動,且聽命于情以為作為輟,為攻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35〕情已發之后,如若有性介入,則在實際的道德實踐中,惡亦會得到有效的遏制。
最后,王船山試圖彰明性情的交相互養之道。“故普天下人只識得個情,不識得性,卻于情上用工夫,則愈為之而愈妄。”〔36〕蘇東坡任情之自然發露,以見性之可善可惡;朱子以四端之善,以顯性之善。二者均在情上用功,并未注意到,情在已發之后,性的制約作用。“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怒、哀、樂之交待以行也,故曰交發其用。”〔37〕此外,情獨立于性的能動性,可以助力善性由內及外的擴充:“今夫情,則迥有人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作者注:兼未發),人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作者注:兼擴充),道心也。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38〕性引導、制約情的生發,情助力、促進性的實現,性情相互交養,共同致力于善之揚、惡之去。
合而論之,王船山批判了蘇東坡與朱子兩派呈互斥之勢的性情思想:以性統情,易陷入枯槁,缺乏生機;混情為性,則人情熾然,物欲橫流。隨后,王船山借由對情之自主性、能動性的凸顯,以及以性之善于人情之惡的提防、抑制,彰明性情的交相互養之道,以存善去惡,無過無不及。
三、價值轉向:王船山在“寬松”與“嚴格”之間的性情觀
侯外廬曾在其“早期啟蒙說”中,將王船山與其他明清之際儒者的理欲與性情觀,劃入道德寬松主義陣營。〔39〕王汎森與侯外廬的“早期啟蒙說”針鋒相對:“許多持自然人性論的思想家其實是非常嚴格的道德主義者。”〔40〕在他看來,王船山雖然是一位自然人性論者,但其理欲觀、性情論均屬于“道德嚴格主義”。郭齊勇借由對朱子、王船山性情觀歧異之比較,認為“王夫之對于‘情’的警惕防范,超過了朱子”。〔41〕
如前所論,從王船山對蘇、朱性情觀之張力的紓解上,可以看到,王船山對情的警惕遠高于以蘇軾為代表的重情主義,此無須贅述。但我們不能以此判斷,王船山之性情觀隸屬于“道德嚴格主義”。
相反,朱子對情在未發露之時的警惕高于王船山:王船山作為宋明理學中身心實踐向社會實踐學說轉向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其以外在結果為導向與判斷標準,認為內在未發的七情,不可稱之為善,因此,不需要耗費過多精力操存、涵養。在朱子看來,未發的喜怒哀樂為性,至善而無惡,王船山質疑朱子的此種論調:“喜怒哀樂未發,則更了無端倪,亦何善之有哉!中節而后善,則不中節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則節也,而非喜怒哀樂也。”〔42〕如依朱子所言,“李林甫未入偃月堂時,殺機未動,而可許彼暫息之時為至于仁乎?”〔43〕朱子主張七情未發為“性”為“仁”,故其尤為重視對于未顯露時“喜怒哀樂愛惡欲”內在的操存,涵養暫時未發“怒”“惡”之“殺機”,即為片刻“性”之“仁”。王船山認為未發的“喜怒哀樂”了無端倪,不可以稱之為“善”,因此,放棄對使“喜怒哀樂”始終保持為未發之“性”狀態的追逐。
此外,朱子對已發之情的警惕,亦不亞于王船山。在朱子那里,情的最優狀態,是恢復到性之平靜如水的局面,如此則天人合一,而方能重現天地之心:“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44〕朱子認為四端之情經天命之性所生,七情之情是由氣質之性生發。性為平靜之水,情為水之流動。而不正當的欲望是由氣所賦之形體,在外界聲色嗅味的引誘下,情的泛濫所導致的。王船山認為“喜、怒、哀、樂,只是人心,不是人欲”。〔45〕其對已發后泛濫之情(即朱子所謂之“欲”)的界定,明顯寬松于朱子。如追求美味,在朱子看來便是“人欲”,而王船山則主張“欲無味,則無如無口”,〔46〕對美味的執著,是人最自然的情感,不需要過度克制。
再者,從肯定已發之時情對性的助力,褒揚“過”與“不及”之情的功效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較之朱子,王船山對情的寬松。其一,船山批判了朱子將情之善對于性的助力,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不善雖情之罪,而為善則非情不為功。蓋道心惟微,須借此以流行充暢也。如行仁時,必以喜心助之。情雖不生于性,而亦兩間自有之幾,發于不容已者。唯其然,則亦但將可以為善獎之,而不須以可為不善責之。故曰‘乃所謂善也’,言其可以謂情善者此也。(作者注:《集注》釋此句未明,蓋謂情也。)”〔47〕情具有自主性與相對獨立性,并不是性的附屬品。其二,王船山認為朱子之說,忽略了已發之情,在實際的道德實踐中,可亦助性的一面:“孟子言‘情可以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于情之中也。”〔48〕過與不及之情,亦可以為善。
所以,我們可以將王船山的性情觀,劃分在涵化“放情”與“斂性”之間的道德中道主義陣營中。正如船山所言,性與情交相互養、松弛有度,方能相得益彰:“愚于此盡破先儒之說,不賤氣以孤性,而使性托于虛;不寵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節。”〔49〕王船山之性情觀在凸顯情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的基礎上,亦著力于對七情之惡的遏制,較好地彰明了性情的和合之道,為此后儒家性情思想的發展別開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