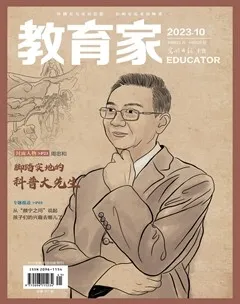對我國基礎教育“學業過剩陷阱”的再思考

中國高等教育體量世界第一、高校數量世界第二,在學研究生年增長比例常年保持在9%以上,基礎教育更是前后歷經八次課程改革,最近十多年PISA測試的表現連年全球遙遙領先。但在諾貝爾獎百年史上,也只有11位華人獲獎,由我國本土培養的諾獎獲得者屈指可數。雖然諾貝爾獎并不完全代表一個國家整體的科技實力,但的確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當前教育系統存在著重大問題。無論是“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還是近期火爆全網的“顏寧之問”,這中國現代教育發展史上的“靈魂三問”,無不時刻刺激著教育工作者的神經。
筆者所在團隊于2019年開展“我國教育未來發展的重大風險研究”,并提出“學業過剩陷阱”這一概念,認為“學業過剩陷阱”已成為阻礙我國教育發展的重大風險,對學生個體的健康成長、民族素質、國民創造力乃至人才強國的戰略都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關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民族復興。“顏寧之問”的提出再一次印證了這一觀點。
什么是“學業過剩陷阱”
所謂學業過剩是指以獲取標準答案和高分數為主要甚至唯一價值取向,以死記硬背、機械模仿為主要方式的學習、教學和評價的總和。學業過剩將導致新一代國民既沒有起碼的身心健康,更缺乏家國情懷、審辨思維、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我們稱這種現象為“學業過剩陷阱”。
中國教育長期以來處于“學業過剩陷阱”當中。早在1990年前后,中央教科所研究員劉遠圖負責組織的國際教育成就測試評價課題中國項目研究中,中國學生在數學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方面得分全球第一,而在問題解決能力、興趣與自信心方面的表現不及美國同齡人。2013年,美國教育研究協會 (AERA)終身Fellow、特拉華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教授蔡金法結合自身實證研究提出,中國學生的基礎知識比較扎實,在計算題、解決簡單問題,以及有標準答案的過程限制復雜性問題方面,表現突出;但在過程開放的復雜問題方面,中國學生與美國同齡人相比略遜一籌。2012年PISA基于計算機的問題解決能力測試結果顯示,在參加的44個國家(地區)中,上海絕對排名第七,相對排名是全球倒數第二(用閱讀、科學和數學測試的成績,來預測問題解決能力的表現,預期值與實際值的差反映的就是相對排名)。2021年《自然》子刊《自然人類行為》雜志發表一項研究指出,在批判性思維能力方面,中國重點高校學生入學得分為1.612,普通高校0.741。該成績與美國學生成績基本相當,但在畢業時,中國重點高校畢業生的批判性思維得分為1.339,較入學時下降17%;普通高校0.234,下降68%。結果表明,歷經大學四年的教育,我國學生批判性思維發展水平不增反降。2021年起,筆者所在團隊與北京豐臺、上海黃浦、晉中榆次、晉中靈石、浙江溫州五地區連續3年針對一萬余名初中學生開展追蹤調查,數據顯示:從2021年9月入學的初一學生,其入學時審辨思維平均分為501分(量尺分數200~800分,標準差100分),到2023年5月時后測平均分為469分,下降幅度為6.4%。以上種種數據表明,我國無論是在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等教育階段,均已落入“學業過剩陷阱”。
“學業過剩陷阱”與“顏寧之問”的聯系
“顏寧之問”看似是對學生感興趣的科學問題的詢問,實則反映的是研究者的科學創新精神、使命與擔當的欠缺,而更進一步的則是對“當前教育系統是否能夠培養出一流科技領軍人才”的“靈魂之問”。
“顏寧之問”的本質是“學業過剩陷阱”在我國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體現。我國經濟增長正從依靠投資擴張和低成本勞動力供給轉向依靠原創性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這一點從二十大報告中對2035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總體發展目標,以及將“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中就可見一斑。2022年,我國成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這預示著未來科技領軍人才、拔尖創新人才及其后備力量的儲備將直接決定2035年總體目標的實現進程。
但當前我國的人力資本發展嚴重不均衡,重復性簡單勞動所需的低層次人力資本存量過剩,具有創造性和高階思維的高層次人力資本嚴重匱乏。2018年PISA測試結果顯示,中國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有48.4%的15歲左右學生被列入“優等生”的范圍,這一比例遠高于美國的12.3%。但是我國“優等生”中將來想要從事科學和工程相關工作的學生比例不足25%,遠低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平均水平。2022年深圳人才集團和清華大學技術創新中心發布的《中國創新人才指數2022》中則指出,我國各城市高層次、高質量人才總量短缺,現有人才隊伍尚不能滿足發展需要,且創新人才在賦能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亟須進一步提高。來自不同類型調研報告的結果均表明,“學業過剩陷阱”正在持續抑制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對我國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帶來“不可逆”的影響。
隨著中央提出要全面提升我國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讓一大批創新人才脫穎而出,近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地區出現了大量紙筆測試、學科競賽,試圖層層選拔、集中培養“拔尖人才”,這是典型的誤區。用“有標準的難題”選拔出未來能夠面對不確定世界、解決非常規復雜問題的創新人才,這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偽命題。事實上,推動各行各業發展的領軍人物,往往并非是在中小學階段各門學科表現優異的學生。他們更加具有科學家早期成長過程中的共性特質,比如強烈的好奇心與求知欲、能長期癡迷于某個領域且表現獨特、具有獨特的個性與批判性思維、具有堅毅的品質和耐挫性等。當學生在6~18歲成長的關鍵階段用絕大部分時間用于應對標準化的考試,當一個國家的優質教育資源主要服務于訓練超強應試能力的“考試高手”時,我們何以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
創造力發展缺失的背后
好奇心和興趣是學生創造力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源泉。“心流之父”、積極心理學大師希斯贊特米哈伊歷時30年對包括14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91名創新者的訪談結果顯示:“如果沒有強烈的好奇心和興趣,他們便不可能長時間堅持,做出重大的新貢獻。這種興趣很少只源自智力活動,它通常根植于深層的情感,存在于令人難忘的經歷中,這些經歷需要某種類型的解決方案,只有通過新的藝術表達或新的理解方式才能實現。只是為了獲得功名利祿的人,也許能努力前進,但很少能有足夠的動機去做分外的事情,去冒險探索未知的領域。”
大量的追蹤數據一再表明,學生為了取得更好的紙筆成績,實際上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在基礎讀寫算等學業訓練上花費過長時間、學習過多內容、嚴重超前學習,必然缺乏在面對非常規、開放性真實世界問題時應有的溝通與合作能力、批判性思考、獨立性與創新精神。
學生創造力發展缺失這一表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整個教育生態環境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集中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問題一,評價標準“無上限”。在基礎教育階段,上至中考、高考等大型學業水平考試,下至學校期中、期末考試乃至月考和班級小測驗等,結果的高低好壞,普遍依賴百分制基礎上的常模參照而非標準參照,必然導致對學生學習成績的期待“水漲船高”,形成典型的“劇場效應”和嚴重內卷。同時其結果導致全社會,包括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以分數高低作為評價教育質量好壞的唯一標準,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要求沒有“上限”,學生不得不拼時間、拼體力,犧牲課余休息與睡眠時間。
問題二,政府權責“無約束”。“唯分數”“唯升學”的政績觀助長了整個教育系統考試文化、狀元文化等不良社會風氣的滋生和蔓延,過度關注考試分數、過度依賴紙筆測驗、過度采用橫向比較、過度聚焦尖子學生的功利化價值取向,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評價內容、評價工具、評價功能以及管理者心態等方面出現偏差。而一些地方政府在權責上缺乏必要的監管和約束,導致教育生態失調,育人環境惡性發展,長此以往導致人才培養質量下降。
問題三,學校辦學“無規矩”。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課程設置實驗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表明,除語文、數學、英語等科目外,還應開展體育、藝術、綜合實踐課(如研究性學習、社區服務與社會實踐等)、地方與學校校本課程等內容。然而,不少學校并未按照“方案”要求執行,以學生基礎讀寫算能力為主的“學業優秀”成為學校考核的硬指標,課堂教學、課后作業和課外補習以學業的重復操練為主,各種隱性排名、生源爭奪導致校際關系緊張,學校畸形發展,學校辦學行為不規范,課程設置“缺斤短兩”,學生課外補習現象依然盛行。
問題四,學生發展“無活力”。學生發展缺乏活力主要體現在好奇心匱乏、創造力缺失和實踐能力薄弱等方面。當前我國基礎教育階段創新人才的培養普遍采用 “層層選拔、集中培養”模式,“學業優異”成為具有創造力的代名詞,他們被早早地“層層選拔”出來進入一個特定人群環境,失去了和不同類型人群相處、溝通、合作的機會,這會嚴重影響這個特殊群體對普通人的共情力、同理心和正常的人際交往能力,進而影響對整個社會的認知和擔當。一部分學生會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缺乏同理心的“創新人才”不會像人們期望的那樣,“改變世界”“造福人類”“構建美好生活”。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讓更多的青少年心懷科學夢想、樹立創新志向”“要教育引導學生培養綜合能力,幫助學生學會自我管理、學會同他人合作、學會過集體生活,激發好奇心、想象力,培養創新思維”。
如何破解“學業過剩陷阱”
“學業過剩陷阱”已成為我國教育發展的重大風險,為破解這一困局,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實踐工作者一方面要理清“學業過剩陷阱”中表現的突出問題,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當前經濟、社會、教育轉型發展所處的關鍵階段,借鑒世界教育發達國家的經驗并中國化,重點在以下四方面著力。
一是明確我國教育發展的基本矛盾,深刻意識到教育資源匱乏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教育不公平的矛盾只是外顯的表層矛盾,而學生自身素養發展的不平衡才是內隱的深層矛盾。二是轉變地方政府教育政績觀,通過督導強化地方黨委政府責任,地方政府定期向同級人大、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社會公眾報告區域中小學生創新潛能發展規劃、工作進展及核銷負面清單情況,主動接受問詢、指導和輿論監督,圍繞“學業過剩”現狀形成政府督導、人大問責、社會公示的監督保障機制。三是建立防止“學業過剩陷阱”的負面清單制度,如管理部門負面清單制度、學校負面清單制度、社會教育機構負面清單制度、宣傳媒體負面清單制度等。四是建立均衡且高質量的現代教育生態,如建設核心素養導向的現代教育生態、構建發展學生核心素養的學與教的文化、實施發展性評價和綜合評價等。
最后,我們從美國科學政策“開山之作”《科學:無盡的前沿》中摘選一段話作結:“在人才培養的問題上,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要營造一種環境,讓我們的每一個男孩和女孩都知道,如果他們能夠展現出自己的能力,他們的前途不可限量。即便后來證明他們沒有取得頂級成就的必備條件,但如果他始終知道自己前面是一片沒有止境的前沿,他也能夠比原本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