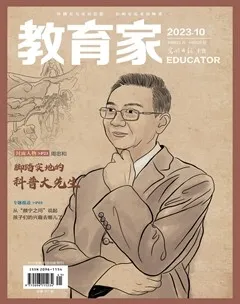杜素娟:我想讓年輕人的人生輕盈一點 文

“我可以很愛你,但我的人生也可以沒有你。”“看不到回報的努力,還要繼續投入嗎?”“如何面對失敗,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在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杜素娟的文學課上,她用《簡·愛》《老人與海》《浮士德》等西方文學經典,講述貼近年輕人生活的人生道理,幫助迷茫的人找到方向。
在華東政法大學,杜素娟的文學通識課很受歡迎,有學生在校四年一次也沒搶上。她上課不講段子,不放視頻,就是帶著微笑,以溫柔而有力量的語氣講文學。“貼著人生講文學,通過文學講人生”,這是杜素娟追求的文學教育,她希望自己的文學課就像曠野里的一棵樹,一些匆匆趕路的年輕人在樹蔭下停留,出發時帶著更加堅定的目光。
他們都是“苦難”的
在養育孩子和接觸學生的過程中,杜素娟發現,孩子們成長中的痛苦太普遍了。“這一代獨生子女,承擔著全家的希望和社會的期待,高分數、好高校、高成就,這個模式是那么單一,好像人生只有一條軌道。”杜素娟痛心地說道,“我覺得我的學生、我的孩子都是一個類型的,我認為他們都是苦難的。”
杜素娟表示,不僅是從好分數到好大學、好人生的單軌人生設想,帶來了艱巨的學業壓力,還有培養孩子的興趣愛好,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單軌思維——因為別的孩子都在學鋼琴,所以我的孩子也應該去學鋼琴。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們面臨著極大的精神壓力,他們的興趣、愛好、特長得不到適合自身且足夠的培養。
很多學生對杜素娟說,覺得自己很失敗,沒能考上某某大學。杜素娟對他們說:“你們來到華政,已經相當了不起了,為什么不欣賞自己的優秀呢?”可是很多學生還是覺得自己這里不夠好,那里不如別人優秀。他們失去了欣賞自己的能力,變成了不自信的人,“他的人生里全是荊棘,如何期待他獲得幸福的人生呢?”。
“只有做人上人才算有成就,在這樣的古老的集體無意識主導下,就會造成魯迅先生所說的‘爬的文化’,人人都往上爬,一邊爬一邊踩,人際關系緊張,多數人也沒有成就感。塔尖上的永遠是少數人,大部分人都是失意者,只能望‘塔’興嘆。”在杜素娟看來,在單軌思維主導的環境中,人人都是焦慮的,最終卷成功的永遠是少數,大部分人體會到的更多是卷的傷害。
作為一個媽媽,在女兒進入初中階段后,杜素娟反思了自己的教育。她痛心地發現,自己也推趕女兒做了許多超前學習、超綱學習的事,而落下了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帶著她思考如何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看待自己、看待情感。“好像我們的教育中,大多數時間里只關心孩子怎么考出更高的分數,而較少關心他們的內心狀況,較少分析他們的性格特點和情感需要,較少關注他們怎樣健康完整地成長。”杜素娟觀察到,孩子們接受充分的知識教育,卻很少有人對他們進行人生教育,甚至于,有時候孩子在人格養成、情感生長等方面受到負面影響。
當看到女兒在一些僵化的應試教育中受到的傷害開始呈現,看到學生們普遍焦慮、不快樂時,杜素娟意識到年輕人的“苦難”有多嚴重,也意識到人生教育有多重要。她之前也寫了幾本學術專著,可是越寫越覺得空虛。杜素娟堅定了念頭,她想要給學生們補足成長中缺失的人生課。雖然明白一個大學老師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她認為這是真正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
不要踩不必要的坑
5年前,配合學校的書院制改革,杜素娟進入文伯書院做了通識教育的專職老師,她認認真真地做這件事,把它當成一項人生事業去做。
在政法大學教文學,杜素娟覺得很幸運,因為“學法律的人知道文學的重要性”。“真正的法律人不是法律機器,只有充分了解人性,法律才有溫度。”華東政法大學提倡學生要做有溫度的法律人,她會在課上給學生們講《悲慘世界》里的沙威。“沙威是一個忠誠的法律人,他自認為站在善的一面,但其實在執行惡,他自認為在主持正義,其實在傷害弱者。沙威最后意識到自己是一臺冷冰冰的法律機器,他只能自殺。”杜素娟也喜歡看判決案例,有些案子比小說還精彩。她覺得,在戲劇化的人生現象和復雜的人性層面,法學和文學是相通的。
2022年,杜素娟開通視頻平臺賬號,將文學課搬上網絡,從文學的角度觀照人生,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有人留言質疑:“你講文學對我們有什么用?”日常生活中,她也遭到過質疑:“你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博士生,受過系統的文學理論培養,應該在學術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何必給本科學生講什么人生?”杜素娟曾為此感到痛苦和寂寞,通過文學講人生真的是“沒有意義”和“小兒科”嗎?她知道自己走了一條“窄路”,面臨著主流之外的艱難和孤獨。但她也有不為人知的快樂,很多學生認可她、喜歡她,學生的支持讓她堅信,文學不只是學術研究的資源或一種學術游戲,還是普通人的思想資源,能為人生提供啟發和參考。文學必須與人生結合,這是文學的力量所在。
“人應該具備兩種能力,一是專業能力,這是我們事業發展的根基,二是人文能力。”杜素娟說,她的文學課就致力于培養學生的人文能力,包括分析社會現象和問題、處理與社會和他人關系的能力,以及展開自我管理、處理與自我關系的能力。在講《奧賽羅》時,她對學生說:“你們覺得自己跟奧賽羅的距離有多遠?你們找找看,內心是不是有伊阿古這么一個心魔?其實那就是你的弱點。”學生們都覺得渾身發涼。杜素娟與學生討論最多的,是年輕人的孤獨問題,她通過哲學家的故事告訴他們:“要耐得住孤單,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雁群。”
“在文學作品中,作家把他們踩過的坑,以及對人生的痛苦的體驗、對社會文化的認知凝結成文字。假如我們能夠把它解讀出來,把人生的智慧教給孩子們,他們也許就不會吃不必要的苦,不踩不必要的坑,不走不必要的彎路了。”杜素娟見過一個失戀的年輕人,十多年了還沒有走出陰影,還有許多年輕人面對人生抉擇時手足無措,他們的長輩可能也無法提供有益的引導。“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付出巨大的試錯成本。雖然人生需要試錯,但是上一代體驗糟糕的事情和模式,如果眼睜睜看著年輕人再走一回,這是人類的愚蠢和對生命的浪費。”
給孩子們補一點點課
有很多學生流著淚向杜素娟傾訴:“老師,我不喜歡我的專業,我該怎么辦?”她常為此感到無力又無奈,學生的哭訴,她沒有答案。多年前,杜素娟像很多年輕人一樣,在長輩意愿的支配下,被迫學了被認為更有前途的專業,但她憑借一份對文學的執拗,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終把專業轉回了自己的熱愛。然而在今天,調整人生方向的成本變得高昂。“這類‘錯誤’本不該出現的。”杜素娟說,教育應該幫助一個孩子不斷發現自己的天賦和才華,應該從更基礎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做起,到了大學,“錯誤”就很難彌補了。而她試圖將文學教育與人生教育掛鉤,只能是“給孩子們補一點點課”。
杜素娟會給學生們講《月亮與六便士》,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在40多歲的年紀,放棄了證券經紀人的生活,改行做畫家。她告訴學生,這個故事不是要大家學斯特里克蘭德的做法,而是說明一個道理:“要尊重自己的體驗,知道自己到底做什么樣的事會感覺是值得的,是幸福的,其實這個就叫理想,就叫成功。”
還有更多的學生表示,自己不知道喜歡什么,也不知道不喜歡什么。杜素娟在她的文學課中,一直想要告訴學生們,所謂成功的人生,就是找到對自己的想象和期待,找到一件自己喜歡做、認為有價值的事情,享受這個過程中的樂趣,同時能夠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不斷地成長、開拓頭腦和視野。但是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又該怎么辦?杜素娟對此再次表示了無奈:“我們塞給孩子們一張張卷子,沒有觀察過他們,沒有培養他們的興趣,他們到了20多歲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然后還被埋怨沒有創造力。這是多么不講道理的事情啊!”
“所以很多時候,我只能‘螺螄殼里做道場’,僅此而已。現實邏輯太難打破了,強大得無法對抗。”有時候杜素娟也想和學生家長聊一聊,興趣和人的天賦才是最終通向成功的道路,而不是硬逼出來的分數,“家長會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他們也有苦衷,雖然我說的有些道理,但社會的競爭機制和反饋機制不是那樣運作的。”
杜素娟沒有因此絕望:“大環境很難改變,但是個體并非完全無力。”她給學生們講《鼠疫》,鼠疫象征著個體無法改變、不能掌控的宏大環境,渺小的個體并不是無可作為,最好的應對手段是“誠摯”,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看似縹緲宏大的東西,通過改變局部和細節,就有所影響。這并非理想主義,而是非常務實的做法。”杜素娟在給學生講述這些的同時,也是在講給自己聽。
“假如身處一片大沙漠,我也想努力種一棵樹,哪怕只有一兩個人在樹底下乘涼,也是可以的。”
世界是曠野,不是軌道
年輕人應該活得有棱有角,勇敢地進行自我想象,不要為外在標準所綁架,這是杜素娟在她的文學課中多次談到的話題。曾有人如此批評道,“你講的‘理想’太理想了”“說到底還是一碗雞湯”。還有人疑惑:“杜老師口中的年輕人,他們的立足之地在哪里呢?”杜素娟說:“從前我也不知道,我走過很漫長的、孤獨的、寂寞的、自我懷疑的階段,我懷疑過自己的職業,也懷疑過自己的理想,甚至懷疑過自己活著的意義,我都懷疑過,但是我后來意識到,我的立足之地只是我自己。”
在杜素娟看來,如果按照外在標準,自己算不上一個成功者。在高校里,成功的標準是在學術圈出人頭地,而她是一個教學崗的教授。在上海,50多歲的人群中,成功的標準涉及收入水平、房產數量、有無豪車,等等。按照這個通行的標準來看她仍然是“失敗”的。這些無形的標準“恐嚇著”每一個人,杜素娟拒絕了這份“綁架”,她通過講文學、講自己的案例,告訴年輕人:“我們應該有一份個性化的標準。”
杜素娟常給學生們推薦魯迅的《過客》,“有時候我們需要一點魯迅的力量”,當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之后,走什么樣的路,大家的選擇應該有所不同,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社會給我們提供了一套現成的規范標準,我們試圖去接受,有的人很順利,有的人不行,感到很痛苦。我要講的道理就在這里,我們祝賀在軌道上順利奔跑的人,但是那些沒能進入軌道的人,并不是社會的淘汰品和殘次品,不要在自責自愧中度過一生。”“世界是曠野,不是軌道。不要傷害自己,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合理性。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這是另外一種幸運,如果懂得在主流軌道之外開拓自己的道路,其實就承擔了另外一種使命,創造個性化,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豐富多樣,讓人類生命的概念變得更加豐富多樣,我們的存在能夠證明這個世界和社會的自由和包容。”
很多時候,杜素娟覺得自己是在盡年長者的責任,她無法對年輕人的痛苦視而不見,就把自己看到的生活真相告訴年輕人,告訴他們不必糾結,“那么年輕人會活得輕松一點,人生的路會輕盈一點,不那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