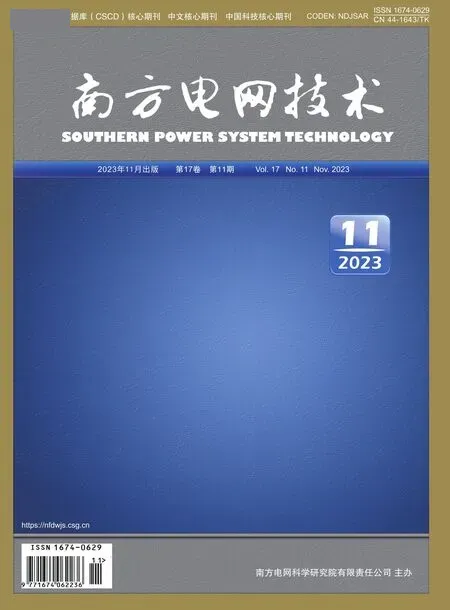臺風“妮妲”登陸期間沿海輸電線路局地風場數值模擬研究
蔡彥楓,黃穗,黃增浩
(1.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廣州 510663;2.廣東科諾勘測工程有限公司,廣州 510663;3.南方電網科學研究院,廣州 510663)
0 引言
臺風是造成電力設施損毀,威脅沿海輸電線路安全穩定運行的最主要自然災害。以南方電網為例,自2003 年以來,110 kV 等級及以上的主干電網因登陸臺風造成的倒塔、桿塔受損、斷線等的重大風災事故共發生10 起,其中2011—2015 年更是連續5 年每年出現1 起[1],國民經濟蒙受巨大損失。因此,防范和應對臺風引起的風災事故一直都是電網防災減災工作的重、難點[2-4]。為了準確掌握臺風的致災機理,科學制定防災減災措施,有必要針對沿海輸電線路局地風場開展觀測、數值模擬等一系列基礎研究。
沿海輸電線路普遍采用架空線-塔形式,對風荷載的變化較為敏感[5-6]。輸電線路風荷載計算需要輸入的風特性參數有:10 m高度風速、水平風速廓線、湍流強度、陣風系數等。臺風作為低壓渦旋性天氣系統,其自身的風特性參數顯著區別于輸電線路結構設計所依據的一般風特性參數[7-8],因此引起了工程技術人員的廣泛關注。目前在結構風工程領域中,關于臺風影響的研究手段主要有現場觀測、風洞實驗、數值模擬等3 種。其中,現場觀測利用風速傳感器、超聲測風儀等觀測儀器獲取臺風風場內實際風特性參數,并配合加速度傳感器、應變計等傳感器獲取結構的真實動力響應進行分析[9-10]。風洞實驗依托大氣邊界層風洞設施,在實驗室環境中還原臺風近地面的平均風速廓線,針對不同形式的線-塔氣彈模型,獲取動力響應特征[11]。數值模擬則借助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軟件模擬不同地形下的臺風風場空間分布,由于CFD模擬過程可重復,模擬結果具有物理意義,可以與現場觀測、風洞試驗等相互印證,互為補充,因此特別適合復雜地形的研究工作[12-16]。
文獻[17]在1604 號強臺風“妮妲”登陸期間,在距離臺風中心約15 km 的丘陵地形,利用激光測風雷達進行了輸電線路局地風場觀測。針對臺風“妮妲”,本文利用中、微尺度兩類數值模擬工具,開展臺風期間的沿海輸電線路局地風場模擬研究,驗證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方法的適用性,分析臺風影響下水平風速廓線的差異及成因,并為今后沿海輸電線路臺風防災減災研究提出建議。
1 模型與資料
1.1 中尺度氣象模式
選用由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AR)、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CEP)以及多個大學、研究院所聯合研發的新一代區域中尺度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WRF),對1604 號強臺風“妮妲”登陸期間的臺風風場開展數值模擬。WRF 模式包含三維大氣運動方程、連續方程、能量守恒方程、大氣狀態方程、水汽守恒方程等組成的動力框架,以及輻射傳輸、云微物理、行星邊界層、近地層與陸面過程等物理過程參數化方案,重點解決1~10 km 空間分辨率尺度、時效為60h 以內的有限區域天氣預報和模擬問題,也常與CFD 軟件聯合使用[18-20]。本文所使用的WRF版本為v4.1.5。
1.2 微尺度CFD工具
選用挪威WindSim AS 公司開發的CFD 計算流體力學軟件WindSim,對1604 號強臺風“妮妲”登陸期間的微地形風場進行數值模擬。WindSim 軟件內置英國CHAM 公司的Phoenics CFD 求解器,通過求解地形跟隨坐標下的雷諾平均Navier-Stokes 方程(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 equations,RANS),重點解決10~100 m 空間分辨率量級的各種復雜地形條件下近地層風場模擬問題。該軟件計算收斂速度快,能考慮不同大氣穩定度,邊界條件設置靈活,在風電領域應用較廣泛[21-22]。本文所使用的WindSim版本為v10.0。
1.3 實測資料
1.3.1 地面觀測
“妮妲”登陸期間,香港橫瀾島氣象站、香港國際機場氣象站、澳門國際機場氣象站記錄了較為完整的風速、風向、氣壓等氣象要素,可用來對中尺度氣象模式的模擬結果進行驗證。
1.3.2 梯度觀測
除參考文獻[17]中的激光測風雷達觀測資料,深圳氣象局350 m 氣象梯度觀測鐵塔也獲取了“妮妲”登陸期間的實測風速、風向特征[23],上述風廓線觀測資料可用來對微尺度CFD的模擬結果進行驗證。實測資料說明見表1。

表1 用于驗證的實測資料Tab.1 Observation data for simulation validation
2 分析方法
2.1 模擬方案
設置3 組數值試驗,記為T1、T2 和T3。T1 為基于WRF 的中尺度模擬,T2 為基于WindSim 的微尺度模擬,T3 為WRF +WindSim 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
2.1.1 T1試驗設置
在T1 試驗中,共設4 層水平網格,前3 層模擬區域如圖1(a)所示,最內層模擬區域如圖1(b)所示;空間分辨率依次為27 km、9 km、3 km、1 km,每層網格數分別為251×201、196×166、196×166、193×163。模式垂直分層為50 層,為了更精確地模擬近地面風廓線形態,200 m 高度以下設置8 層,模式頂氣壓50 hPa。模擬時段為8 月1 日00:00 時~8 月2 日23:00 時,模式時間積分步長135 s(確保積分穩定),輸出逐10 min的風速、風向、氣壓、氣溫等要素(運行前12 h 作為模式啟動時間不予分析)。模式運行的氣象初始場與邊界場均來自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的ERA5 再分析資料。地形高程與下墊面類型等靜態數據來自模式自帶的地形數據集(Global Multiresolution Terrain Elevation Data 2010,GMTED2010)與基于中分辨率成像光譜儀(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MODIS)反演數據的土地利用類型數據集,空間分辨率30″(約0.9km)。根據WRF 模式在以往臺風個例模擬上的最佳物理過程參數化方案選項與組合研究成果[24-26],并且在本次個例模擬上經過反復比選,臺風路徑與強度模擬誤差最小的主要物理過程參數化方案如下:長、短波輻射方案為RRTMG(rapid radiative transfer model for global climate model),云微物理方案為WSM5(WRF-singlemoment-microphysics classes 5),行星邊界層參數化方案為YSU(Yonsei University),陸面過程方案為Noah(Noah land model)。

圖1 T1、T2、T3試驗中的模擬區域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s of simulation area in T1,T2 and T3 case
2.1.2 T2試驗設置
在T2 試驗中,模擬區域如圖1(c)所示,即以激光雷達為中心的10 km×10 km 范圍;中心區域3 km×3 km 范圍進行水平網格加密,加密區域內空間分辨率相同(600 m、300 m、100 m、30 m 共4 種情形),其余區域的網格分辨率依次線性增加。垂直分層52 層,為了更精確地模擬近地面風廓線形態,離地10~190 m 高度間隔20 m 設1 層;模擬區域頂高程5 000 m(確保網格空區比大于0.95,避免非物理加速影響)。對特定風向下的定常風場進行CFD 模擬,地形高程與下墊面類型數據來自ASTER GDEM 數據集與Globalcover 數據集。依照WindSim 軟件在復雜地形環境的應用經驗,確保CFD 模擬結果穩定收斂的模型設置有:求解器GCV(generalized cross validation),湍流模型RNG(renormalization group),迭代殘差收斂閾值0.001,大氣穩定度為中性,頂邊界條件為固定壓力,側邊界條件為軟件默認廓線形式。
2.1.3 T3試驗設置
在T2 試驗的基礎上,利用WindSim 軟件提供WRF 模式接口程序,將T1 試驗中的逐10 min 經向風、緯向風、垂直速度、氣壓和氣溫等輸出結果插值到圖1(c)的格點上,形成“妮妲”影響期間隨時間變化的風、溫廓線,代替T2 試驗中的邊界條件與大氣穩定度設置,進行逐10 min 風場的CFD模擬。
2.2 模擬誤差統計
設置平均誤差E、絕對誤差M、均方根誤差S和相關系數R等4個統計指標對T1試驗的模擬時間序列進行驗證,表達式如下。
式中:xs,i為模擬序列中的第i個樣本;xo,i為實測序列中的第i個樣本;n為序列樣本數量;為模擬序列均值;為實測序列均值。
2.3 模擬結果分析
設置無量綱水平風速廓線V'(z)與無量綱垂直速度廓線W'(z),對各試驗中的風廓線形態進行驗證,表達式如下。
式中:V(z)為任一高度z的水平風速;V100m為離地100 m 高度的水平風速;W(z)為任一高度z的垂直速度;W100m為離地100 m高度的垂直速度。
另外,設置徑向速度Vr,對T3 試驗中的風場空間分布形態進行對比,表達式如下。
式中:u、v、w分別為WindSim 輸出的x-y-z坐標系中的風速分量,分別代表東向、北向和垂直方向上的風速值;φ為方位角(與正東方向的夾角);θ為傾角(與天頂之間的夾角)。
3 結果與討論
3.1 T1試驗
如圖2所示,就激光雷達點位而言,基于WRF的中尺度模擬較好地再現了“妮妲”登陸期間的氣象要素時間變化過程,氣壓的“U”型變化、風速的“雙峰”型變化、超過120°的風向連續變化特征均在模擬值中得以體現。此外,模擬值在氣象梯度鐵塔、香港橫瀾島氣象站、香港國際機場氣象站、澳門國際機場氣象站等點位也呈現出與實測值較為一致的變化過程。各點位的模擬誤差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氣壓的相關系數在0.965~0.986 之間,風速的相關系數在0.682~0.941 之間,風向的相關系數在0.766~0.988 之間,印證了中尺度模式模擬的可行性。

圖2 T1試驗中的激光雷達點位結果對比Fig.2 Comparison of LiDAR locations in T1 case

表2 T1試驗的模擬值誤差統計Tab.2 Simulation error statistics in T1 case
另外,就氣壓而言,各點位的平均誤差、平均絕對誤差、均方根誤差均很小,數值不超過2 hPa,反映了WRF 模式對氣壓場強度的模擬具有高精度。就風速而言,大部分點位的平均誤差為正值,表明WRF 模式對風速有一定程度的高估。上述情況與模式空間分辨率有關,即使T1 試驗中的最高空間分辨率為1 km,但由于WRF模式自身的限制,10~100 m 空間分辨率量級的微小地形仍然無法在模式中得到體現,從而造成模式中地形對風場的阻塞效應可能被低估,相應的絕對誤差、均方根誤差基本穩定在2.2~3.6 m/s之間,模擬精度不及氣壓。就風向而言,各點位的平均誤差在14 °~30 °之間,若按16 個風向扇區而言,誤差控制在左、右1 個扇區之內,但部分點位的絕對誤差、均方根誤差較大,其原因也可能與中尺度模式中的地形效應偏差,以及本次臺風眼區影響時段內觀測風向較為離散有關。
進一步利用無量綱水平風速廓線V'(z),對激光雷達和氣象鐵塔點位的局地風廓線進行驗證,如圖3所示。依照參考文獻[17]的做法,選取3個時段進行對比:時段A(8 月1 日23:00 時—8 月2 日02:00 時,對應“妮妲”登陸前的眼壁強風區影響時段)、時段B(8月2日04:00時—06:00時,對應“妮妲”眼區影響時段)、時段C(8 月2 日07:00 時—10:00時,對應“妮妲”登陸后的眼壁強風區影響時段)。由圖3可知,時段B的模擬廓線與實測值較為一致,而時段A、C 的模擬廓線在200 m 高度以上出現明顯偏離。具體表現為實測V'(z)更加傾斜,而模擬值的高、低層之間水平風速梯度小于實測值,原因也與局地風場的地形阻塞效應可能在模式中被低估有關,并且這種情況在大風影響時段內更為顯著。

圖3 T1試驗中的水平風速廓線對比Fig.3 Comparison of horizontal wind speed profiles in T1 case
3.2 T2試驗
鑒于中尺度氣象模式在空間分辨率上的限制,通過基于WindSim 的微尺度模擬得到更高分辨率的風場模擬結果,并對比不同分辨率情形下的無量綱水平風速廓線V'(z)與無量綱垂直速度廓線W'(z),揭示地形影響局地風場的細節。
如圖4 所示,對于激光雷達點位,利用335 °~15 °之間的7 個典型風向,模擬時段A 內臺風眼壁強風的可能風向,模擬結果均穩定收斂(迭代殘差小于或等于閾值),結果可信。隨著空間分辨率提高,各個典型風向下無量綱水平風速廓線V'(z)與無量綱垂直速度廓線W'(z)出現顯著差異,反映了不同空間尺度的地形效應。另一方面,當分辨率提高為100 m 甚至更高的30 m 時,會出現某個風向或某兩個臨近風向的廓線模擬值迅速逼近實測值的現象,時段C 則利用150 °~190 °之間的8 個典型風向進行模擬,也出現類似趨勢,上述現象與臺風環流背景下局地風廓線的形成機理密切相關。

圖4 T2試驗中激光雷達點位的水平風速廓線對比Fig.4 Comparison of horizontal wind speed profiles at LiDAR location in T2 case
進一步利用WindSim 的定向模擬結果來分析激光雷達點位的風廓線形成機理。根據參考文獻[17]的介紹,激光雷達觀測點位周圍地形呈現北高南低的特征,其西北方向和東南方向有低矮丘陵分布。如圖5所示,選擇激光雷達點位南-北方向的地形剖面進行分析,在時段A 內,受西北偏北氣流控制,當氣流經過雷達北側2 km 附近的丘陵地形時,由于受到山體阻擋、遲滯,翻山后氣流下沉,風速降低,形成回流區并擴展至激光雷達點位上空,導致激光雷達V'(z)更為傾斜,W'(z)出現負值。在時段C 內,受偏南氣流控制,氣流受地形強迫抬升,導致激光雷達W'(z)出現正值。可以看到,上述現象與特定風向內10~100 m 空間分辨率量級的局地地形效應有關,在T2 試驗中隨著空間分辨率的提升,這種局地地形效應才得以體現,而在空間分辨率有限的T1試驗中,無法被中尺度氣象模式所反映。

圖5 T2試驗中的局地風速剖面對比(南-北方向)Fig.5 Comparison of local wind speed profiles h in T2 case(from north to sout)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臺風眼壁強風區內湍流活動旺盛,時段A、C內的大氣穩定度可能偏離中性,因此基于中性大氣穩定度的T2 試驗在垂直速度模擬上仍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時段A、C 內風向會發生一定幅度擺動;而隨著風向的不同,氣流途徑地形的坡度、坡向發生變化,地形效應也出現差異。因此基于固定邊界條件的T2 試驗無法反映臺風環流的實際特征,存在一定不足。
3.3 T3試驗
鑒于T2 試驗的邊界條件與大氣穩定度局限,通過WRF +WindSim 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響應臺風眼壁強風區逐10 min的風速、風向、氣壓、氣溫變化,并將高空間分辨率的CFD模擬擴展至整個時段A和時段C。
同樣針對激光雷達點位進行對比,將時段A、C 全時段內的水平風速廓線、垂直速度廓線進行平均,如圖6 所示。WRF +WindSim 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既修正了單獨WRF 模擬的地形效應偏差,又改善了單獨WindSim 模擬的邊界條件和大氣穩定度,垂直速度模擬精度更高。可以看到,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方式結合了中尺度氣象模式、微尺度CFD 工具各自的模擬優勢,對比圖3—5 的模擬值,與實測值的偏差更小。

圖6 T3試驗中激光雷達點位的水平風速廓線對比Fig.6 Comparison of horizontal wind speed profiles at LiDAR location in T3 case
筆者在時段C 的激光雷達觀測過程中,還采集了激光雷達水平方位掃描(PPI)的徑向速度數據,在此按照2.3節的表達式,將T3試驗中時段C 的三維風場模擬結果合成出徑向速度Vr,與激光雷達實際測量的Vr進行對比。如圖7(a)所示,WRF+WindSim 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得到的徑向速度場中的零速度線方位、正值區和負值區的方位與覆蓋范圍、徑向速度的具體大小等均與圖7(b)的實測結果具有一致性。由于徑向速度是風矢量在某一特定方位和傾角下的投影,綜合體現了局地風速、風向的實際特征,因而徑向速度模擬的精確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三維風場模擬的準確性。因此認為WRF +WindSim 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具備臺風影響期間復雜地形下的三維風場模擬能力。

圖7 T3試驗中風場空間分布對比Fig.7 Comparison of wind field spatial distributions in T3 case
3.4 討論
結合3.1至3.3節的結果分析,T3試驗中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方式綜合了中尺度氣象模式與微尺度CFD工具各自的優勢,在臺風“妮妲”登陸期間沿海局地風場的數值模擬上具有更高精度,能夠為風災事故的原因分析和情景再現提供更為豐富的風場資料;下一步還需要收集更多臺風個例進行模擬結果檢驗,確定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方式的可靠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T3 試驗中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方式在提高模擬精度的同時,逐10 min的CFD 模擬也需要消耗較大量的計算資源與時間,從而無法直接在沿海輸電線路風災預警中應用。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還需要發展新的中、微尺度嵌套預測方法,在提高空間分辨率的同時保證相應的預報時效。
4 結論
本文針對1614 號強臺風“妮妲”登陸期間的沿海輸電線路局地風場進行數值模擬研究,通過單獨中尺度模擬、單獨微尺度模擬以及中、微尺度嵌套模擬等三組試驗,并與臺風期間的實測資料進行對比,取得如下結論。
1)基于WRF 的中尺度模擬較好地再現出“妮妲”登陸期間的氣象要素時間變化過程,WRF 模式對氣壓場強度的模擬具有高精度,對風場的模擬精度不及氣壓,眼壁強風區影響時段內的風廓線與實測值相比出現偏離,原因與局地風場的地形阻塞效應在WRF模式中被低估有關。
2)基于WindSim 的微尺度模擬較好地再現特定風向內10~100 m 空間分辨率量級的風場地形效應;當空間分辨率提高為100 m 甚至更高的30 m 時,會出現某個風向或某兩個臨近風向的風廓線迅速逼近實測值的現象,揭示了臺風環流背景下局地風廓線的形成機理。
3)WRF +WindSim 的中、微尺度嵌套模擬既能修正單獨WRF 模擬的地形效應偏差,又能改善單獨WindSim 模擬的邊界條件和大氣穩定度,具備臺風影響期間復雜地形下的三維風場模擬能力,模擬結果精度高于單獨中、微尺度模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