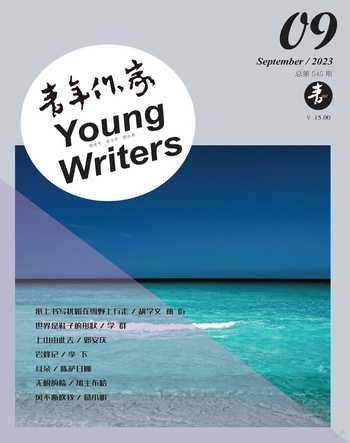辨識度的意義
有一說一,如果你非要問我《無根的臉》寫了什么,我只能告訴你,我也不知道。或者說,我可以告訴你,這小說寫了悲傷如何逆流成河,寫了親人間冰冷的溫情,寫了一個少年怎樣在非常態的生活中孤獨地成長,寫了命運的不可知,寫了彝族某處的現實一種。類似的“中心思想”還可以總結出一串子。但這些“中心思想”在我合上小說之后,發現它們中無一能讓我與這篇小說建立起精確的聯系。而我必須承認,小說讀過之后,記憶如此深刻,我幾乎不需要任何“中心思想”就可以完整地想象出整部小說。
這感覺有點像大學里讀的卡森·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二十多年過去,我依然記得小說中人物歪歪扭扭的古怪生活。《傷心咖啡館之歌》寫了什么?至今我也只能語焉不詳,但那么多“中心思想”正大、深刻的小說都煙消云散了,艾米莉亞小姐、馬文·梅西和雷蒙表哥三個人之間詭譎的愛情還記憶猶新。原因無他,辨識度高也。它的詭異的故事、它的獨特的語言、它的陰郁的氛圍、它的決不迎合讀者的結局,以及敘事藝術上的幾乎無可挑剔,讓它跟其他小說醒目地區別了開來,單獨站成一支隊伍。這就是它的辨識度。
《無根的臉》也是獨自站成一支隊伍的小說。當然,我不是說它就好成了《傷心咖啡館之歌》,而是說它自有其辨識度。
首先取材就稀罕,彝族生活。我讀過一些講述彝族生活的作品,也認識一些彝族作家朋友,但這“一些”放在整個閱讀視野中還是極少數。彝族生活對絕大多數讀者來說依然是陌生的領域,尤其是更為本質化的彝族生活。小說中的人名、生活習慣、民俗風情,處理家庭和感情的方式,都有其強烈的陌生化效果。還有作者加主布哈,這名字你看一眼未必能記住,但下次再見,你多半想得起來。
然后是故事。即使不如作者一再渲染得那般“悲傷”,起碼是個壓抑的故事。歡欣的故事轉瞬即逝,壓抑了,你得緩半天才能吐出憋心里的那股悶氣。對少年普諾的命運我斷無樂觀的期許,但他們回到奶吉鎮自己家里,又兼父親刑滿釋放,想一個孩子,十年辛苦不尋常,總不能讓他一條道走到黑吧?嘿,都不是走到黑,而是走到更黑。當然,其他人物也各自有戲,舅舅達野的秘密,父親鳩阿垛的急速赴死,母親諾莫施澤慌亂又絕望的人生,姐姐戈瑪的隱忍、愛和堅硬,就連相對單面的科莫阿果,哪一個人的故事單拎出來,都可以敷衍出蕩氣回腸的一段故事。這些故事很容易跟別的故事區別開來。
最具辨識度的,當屬詩歌的語言和敘述。加主布哈應該是個詩人,起碼在這個小說之前寫過非常成熟的詩。通篇都彌漫著濃濃的詩意,很多句子摘出來,不分行也是相當棒的詩,遵循的也是詩歌的思維和語法。“這一生都在適應,抱緊不會發光的木頭”。“一些風在另一些風里走散,一個人注定在另一個人的世界徘徊不止”。這是小說中的歌詞,有詩的屬性正常。扎眼的是小說中不斷閃現的比喻句,絕大多數比喻放在詩歌里當更從容自在,在小說相對現實和平實的故事邏輯里就顯得跳脫。當然跳脫也有跳脫的美,在“吹著細長的口哨”也是“召喚風”的氛圍里,詩是對小說強調和提升。
如果《無根的臉》之詩意僅枝蔓于語言和敘述,那也只能算“無根的詩意”,加主布哈讓他的詩意滲透到了人物的骨子里,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詩化”小說——至少作者在做著這般的努力:不論小說里的人物歌哭與哀樂,他們說到底都在過著一種詩化的人生,那些流浪的、自我放逐的,乃至好勇斗狠、快意恩仇的生活里,隱隱都飄出來笛子、月琴和木吉他的音樂之聲。
這些共同成就了《無根的臉》的辨識度。就一個短篇小說而言,如果無意創造為社會、為人生、為形而上的意義,那么,經營出獨特的辨識度,也是小說可堪立足的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說,辨識度本身也是好小說的標準之一。
認真地表揚完了小說,照例也得說說作為讀者的遺憾。我不是一個較真的讀者,比如埋在樹下那神秘之物究竟為何,能知道當然很好,不知道也無妨;就小說藝術論,大可略過不提。但我是個認真的讀者,我覺得鳩阿垛之死還是草率了。他可以死,死也可以來得更猛烈些,只是鋪墊必須夠,對一個人來說,死比活著更需要充分的理由。
徐則臣,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