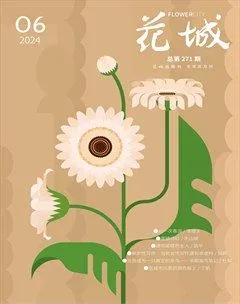異鄉人
一
我和父親是在21年前一個初秋的早晨抵達北京的,同行的還有和我同一年考上北京大學的老鄉小塔。父親拖著兩個巨大的行李箱,肩膀上還扛著一個沉重的旅行袋,汗水濡濕了他的藍色襯衫。
旅途很長,像是耗盡了半生的運氣,我們在縣城里的客運中心乘坐汽車轉道杭州站,還需要在特快火車上待整整一個晚上,才能從浙江東部的一個小縣城,到達曾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首都北京。即便如此,旅途中的情緒一直是雀躍的,在懵懵懂懂中我覺得新的命運要來臨了,于是也便多了一些耐心,等待是有重量的。我趴在火車車窗上,窗外的景色從熟悉的水田、茶園和青綠色的群山,變成了灰撲撲的原野、用黃泥磚砌成的瓦房。有幾只土狗在距離鐵軌十來米的土路上追著火車跑,直到黑黢黢的夜色像墨汁一樣潑下來,黎明又一點點從墨水里擠出來,窗外的路牌、城鄉接合部商店的門匾,還有零星出現的高大建筑上懸掛的牌子,開始出現“北京”這兩個字。對于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江浙人來說,北京實在是太遙遠了,遙遠到只存在在《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歌詞里。父親是因為出差來過好幾次北京的,他指著“北京站”三個字說,瞧,那是毛主席題的字。
廣場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一眼望不到頭。根據北大招生老師的通知,學校安排了幾輛大巴接送新生,可是人實在太多了,我們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小船,被潮水裹挾著一步一步往前挪。然而,年輕的心,是驕傲的,是歡喜的,是確定的,也許還帶了一點躊躇滿志的迷惘。但在這一天,迷惘也顯得并不那么重要,總歸是淡淡的,有閃閃發光的未來,像海市蜃樓一般,在我們的面前鋪陳開來。掌聲、歡呼聲、喝彩聲“嘩嘩嘩”地像浪頭一樣涌上來,是鋪天蓋地的,讓年少的虛榮和淺薄一下子露出了本來面目。
這是2003年的初秋。我和小塔還不知道,并且來不及想象,這一張來自命運的車票,最終會讓來自縣城的女孩飄向何方。2003年是癸未年,無閏月,共365天。對于不同的人來說,不同的年份會有它獨有的印痕,就像是歲月蓋下的印章,輕重緩急,力氣用得參差不齊。2003年發生過很多大事情,非典、美伊戰爭,還有一位著名的香港巨星因為抑郁癥復發選擇在愚人節當天墜樓自殺。對于高考生來說,世界則單純得多,當然也是殘酷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切外部的變量,都改變不了一個恒定的度量衡,就是高考分數。這一年,高考時間史無前例地從7月提前到了6月,就連經驗最豐富的金牌老師也沒講完按照經驗主義備課的模擬題。進考場前,需要測量體溫,而讓體溫飆升的是,高考的數學試卷出乎意料地難,理科班的一個尖子生甚至在考場上崩潰痛哭。
我所在的縣城中學,創辦于清光緒年間,也因這一悠久的歷史,背上了勢必爭先的好勝心,比如對于結果和效率的極度渴望,并如愿在2001年、2002年以強悍的高考排名在浙江省霸榜。好勝心也體現在對于規模和場面的追求,我們是第一屆從老校址搬入城郊新校園的高三學生。新校園的建成,幾乎是當時縣城頭一等的大事,花了幾個億,占地幾百畝,設施設備號稱都是按照省一級重點中學配置,并且“適當超越”了。
然而,新校園正大門的前方,還是長滿雜草的荒地,一眼望過去,荒地的盡頭是蒼郁的樹林,還有一小片正在建設的廠房工地。視線往另一個方向轉一轉,是一片高低錯落的城鄉接合部,往里面走一走,是幽寂的石板巷。來自四面八方的電線纏繞在一起,有一戶人家在大門上貼了過年的春聯,春聯上的墨筆字已經被穿堂風蝕去了一橫、一撇、一豎、一捺。爬山虎沿著斑駁的圍墻寂寞地攀緣上去,偶爾從巷子深處傳來“咚咚”的木魚聲,像是敲打著漫長的、陳舊的時間,是上了年歲的老太婆成群結隊地正在做日課。即便擁有最豐富的想象力,也不能知道,十多年后,這一片荒涼敝敗的所在將建成鱗次櫛比的學區房小區,在前幾年房價最高峰的時期每平方米直逼2萬元人民幣。房價不僅受宏觀大勢的影響,也隨著這一所中學的高考成績起伏呈現正向波動。
不管怎樣,在2003年,學校的高考成績遭遇了滑鐵盧:文科班只有我考上了北大,另外有兩個理科班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小塔是另一所中學的文科第一名。流言四起,市民們達成共識的是,就因為從老校址搬走,動了科考的氣運,影響了學校的運勢,甚至有一些望子成龍的家長,帶著即將升入高三的孩子去外地求學。
學校不想認輸,愈發在縣城的老街上,到處張貼出紅彤彤的海報、橫幅和招生廣告,上面是我們被用力放到最大的名字。老街是南北向的,貫穿了當時最熱鬧的市區,從藍色幕墻的國商大廈,經過氣勢恢宏的縣政府大樓、灰色磚墻的人民電影院,再一徑到國營竹編廠、政府迎賓館,甚至居民區犄角旮旯里的居委會、說不上名字的體制內單位,即便是最為漫不經心的行人,都能毫無例外地撞上那一坨坨紅色,在暑日陽光下閃耀著刺眼的光芒。
許多年后,我行走在溫哥華、洛杉磯、胡志明市或新加坡的中國城老街上,偶爾也能撞見類似的紅色宣傳,一抹又一抹,在異國深藍色的天空下,像是暈染開來的杜鵑花。廣東、福建的同鄉會要開團宴或尾牙了,李家店鋪新開業了,王家老太太過壽誕了,還有陸家的孩子被最好的大學錄取了,這是中國式的特有的熱鬧,是指向世俗生活的,竟然也是和縣城生活一樣真實且生龍活虎的。從小鎮出走半生,在與命運欲拒還迎的過招里,我卻已經是一個異鄉人了。那一年遙遠的南方夏日,穿越了年月里幽深的彎彎繞繞,只剩下一坨又一坨無處不在的紅色,可又是模模糊糊的、零零落落的,沾了記憶里的水漬,是濕濕的,是遙遠的、虛無縹緲的。對于行將中年的人來說,又何嘗不是一個氤氳的、悵惘的、半睡半醒的年少夢境?
我一次又一次回到夢境里,抱著一袋沉重的作業,在新建成的高中校園里默默地走路,頭頂是一個大太陽,陽光凌厲地打在我的身上。籃球場還沒建好,澆了一半的瀝青跑道被曬出了水,我低著頭路過暗戀的男生的教室窗口,他正在和同年級的校花說著什么。我路過正在搬運藏書的圖書館,校長看到我,跑過來問:“下一次模擬考準備好了嗎?”我路過只長了幾朵野花的花壇,路過剛剛粉刷完的體育館,這一座龐然大物的門上懸掛著巨大的橫幅——“奮斗30天,沖刺未名湖”。我并不知道,在一個多月后的高考表彰大會里,我將局促地坐在體育館的主席臺上,滿墻都是我的照片和名字。我對著臺下黑壓壓的人頭講述學習經驗,努力裝出不太努力的松弛感。而在一遍遍重復的夢境里,我被明晃晃的陽光追到無路可逃,只想找一處陰涼停下來,大哭一場,為重壓之下未卜的前途,以及面目模糊的遠方。
每一個縣城的孩子,生來便不是上天的寵兒;而每一個這樣的孩子,大約都是想著走出逼仄的家鄉,去遼闊而遙遠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而我們的眼界是有限的,前面的路徑是狹窄的,是泥濘的,是需要用掉全部力氣的。就像在無窮無盡的夢里,看不清楚面目的怪獸在背后追趕著,我們不能回頭,只有努力地跑,不停地跑。
我和小塔是縣城的幸運兒,我們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旅程,終于抵達了北京站的廣場。人流像漲潮時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撞過來,彌散著汗味、殘余的煙草味和方便面的味道。我們沒有找到迎接新生的大巴。父親帶著我倆在廣場邊上的打車點排了大半個小時的長隊,終于打上了一輛出租車,是紅色的桑塔納,里程計費是每公里一塊二。
北京初秋的太陽照耀著寬敞平整的大街,照耀著鱗次櫛比的高樓,照耀著路邊的白樺樹、銀杏樹、梧桐樹。叫不出名字的花開得很熱鬧,一簇簇、一壇壇。經過天安門的時候,父親指著遠處的廣場說,每天凌晨,都會有全國各地的人來這里看升旗。陽光打在我的臉上,有塵土顆粒在出租車里閃著細碎的光。我打開車窗,是北方秋風陌生的味道,像是牙膏泡沫的清香,又微微帶了一點堅硬,與家鄉慢悠悠的柔風是不一樣的。我和小塔都沒有說話,看著在車窗外流過的北京,像是要走進一個陌生的、巨大的、金光閃閃的時空里,一切都是美的,是新奇的,是充滿希望的。
我們在北大南門下車,朝里張望,由南至北的主干道,早已被橫幅、易拉寶和歡聲笑語的人群占領,兩側擺滿了各個學院爭奇斗艷的迎新攤位。有穿著文化衫的師兄師姐們來回穿梭,他們歡笑著,吆喝著,給新生發手冊和傳單,或幫忙推著行李往宿舍樓走。出租車司機跑下來,幫父親從后備廂搬行李,他說:“您呀,好福氣,今兒我也是沾沾喜氣。”父親沒說話,我抬頭看他,他的眼睛里竟有一些濕濕的東西。有迎新的鑼鼓聲罩上來,父親從旅行袋里尋摸出一包沒拆封的煙,軟盒有點壓扁了,是浙江的香煙品牌“大紅鷹”。父親遞給司機,用帶著南方口音的普通話說:“同喜,同喜。”
二
小時候,我在《古詩十九首》里翻到一句詩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我問爺爺:“什么是‘游子’?”爺爺拿過老花眼鏡,仔細看了看,便又把老花眼鏡放在藤椅把手上,慢悠悠地搖著蒲扇說:“譬如你,考上了大學,離開了家鄉,就是‘游子’嘍。”
爺爺是老家一所山區小學的校長,出身鄉村的小地主家庭,兄妹幾個是寡母依靠著一點積蓄養大的。后來愈發入不敷出,但太婆堅持讓爺爺上私塾,為了給小兒子掙學費,踮著小腳去幫村里的茶葉大戶干活。爺爺說,太婆做手工高山茶是頂頂靈光的,灶膛是要用柴火燒熱的,從高山采的新茶,要仔仔細細地撒進滾燙的鐵鍋里去。太婆不惜身,每次制茶,手掌都被燙得長出一個又一個的水皰,也靠著這些水皰換來的銀洋,培養出了讀過書的子女。
爺爺不嗜煙酒,奶奶去世后很多年他都沒有再娶,在家里喝茶、寫毛筆字和看書,偶爾看看《新聞聯播》,就是所有的娛樂了。小時候,我和堂兄看到他,都會繞著墻角走,防止一不小心被捉住去寫毛筆字,或者背唐詩。爺爺有一間書房,等秋天到了,天氣變得高爽干燥的時候,他會把書房里的書,一摞摞地搬到陽臺上曬一曬。南方的書蟲是很厲害的,一不小心,書頁上就會被咬出一口口的小洞。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卻還記得曬過陽光的油墨香,原來是那么好聞,就像一個染了金色的夢境,一口氣吐出秦皇漢武的錦繡山河。
識字多了一些之后,我放了學,就偷偷溜進爺爺的書房,借著夕陽的余光,在木制的樓板間讀書。天色暗下去,外面的世界在我的心里亮起來。爺爺的幾個竹藤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摞了許多書,有四大名著的線裝本,有四書五經,還有《山海經》《儒林外史》《資治通鑒》;有《國史大綱》《中國哲學史》,竟還有各種世界名著。有的書是新的,想來是爺爺藏起來想要給到我們幾個孫子孫女的春節禮物,有的書頁已經發黃了,像是隨手一碰,紙頁便會脆得“啪嗒”碎掉一樣。
在我的家鄉,讀書是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情。讀書讀出息了,是光宗耀祖的。哪怕一輩子就在村子里采茶、養豬、種水稻,哪怕一輩子只在老城關的菜市場擺了一個小攤,或是在老街上拉黃包車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但在孩子的教育花費上,這座小城里的家長們是毫不吝嗇的。他們也早早在心里做了打算,不管自己怎么苦,都要存錢給孩子讀書。讀書讀好了,當然是要留在“外面”的,但這個“外面”又局限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老家人對于“外面”的想象里。比如做生意最好往廣州、深圳跑,讀書要去杭州、上海,而北京是有點遠的。有一天,在深圳開服裝廠的大姑回老家,她跟爺爺提起,有一個深圳朋友的孩子在紐約讀大學。紐約在哪里呢?在美國。爺爺驚了,戴上老花鏡,拿起地球儀,轉了一圈,才找到美國。他搖搖頭說:“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太遠了。”他又看著我和堂兄說:“念大學,就在杭州、上海念啊,這樣我還能常常看到你們。”
而我心里卻是向往著遙遠的生活的,并且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這個“遙遠”不是杭州,不是上海,或許也不是北京。不過,回到日常里來,和大多數中學生一樣,我的生活是單調的、乏味的,除了上課還是上課,活動半徑局限在學校、家和老街上。于是,我便很喜歡參加各類知識競賽、作文比賽和優等生夏令營,只有不停地做題,不停地“打怪”,得到地級市、省里的名次,才能在領獎的時候短暫地離開縣城。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父親微薄的工資收入有了改善,于是我又多了一個獎勵項目——短途旅行。只要關鍵考試得了第一名,父母便會帶著我在江浙滬的景點轉一圈,比如橫店影視城、蘇州拙政園。2000年結束中考的夏天,父親帶我去杭州走了一圈,返程前去了當時最時髦的高端商場銀泰百貨,那是縣城女孩心中的人間繁華。我穿著“以純”的粉色T恤,怯生生地在四樓的女裝部轉了一圈,選了一條“艾格”品牌的連衣裙,399元,嵌上了精致的蕾絲邊,對少女時期的我來說,已經是衣服里最貴的了。每次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比如主持學校活動,或作為優秀學生接受媒體訪談時,我才舍得穿上它。
在大多數時候,我看到“遠方”的方式,是沿著縣城的溪流往上走。幾乎每一座江南小城都會有一條屬于她的溪流,我老家也不例外,但例外的是,這一條溪流,是在李白的詩歌里明晃晃地存在過的,是因了詩仙旖旎的詩詞,在我年少的心里,寫上了浪漫與風流,寫上了希冀與野望,寫上了長安三萬里的。
平常的時候,這一條溪流是秀麗的、耐心的,是寵辱不驚的,是與熱烈的、俗氣的、算計的縣城生活相悖的。我至今還記得水邊有幾株柳樹,濃稠的知了聲直直地漏下來,暖風悠悠地吹過,江面泛起點點白光,白色的水鳥飛過,在水面上打了一圈優美的漣漪。好不容易有下雪的冬日,霰子、雪花,就這樣揮灑著形狀,落進柔和的水里,或飄在幽寂的江面上,是江南的冬景,即使和《湖心亭看雪》里的場景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
有一年初夏,我剛學會騎自行車,和幾個朋友往溪流的上風口騎,我想知道,這一條從唐詩里流淌出來的溪流,會經過哪些村鎮,會通往哪些遠方,那一些遠方又是怎樣的模樣。江風吹起我們白色的校服衣擺,像是吹起一個蓬勃的夏天。我們奮力地騎啊騎,在風里經過堤岸上的露天卡拉OK,經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菜市場(是用塑料布搭起來的),經過油條、粢飯、豆腐包子飄過來的香味,經過江邊小巷里發廊彌散出的曖昧燈光,經過音像店里的《忘情水》《傷心太平洋》《千年等一回》。我們就這樣不回頭地,經過一切無憂無慮,經過一切真實的、熱鬧的、傷感的、活色生香的、轉瞬即逝的市井歲月。
不過到了梅雨季節,我們便被禁止去江邊了。每年6月,老家會一直落雨,從淅淅瀝瀝到嘩啦啦,溪流也像是在秀麗的詩句里忍耐了太久,一夜之間就露出暴戾的本來面目,不管不顧地漲,直到淹沒江邊高高的蘆葦叢。每到這一個時節,父親就會有好幾天不著家,他需要參加一個叫作“防汛抗洪”的工作;而我也被囑咐,在他結束值班前,讀完他留給我的書。
一個梅雨季節快要過去的黃昏,我在學校樓道的轉角口,遇見了父親的一位朋友,他的獨子和我一個班級。他笑著對我說:“磊磊要去新加坡讀中學了。”我在腦海里旋轉了一下爺爺的地球儀,新加坡應該是在赤道上,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我說:“那多熱啊。”第二天,磊磊就沒再來上課了。后來,他的名字只活在從遙遠的赤道飄回來的傳說里,這是我第一個離開縣城去遠方的同學。再后來,我聽說,從美國的一所大學畢業后,磊磊又被要求回到了家鄉,繼承了家里的廠子。又過了幾年,有中學同學告訴我,磊磊走了,跳進了李白寫過的那一條溪流,是因為抑郁癥。在外面的時候就得了,他和抑郁癥搏斗了十幾年。我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了很久很久,想起溪流邊上有風吹過的夏天,想起中學教室里明晃晃的勵志標語和排名表,想起磊磊坐在我后排的后排,是那樣愛笑,笑著在自習課給鄰排的同學扔紙團,笑著扯一扯前排男生的校服領子,就連被班主任厲聲批評時也是微微笑著的。這一個愛笑的男孩,去過那么多遠方,在那些遠方,他得到過什么?失去過什么?他怎么忍心帶著那些遠方的痕跡,在家鄉奔涌的溪流里,永不回頭?
那時,我已經在一家報社工作了,在全國各地東奔西跑,山高水長,每年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有一天,我正在開選題會,收到了父親的電話,說爺爺快不行了。我打開軟件,買了當天飛往杭州的機票,到了杭州又找了朋友接應。還沒到家,就遠遠聽見了哀樂聲。爺爺已經穿上了壽衣,白頭發梳得一絲不茍,安靜地躺在他的床上,他再也不能捉住我們背唐詩、寫毛筆字了。
白事畢了,我和幾個堂兄妹整理爺爺的書房,在四書五經的邊上,翻到一本厚厚的牛皮紙工作筆記,打開看,是一摞剪報,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是我從大學開始在各報紙、雜志發表過的文章。有的剪報上,爺爺還特意用筆畫了圈、加了備注,比如“這句寫得不錯”“這個詞語換成××比較好”。我聽到空氣里有一些破碎的聲音,眼淚就這樣掉下來。這些年,我回老家過年,見到爺爺,不過是簡單聊上幾句,跟他說說外面。他總會問我:“我們縣又有幾個學生考上北大了啊?北京這幾年還有沙塵暴嗎?去郵局能訂到你單位的報紙嗎?”再后來,我懂事了些,過年會給他一個紅包。因為做記者的薪水微薄,紅包的數額并不大,轉天爺爺會添一點錢,在我離家的時候,硬是要塞回來。我不要,他就直接塞在我的行李箱里。爺爺說:“你離得遠了,見面次數就少了,在外面照顧好自己,過年要回來啊。”最后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將買的水果籃放在爺爺的床頭,像小時候一樣,爺爺塞了一盒牛奶給我。我走出很遠,回頭看到爺爺拄著手杖,掛著一個暖水袋,在醫院走廊的盡頭朝我揮手。
我在回外地工作的時候,帶上了爺爺留下的剪報本,飛機穿越平流層的時候,我打開舷窗,刺眼的光線鉆進我的眼睛,酸澀的,滯脹的,我看見窗外的白云,一團又一團,變幻著形狀。別處的云和家鄉的云是不一樣的,我想起“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我終于成了小城的游子,也是歲月的游子了。
三
我和小塔都是很喜歡北京的。走在冬天飄滿糖炒栗子味道的街上,感覺滿大街都翻滾著希望,有無數種生活的可能性,帶著令人迷醉的開闊與熱情撲面而來。北京好大啊!從東到西就得花上幾個小時,不像縣城老街,只要花上半小時就能從南走到北。那會兒,五道口還未成為“宇宙中心”,光合作用咖啡館橙色的燈光下,穿著絲綢襯衫的女白領正在對著筆記本電腦敲字,椅背上是當季最流行的軍綠色大衣,我猜她是某一家外企的員工。長著一頭金發的外國留學生踩著滑板一躍而過,順帶著劃過一聲快樂的口哨。從靠近北大南門的宿舍陽臺遠望,能看到蘇州街上的“十七英里”KTV和中關村巨大的“家樂福”標志。理想國際大廈的樓頂,有幾家互聯網公司的名牌用偌大的紅色字體豎起,在藍色的天際下閃閃發亮。這里的一切都是奔騰的、充滿欲望的,有著不可測的未來。
高考帶來的一切榮耀與熱鬧,很快回復平靜。這一波熱鬧過去了,便會有下一波的熱鬧,每一年都會有自己的熱鬧。本科畢業的時候,小塔去了一家韓國電影公司做管培生,被分派在學校附近的一家電影院做項目經理。我保研了,新聞學的碩士研究生學制是兩年,于是一邊繼續在燕園學習,一邊在外面找實習。我去看小塔,電影院位于中關村一家新開商場的地下一層,還是一片工地,在尖利的裝修聲里,小塔從三格板木材與泡沫的空隙里鉆出來,小小的個子,穿了一身黑色的制服,頭上還沾了一點木屑。我扯了扯她的領結,笑著說:“怎么像個服務生?”小塔打了一下我的手,說:“走,吃飯去。”
接近中午的陽光很烈,我們走進中關村電子城的一家牛肉面館,面館里零零散散地坐了幾個通宵自習的學生,有的趴在座位上睡覺,紅色的GRE詞匯書像一塊磚頭攤在桌上。一碗牛肉面是4塊錢,小塔一邊往碗里狠狠地加香菜,一邊說:“你知道美國次貸危機吧,對世界經濟影響挺大的,估計你們這一屆工作不好找,你得抓緊準備著。”我沒有說話,小塔便也沉默了。我們一邊吃面,一邊看向門外,隔著沾了塵土的玻璃門,是一幢灰色的四層樓房,因為年代久了,墻面略微有些發黑,不過門牌上“新東方學校”這幾個字倒是擦得亮亮堂堂。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的標語下,有學生模樣的男女抱著厚厚的教材走進門廊,是氤氳的迷惘的總歸要抓住什么的味道。
無論怎樣,那卻是中國的2008年啊,是在記憶里閃閃發光的年份,是十多年后想起來就會憂傷、欣喜與悵惘的年份,五道口、三里屯、國貿、大望路、金融街……空氣里都是濃稠得化不開的蒸蒸日上的味道。我在一家外媒實習,是一位混血女主持的小助理。奧運會開幕式的那天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出外景,人潮涌動,人們身上穿著五星紅旗,臉上畫著五星紅旗,就連額頭上也綁著五星紅旗。開幕式的鐘聲響起,有絢爛的煙花像一個又一個大腳印,踏過北京城的天空,不同口音、不同膚色的人群歡呼起來,人群發出一波又一波的聲浪,潮水一般的“北京歡迎你”“北京加油”“我愛你,中國”,有一群穿著紅T恤的年輕人喊到聲嘶力竭,在熱烈盛大的氣氛里,索性抱成一團,開心地痛哭起來。
找工作還是經歷了一點小小的周折,我最后考進了一家大報,留在了北京,并擁有了北京戶口。小塔決定為我慶祝,邀請我到她新租的房子里做客。那是一個初夏的中午,居民樓在頤和園路的盡頭,黃色的外墻,有些舊了。小區中間有一個廣場,廣場上有一個噴泉池,可能因為真正的夏天還沒到,噴泉還沒開始工作,池子是干涸的,一座光禿禿的假山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廣場一邊的樹蔭下,有一個賣蔬果的攤子,泡沫盒子一只又一只敞開著,掛著泥的心里美蘿卜、還沒熟透的番茄堆在一邊,桃子、西瓜堆在另一邊。攤主穿著白汗衫,搖著大蒲扇吆喝著:“剛上市的平谷桃子、大興西瓜,不甜不要錢。”
單元門禁敞開著,我拎了幾個桃子、一個西瓜上樓。租房不大,一室一廳,臥室角落放了一個簡易衣柜,還有一個出差用的旅行箱,像是主人拔腿就要走似的。小塔做了一桌子菜,是老家的口味,有蝦米絲瓜湯、番茄炒蛋、紅燒鯽魚,還有家鄉炒年糕。
在北京生活了這么些年,我們的腸胃開始變得五湖四海,但很多時候,味蕾這一個東西,是最認生的,是更歡喜自出生以來就熟悉的味道的。來自家鄉的味道,就是游子對來處欲說還休的曖昧感情。
在一切關于家鄉的食物里,我最喜歡炒年糕。在我的記憶里,外婆做的家鄉炒年糕是最好吃的。外婆住的是浙江鄉下的老臺門,前門院子里種了一畦小白菜、甜椒和蔥蒜。下午的太陽斜著進到臺門里,連帶著古舊的窗欞也亮堂起來。那時,外婆還沒患上阿爾茨海默病,還記得我的模樣。她輕輕地喚我“阿凱”,側著頭抱怨“讀書辛苦,阿囡又瘦了”。這話是說給母親聽的。外婆每次都會去灶頭間不厭其煩地燒點心給我吃。她蹲在柴灶后頭,往灶坑里塞刨花,點火,再添上干樹枝、茅草。家鄉炒年糕的制作,是極煩瑣的,需要很多配料,比如肉絲、蘑菇片、春筍絲、胡蘿卜絲、炒雞蛋絲、豆腐片和大蒜葉,以及糖、鹽和生抽。但也是最簡單的,到最后頂要緊的不是手藝,而是耐心。也因為這一點耐心,這一碗最家常的炒年糕,是放進了情誼與愛的。
灶頭間的后窗外是幾叢翠竹,郁郁蔥蔥的,有細碎的陽光穿過竹葉的間隙漏進來,在外婆清癯的臉上若即若離,影影綽綽。我坐在條凳上一邊吃著炒年糕,一邊數著外婆臉上的光影。這樣悠長而閑暇的暑日,帶著時光過濾后黏膩而溫熱的氣息,填滿了多年漂泊里偶爾像潮水一樣襲來的孤單與迷惘。
我對小塔說,我好久沒吃上家鄉炒年糕了。小塔說,那就多吃兩碗。桌子上放了兩罐嘉士伯,小塔開了啤酒,遞給我,我們一齊喊:“北漂快樂!”碰杯聲是年輕的、快樂的,帶著一些虛妄的夢想,或許也有一點前路茫茫的惆悵。
過了一會兒,小塔對我說,她馬上要調到另一個電影院了,在望京,離學校很遠,轉公交車都得轉上好多趟。那時望京還沒有地鐵。我說,北京那么大,我們見面就少了。小塔喝了一口啤酒說,想開點,說不準,過幾年我們就分開了,在別的地方了。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位作家描述了那時我們的心情:離開故鄉,進入一座大城市,就像被吞進一只怪獸的肚子里。過往的、未來的,確定的、不確定的東西,像是水霧一樣,是縹緲的、抓不住的。
是啊,沒有什么會為渺小的人們停留。在我們缺席的時光里,縣城就像蛻皮一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老街不再是市民購物、逛街、散步的那個無可辯駁的中心了;國商大廈重組了;縣政府從老街上搬到了新開發的城南工業區;人民電影院倒閉了,被改建成了眼鏡城;竹編廠正在鼓勵職工自謀生路;棉紡廠也倒閉了,工人們被安置到運輸公司;政府迎賓館改制了,正在新裝修。
江邊的堤壩上,不再流行露天卡拉OK,攤販們早已撤走了桌凳、VCD機和音響,一到夕陽西下,就有退休的阿伯阿嬸們,提了音箱,來跳廣場舞。沿岸空置的荒地上豎起了黃色的施工標志,有龐大的重機械工程車開始進場,不遠處的工棚門口,有建筑工人們晾曬的衣服在風里飄揚。青石板小巷被拆掉了,染了黃頭發的發廊女郎早已不知去向。菜市場也要拆了重建。號稱擁有黃金潛力的沿江地塊,早已被幾家知名房地產商瓜分完畢,根據政府工作報告表述,隨著五年內建成直通北京的高鐵站,這一區塊將成為縣城最豪華的商圈。
正是蒸蒸日上的時代,裹挾著一股來勢洶洶的金色浪潮,所有人都被卷入了時代踩著鼓點的進行曲里。我家原來居住在老街邊上的一個小區,有一位鄰居是本地有名的越劇女演員。小時候,孩子們在小區的空地上玩捉迷藏,不知道誰喊了一聲“王老師來了”,我們就好奇地、羞怯地四散開去。她已經是中年女人了,卻還是那么講究,挎著一個小黑皮包,穿了一條紅色的連衣裙。她就這樣踩著閃亮的高跟鞋,緩緩地,在縣城的黃昏里一扭一扭地走過來。南方的風吹起她的裙擺,像是一個濃烈的夢境。有一次回家,母親對我說,王老師這幾年炒房發了財,不唱戲了,搬去上海了。母親還說,老鄰居們開始陸陸續續搬走了,搬到新開發的城南去了,那邊小區的名字可花哨了,動不動就是什么星河灣、御金府、白鷺園之類的,聽著跟在大城市似的。母親頓了頓說:“我和你爸也打算搬走了。”
我們搬到了一個靠江的小區,和星河灣、御金府、白鷺園一樣,擁有著磅礴的時髦的卻俗氣的名字。母親說,這里原來也是一個舊村落。有一座新的商場,在原先的村口矗立起來,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和北京、上海、新加坡的購物中心一樣有著繁華而雷同的面貌。我沿著新的熱鬧的商業街走著,經過了六家咖啡店、四家奶茶店、兩家麥當勞、一個電動汽車門市部和一家進口超市,經過安徽土菜館、湖南湘菜館、驢肉火燒,還有家鄉的小籠包鋪子。嘈雜的、陌生的、無序的、來自五湖四海的口音,和歲月一起碾壓過來。在泛黃的歲月里,我竟還是二十多年前那個穿著校服的女孩,就這樣迎著霞光,和兒時的朋友們騎著自行車,從堤壩上一徑入了青石板巷,經過修車鋪、狹小的小賣部,以及大人口中神秘得像吃人妖怪一樣的溫州發廊,經過混雜著磨剪刀、賣雪糕和收破爛的吆喝聲,經過所有泰然的、隱蔽的,熱烈的、憂傷的,一往無前的又無法回頭的生活現場。
中年的小塔在微信里打字,她和家人定居在深圳。她說,不能去探究2003年在我們的生命里留下了什么,我們以為它過去了,而它只是穿過了命運的表層,終極結果是,我們成了回不去故鄉的異鄉人。我說,也許,它只是一個向導,給當時的我們買了一張不知道去哪里的車票,將我們從縣城帶到了北京,讓我們去見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之后它便管不了了。于是我們像最微小的螺絲釘,嵌在龐大機器的齒輪里,不知疲倦又毫無間隙地滾滾向前。而它一直在歲月的驚濤里看著我們:看著我們怎樣一頭扎進大時代;看著我們怎樣被后浪拍肩;看著我們被人遺忘、忘了自己;看著我們作為過時的做題家,在漫長的逆旅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四
我終于定居在新加坡。母親說,我小時候遇上過一位算命先生,先生說,小囡的八字注定要走到很遠的地方。然而,母親一直不愿意提起這一個“預言”,她無法面對根植在心底的隱秘的擔憂:我是她唯一的孩子,不該去很遠的地方。
就連北京,母親也覺得是很遠的。2003年我離家上大學的那一天,父親忙著將行李箱從沒有電梯的老公房搬到樓下,母親索性躲在房間不出來了。我去和她告別,卻看到她坐在床沿上,抱著一卷紙,哭到喘不上氣來。母親說:“北京那么遠,你要照顧好自己啊。”當時的我還沒學會和中國式的父母表達感情,只握了握她的手。年輕的心里是沒有那么多離愁別緒的,而對于將要去北京的少年來說,更是迫不及待的、野心勃勃的、一心想要逃離的。我對母親簡單地說了“再會”,就像往常吃完早飯離家去學校上早自習一樣,是經年里最平常的告別。
年歲大了,我才意識到那一年與家鄉告別的重量,是說不清楚的,是神奇的,是不可預測的。有一些機緣,在暗地里推動著人的命運,離開有時,聚散有時,每一個在當下看起來細微而平常的節點,卻指向了不同的路途。
有一年,我在洛杉磯一家中餐館吃飯的時候,遇見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頭發全白了,鄉音卻還在。他說,他是從福建老家偷渡過來的,是哪一年呢,記不清了,總歸是吃不飽飯的一年。我問他:“回過家鄉嗎?”他點點頭說:“回去過一次的,變化很大。”他頓了頓說:“父母早就過世了,兄弟姐妹老了,村子也變了。”他的目光里有一些歲月流動起來。
鄰桌喧鬧起來,是有人過生日,壽星是一個中年女人,染了紫頭發,化了煙熏妝,穿著一條很短的包臀皮裙。同桌的人們歡笑著,雀躍著,唱完“祝你生日快樂”,有男人朝著餐館老板娘喊起來,點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東北口音。
鄧麗君的聲音,從天花板一角的廣播里忽地墜下來。嘈雜的餐館像被按下暫停鍵一樣靜了幾秒鐘,甜蜜蜜的華語旋律像是穿越了山林、盆地、沙漠、雪原和海洋,來自一個遙遠的熟悉的地方。
就在所有關于山林、盆地、沙漠、雪原和海洋的跋涉中,我終歸是一個異鄉人了,我在更遠的遠方了。二十多年前的我,并不知道縣城與遠方的故事原來如此漫長,一個平凡而勇敢的少年,沿著李白詩里的溪流往上風口走,遇見春夏秋冬,遇見風霜雨雪,遇見悲歡離合,流過的是臺門老宅里晝長人靜的暑日,是老街行道樹上的蟬鳴,是歲月里斑斕而浩蕩的霞光。人世蒼茫,在遼遠而豐盛的大自然前,即便足夠多的個人敘事,也是蒼白虛弱的。異鄉的我用記憶和兒時的故鄉溫存,就像在時間的曠野里從未曾離開過一樣。
責任編輯 許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