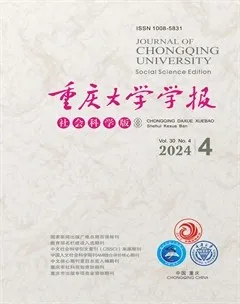整體系統(tǒng)觀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法治進路:梗阻、法理與向度
摘要: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加快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xié)同性”背景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戰(zhàn)略目標的實現(xiàn)需要將整體系統(tǒng)觀作為一種方式變相嵌入到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法治保障命題之中,以塑造整體主義思維范式融貫其中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話語體系與規(guī)范秩序。以整體系統(tǒng)觀為分析工具,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進路關涉問題導向、理論追溯與邏輯向度三個核心議題。于前者,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面臨以“形式理性”為表征的黃河保護法律規(guī)范縱向體系化任務尚未完成、以“行政命令—控制”為內(nèi)在邏輯的權威管制型法律實施機制存在漏洞、以“風險預防”為內(nèi)核的動態(tài)回應性流域司法保障體系付之闕如三重梗阻;于中者,因應現(xiàn)代法治是融合時間、理念與規(guī)范而生成的特定統(tǒng)一體,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構造的基本法理應沿循縱向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tǒng)一、內(nèi)在專業(yè)主義與權力主義的互動、外在公私法的交融而展開;于后者,為達致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良法善治”的目標,宜構建“形神兼?zhèn)洹钡狞S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體系,塑造“軟硬兼施”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執(zhí)法體系以及建立“防治結合”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司法體系。
關鍵詞:習近平法治思想;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整體系統(tǒng)觀;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良法善治
中圖分類號:D922.68;X3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4-0212-13
作為孕育燦爛華夏文明的母親河,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稟賦優(yōu)越,是我國重要的經(jīng)濟走廊。然而,囿于歷史、自然及人文等諸多因素影響,加之近年來人們對資源環(huán)境進行的不合理開發(fā)利用活動,這使原本生態(tài)本底較差、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相對滯后的黃河流域正面臨區(qū)域經(jīng)濟結構失衡、生態(tài)功能失序的雙重風險。在此背景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和經(jīng)濟高質(zhì)量發(fā)展成為新時代推進我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實施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踐行綠色發(fā)展理念等構建新發(fā)展格局過程中的重大時代議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立基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高度,對黃河體弱多病的內(nèi)因與外因進行“循脈問診”與“把脈開方”。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座談會時強調(diào),“黃河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一個有機整體,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系統(tǒng)治理、源頭治理”[1]。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重要論述為根本價值遵循,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把握好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好立場觀點及方法是繼續(xù)在實踐基礎上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基本前提”[2]。整體系統(tǒng)觀作為凝萃于政治、哲學與文化等諸多學科的思維范式,因適配于新時代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空間的秩序期待,而成為推進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切口與科學方法。
相較于其他治理模式,法治以獨具的權威性、約束性而成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根本保障,立法、執(zhí)法、司法等多元要素的耦合性構成了法治系統(tǒng)現(xiàn)代化的基本表征。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作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在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與美麗中國建設雙重宏闊背景的裹挾下,將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重大時代議題全面納入法治保障軌道,對于實現(xiàn)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式現(xiàn)代化目標”無疑具有戰(zhàn)略性支撐作用。是故,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加快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xié)同性”背景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戰(zhàn)略目標的實現(xiàn)需要將作為現(xiàn)代法治衡量標準的“良法善治”與邏輯方法上的“整體系統(tǒng)觀”相結合,即將整體系統(tǒng)觀作為一種方式變相嵌入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法治保障理論與實踐命題之中,以塑造成熟且自洽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話語體系與規(guī)范秩序,明確的問題導向、周延的法理凝練以及系統(tǒng)的法治構造集中映射出整體系統(tǒng)觀視域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法治進路的多維立體化特征。
一、問題導向:整體系統(tǒng)觀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進路的困境審思
整體系統(tǒng)觀作為統(tǒng)攝系統(tǒng)性與整體性兩種科學思維范式的方法論綱,為系統(tǒng)揭示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實踐暴露出的現(xiàn)實梗阻提供了基本價值遵循。
(一)以“形式理性”為表征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縱向體系化任務尚未完成
作為法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體系化方法不僅象征著法學學科所具有的內(nèi)在理性和邏輯嚴密性,還發(fā)揮著維系法秩序穩(wěn)定的關鍵作用。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戰(zhàn)略的系統(tǒng)推進,新時代包括環(huán)境法在內(nèi)的大量立法與修法活動接踵而至,為此亟須將體系化方法作為法律體系科學化建構和立法完善的方法論綱進行運用,這意味著既要制定出內(nèi)容上具有統(tǒng)攝性的經(jīng)典性法律文本,還要構建出形式完備的法律框架。映射到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領域,體系化方法對于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科學建構的指導意義在于: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框架無論是從內(nèi)容還是形式上均需進行一體化建構,以切實將整體系統(tǒng)觀這一立法邏輯貫穿于從內(nèi)容形成至體系完備的每一環(huán)節(jié)。
當前,從調(diào)整內(nèi)容的完整性程度上講,我國《黃河保護法》的出臺既反映了流域以水為核心要素的自然特征,又突出了流域水問題的整體特性,其以分章的形式將水資源、水環(huán)境、水生態(tài)、水經(jīng)濟與水文化串聯(lián)起來,實現(xiàn)了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客體從單一涉水管理向流域一體化治理的結構轉型。整體系統(tǒng)觀視角下,客觀意義上的黃河保護法律制度及其流域生態(tài)保護機制大體是融貫且完整的。然而,從法律體系化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看,以“形式理性”為表征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縱向體系化任務仍處于未竟之狀態(tài)。作為一部涵攝整個流域的綜合性立法,《黃河保護法》規(guī)定的內(nèi)容顯然是較為宏觀的,其雖具備法律內(nèi)容的完整性卻無法以一己之力實現(xiàn)黃河保護法律體系在形式結構上的融貫程度。是故,為保證《黃河保護法》施行過程中呈現(xiàn)出應然的流暢度,對于法律文本中幾乎無涉或者規(guī)定粗糙的法律制度與考核評價機制,亟須黃河流域九省區(qū)以制定更加嚴格、細致的地方性法規(guī)或規(guī)章的形式加以跟進。一方面,法律體系應是一個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的整體,縱向法律規(guī)范體系的形成本質(zhì)為國家立法權縱向分配的結果,在此意義上,整體系統(tǒng)觀視野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的建構邏輯理應對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互動互補形成合理性關照;另一方面,黃河流域涉及空間范圍廣闊,自然地理條件的特殊風貌及不同地方的人文歷史情況決定了流域內(nèi)配套性立法的不可或缺。客觀來講,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地方性配套立法的制定與完善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黃河治理的現(xiàn)代化水平。然而,較為遺憾的是,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領域,黃河經(jīng)濟協(xié)作區(qū)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有關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領域的立法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陜西省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在法律屬性上歸屬為黃河流經(jīng)省區(qū)制定的關于流域部分河道及支流管理的地方性法規(guī),其他省份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立法問題上大多以決議、通知等不具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政策性文件的形式予以回應。在此意義上講,我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縱向法律體系建構仍處在進行中,其所追尋的“法體系邏輯自洽”尚且表現(xiàn)為一種未竟之狀態(tài)。
(二)以“行政命令—控制”為內(nèi)在邏輯的權威管制型黃河法律實施機制存在漏洞
為保證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系統(tǒng)的有效運行,有必要建設以嚴格執(zhí)法為核心環(huán)節(jié)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法律實施系統(tǒng)。當前,我國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施行以流域管理與行政區(qū)域管理相結合的“統(tǒng)管+分管”的管理體制,并以此種體制為基礎逐漸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以“行政命令—控制”為內(nèi)在邏輯的權威管制型黃河法律實施機制。客觀意義上講,因應環(huán)境問題“負外部性”本質(zhì)屬性,政府以權威性管制手段為根本依托在應對復雜多變的流域治理情勢方面無疑具備一定條件優(yōu)勢。然而,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以“行政命令—控制”為內(nèi)在運行邏輯的權威管制型黃河法律實施機制因應自身固有的缺陷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域內(nèi)存在的所有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首先,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產(chǎn)生于自然資源的開發(fā)利用過程之中,是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副產(chǎn)品”[3],以政府行政權能為主導的單向度權力配置與環(huán)境法實施機制無法解決流域范圍內(nèi)發(fā)生的資源節(jié)約集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內(nèi)生性動力問題。這意味著,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除循環(huán)使用加強命令控制的老辦法外,很難以主動、互惠的方式使流域環(huán)境問題得到更妥善的解決。其次,以“行政命令—控制”為內(nèi)在運行邏輯的權威管制型黃河法律實施機制的目標和效果往往受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影響來自政治上的壓力,也來自污染企業(yè)的尋租。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實踐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機構與污染企業(yè)形成了千絲萬縷的利益牽連,在缺少行之有效環(huán)境行政管制權外在監(jiān)督機制的背景下,單純的政府統(tǒng)管法律實施機制會導致政府被管制企業(yè)俘獲,不愿執(zhí)法,甚至產(chǎn)生由環(huán)境事務“管理者”轉變?yōu)榄h(huán)境問題“制造者”的異化風險[4]。最后,基于環(huán)境行政管制條件的欠缺和資源的短缺,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機構及其人員理性的有限性,環(huán)境行政管制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不確定性等客觀因素的存在,以“行政命令—控制”為運行邏輯的權威管制型黃河法律實施機制可能因高昂的行政管制成本而難以對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形成全方位管制。對此,正如布魯斯在《重塑環(huán)境法》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污染源不斷擴大時,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及為搜集信息付出的行政成本給行政部門帶來了巨大壓力,致使以單向度權力運行為表征和以“標準設定”為中心模式的環(huán)境執(zhí)法機制既無法全面控制污染和環(huán)境風險,也無法提供立法者事先承諾的環(huán)境利益[5]。
(三)以“風險預防”為內(nèi)核的動態(tài)回應性黃河流域司法保障體系付之闕如
對于流域生態(tài)保護面臨的實質(zhì)不確定風險,新時代流域環(huán)境司法審判理念應突破傳統(tǒng)意義上“生態(tài)環(huán)境無損害則無救濟”思維范式,將對流域風險的干預行動上升為司法裁判,確保流域司法治理理念實現(xiàn)從末端損害救濟到前端風險預防的歷史性變革。在我國,風險預防原則在環(huán)境司法中的適用進路主要通過帶有預防性司法救濟性質(zhì)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得以實現(xiàn)。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關于全面加強環(huán)境資源審判工作為推進生態(tài)文明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明確要求通過事前預防措施降低環(huán)境風險發(fā)生的可能性及損害程度;《關于審理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亦對“事后損害”與“事前預防”作了明確區(qū)分,將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啟動條件劃分為“已經(jīng)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污染環(huán)境、破壞生態(tài)的行為”和“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污染環(huán)境、破壞生態(tài)的行為”。雖然司法解釋為預防原則在環(huán)境司法中的適用作了一定的規(guī)范性指引,但傳統(tǒng)環(huán)境司法在風險預防原則的貫徹上仍凸顯出不力的局面。目前司法實踐中,除“五小葉槭案”與“綠孔雀案”是以高度蓋然性為標準提起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風險預防的公益訴訟案件,真正以風險預防原則作為司法裁判要旨的案件少之又少。這一環(huán)境司法現(xiàn)狀映射到流域司法層面,客觀上講,面對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實踐中存在的產(chǎn)業(yè)結構性風險、跨域格局性風險和系統(tǒng)失衡性風險,黃河流域環(huán)境司法理應將風險預防原則融貫到現(xiàn)代司法審判理念之中,以充分發(fā)揮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全部制度功能。然而,遺憾的是,當前包括黃河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流域環(huán)境污染案件通常表現(xiàn)為對損害發(fā)生后風險擴大的預防,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公益訴訟仍以救濟性為主,真正以排除具有生態(tài)環(huán)境風險行為的黃河流域預防性環(huán)境公益訴訟至今未見一起,預防性訴訟條款在黃河流域司法治理中被束之高閣而幾乎淪為“冷凍條款”[6]。
二、價值溯源:整體系統(tǒng)觀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進路的法理凝練
整體系統(tǒng)觀視域下,提煉或凝練法理要把握法理的時間維度、價值維度、規(guī)范維度等基本內(nèi)容。映射到法治領域,縱向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tǒng)一、內(nèi)在的專業(yè)主義與權力主義的衡平以及外在的公私法的交融互動共同構成了整體系統(tǒng)觀視域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進路的法理依據(jù)。
(一)縱向時間: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有機統(tǒng)一
作為結構主義學派奠基人、著名語言學家費爾狄南·索緒爾在其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的兩個統(tǒng)一性概念——共時性與歷時性,分別以縱向與橫向、歷史與現(xiàn)實、動態(tài)與靜態(tài)的全方位視角為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與研究結論的普遍性提供了基本的價值遵循[7]。法釋義學下,共時性思維從結構主義角度揭示出同一歷史時期內(nèi)存在的諸要素間的狀態(tài)關系,而歷時性原理強調(diào)的是從歷史向度探究時間相連續(xù)的事物之間的演進規(guī)律。以語言劃分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原則為價值遵循,在推進我國環(huán)境法治實踐過程中啟示我們,一方面應對環(huán)境法律體系、框架相對靜止的結構性特征予以必要性關照;另一方面應注意到環(huán)境法規(guī)范代際演替的必然規(guī)律,把歷時性維度中的利益衡平機制納入現(xiàn)代環(huán)境法治的宏觀結構之中。映射到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保障命題上,應牢記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法治保障系統(tǒng)的建構在時間維度是共時性考察與歷時性判斷有機統(tǒng)一的科學機理。對此,亟須對黃河生態(tài)治理階段性目標與未來圖景予以統(tǒng)籌考量、科學研判,特別是在整體系統(tǒng)觀下,要對過去、現(xiàn)在以及未來間存在的前后相繼、遙相呼應的因果關系形成理性且周延認知。
一方面,實現(xiàn)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目標的法治保障應當具有回顧性。由于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是由過去長期疊加的“負外部性”后果造成的,是故,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目標的實現(xiàn)面臨著“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嚴峻挑戰(zhàn)。特別是鑒于黃河流域內(nèi)不同行政區(qū)域?qū)υ斐闪饔蛏鷳B(tài)問題的“貢獻率”存在較大差異,在推進流域環(huán)境治理及其法治系統(tǒng)建構時,應考慮到歷史累積因素,將對作為技術性和經(jīng)濟性權利的區(qū)域發(fā)展權、作為社會性與政治性權利的區(qū)域治理權、作為自然性與生態(tài)性權利的區(qū)域環(huán)境權等三重權利關系的理性配置奉為圭臬。另一方面,黃河流域法治建設深深地扎根于時代中,其立足現(xiàn)實和著眼未來,與時代同呼吸,與時代共發(fā)展,本質(zhì)是一個歷史活動過程。為此,實現(xiàn)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目標的法治保障還需具有前瞻性。這既包括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應著力構建一個跨時代實現(xiàn)環(huán)境正義的規(guī)范框架,在保證流域內(nèi)當代人享有正當環(huán)境權益的同時也要滿足后代人基于其發(fā)展能力所享有的環(huán)境利益,實現(xiàn)從代內(nèi)公平向代際關懷的思維拓展;也包括在流域環(huán)境風險不確定性背景下,黃河法治應依循風險預防原則,確保實現(xiàn)流域環(huán)境風險事后規(guī)制與事前預防的有機統(tǒng)合。
(二)內(nèi)在理念:專業(yè)主義與權力主義的互動配合
在規(guī)制內(nèi)涵變遷與現(xiàn)代環(huán)境法演進過程中,專業(yè)主義與權力主義作為貫穿現(xiàn)代環(huán)境法治事業(yè)始終的兩種彼此獨立且又相互關聯(lián)的價值理念,揭示出新時代環(huán)境法治的應然走向和實踐邏輯。具言之,因應社會結構的優(yōu)化組合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在此背景下,現(xiàn)代環(huán)境治理作為法律與科學交融互惠的典型場域,其勢必需要在專業(yè)主義與權力主義雙重價值的嵌合驅(qū)動之下方能達致環(huán)境治理的預期目標。之于前者,權力主義因具有高效率、普適性和強制拘束力等優(yōu)勢,其自不待言地處于現(xiàn)代環(huán)境法治價值理念的主導地位;之于后者,環(huán)境法治的技術性特征也決定了科技進步、信息系統(tǒng)與知識權威的創(chuàng)建對我國環(huán)境法治的轉型具有重要支撐作用[8]。因此,作為現(xiàn)代環(huán)境治理中的一條隱形主線,專業(yè)主義理念強調(diào)將專業(yè)知識、信息技術、科學原理運用于與科技信息緊密關聯(lián)的環(huán)境法之中,旨在用全社會的知識與理性降低或控制環(huán)境風險,具有補救權力機關在某些專業(yè)領域因知識狹隘而成為“外行”的功能。
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作為集科學機理與法學原理于一身的論域,在整體系統(tǒng)觀視域下,如何“雙管齊下”,以使相互交織的兩種理念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建構過程中實現(xiàn)衡平,這無疑是新時代生態(tài)文明法治建設不容忽視的重要時代議題。《黃河保護法》第14條創(chuàng)設的以智慧賦能黃河流域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機制科學運作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制度,便是證成專業(yè)主義與權力主義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過程中以融貫互通、交織互動形式存在的典型例證。一方面,黃河流域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機制作為流域合作協(xié)商型事權的協(xié)調(diào)者以及權威型事權的議題發(fā)起者,在流域決策過程中難免存在專業(yè)盲區(qū)或知識漏洞而需要以環(huán)境法或環(huán)境科學等領域?qū)<覍W者為代表的環(huán)境權利主體充分利用專業(yè)知識、技術與資源,從而為實現(xiàn)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良性有序管理提供科學性知識與方法性支撐;另一方面,專業(yè)知識只是扮演著環(huán)境治理事實認定環(huán)節(jié)判斷依據(jù)的工具性角色,黃河流域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機制有權對基于專業(yè)知識作出的法律結論作出采納與否的評價。
(三)外在規(guī)范:公法與私法的融貫互通
自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首次將法律區(qū)分為私法與公法概念以來,公私法的屬性劃分便一直為大陸法國家所承認并堅持[9],現(xiàn)代法治的形式載體為此也游走于公法與私法之間。傳統(tǒng)觀點認為,公法與私法的二元區(qū)隔本質(zhì)上是西方法律文明發(fā)展演變的產(chǎn)物,其源于社會生活的應然需求,反映法律調(diào)整的基本規(guī)律,通常呈現(xiàn)一幅保障私權、限制公權的法治圖景[10]。然而,受到自由放任主義修正、社會矛盾激化、政府權力運用等因素的影響,本為“楚河漢界”相隔的公法與私法之間逐漸破除了橫亙在二者中間的墻幃[11],公私法融貫互通的法律現(xiàn)象日漸顯現(xiàn)。映射到環(huán)境法領域,《民法典》第1234條規(guī)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代修復制度”本質(zhì)上是公法機制在私法領域的拓展應用與制度延伸,其創(chuàng)設出“公法義務、私法操作”的新型環(huán)境救濟思維范式。在《民法典》呈現(xiàn)出“私法公法化”這一法律現(xiàn)象的背后,人們越發(fā)注意到單純靠公法或私法某一種法律機制已經(jīng)無法對關涉環(huán)境公共利益屬性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救濟制度作出自洽的理解。另外,從比較法審視,各國法秩序也均拋棄了公法與私法彼此分離、相互對立的思維方式,轉向?qū)で蠊椒ㄈ诤系穆窂絹斫鉀Q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12]。可見,因應現(xiàn)代環(huán)境問題所具有的復雜性、科技性及綜合性面向,加之公私互動治理頻率顯著增強,公法與私法兩大機制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過程中交融滲透、彼此借力的情形已為大勢所趨。
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法學發(fā)展的必然走向,公私法間的融合互通并不是全然漠視公私法間的區(qū)分,它不等同于凱爾森所論“純粹”的“法一元說”的極端觀點[13],本質(zhì)邏輯在于: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從最初的對抗博弈轉換為如今的合作共贏。對此,最直觀的體現(xiàn)是,由于政府命令控制式管制工具隨著治理要求的拓展而日漸乏力,使基于激勵的規(guī)范(如特許)、透過對市場控制的規(guī)范、公共補償、社會保險等體現(xiàn)公私融合屬性的新型環(huán)境治理工具逐漸演變?yōu)榄h(huán)境法建制的重心所在[14]。以公私法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復雜場景中所呈現(xiàn)的彼此交融的邏輯關系為遵循,整體系統(tǒng)觀視域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法治進路在規(guī)范維度毋庸置疑亦以公私法的融匯協(xié)作為基本表征,任何單一公法或私法都難以為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戰(zhàn)略目標的實現(xiàn)提供牢靠支撐,為此需匯集公私法兩大機制之治理合力。以流域內(nèi)排污權交易機制的建構原理為例,作為實現(xiàn)流域內(nèi)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的制度載體,排污權交易制度既體現(xiàn)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及以排污許可證為形式載體而對企業(yè)排污行為進行管控的公法特征,同時也蘊含著基于意思自治原則所催生的排污權有償使用的私法意涵,在傳統(tǒng)“公私法分隔對立”思維范式下,排污權交易機制的法律屬性難以找尋到邏輯自洽的解釋理路。整體系統(tǒng)觀背景下,通過引入以公私法融會互通為核心價值的德國雙階理論對流域排污權交易法律屬性進行體系重構,這對厘清排污權本身的內(nèi)在邏輯、明晰新時代黃河流域排污權交易制度的設計思路以及指導排污權交易的司法實踐均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由此觀之,在推進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戰(zhàn)略過程中,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相互嵌套,環(huán)境公益性與私益性交錯縱橫,這決定了應在公私法融合互動背景下對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予以統(tǒng)籌考量。
三、應然構造:整體系統(tǒng)觀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治進路的邏輯向度
整體系統(tǒng)觀視野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良法善治”目標的達成亦應建立在由立法、執(zhí)法、司法等多種要素耦合而成的流域生態(tài)法治系統(tǒng)構造基礎之上,即通過構建“形神兼?zhèn)洹钡狞S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體系,塑造“軟硬兼施”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執(zhí)法體系以及建立“防治結合”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司法體系,統(tǒng)籌推進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
(一)構建“形神兼?zhèn)洹钡狞S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
理想層面的“良善型法律規(guī)范體系”應為統(tǒng)合實質(zhì)理性與形式理性而生成的現(xiàn)代法治產(chǎn)物,即外部結構完整和內(nèi)在價值統(tǒng)一構成了某一部門法律體系科學建構與否的最終衡量標準。
1.“形”: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的建構需遵循“形式理性”
根據(jù)法律體系形式理性建構原理法律規(guī)范體系的形式理性追求的法律規(guī)范外在體系由內(nèi)容完備、結構耦合、邏輯自洽、層次分明的有機整體組成。,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的體系化塑造,需在統(tǒng)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整合好內(nèi)部規(guī)范體系,協(xié)調(diào)好外部規(guī)范體系,以完善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立法的整體組成及其結構。
(1)整合完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內(nèi)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
按照環(huán)境法規(guī)范制定的立法權限與位階關系,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內(nèi)部法律體系通常由統(tǒng)籌流域生態(tài)保護與綠色發(fā)展為直接立法目的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基本法、單行法律、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具體領域治理的行政法規(guī)與部門規(guī)章以及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地方性法規(guī)與規(guī)章等幾部分內(nèi)容統(tǒng)合而成。其中,作為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構建的關鍵步驟和引領主體,《黃河保護法》的頒布不僅有利于彌補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綜合性立法缺失的空白,改變黃河流域環(huán)境要素間分而治之的局面,而且可以憑借其更權威的立法層級而為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規(guī)章、條例、規(guī)范性文件等提供上位法依托,使《黃河保護法》傳遞的價值理念成為整個法律體系內(nèi)部共同的價值遵循,該法在內(nèi)容設置以及程序?qū)徸h上無疑處于整體系統(tǒng)觀視域下“總則法”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黃河保護法》誠然創(chuàng)造性地將流域資源利用、生態(tài)環(huán)境修復與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發(fā)展間的關系融合到統(tǒng)一的法律規(guī)范之中,但囿于流域治理空間的廣闊性以及流域治理事項的繁雜性,這意味著僅依靠一部具有總領屬性的《黃河保護法》無法涵蓋與流域生態(tài)治理和經(jīng)濟高質(zhì)量發(fā)展有關的所有內(nèi)容,即《黃河保護法》的出臺并不意味著完備且融貫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體系已經(jīng)形成,事實上其只是開啟了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重大國家戰(zhàn)略有法可依的新局面。為此,需以立法規(guī)范制定的位階關系與順次先后為指引,通過整合與完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內(nèi)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以保障黃河流域法律體系在內(nèi)部結構上形成不同層級法律規(guī)范以黃河保護基本法為焦點的眾星拱月之勢。首先,應對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進行類型化梳理,為內(nèi)部規(guī)范的體系化建設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其次,應當在《黃河保護法》的統(tǒng)領下推動黃河流域內(nèi)的地方立法進程,通過地方性法規(guī)或規(guī)章對地區(qū)特殊性作出回應,將相關法律制度細化為具體實施規(guī)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必須同時考慮到地方立法的協(xié)同問題,避免產(chǎn)生無法銜接甚至相互沖突的法律規(guī)范,實現(xiàn)既有差異又能相互協(xié)調(diào)的區(qū)域協(xié)同立法。區(qū)域協(xié)同立法可以為具有區(qū)域性的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提供一致性的制度保障,平衡復雜的利益關系,推進流域整體法治進程[15],在黃河流域展開區(qū)域協(xié)同立法是健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縱向法律體系的必然選擇。最后,以我國《立法法》和立法理論對法律規(guī)范的協(xié)調(diào)性與系統(tǒng)化要求為方法遵循,整體系統(tǒng)觀視野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內(nèi)部法律規(guī)范的體系化構建應達致同一位階的法律規(guī)定需保持相互一致,低位階的立法不能與高位階的立法相抵觸,法律規(guī)定之間應當避免重復以及避免出現(xiàn)法律調(diào)整的空白[16]等目標。對此,要加快推進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法規(guī)的“立改廢釋”工作,剔除重復和矛盾的條款,更新陳舊的法律規(guī)范,升級效力層級較低的法律法規(guī),以保障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則實現(xiàn)內(nèi)容上的全面性、規(guī)范上的一致性以及邏輯上的自洽性。具體而言:一方面,對于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既有立法與《黃河保護法》的規(guī)制內(nèi)容可能存在的交叉重疊之處,應妥善處理《黃河保護法》與同一層級其他水事調(diào)整、資源開發(fā)、空間布局等單行法律規(guī)范的關系,建議以“特殊法優(yōu)于一般法”“新法優(yōu)于舊法”的原則為方法論綱,對相關法律及時作出合理解釋與適用,做好新法舊法的銜接工作;另一方面,對于《黃河保護法》框架構造與制度體系設計可能寬泛、既有法律幾乎無涉之處,如運用市場機制解決流域環(huán)境污染問題的排污權交易、流域生態(tài)補償、環(huán)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具體制度,建議通過制定規(guī)章、條例、規(guī)范性文件的形式對其進行補充,在縱向上形成效力階層合理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內(nèi)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
(2)妥善協(xié)調(diào)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外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
每一部法律規(guī)范都不是以孤立、封閉的狀態(tài)存在,它始終以與其他法律規(guī)范緊密關聯(lián)和相互作用的形式發(fā)展與演變,共同存在于國家統(tǒng)一的法律體系之中[17]。由此,為達致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建構所追求的形式理性目標,除了整合完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內(nèi)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還需要妥善協(xié)調(diào)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外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即做好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與外圍法律規(guī)范的有機銜接。
具體來說,作為支撐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運行的中心,《黃河保護法》在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的有效運作,需要在其他法律規(guī)范或制度設計原理下輔助進行。為此,在塑造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外部法律規(guī)范體系的過程中,既要協(xié)調(diào)好《黃河保護法》與其他環(huán)境單行法規(guī)范的銜接與理念拓展工作,同時也要做好《黃河保護法》與傳統(tǒng)部門法律之間的協(xié)同對接。例如,《黃河保護法》第120條明確規(guī)定“違反本法規(guī)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一“附屬刑法”條款為《黃河保護法》與刑法間存在的銜接關系提供了直接立法依據(jù)。一方面,《黃河保護法》的出臺是從立法層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之“嚴密法治觀”直觀寫照,為保護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jù);另一方面,要實現(xiàn)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最嚴”保護,毋庸置疑需要刑法發(fā)揮其應有的兜底保障功能。因此,刑法與《黃河保護法》的對接應堅持“最嚴”生態(tài)法治觀,并在規(guī)制范圍上實現(xiàn)對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益的全方位保護。
2.“神”: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的建構需貫徹“實質(zhì)理性”
僅從單一形式理性出發(fā)難以對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的精準定義形成周延的理性認知,其可能陷入“法律迷信”抑或“惡法亦法”的思維桎梏之中。對此,可通過塑造或賦予法律規(guī)范內(nèi)在正當性的實質(zhì)理性來彌合上述缺陷。根據(jù)法律體系的一般原理,法律規(guī)范體系的“內(nèi)在價值體系”強調(diào)的是各種規(guī)范的價值目標或法律理念需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具體表現(xiàn)為由法律理念作為基石的法律原則所追求的價值在具體的法律規(guī)則和由法律規(guī)則所組成的法律制度能夠一貫性表達[18]。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為價值融貫性所指向的法律的理念, 其本身不能從法律體系內(nèi)部得到證立[19],是故,價值融貫性并非法律體系的本體性構成要素。為此,倘若立法者沒有注意到價值融貫性,那么對法律體系所施加的融貫性要求于這個體系而言就是可被追求的品質(zhì)。而且,價值融貫性有程度之分,價值融貫性越高,法律體系越好[20]。當前,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正處于價值融貫性的重塑過程之中,為保證法律體系的“實質(zhì)理性”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建構過程中得以貫徹,首先須對隱藏在《黃河保護法》背后的價值追求與邏輯主線進行精準識別,并保證該價值主線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外部法律體系建構以及具體制度設計過程中得以始終如一地貫徹。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本質(zhì)要求”。以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根本指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便是矗立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背后的“價值主線”,其既扮演著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背景墻的角色,同時也構成了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是否具備價值融貫性的關鍵性判斷標準。
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核心建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內(nèi)在價值體系的基本進路包括: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嵌入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外部法律體系之中,嚴格貫徹“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發(fā)展”的基本原則,構建以人體健康和生態(tài)安全為初級目標,以不斷提升生態(tài)環(huán)境品質(zhì)為高級目標的制度體系[21],推動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方面實現(xiàn)內(nèi)部體系的價值融貫與外部體系的邏輯自洽。
(二)塑造“軟硬兼施”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執(zhí)法體系
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之生命力及其權威性均在于實施。伴隨著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的形成及日臻完善,構建以嚴格執(zhí)法為核心環(huán)節(jié)的流域法治實施系統(tǒng),成為創(chuàng)造生態(tài)法治文明新形態(tài)的使命所在。作為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實施的形式載體,以是否具有強制約束性為標準,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的執(zhí)法構造可劃分為權威管制型與激勵促進型兩種機制,二者統(tǒng)一于將黃河流域管理規(guī)范的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流域治理效能的法治實踐之中。
1.“硬”:塑造權威管制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執(zhí)法體系
因應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外部性,政府因本身具有的人才、資金、技術等優(yōu)勢而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這一典型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扮演著管理者、組織者以及決策者的角色。以此為基礎,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的執(zhí)行機制即為負有流域環(huán)境管理權限的行政主體依據(jù)一定法律程序推動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落地實施的動態(tài)過程。在此過程中,行政管制構成了行政機關進行流域環(huán)境保護的重要法治手段,以《黃河保護法》為表征的環(huán)境保護法律規(guī)范由此也呈現(xiàn)出“行政管制型立法”的特征。作為流域環(huán)境管理機關執(zhí)法功能的主要形式載體,管制型機制為達致立竿見影的環(huán)境治理效果,其通常以“命令—控制”為根本行動邏輯,本質(zhì)是對行政相對人可負義務或減損利益的權力約束,具體包括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執(zhí)行、行政監(jiān)督檢查等規(guī)制方式。為此,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法治的執(zhí)法構造中,須逐步建立與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目標相適配的規(guī)劃、標準、評估、許可等管制型機制。具言之:在規(guī)劃方面,2019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并監(jiān)督實施的若干意見》規(guī)定了用途管制、空間規(guī)劃等各項措施。為此,應逐步將黃河治理策略融入國土空間規(guī)劃與“三線一單”生態(tài)環(huán)境分區(qū)管控,加快流域綜合規(guī)劃制定的同時推進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專項規(guī)劃的編制。此外,還應以黃河流域生態(tài)空間管控為價值遵循,禁止或者限制社會經(jīng)濟主體在黃河重要生態(tài)功能區(qū)、環(huán)境敏感區(qū)或脆弱區(qū)的開發(fā)利用活動,以確保從源頭防范流域環(huán)境風險。在標準方面,加快黃河流域內(nèi)工業(yè)企業(yè)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產(chǎn)品能效標準、流域生態(tài)補償標準、黃河流域水環(huán)境質(zhì)量標準、流域生態(tài)修復標準(河口、物種棲息地、河湖岸線)等技術標準的制定或修訂。在評估與許可等管制型機制方面,應結合當前需求,著力構建適配于黃河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法治需求的流域水資源利用全過程管控、流域新污染物環(huán)境調(diào)查和評估、河道采砂許可以及排污許可等制度譜系。
2.“軟”:塑造激勵促進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執(zhí)法體系
從環(huán)境治理實踐角度考察,單一管制型機制在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中難免出現(xiàn)內(nèi)生動力缺乏、治理合力基礎薄弱、行政執(zhí)法一刀切等痼疾[22]。基于此,對行政機關在流域環(huán)境治理過程中所具有的管制性功能進行肯認的同時,還需充分挖掘并釋放行政機關所肩負的實施積極行為,為公眾提供集體福利之任務以及承擔給付、服務、指導、激勵等柔性治理手段的促進性功能[23],即塑造激勵促進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執(zhí)法體系。當前,適配于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戰(zhàn)略目標實現(xiàn)的較為重要的促進型行政機制主要包括行政合同、行政指導以及行政獎勵等柔性規(guī)制工具。
其一,行政合同機制。作為環(huán)境管理的創(chuàng)新形式,區(qū)別于權威管制型執(zhí)法機制基于單方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即可發(fā)生法律效力,行政合同機制需要貫徹實施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多方當事人達成合意。映射到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柔性執(zhí)法機制事項上,通過以合同的形式進行談判,流域范圍內(nèi)的企業(yè)或土著民眾可以提出適切性更高、治理成本更低的環(huán)境保育措施。與此同時,流域環(huán)境管理機關亦可提出現(xiàn)有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規(guī)范中尚未明確規(guī)定但更為強力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措施,并在合同中保留一定的干預權限[24]。對此,美國的“棲息地保育計劃”棲息地保育計劃(Habitat Conservation Plans)雖名為計劃,實為由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局(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與私人土地所有者達成的合同。在該合同下,只要物種在總體上得益,土地所有人就被允許在其部分土地上捕獲動植物資源或進行修筑。參見:CUNNINGHAM W P. Mary Ann Cunningham.Environmental Science:A Global Concern[M].13th ed.Boston:McGraw Hill Educ -ation,2018:226.以及我國錢江源國家公園管理中的農(nóng)田地役權改革錢江源國家公園通過合同的方式完成農(nóng)田地役權改革以平衡生態(tài)利益與私人土地權利:在不改變土地權屬的同時,建立地役權補償機制和社區(qū)共管機制,在限制農(nóng)民一定使用權前提下,對相應損失給予補償。均可為行政合同機制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激勵促進型執(zhí)法構造中的嵌入提供有益鏡鑒。
其二,行政指導機制。法釋義學視角下,行政指導系指行政機關在其法定職權范圍內(nèi),通過建議、示范、約談等非強制性方式,引導行政相對人自愿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種行為,以實現(xiàn)一定行政管理目的[25]。在此語境下,行政指導的本質(zhì)在于“非強制”,“引導”則構成行政管理目的達成的根本方式。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柔性執(zhí)法構造中,行政指導主要通過行政機關對流域范圍內(nèi)的當?shù)孛癖娕c生產(chǎn)服務企業(yè)展開宣傳教化的方式發(fā)揮作用,以營造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發(fā)展以及低碳環(huán)保的社會氛圍,進而彰顯行政指導對實現(xiàn)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重大戰(zhàn)略目標的正向引導功能。
其三,行政獎勵機制。該機制發(fā)揮作用的內(nèi)在機理主要為:行政機關通過充分挖掘行政相對人的潛在智力、財力和物力等系列資源,最大限度調(diào)動行政相對人為實現(xiàn)既定行政目標而發(fā)揮各自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26]。以此為遵循,在塑造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柔性執(zhí)法構造過程中,為保證行政獎勵機制蘊含的激勵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得到應有的發(fā)揮,應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法律體系中對行政獎勵的條件以及救濟等內(nèi)容作出詳細規(guī)定,包括明確何種情況下社會公眾可以獲得行政獎勵,至少應設置一個受獎勵的標準或者以數(shù)值確定個人參與黃河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而理應受到獎勵的門檻;以法律形式賦予相對人在行政機關因拒絕、拖延等原因不發(fā)放環(huán)境保護獎勵時而享有的提起復議、訴訟的權利。
(三)建立“防治結合”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司法治理體系
當前,隨著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這一國家戰(zhàn)略的縱深推進,流域內(nèi)耕地保護、國土空間規(guī)劃、生物多樣性保育、碳排放權交易以及排污許可等糾紛矛盾日趨多樣化。在此背景下,司法作為法權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法治系統(tǒng)構建的關鍵一環(huán),應充分發(fā)揮其在守護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原貌底色以及維護流域生態(tài)正義中所具有的最后一道法治保障的防線作用[27]。具言之,風險社會下,為有效預防流域重大環(huán)境風險的發(fā)生以及為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提供及時有效的救濟,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司法治理體系建構應以“前延后伸”的邏輯理路為遵循,切實推動新時代我國流域環(huán)境司法治理理念的轉型與重構。
1.“防”:建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預防性司法治理體系
自從貝克提出“風險社會”這一重要論斷以來,風險正以科學不確定的基本面向在社會化道路上大踏步邁進,其充斥著包括生物安全、氣候變化在內(nèi)的各個領域。映射到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領域,因應“流域”意涵的關涉面頗為廣泛,既指向河流湖庫等聚水區(qū)為一體,具有顯著生態(tài)邊界的自然生態(tài)空間,同時也關涉流域內(nèi)“人—自然”“人—人”等基本關系構造的社會因素,因此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風險呈現(xiàn)出系統(tǒng)化、多樣化以及復雜化的特性,主要包括產(chǎn)業(yè)結構性風險、跨域格局性風險和系統(tǒng)失衡性風險三重面向。基于此,新時代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預防性司法體系的建立應突破傳統(tǒng)意義上“生態(tài)環(huán)境無損害則無救濟”思維范式,將對流域風險的干預行動上升為司法裁判,確保流域司法治理理念實現(xiàn)從末端損害救濟到前端風險預防的邏輯轉型。
具體而言,要把環(huán)境風險預防納入制度范疇,使《黃河保護法》中諸多體現(xiàn)風險預防理念的條款得以通過訴訟獲得實施[28]。一方面,可聯(lián)合檢察機關引入預防性行政公益訴訟機制,即當檢察機關綜合判定行政機關的行為存在風險發(fā)生的高度蓋然性時,允許在行政行為作出之前或損害結果實際出現(xiàn)之前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29],以此形成對政府風險治理行為的規(guī)制和監(jiān)督,使政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擔負更高的注意義務,并促進其主動采取風險行政規(guī)制措施來更好地履行環(huán)境保護的作為義務。另一方面,應增強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預防性救濟案件的可訴性,完善風險評估鑒定機制與健全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重大風險”認定標準;嚴格適用“危險排除責任”并輔以合理的證明責任分配標準;以禁止令在流域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的適用為指引,完善行為保全性質(zhì)的禁止令和非訴強制執(zhí)行性質(zhì)的禁止令等[30],通過將風險預防理念貫穿于流域司法機關的司法裁判中,從而實現(xiàn)流域司法理念從“反應—救濟”向“預測—預防”思維范式的歷史性轉變。
2.“治”:建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的救濟性司法治理體系
首先,充分發(fā)揮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救濟中的功能適用。根據(jù)《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有關規(guī)定,較大或者嚴重影響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環(huán)境污染或生態(tài)破壞事件構成了依法提起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的基本情形,從一般意義上講,流域環(huán)境污染或生態(tài)破壞在影響范圍、程度、后果等方面顯然符合上述規(guī)范要求,但現(xiàn)實中流域性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十分罕見,為此需推動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賠償訴訟在黃河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過程中的能動適用。
其次,對于發(fā)生在黃河流域重要生態(tài)功能區(qū)或敏感脆弱區(qū)的環(huán)境損害,要在救濟性環(huán)境公益訴狀中及時適用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懲罰性賠償制度予以懲治與威懾,即在探索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懲罰性賠償?shù)乃痉ㄟm用進路方面,應以司法謙抑性為適用前提、以責任要件為適用依據(jù)、以數(shù)額認定為適用保障,切實保障好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之“嚴密法治觀”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場景的貫徹應用。
再次,因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與《民法典》均明確將生態(tài)環(huán)境修復義務作為環(huán)境侵權人承擔的責任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針對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污染嚴重、資金投入大、修復過程緩慢,且實踐中對誰來修復、如何修復、修復監(jiān)督及保障等事關流域修復效能的關鍵性問題,應通過對《黃河保護法》之“生態(tài)環(huán)境修復條款”進行規(guī)范解讀,確定修復方式,加強修復保障,規(guī)定修復監(jiān)督,以拓展與完善黃河流域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生態(tài)修復的實現(xiàn)路徑。
最后,為充分發(fā)揮司法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命題中的救濟性功能,法院不應依賴不予立案或駁回起訴加以回避,而應在法律規(guī)范容許的解釋空間內(nèi)運用司法策略化解難題,如此可將黃河生態(tài)保護的國家戰(zhàn)略意義考量融入司法過程。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奮斗,2019(20):4-10.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R/OL].(2022-10-25)[2023-06-01].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3] 呂忠梅,竇海陽.以“生態(tài)恢復論”重構環(huán)境侵權救濟體系[J].中國社會科學,2020(2):118-140,206.
[4] 李冰強,王楠.論黃河法的立法定位[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128-136.
[5] ACKERMAN B,STEWART R B.Reforming environmental law[J].Stanford Law Review,1985(5):52-71.
[6] 秦天寶.我國流域環(huán)境司法保護的轉型與重構[J].東方法學,2021(2):158-167.
[7]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43.
[8] 沈百鑫.淺析以科技信息為主線的環(huán)境協(xié)同治理[J].中國環(huán)境管理,2015 (6):84-89.
[9] 孫文楨.私法概念之再研究:兼論私法觀念的革命[J].北方法學,2013 (3):5-13.
[10] 孫國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研究:概念、理論、結構[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37.
[11] 彭中遙.《民法典》中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代修復制度之探析[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2(1):60-69,158.
[12] 沈陽.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政府索賠制度的困局與出路:以公私法融合為視角[J].四川環(huán)境,2021(3):199-204.
[13] 秦天寶.整體系統(tǒng)觀下實現(xiàn)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法治保障[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2(2):101-112.
[14] 杜輝.公私交融秩序下環(huán)境法的體系化[J].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19-29,115.
[15] 王敏.流域保護區(qū)域協(xié)同立法的功能定位與規(guī)范進路[J].中國環(huán)境管理,2024(2):121-128.
[16] 李萱,沈曉悅.水污染防治法律規(guī)范體系協(xié)調(diào)性評估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45.
[17] M.H.馬爾琴科.國家與法的理論[M].徐曉晴,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416.
[18] 趙宏.行政法學的體系化建構與均衡[J].法學家,2013(5):34-54,176.
[19] 雷磊.融貫性與法律體系的建構:兼論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融貫化[J].法學家,2012(2):1-16,176.
[20] 黃錫生,黃淑婷.法典化視域下自然資源立法的體系化路徑[J].河北法學,2023(5):2-19.
[21] 徐以祥.論我國環(huán)境法律的體系化[J].現(xiàn)代法學,2019(3):83-95.
[22] 王曦.論規(guī)范和制約有關環(huán)境的政府決策之必要性[J].法學評論,2013 (2):94-102.
[23] 杜輝.環(huán)境公共治理與環(huán)境法的更新[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27.
[24] STEWART R B.A new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Capital Univer -Sity Law Review,2001(21):21-182.
[25] 張璐,王其樂.生物多樣性保護規(guī)制工具更新:規(guī)范層面的分析[J].中國環(huán)境管理,2021(4):21-28.
[26] 傅紅偉.行政獎勵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67-68.
[27] 邸衛(wèi)佳,張祖增.黃河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司法治理的問題檢視與完善建議[J].江西理工大學學報,2022(6):33-41.
[28] 鞏固.進一步完善黃河保護法治體系[N].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2024-04-02.
[29] 張百靈.預防性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展開[J].行政法學研究,2021(6):56-67.
[30] 于文軒,宋麗容.論環(huán)境司法中預防原則的實現(xiàn)路徑[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168-175.
The overall system view of the legal approach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bstruction, jurisprudence and dimension
ZHANG Zuzeng
(School of Law,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requiring the “system, integrity and coordination” of accelerat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eeds to embed the overall system view into the proposition of legal guarante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o shape the integralist thinking paradigm consist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discourse system and standard order. Taking the overall system view as the analysis tool, the legal approach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three core issues: problem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traceability and logical orientation.In the former, a“rational” system is unfinished, an “administrative order-control”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is leaky and a “risk prevention” dynamic response basin judi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bsent. In the middle, the modern rule of law is a specific unity integrating time, ideas and norms. The basic law of the legal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be carried out along the unity of vertical commonness and diachronic,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professionalism and power doctrin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public and private laws. In the latt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i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t is advisable to build an ecological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with both shape and spirit, an ecologic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at “combines the carrot and the stick” and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protection judicial 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at “combin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Yellow River Basin; overall system view; ecological law in Yellow River Basin;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責任編輯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