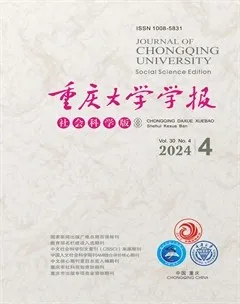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樣態、成因與對策
摘要: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問題持續存在,體現為值班律師在偵查階段向辦案人員了解案情受阻、值班律師會見被追訴人及閱卷依然被動、具結程序中值班律師在場見證形式化等等。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在于:其一,值班律師制度運行因可能造成程序流轉降速、辦案周期延長而與當前辦案機關認罪認罰案件業務考核制度的效率價值導向有所沖突,一些辦案人員對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訴訟程序存在抵觸心理。其二,控辯雙方平等對話、理性協商進而達成妥協的協商性司法理念尚未在認罪認罰案件訴訟過程中真正得到貫徹,部分辦案人員對于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協商程序中的作用和能力存在著認知誤區。其三,認罪認罰案件權力主導模式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乏力造成了寬縱影響,辦案機關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規則制定和具體訴訟程序中將其利益現實化、擴大化。對此應當認識到,一方面,現階段值班律師制度對于實現認罪認罰案件訴訟公正與訴訟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對公權力的依賴與制約已經構成了影響當下值班律師制度運行效果的最為重要的兩個層面。基于此,順應我國刑事司法改革趨向,綜合考慮目前的刑事司法實踐環境,宜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值班律師制度及其相關機制的系統性建設,以解決值班律師功能虛化問題:一是,規范落實辦案機關告知程序,保障值班律師會見被追訴人的及時性,并從法律層面賦予值班律師完整的閱卷權。二是,改革辦案機關認罪認罰案件業務考核制度,屏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的考核指標,合理運用定量和定性兩種考核方法對辦案人員保障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辦理的情況進行評價。三是,完善認罪認罰案件審前階段的權力監督體系。在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同時,深化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健全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察機關權力運行的外部監督制約機制,以促進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相結合,實現對公安司法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全方位監督,由此改善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訴訟參與整體環境。
關鍵詞:值班律師;法律幫助;認罪認罰;權力主導;效率價值;人民監督員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4-0252-12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我國刑事司法領域輕罪案件數量劇增,有限的司法資源與化解糾紛的社會需求間的張力凸顯[1]。為緩解“案多人少”的實踐困境,結合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現實要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大改革部署。目前,實踐中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基本訴訟模式的刑事訴訟新常態已經形成,認罪認罰案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保持在85%以上[2],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甚至接近九成的認罪認罰案件均由值班律師參與辦理[3]。在我國,值班律師制度確立的初衷和現階段的功能主要是填補認罪認罰案件中律師辯護覆蓋范圍上的缺欠,確保被追訴人認罪的自愿性。然而,司法實踐中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現象始終存在,這不僅減損了值班律師制度本身的實施效果,也使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正當性持續面臨風險。
對此,學界已有不少討論,在有關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成因上也取得了諸多研究成果,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值班律師訴訟身份不明、行權受限[4],司法行政機關監管不力[5],值班律師人手緊缺[6],補貼標準過低[7]等等。但在筆者看來,上述并非癥結所在。其一,在值班律師訴訟身份和職責權利方面,一些學者指出,目前值班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前階段參與的工作與辯護職責并無本質區別[8],應當為值班律師正名,賦予值班律師“辯護人”的身份地位[9],以保障值班律師有效行使訴訟權利。然而,訴訟地位與訴訟權利二者并不必然存在著先后次序,恰恰是現有規范和實踐背景下值班律師職責與刑事辯護職責的相似性,表明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訴訟程序直接依托具體訴訟權利,而非訴訟地位。因此,從實然的運作樣態出發,無論將值班律師定位為法律幫助者還是辯護人,并不會對當前值班律師的實際履職效果產生顯著影響。另外,直接采取擴展值班律師權利范圍的思路,賦予值班律師訊問在場權的理論方案[10]也難以達到預期,其理由將在文章中予以回應。其二,如果認為是司法行政機關監管不力導致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形式化,那么這一判斷的逆否命題,即若要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辦理,司法行政機關應當積極監管,也必須成立。但事實上,當前促進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辦理并不依賴于司法行政機關加強監管。這是因為,在參與規則粗疏、辦案機關強勢且保障機制不健全的實踐現狀下,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積極性本就不高,此時若再采取高壓監管態勢,嚴格要求值班律師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很可能使得值班律師制度的運行陷入一種尷尬境地。亦即,實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正當性要求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案件辦理,但監管壓力進一步挫傷了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履職動力并進而對其履職效果形成消極影響。如此,不但值班律師訴訟參與實質化的目標無法達成,反而很可能阻滯值班律師制度的后續發展。基于互為逆否命題的兩個命題真假性相一致,原命題也就不能成立。其三,值班律師負荷過重并因此影響到其法律幫助工作質量的判斷缺乏細致、準確的實證分析。雖然實踐中值班律師在工作時間段內時常需要處理多起案件,但事實上我國多數省市已經具備人員較為穩定的刑事值班律師團隊,并且普遍建立了值班律師統籌調配和跨區域派駐機制,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一些地區律師資源不足的壓力。此外,伴隨著值班律師制度建設持續推進,實踐中值班律師的補貼標準得到了較大提升,但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狀況仍未得到有效緩解。
事實上,任何一項法律制度要有效運行,必須同與之相關的其他制度相互協調;反之,法律制度的效益就會受到損害。針對值班律師制度面臨的困境,不能簡單、片面地將原因歸結為制度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幾點不足,而應當堅持系統研究的思路,關注值班律師制度運行的實踐背景,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于值班律師制度的作用和影響。在對此進行審視、剖析的基礎之上,才可以進一步明確改革方向和找尋可能的解決方案。
二、認罪認罰案件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現實樣態
我國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主要參與確定認罪合意、控辯量刑協商和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三個訴訟環節。在確定認罪合意的過程中,控辯雙方的互動基本在公安司法機關與被追訴人之間展開,值班律師間接參與其中,通過提供法律咨詢確保被追訴人充分了解其涉嫌或被指控的罪名和認罪認罰的性質及其法律后果。在被追訴人自愿認罪的前提下,由檢察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和量刑指導意見等,結合案件犯罪事實和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等量刑情節,提出一份確定刑建議或者幅度刑建議[11],對此被追訴人、值班律師可以表示沒有異議,也可以提出降低量刑幅度的意見。因此,為了確保被追訴人自主作出認罪與否的選擇并盡量幫助被追訴人在控辯協商程序中爭取到最大限度的訴訟收益,值班律師需要在充分了解案件有關情況的前提下提供法律咨詢,并對量刑建議的內容是否考慮到各種法定、酌定從輕、減輕情節以及案件是否出現了新的證據、事實作出全面、謹慎的判斷。但是,實踐中值班律師了解案情受阻以及會見、閱卷被動的情況依然存在,致使值班律師難以有效為被追訴人提供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深度法律幫助[12],也無法在量刑協商過程中發揮有效作用。
關于值班律師通過辦案人員了解案情,目前《刑事訴訟法》第38條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50條僅規定了公安機關依法將案件有關情況告知辯護律師的職責,而把值班律師排除在告知范圍之外;《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以下簡稱《值班律師工作辦法》)第21條雖然規定值班律師可以向公安機關了解案情,但規范內容粗疏,存在“司法隨意解釋”的風險,這些都可能導致實踐中值班律師向公安機關了解偵查階段已查明的主要事實、強制措施適用以及偵查羈押期限的延長等案件情況時受到阻礙。在會見方面,當前值班律師會見包括應被追訴人約見進行會見和經辦案機關允許主動會見兩種方式。針對前者,《刑事訴訟法》第36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高檢規則》)第268條及《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49條均對辦案機關告知被追訴人有權約見值班律師的職責義務作出了明確規定;公安部發布的《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進一步規范了公安機關履行告知義務的具體時間,即公安機關應在第一次對被追訴人進行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將告知書交給被追訴人。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各地辦案機關提供告知書、履行告知義務的時間不盡統一,甚至部分辦案機關尚未在告知書中寫明被追訴人約見值班律師的權利。另外,關于辦案機關安排值班律師會見程序的規定欠缺細化也使得值班律師會見的及時性、充分性無法得到有效保證。而在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環節,閱卷不暢使得值班律師無法有效就量刑問題提出意見。一方面,目前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臨時通知值班律師參與訴訟程序的情況依然較為普遍,這種做法難以保障值班律師具有充足的閱卷時間。另一方面,在閱卷方式上,《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值班律師工作辦法》等規范性文件對值班律師閱卷權作出了有別于辯護律師的表述,即值班律師僅能“查閱”,而不能“摘抄”、“復制”案卷材料[13]。實踐中值班律師的閱卷途徑也基本限于“現場閱卷”。然而,當前我國基層辦案機關案件數量大且多數地區的公共法律服務資源薄弱,值班律師在工作時間段內通常需要集中查閱多起案件的案卷材料。因此在不能摘抄、復制案卷且必須現場閱卷的情形下,值班律師難以準確了解多起案件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在辦理犯罪事實、證據材料或相關情節較為復雜的認罪認罰案件時,量刑合意的達成可能需要控辯雙方反復進行協商和溝通,這種閱卷方式不利于值班律師了解案件證據信息,進而會減損值班律師向檢察機關提出意見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在就量刑問題與檢察機關形成共識后,被追訴人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作為控辯雙方對于犯罪事實、指控罪名、量刑建議及程序適用等事項達成合意的書面確認。此時若被追訴人沒有辯護人,值班律師應當履行在場見證職責。依據《值班律師工作辦法》第10條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第27條的規定,值班律師在場見證具結程序可被區分為三種情形:其一,值班律師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自愿性、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程序適用等事項均無異議時,應現場簽字;其二,值班律師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程序適用有異議,但能夠確認被追訴人系自愿認罪認罰時,應現場見證并簽字;從地方辦法來看,此時可以注明值班律師僅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過程的自愿性”進行見證參見2021年9月14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安徽省公安廳、安徽省國家安全廳、安徽省司法廳聯合發布的《安徽省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皖司發[2021]40號)第11條。;其三,被追訴人拒絕值班律師幫助的,值班律師需現場見證,無需在具結書上簽字。實踐中值班律師履職形式化的問題在后兩種情形下均較為突出。其中,前者為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提供法律幫助“走過場”留下了空間,致使值班律師法律幫助缺乏實質的內涵[14];而后者情形下,值班律師缺席了會見被追訴人、查閱案卷材料和向辦案機關提出意見等重要環節,“見證”由此喪失了保障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功能和意義。
三、認罪認罰案件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成因辨析
在刑事訴訟中,若非受到外來強制壓迫,控辯雙方所作出的決定都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理性權衡利弊的過程[15]。由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以使公安司法機關最大限度地縮短辦案周期、緩解案件積壓,面對“案多人少”的實踐困境,公安司法機關原本就具有推動認罪協商的內在動機。但為了追求認罪協商機制的效率價值,司法實踐過分加速催化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推行過程。這使得,一方面,認罪協商機制異化為實現訴訟效率目標和績效考核要求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認罪認罰案件中控辯雙方的訴訟關系未能實現從以對抗為主到以合作、協商為主的調整過渡。在此情況下,辦案機關作為認罪認罰案件訴訟程序的主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自身優勢地位限制了值班律師的功能發揮。
(一)值班律師制度與當下效率價值導向的認罪認罰案件考核制度沖突
從制度發展歷程來看,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發展態勢與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緊密關聯。為貫徹落實黨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在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進會上強調,各級檢察機關應承擔起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主導責任,加大制度適用力度[16],此后各地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在較短時間內不斷攀升。時至今日,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已超過90%[17]。在此過程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情況成為了辦案人員績效考核的一項重要標準。在規范層面,《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督管理辦法》第23條明確提出應對檢察官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情況進行績效考核,并將考核結果納入司法業績檔案;《檢察機關案件質量主要評價指標》則規定了以“案—件比”“案—件比”是指發生在人民群眾身邊的具體案件,與這些具體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所經歷的有關訴訟環節所統計出來的案件數量相比,而形成的一組對比關系。參見:韓旭.“案—件比”:最大限度提升辦案質效[N].檢察日報,2021-03-15(03).為核心的案件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能使檢察官最大限度地減少辦案環節以在該評價指標體系下降低刑事檢察“案—件比”[18]。在實務層面,公安司法機關普遍通過制定數字指標的方式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甚至對不同地區、不同層級辦案機關提出了統一的指標要求2019年8月,在全國檢察機關刑事檢察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曾明確提出要在年底當月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提升至70%左右。參見:蔣安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若干爭議問題解析——專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國慶(下)[N].法制日報,2020-05-13(09).。因而在現有績效考評體系下,辦案人員必然盡可能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促使被追訴人及早認罪認罰,以節略業務活動、節省辦案時間。然而,對于公安司法機關而言,值班律師會見、閱卷會增加其工作量并延長辦案周期。特別是目前已有多地公安司法機關探索適用“全流程速裁機制”[19]辦理犯罪事實、證據和情節相對簡單的認罪認罰案件,安排值班律師會見被追訴人的獨立環節將在這種快速處理機制下對個案造成明顯的程序流轉降速,進而導致“全流程速裁機制”的辦案提速效能減弱。而對于較為復雜的認罪認罰案件,值班律師有時需要通過多次會見、閱卷確保完整了解案情和有效提供法律幫助,但多次會見和閱卷也意味著辦案時長增加、訴訟流程趨于繁復,這都與當前公安司法機關業務考評體系的主體要求相悖,因而不可避免會遭到辦案機關抵觸。
(二)辦案人員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的協商作用存在認知誤區
出于對實質刑法正義的積極追求以及受到實質真實主義理念的明顯影響,相較于辯訴交易等域外協商模式,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協商范圍更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排斥控辯雙方就定罪標準、罪名及罪數等進行協商,而且對量刑協商的幅度施加了嚴格限制。實踐中值班律師履職情況未受重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即部分辦案人員認為值班律師并不具有對量刑建議施加實質性影響的能力和空間。事實上,雖然當前檢察機關傾向于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但“精準提出量刑建議、準確裁量刑罰”的改革要求在司法實踐中必然存有一定的彈性[20]。一是,所謂對于個案中的特定被追訴人而言不可能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合理量刑建議[21],或許在理論上可以成立,現實中卻并不存在判斷一份確定刑量刑建議是否為個案之唯一合理且絕對正確的量刑建議的標準。二是,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建議方面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因此針對相同罪名且量刑情節相似的認罪認罰案件,不同公訴人提出的量刑建議很可能有所出入。無論這種差距大小,身陷囹圄的被追訴人都希望落在自己頭上的刑罰能輕則輕[22]。最后,在認罪認罰案件案由超出現有量刑指導意見涉及的刑事案件案由范圍的情況下,檢察機關量刑活動缺乏規范性指導,此時更應當強調值班律師在量刑協商中的重要作用。同時,這一誤區反映出實踐中認罪認罰案件的辦理仍由對抗性司法理念主導。盡管目前認罪認罰案件中普遍存在著控辯雙方訴訟合作的形式,但控辯雙方平等對話、理性協商進而達成妥協的協商性司法理念尚未真正得到貫徹。因而在對抗性司法理念的指導下,當被追訴人認罪且協商范圍受到法律嚴格限制時,檢察機關將傾向于直接依法對罪名、罪數和量刑等對于法庭審理和裁判結果而言更為重要的事項提出量刑建議,而不會因擔心值班律師——這樣一位看似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基本沒有與之對抗的能力的對手——與其訴訟對抗并可能影響到其追訴利益而對值班律師參與訴訟程序予以格外重視。
(三)認罪認罰案件權力主導模式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乏力造成寬縱影響
長期以來,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的職權因素凸顯,這一特征亦自然、持續地作用于包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內的具體刑事訴訟制度的構架、運行過程中,即相較于被追訴人和值班律師,公安司法機關在認罪認罰案件審前階段的訴訟程序中具有明顯優勢地位。這體現在,偵查期間為保障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收集犯罪證據,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公安機關可能對被追訴人采取強制措施和其他強制性偵查行為,使得被追訴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或隱私權在一定期限內被限制、剝奪或強制處分,且目前仍有一定比例的被追訴人在刑事訴訟中被審前羈押 2022年度,我國刑事案件訴前羈押率為26.7%。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3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R/OL].(2023-03-17)[2023-03-18].https://ww
w.spp.gov.cn//gzbg/202303/t20230317_608767.shtml.,被羈押的被追訴人往往處于更為恐懼且與外界隔離的狀態。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公安機關進一步通過開展認罪教育鞏固了其強勢地位。與之相對的是,被追訴人并不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應當“如實回答訊問”[23]。而一旦被追訴人產生不認罪會受到重判的心理,就可能動搖意志,進而影響其做出理性判斷[24]。在認罪認罰案件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的程序主導地位主要表現為:辦理案件時聽取被追訴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且實踐中量刑建議基本被法院采納2022年度,我國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采納率為98.3%。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
報告——2023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R/OL].(2023-03-17)[2023-03-18].
https://www.spp.gov.cn//gzbg/202303/t20230317_608767.shtml.;主持認罪認罰具結書簽署活動;以及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輕微刑事案件依法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等等。
基于此,權力主導是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運行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模式。誠然,這一運行模式具有明顯的優勢。一方面,認罪認罰案件權力主導的運行模式與我國刑事訴訟中追求客觀真實的司法傳統和國家權力主導的制度背景相契合,從而可以有效避免刑事司法改革對于當下的刑事價值理念和適用機制形成過度的沖擊及其帶來的司法實踐失序。另一方面,為緩解辦案壓力,公安司法機關具有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意向和動力,這使得在權力主導模式下運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有利于兼顧提高訴訟效率的改革要求以及化解糾紛矛盾、修復社會關系的現實需要。但與此同時,辦案人員在訴訟過程中基于其主導地位壓制被追訴方的風險實際存在,即偵查行為的強制性、羈押狀態的封閉性以及訴訟階段次第流轉對公權力機關程序主導能力的夯實鞏固,使得辦案人員有能力將限制被追訴方訴訟參與的主觀傾向外化為實際行為。而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乏力的實踐現狀進一步將這種風險的可能性轉化為了現實性。一是,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決定了其訴訟立場在事實上的非中立性,實踐中檢察機關對于審前階段侵犯認罪認罰案件被追訴人、值班律師合法權益之行為存在監督不嚴的問題。二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同體破壞了權力監督的有效性。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控辯協商和具結活動均在檢察機關主導下進行,并以檢察機關決定的單方性為前提,因此對于其中可能出現的阻礙被追訴方行使訴訟權利的行為,值班律師難以通過向辦理案件的檢察機關申訴或控告的方式進行抗御。三是,值班律師向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訴或控告也難以達到效果:第一,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周期明顯較短,上級監督因時間成本相對過高而不切實際;第二,上級監督無法實現監督全覆蓋,實踐中往往只有針對明顯違反法律規定且已造成較為嚴重法律后果的侵犯值班律師權利之辦案行為的申訴或控告能夠通過上級監督得到及時審查和處理,而諸如值班律師會見、閱卷受限這一類問題基本得不到上級監督、回應。由此,公安司法機關得以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規則制定和具體訴訟程序中將其部門利益現實化、擴大化。
四、認罪認罰案件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紓困路徑
通過上文分析,當前公安司法機關對于認罪認罰案件效率價值的重視程度遠勝過其程序價值[25],并且,雖然改革頂層設計者與相關規范制定者已多次強調控辯雙方應對量刑建議展開積極協商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合意,但實踐中指導辦案工作的對抗性司法理念并未發生改變,加之在權力主導的運行模式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相對乏力,公安司法機關確有利用其訴訟優勢地位對被追訴人和值班律師形成壓制的動機、能力和趨向。這三個方面彼此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功能虛化的主要原因。對此應當認識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節約司法資源、實現訴訟經濟的價值功能只有在維護司法公正、落實權利保障的基本前提下才能真正得到發揮,而現階段實現認罪認罰案件訴訟公正與訴訟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平衡離不開值班律師制度的支持與不斷完善。因此,必須警惕以提高訴訟效率為單一價值的錯誤傾向。同時,對公權力的依賴與制約已經構成了影響當前值班律師制度運行效果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辦案人員需要轉變原有的對抗性司法理念,增強對話、協商意識,將促進值班律師工作開展作為自身重要職責。另外,針對公安司法機關壓制被追訴方的實踐風險,應當進一步健全認罪認罰案件權力運行的監督體系。明確了改革方向之后,在具體的舉措上,可以考慮從以下幾點進行完善:
(一)規范落實辦案機關告知程序及保障值班律師會見閱卷
一方面,必須落實辦案機關告知被追訴人有權獲得值班律師法律幫助和約見值班律師,確保被追訴人對其獲得法律幫助之訴訟權利的知悉權,這是發揮值班律師制度功能的前提條件。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目前公安司法機關主要采取書面形式進行權利告知,但部分辦案機關至今未在告知書中寫入值班律師制度相關內容。對此,各地辦案機關應當嚴格貫徹《刑事訴訟法》《高檢規則》及《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等的要求,盡快在辦案信息系統中檢查并更新被追訴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同時,實踐中值班律師制度相關告知書事項的表述過于籠統亦不利于被追訴人真正理解值班律師的職責功能,對此應予以細化,在告知書中明確列舉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這四項值班律師工作的主要內容,并對值班律師的前述職責逐項進行簡要書面釋明。在告知時間上,建議從法律層面規定公安機關應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其采取強制措施之日履行告知義務;檢察機關應在已經收到公安機關移送的案卷但尚未開展控辯量刑協商活動時進行權利告知,其中對于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后超過三日開始量刑協商的,檢察機關應當自收到案卷之日起三日以內履行告知義務,以保障被追訴人及時知悉值班律師制度功能和依法獲得法律幫助。另外,無論告知后被追訴人是否接受值班律師法律幫助,被追訴人均應先行對其已經知悉值班律師職責、法律幫助范圍及其有權約見值班律師和獲得法律幫助等事項進行書面簽字確認,且辦案機關應當將該書面材料留存一份歸檔,以便于法官在庭審階段審查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另一方面,由于實踐中多數被追訴人缺少法律知識和訴訟經驗,在沒有辯護人的情形下,為有效保護其合法權益,通常需要值班律師代表被追訴人與檢察機關就量刑問題展開協商。基于此,應當明確規定辦案機關告知值班律師被追訴人涉嫌的罪名、強制措施適用情況、偵查羈押期限的延長或重新計算等有關案情的職責義務,以確保值班律師在了解案情的前提下參與量刑協商活動。
而在保障值班律師會見和閱卷方面,一是,為了保障會見的及時性,建議增加規定除了偵查期間會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的被追訴人需經許可之外,辦案機關應在值班律師辦理會見手續后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二是,應盡快在法律層面賦予值班律師完整的閱卷權,規定值班律師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案卷材料,并在實踐層面要求辦案機關負責案件管理的部門配合值班律師閱卷工作。同時,可以嘗試開展值班律師互聯網閱卷試點,逐步轉變當前“網上預約、現場閱卷”的閱卷模式,使值班律師能夠在線上系統申請并直接通過電子卷宗閱卷終端設備查閱案卷材料。
(二)合理完善辦案機關認罪認罰案件業務考核制度
公安司法機關業務考核制度對于辦案人員開展訴訟活動具有重要引導功能,而當前以實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效率價值為主要導向的考核標準和考核方式并不利于保障被追訴方訴訟權利和在司法實踐中落實協商性司法理念,對此應當予以改革完善,兼顧實體公正、繁簡分流、人權保障等多維價值需求,將保障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納入考核范圍,并合理運用定量和定性兩種績效考核基本方法對辦案人員辦案情況進行評價。
其一,建議屏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這一考核指標,同時將保障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辦理的情況納入評價體系。當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仍然是辦案人員尤其是檢察官業務考核的一項重要標準,但這無法達到促進司法資源合理配置以及體現公安司法機關辦案質效的預期目標。針對前者,應當認識到,考察辦案人員是否通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現司法資源合理配置不能不對實踐中刑事案件繁簡分流之條件及其適用恰當與否,以及案件繁簡分流之后辦案人員所節省下的精力是否真正投入到了“應繁則繁”的案件中進行縝密的考核[22]。針對后者,制度適用率顯然難以用于評價個案或者總體的辦案質量。再者,如前所述,辦案人員原本就具有推動認罪協商從而加快訴訟進程、緩解案件積壓的傾向,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列為評價指標就更無必要。而將認罪認罰案件中保障值班律師履職情況列入辦案評價體系則有其重要性和可行性。“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6]。設置保障值班律師訴訟權利行使的相關考核標準不僅能促進值班律師工作保障機制發展完善,提高辦案人員保障值班律師履職的積極性,進而改善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訴訟參與整體環境,其對于培養辦案人員的協商性司法理念和對話協商精神亦有所裨益。基于此,以當前各地司法機關開展辦案人員與律師互督互評工作為契機,可以考慮增添“保障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案件的情況”為辦案人員業務評議主要內容之一,并探索將評議結果作為辦案人員績效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其二,公安司法機關在考核辦案人員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情況時應當合理運用定量和定性這兩種績效考核基本方法。一是,需要全面、審慎地考查目前公安司法機關在對辦案人員認罪認罰案件辦理情況進行定量評價的過程中其業績指標和評分規則的制定是否具有合理性。畢竟歷史經驗已反復證明,即便決策者本意良善,人為劃定“定時定量”的任務總會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諸多扭曲與變形[27]。在一定程度上,當前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功能虛化即為效率價值導向下數字指標所造成的實踐扭曲的具象之一。二是,不同地區、不同層級辦案機關的考核評價方式和側重點應當有所區分。一般而言,位于發達省市的和層級較高的公安司法機關,其辦案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水平較高,辦案人員具備扎實的知識基礎和良好的工作能力,因此在考核辦案人員認罪認罰案件辦理情況時可以適當運用定性評價方法。而對于處在欠發達地區的和部分基層辦案機關,則應當將辦案人員是否聽取被追訴人、值班律師意見及其保障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行使會見權、閱卷權等訴訟權利的情況合理量化為具體的評價指標,并將考核結果直接與辦案人員的績效獎金相掛鉤,以便于促進司法管理監督和保證工作質量。
(三)強化針對認罪認罰案件權力運行的監督體系
應當承認,從刑事訴訟實踐環境來看,認罪認罰案件權力主導的運行模式總體符合我國當下刑事訴訟制度特征、刑事司法改革需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民眾內在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特性要求。因此,針對辦案機關基于程序主導地位限制值班律師訴訟參與的問題,相對而言低成本高成效的解決方案不是通過增列訴訟權利這一類方法追求控辯力量平等,更不是主張從根本上轉變認罪認罰案件的權力主導特征及運行模式,而是加快完善對于權力運行的監督體系。同時,雖然如上文所述,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乏力極大地提高了辦案機關在權力主導模式下壓制值班律師的風險的現實性,但綜合考慮到認罪認罰案件中法官司法審查所處的訴訟階段及其審查的重點內容、主要方式[28]和提高庭審效率的總體要求,值班律師履職受限的問題難以在法庭審理階段得到解決,而仍然需要依靠審前階段的權力監督體系予以疏解。
其一,加強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案件審前階段辦案活動的法律監督。目前伴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持續推進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全面深化,檢察機關的工作重心更多轉向了發揮公訴及訴訟監督職能[29],在此背景下檢察機關應當強化對偵查活動法律監督,及時對認罪認罰案件偵查階段阻礙值班律師了解案情、限制值班律師參與訴訟程序的情況提出糾正意見或檢察建議。檢察機關內部也應當進一步完善案件管理工作,以《人民檢察院刑事案件辦理流程監控要點》為指引,充分發揮案件管理部門對于檢察官承辦認罪認罰案件和保障值班律師訴訟權利的集中、統一監管功能,并在量刑協商、具結書簽署等重要程序和關鍵節點上重點監控檢察官落實值班律師訴訟參與的實際情況。
其二,加快健全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察機關權力運行的外部監督制約機制。在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協商和具結活動中,檢察機關既是程序主導者,又是法律監督者。基于此,除了檢察機關應進一步增強和改進自我監督以外,也需要充分發揮外部監督力量,促進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相結合,實現對檢察機關辦案活動的全方位監督。經過多年建設,當前我國人民監督員制度已取得較為良好的工作基礎。在此背景下,可以在現有的制度總體框架下深化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將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察機關保障值班律師訴訟參與的情況納入人民監督員的監督范圍,以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權力運行的外部監督制約機制和促進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訴訟程序。具體而言,規定對于案件承辦檢察官阻礙或者變相阻礙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辦理的情形,值班律師有權向檢察機關人民監督員工作機構提出申訴,人民監督員工作機構需要在受理申訴后及時、隨機抽選一位或多位人民監督員展開監督。在此過程中,人民監督員應當直接向值班律師了解辦案人員侵犯其訴訟權利的具體情況,承辦檢察官亦必須配合監督工作,向人民監督員介紹基本案情、聽取意見情況、量刑建議內容以及作出量刑建議的理由和依據等。必要時,人民監督員可以要求檢察機關通知承辦檢察官、被追訴人和值班律師到場發表意見。而在人民監督員就有關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后,檢察機關應當盡快審查處理,并將意見建議如實記錄在案,隨案移送。同時,考慮到目前人民監督員法律專業水平整體偏低的實踐現狀,可以規定人民監督員在履行上述監督職責時應重點對檢察機關是否存在侵犯值班律師訴訟權利的行為作出獨立判斷,而不宜將評價量刑建議內容的合法性、合理性作為其主要任務。另外,這一方案或許會面臨著造成程序繁瑣化并降低訴訟效率的質疑。的確,在人民監督員介入的認罪認罰案件中,案件處理程序更為復雜。正因如此,筆者主張人民監督員介入認罪認罰案件的條件為值班律師提出申訴,而沒有建議將人民監督員外部監督設置為認罪認罰案件的必經程序。人民監督員基于具備法律專業能力的值班律師所提出的申訴展開監督工作,亦是兼顧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的舉措,而并非無意義地耗費司法資源或者拖延訴訟時間。
余論
當前我國正處在司法體制改革和社會治理體系變革的歷史轉折點,在這個“轉型期”中,會有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機制誕生,但同時任何制度要獲得社會的認可并進而得以有效運行都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理論工作者將目光不斷往返于規范與現實,真正投入精力和成本反復地探討、論證一項法律制度是否與其他相關制度彼此協調,并在此基礎上審慎地對具體制度內容進行調整和完善,注重對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的系統性建設。應當看到,目前我國值班律師制度迎來這一輪建設熱潮是基于構建認罪認罰自愿性保障機制的需要。然而實踐中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效率價值的過分追求造成了認罪協商機制功能異化,對抗性司法理念也沒有在司法實踐層面真正發生轉變,部分辦案人員仍然排斥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辦理,加之權力主導模式下法律監督不夠充分,使得值班律師履職困難重重。基于此,為疏解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的訴訟參與問題,除了必須落實規范權利義務告知程序、保障值班律師會見閱卷權利等前提性工作,還需要培養辦案人員的協商性司法理念,改革辦案機關效率價值導向的認罪認罰案件考核制度,以及強化認罪認罰案件權力運行的監督體系。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有學者曾提出賦予值班律師訊問在場權的改革方案。但是,受制于我國刑事案件數量快速增長而律師資源總體較為有限、律師數量區域分布不均等的現實情況,即便法律規定值班律師有權訊問時在場,這一權利也很可能難逃形式化困境。并且,從權利外部環境來看,在犯罪行為逐漸復雜、犯罪類型日趨多樣的新形勢下,口供仍在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通常經過現場勘查、外圍調查獲得一定證據、確定被追訴人,然后對該被追訴人進行訊問以突破口供,再根據口供進一步收集證據。參見:朱孝清.偵查階段是否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1):114-115.,而值班律師在場不免與相關偵查工作形成抵牾,推行訊問在場權必然面臨著來自辦案機關的相當阻力。即便辦案機關愿意配合,為落實值班律師訊問在場制度,辦案人員必須與值班律師溝通訊問時間,值班律師缺席時訊問中止,這將耗費較高的司法成本并降低值班律師訊問在場權的實際效益。因此,綜合考量值班律師發展水平、制度改革實際阻力、方案運行整體收益等因素,雖然針對值班律師訊問在場權的討論在理論層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卻不得不讓人懷疑其作為改革方案是否具有較高的可行性。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確立和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模式開始由全面的對抗性司法轉向發展協商性司法,在此背景下如何促進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相平衡以及如何利用與制約公權力成為了重大時代課題,當前對于值班律師制度困境的回應也需要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而伴隨著值班律師制度建設的持續推進,這一制度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實際運作還有待更精細的考察,如何保障值班律師實質性參與認罪認罰案件也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陳衛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J].中國法學,2016(2): 48-64.
[2] 王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穩定保持在85%以上[EB/OL].(2023-02-15)[2023-07-17].https://www.spp.gov.cn/zdgz/202302/t20230215_601755.shtml.
[3] 南茂林.甘肅: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案件占比84.54%[N].檢察日報,2021-01-08(01).
[4] 魏曉娜.結構視角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J].法學家,2019(2):111-123.
[5] 馬明亮.論值班律師的勤勉盡責義務[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0(3):35-48.
[6] 閔春雷.認罪認罰案件中的有效辯護[J].當代法學,2017(4):27-37.
[7] 龍宗智.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關鍵是控辯平衡[J].環球法律評論,2020(2),5-22.
[8] 胡銘.刑事辯護全覆蓋與值班律師制度的定位及其完善:兼論刑事辯護全覆蓋融入監察體制改革[J].法治研究,2020(3):65-66.
[9] 顧永忠.刑事辯護制度改革實證研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5):129-144.
[10] 韓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協商問題[J].法學論壇,2022(6):90-99.
[11] 陳瑞華.論量刑協商的性質和效力[J].中外法學,2020(5):1126-1149.
[12] 羅海敏.被審前羈押者獲得律師幫助權探究[J].當代法學,2022(4):151-160.
[13] 賈志強.回歸法律規范:刑事值班律師制度適用問題再反思[J].法學研究,2022(1):120-134.
[14] 劉泊寧.認罪認罰案件中值班律師有效法律幫助制度探究[J].法商研究,2021(3):188-200.
[15] 冀祥德.建立中國控辯協商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45.
[16] 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檢:加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力度[EB/OL].(2019-10-31)[2022-11-22].https://www.spp.gov.cn/zdgz/201910/t20191031_436814.shtml.
[17] 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3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R/OL].(2023-03-17)[2023-03-18].https://www.spp.gov.cn//gzbg/202303/t20230317_608767.shtml.
[18] 申國軍.論“案—件比”評價指標的豐富內涵[J].中國檢察官,2022(21):73-77.
[19] 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加速度”:杭州首例48小時刑事速裁程序案件快速辦理![EB/OL].(2020-07-30)[2022-11-24].http://www.fyjcy.gov.cn/articleView.do?art_id=1012.
[20] 陳國慶.量刑建議的若干問題[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5):3-18.
[21] 閆召華.聽取意見式司法的理性建構: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中心[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4):56-79
[22] 張建偉.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內涵解讀與技術分析[J].法律適用,2016(11): 2-8
[23] 陳瑞華.論協商性的程序正義[J].比較法研究,2021(1): 1-20.
[24] 周新.公安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實證審思:以G市、S市為考察樣本[J].現代法學,2019(5):152-167.
[25] 陳衛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問題再探討[J].環球法律評論,2020(2): 23-36.
[2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27] 郭爍.認罪認罰背景下屈從型自愿的防范:以確立供述失權規則為例[J].法商研究,2020(6):127-138.
[28]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公力合作模式:量刑協商制度在中國的興起[J].法學論壇,2019(4):5-19
[29] 胡勇.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察機關的再定位與職能調整[J].法治研究,2017(3):88-94.
The weakened functionality of duty lawyers in cases involving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Pattern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WEI Yuening, ZHU Yuqing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P. R.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weakened functionality of duty lawyers in cases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persists, as evidenced by the obstacles encountered by these lawyers in obtaining case information from police investigators, their passive involvement in meeting with the accused person and reviewing dossiers, and the formalities surrounding their presence during pledging procedur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operation of the duty lawyer system may conflict with the efficiency-oriented values embedded within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processing the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cases, potentially slowing down procedural flow and prolonging case processing cycles. Some personnel may harbor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owards the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f duty lawyers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Secondly, the consultative judicial concept promoting equal dialogue and rational negotiation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parties has no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within the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case processes; some personnel hold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 role and capabilities of duty lawyers during sentencing negotiations. Thirdly, the lack of legal supervision by prosecutors in power-dominated models prevalent within the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cases has resulted in connivance, enabling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expansion of interests by the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processing the cases through rule-making processes and specific judicial procedures. It should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current duty lawyer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punishment of crimes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ases involving the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Moreo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 reliance and control on public power are two significant factors impacting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the duty lawyer system. In line with China’s ongoing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nd considering the existing practice environment, it is advisable to promot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the duty lawyer system and related mechanism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weakened functionalit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ly, standardize and implement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by case-handling authorities to ensure timely meetings between duty lawyers and accused individuals while granting complete access to case dossiers. Secondly, refor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for case-handling authorities in the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cases by eliminat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based on application rates for the system of admitting guilt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instead, emplo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assess case-handling personnel’s performance to facilitate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f duty lawyers in handling such cases. Thirdly, enhance supervision over powers at the pre-trial stages. Thi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legal oversight by prosecutorial organs and deepening reforms within the people’s supervisor system, which establish external supervisory mechanisms restraining powers wielded by prosecutorial organs, thereby promoting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aimed at comprehensive oversight over police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involved in handling such cases.
Key words:
duty lawyer; legal assistance;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the dominance of power; efficiency value; people’s supervisor(責任編輯 劉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