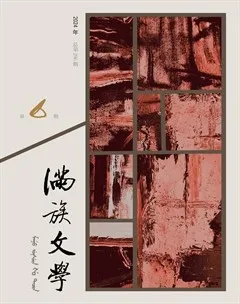蛤叉的味道(散文)
秋風漸起,黑臉琵鷺已開始陸續飛向南方。春天孕育,夏季生長,一切都成熟起來。站在海邊,堿蓬草鋪滿了紅海灘,海浪聲也有了幾分沉穩,少有人知道這意味著什么,而海邊的農家人已呼朋引伴,追逐落潮,沿著海路蜿蜒向前。北緯39度,黃海北岸中部這片繁盛的海域,20世紀30年代一家著名的報紙稱之為:世界蜆庫。
一
三河入海,兩水交融,大自然的造化給了這方貝類家族優越的條件,白蜆、沙蜆、黃蜆、毛蚶、文蛤等相擁相生,廣袤無際。
然而,熱鬧之中總有孤獨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反正是這方蜆庫中竟也生出一個另類。它不受潮汐的影響隨處遷移,只堅守在這方海域;也不與尋常的蛤貝混在一起,只深居在深一層的灘地。北岸的人家費盡心思采集上來,更是多了幾分自豪,每有客人到來,都會介紹說,這是我們的特產,叫蛤叉。
冬天攜著一場又一場的雪來了。我們一路唱著“潔白的雪花飛滿天,白雪覆蓋著我的校園”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隨便找個木棍什么的,就從院子的雪堆中往外劃拉出一個個蛤來,或直接砸開,感受那生猛溜鮮的味道;或更多的扔到草火漸旺的鍋底坑中,聽著“滋滋”的聲音,想著那些鮮嫩的湯汁都流了出來,怪可惜了。可是,那時大人卻頗不以為然,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海邊人家的尋常之物,并不像今天這樣稀罕。當我們從火堆里扒拉出這些東西時,它們個個都成了煙火色,殼大多已經酥碎,肥嫩的肉質或成了焦黃色或還殘留點湯汁,不管怎樣,一口下去,都是煙熏火燎的鮮香味。但特殊的情況也常有,就是遇到半熟半生的蛤叉,一股苦辣的感覺直沖腦門,一直沖到了記憶深處。大人說,蛤叉不能生吃,這是它的特性。
蛤叉的吃法是有講究的。若要燒烤,須把它均勻地放在火爐上,看著熱氣一點點上來,隨時翻動,幾個來回,它的殼就會漸漸裂開,有的還會“啪啪”蹦出幾塊,頗有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骨氣,這時你吸一口蕩漾在湯殼中的白皙而有韌性的蛤肉,那真是至極至鮮的美味。看來,出類出眾的東西,總要認真對待。
更常見的吃法是把蛤叉一個個投進熱氣騰騰的火鍋中,無論火候大小、時間長短,也無論清水鍋、菌湯鍋、還是什么其他各種酸甜苦辣的鍋,都不會改變它的鮮度,它是火鍋中當仁不讓的味道主角,讓北方的寒冬有了一種漫長的享受。一位會跳舞的朋友說,他最喜歡的是紫銅火鍋,不單是因為炭火,更是因為滿滿的酸菜、豆腐上面鋪上的那一層層蛤叉。在熱氣氤氳中,那些漸漸展開翅膀的殼,像舞臺上長袖舒展的精靈,再一勺一勺喝起那些湯汁來,整個心思都活泛了。這樣的聚會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猶如一場場地方味道的大戲,演繹著各樣的人生過往。偶爾看向窗外,已是燈火闌珊。
二
潮起潮落聲中,農家鐵匠鋪子的爐火也紅了起來。幾錘子下去,就鍛造出一個個物件來。其中有一種上寬下窄類似平口鐵锨的東西,尋來一個角度合適的分叉木柄安上,一把蛤锨就做成了。這是趕海人特有的工具。
小時候讀到“耕海牧魚”四個字時,心中總有一種疑惑,翻滾著浪潮的偌大海面怎么能和莊稼地一樣呢?
大海的潮信就像農耕的節氣一樣。東看看、西聽聽,趕海人就不約而同地武裝起來,穿上長筒水靴或者連體的叉褲,拎著各式裝備,從四面八方匯成長長的隊伍,迎著不斷退去的海浪向著大海出發。走的人多了,海灘上便踩出了一條“涼道”。“涼道”漸漸被甩在身后,趕海人不知不覺間已漸次散開,一望無際的海灘上,只能看到星星點點的身影。腳下的泥水不覺淹沒了腿彎處,他們會用推耙把泥水向四圍推出去,一塊小小的領地又重新得以形成。趕海人深深彎下腰去,左手用勁攏住木柄的前分叉,右手握緊已磨得溜光的后木把,幾蛤锨下去,就會判斷出大體的收成來,要么轉移陣地,要么繼續擴大戰場。隨著蛤锨上下起伏、左右揮動,一蛤锨一蛤锨的海泥被甩向身后,一個個青藍藍、扁圓形的寶貝也驚喜地亮出身份,戰場越來越擴向四周,一片片新翻墾的土地接連蘇醒過來。一筐筐、一兜兜蛤叉在陽光下閃著光,外殼上一圈圈的線條有如樹的年輪。
大潮汛時,趕海人會踏著落潮走得更遠,甚至到了潮線邊際。各種鷗鳥在低空徘徊,海風里挾著咸咸的味道,蛤叉又多又大,小一點的,沒人理會,一場潮水后,海灘又恢復原樣。忽然真有一線潮水來了,不知是誰輕喊一聲“快漲潮了”,趕海人都不約而同地回返,走著走著,又匯合在了一起,手拎肩扛,挑擔背兜,前不見頭,后不見尾。這樣的隊伍后來又不斷加進新的風景,是一種“木牛流馬”似的工具,有人在一塊長方形的平木板上,安裝了裝蛤叉的架子和扶手,一條腿跪在長木板上,靠著另一條扎進海灘的腿的力量,在泥水中快速地向前滑行、滑行。夕陽西下,晚霞中的隊伍隨風傳來陣陣嬉鬧的聲音,收獲的喜悅回蕩在遼闊的海面,岸邊就在眼前。
三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開海季!大海用積攢四個月的力量將各種海鮮一下子推進市場、餐館和酒桌上。感謝朋友在我外出一段時間回到故鄉后,又準備這樣的盛宴找回那日思夜想的味道,有腌蝦爬、腌飛蟹,有生海蠣、生文蛤,當然更少不了鮮熟的蛤叉和有關“蛤叉嫂子”的故事。
聽說“蛤叉嫂子”年輕時,第一次趕海是從隔壁鄰居家借的一把蛤锨,以后趕海回來,經常會挑出一二斤送過去,很得老兩口的歡心。鄰居的小兒子在海軍當兵,回來時經常穿著藍色的呢子大衣,瀟灑得讓人眼熱,也聽說會帶回那種裝滿糖塊、餅干的鐵盒,并且上面有著漂亮的圖案。每當這時,“蛤叉嫂子”就會格外送上更多更亮的蛤叉,有時煮上一盆熱氣騰騰的蛤叉端過去,或許還有蛤叉餃子、蛤叉面條、蛤叉燉白菜什么的。反正大約是蛤叉的緣由吧,兩人后來就成了家,她也就有了“蛤叉嫂子”的稱呼。
“海風你輕輕地吹,海浪你輕輕地搖,遠航的水兵多么辛勞……”兩人剛結婚那陣兒,每逢趕海,周邊的人就會在“蛤叉嫂子”身旁哼唱起這首歌,邊嬉笑邊鬧著。細心的人們發現,“蛤叉嫂子”挖蛤叉的習慣也在不知不覺間改了,常常會在海灘上抬起頭、挺起腰,目光望向遙遠的海面,紅艷艷的頭巾迎著海風飄著。
朋友講述這個故事時,另一個朋友夾著一個蛤叉說,這種蛤叉叫“牛眼蛤”,他也有一個叫“牛眼蛤”的朋友。
朋友的“牛眼蛤”朋友其實是瞇瞇眼。初中時,一次到海邊閑逛,可能他要顯顯本事,就拿著向趕海人討來的蛤叉,炫耀地說他能生吃下去。大家想看他的笑話,就不斷地慫恿,也有一位伙伴用鐵片完整地掀開一個大的殼來,圓鼓鼓的肉,滿滿的汁。這哥們猶豫一下,伸手接住,然后蹲樁、運氣,狠狠閉著眼睛猛嘬進嘴里,大口嚼著說,鮮溜鮮溜啊!一會兒,又見他額頭泛起汗珠,眼睛瞪得“牛眼”一般,嘴張得大大的,雙手舞得更歡,呼著氣說,辣呀,辣呀辣!
因為這個“辣”,“牛眼蛤”出了名,并開始研究起蛤叉來。任誰也沒想到,他有一次竟專門為了“辣”,給女兒快遞了一保溫箱蛤叉。原來,他的女兒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學,一次周末聚餐時,班長說要AA,當地一位同學隨口道:你真嘎叉嘎叉呀!他女兒接話說,我家鄉的蛤叉真鮮真鮮呀!一時間,大家搞得有點蒙,哄笑一陣兒,然后才恍然大悟。那位南方同學的家鄉話中,“嘎叉”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很小氣、斤斤計較,沒想到同北方大海里的美味混同在了一起,也成了校園的一個經典段子。因為這事兒,班長請他女兒吃了一頓麻辣火鍋,辣得她一直在念叨,有蛤叉才好、才好呀!
那幾天,“牛眼蛤”一直拉著朋友在市場選蛤叉。他說:我就想試試咱這地方的蛤叉投進南方的麻辣火鍋中,這個鍋的味道是辣還是鮮?
后來,女兒微信回復:小伙伴們都驚呆了!“牛眼蛤”再回復:蛤叉,學名“藍面鏡蛤”。
春天在新鮮的浪花中穿梭而來,黑臉琵鷺的繁殖羽在陽光下發出艷麗的訊號,它們甩著湯匙一般的長嘴晃動于海灘之中,尋覓著屬于它們的魚、蝦、蟹,還有未知的伴侶。我想起小時候,我們光著腳在沙灘奔跑,追逐海浪,不知疲憊,而海面晃動著耀眼的晨光,似乎很近,又似乎很遠。
【責任編輯】涉 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