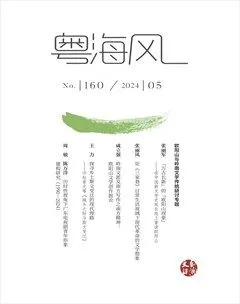在“誤投”的空間中邂逅公共性

作為享譽國內(nèi)外的日本文化學(xué)者,東浩紀(jì)的兩本代表性著述《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御宅族如何影響社會》《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2:游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是當(dāng)下中文學(xué)界闡釋動漫、游戲、電影、網(wǎng)絡(luò)小說可以借鑒的重要理論資源。由他提出的“數(shù)據(jù)庫消費”“數(shù)據(jù)庫動物”“游戲?qū)憣嵵髁x”等概念亦是當(dāng)前亞文化研究的高頻熱詞。《觀光客的哲學(xué)》是東浩紀(jì)的最新著述,它并非橫空出世,而是生長在東浩紀(jì)長久以來思考的延長線上,與其《存在論的、郵件性的》《一般意志2.0》《弱聯(lián)系:尋找搜索詞之旅》《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等作品有著明顯的接續(xù)性,可以說是貫穿東浩紀(jì)十?dāng)?shù)年工作成果、凝結(jié)著其最新智性思考的一部作品。在本書中,東浩紀(jì)的探討始于這樣一個問題:21世紀(jì),當(dāng)現(xiàn)代意義上的普遍性走向崩潰,“他者”遭到人們的厭惡和驅(qū)逐之時,我們何以想象、建構(gòu)一種新的公共性?
一、雙層構(gòu)造的時代
東浩紀(jì)發(fā)現(xiàn)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雙層構(gòu)造的時代”。所謂“雙層構(gòu)造”,即在經(jīng)濟與文化全球化加速的同時,國民國家、國族主義觀念也在不斷膨脹。他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經(jīng)歷了英國脫歐,特朗普當(dāng)選美國總統(tǒng);本書付梓之際,新冠疫情開始肆虐全球,為阻止病毒蔓延,各個國家開始封鎖國境線,減少國民間的流動;疫情有所好轉(zhuǎn)后不久,俄烏戰(zhàn)爭和巴以戰(zhàn)爭相繼爆發(fā)……這一切都證明了政治全球化正在迅速衰退。而我們又生活在一個“幾乎所有一切商品包括吃的東西,穿的東西,看的東西都跨越國界,仿佛國民國家不存在一般地,不斷流通的世界。”[1]“消費”正使全球迅速坍塌成一個社會。我們即是生活在這樣一種分裂的狀態(tài)下:一方面,不管我們身處世界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都吃著一樣的連鎖快餐,身穿同一品牌的服飾,觀看沒有差別的電影電視節(jié)目;另一方面,我們只關(guān)心自己所屬共同體的利益,總是從共同體內(nèi)部出發(fā)去看待世界與他者,因此更容易被裹挾、被煽動并開始厭倦或仇恨“他者”。康德所設(shè)想的“世界公民”和黑格爾所生存的“樸素國族主義”時代已不可能存在。
康德以其設(shè)想的倫理共同體為基礎(chǔ)提出了“世界公民”的范疇。在現(xiàn)實世界中,這種倫理共同體以“自由國家聯(lián)盟”的形式存在,這種聯(lián)盟并非拒斥國家,也不是在構(gòu)造“世界帝國”,而是一個權(quán)力極度弱化的共和制國家,它摒棄了一切強制性、暴力的力量,以永久和平為目標(biāo),通過理性的自我立法,使世界上每一個道德主體都獲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此,人們即成為平等地享有普遍權(quán)利、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公民,得以直接分享普遍。但在倫理共同體的語境下,人被預(yù)設(shè)為一種必然向善的道德主體。
與康德將人視為道德主體不同,黑格爾發(fā)現(xiàn)了被私欲裹挾的主體。他認(rèn)為人們通過進入公民社會而成為公民,在公民社會中,人們不再通過家庭之愛而是通過語言和金錢媒介進行互動,個體總是以自身的特殊目的和需要的滿足為目標(biāo)。這就使得市民社會成為普遍性的破壞者:一方面,它破壞了以家庭為代表的最初的倫理共同體;另一方面,市民社會中個人對主觀自由的欲求、普遍存在的利己主義道德觀并不會建構(gòu)起新的普遍性,反而會催生個人與集體間新的沖突。因此,黑格爾認(rèn)為市民社會并非真正的國家,要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國家,就需要一個具備政治整備功能的單位,國家即是這樣的存在。國家并非個體的簡單拼湊,而是一個倫理學(xué)整體,國家統(tǒng)治著市民社會,整合了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用政治意識壓抑著經(jīng)濟的無意識,以群體性的統(tǒng)一敘事壓抑著個體的欲望敘事,克服了市民社會的普遍性危機,重新創(chuàng)造了一種個人與社會共處的可能。因而黑格爾認(rèn)為,人必須經(jīng)由國家才會變得成熟。東浩紀(jì)將這種國家觀稱為“樸素的國族主義”。
但進入21世紀(jì),“國民國家”已不再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共同基礎(chǔ),國家對經(jīng)濟和政治的整合力消失了,這是“雙層構(gòu)造”之所以會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那么,在這樣一個經(jīng)濟全球化與國族主義相伴相生的時代,不通過黑格爾的范式,是否還有另一種連接全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線路?或者說,在市民停留在市民社會的狀態(tài)下,個人忠實于個人的欲望之狀態(tài)下,是否會有新的公共性、普遍性產(chǎn)生的可能?東浩紀(jì)的回答是肯定的。觀光客的哲學(xué),即是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而構(gòu)思的概念。
在2014年出版的《弱聯(lián)系:尋找搜索詞之旅》一書中,東浩紀(jì)已經(jīng)對“觀光客”這一主體進行了描述。他觀察到當(dāng)下人類社會中兩種不同的生存模式:“村人”和“旅人”。村人代表一種穩(wěn)定的圈層關(guān)系和生活模式,旅人則與之相反,代表著變動、遷徙與不停地流浪。如果將村人視為人與共同體建立的確定關(guān)系的話,旅人則代表著人與共同體沒有關(guān)系。在這兩種模式之外,東浩紀(jì)提出了第三種生存模式——觀光客。即指那些穩(wěn)定地生活在某一共同體中,卻又偶爾會離開、往返于其他共同體的人們。[2]
但將觀光客當(dāng)作一個哲學(xué)話題加以討論卻是困難的,因為一直以來它都作為“人文思想全體的敵人”,長久地被排除在政治討論之外。若對“觀光”的歷史加以考察,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觀光”與17世紀(jì)歐洲以教養(yǎng)為目的的“壯游”(Grand Tour)的區(qū)別在于,觀光是大眾性的、以休閑為目的的、以商業(yè)消費為途徑的游覽。東浩紀(jì)如此描述觀光客:“觀光客是大眾。既是勞動者也是消費者。觀光客是私我性的存在,觀光客不擔(dān)負(fù)公共性的功能。觀光客是匿名的。觀光客不會與訪問的地方的居民互相一起議論。觀光客也不關(guān)切干涉到訪問地的歷史。也不會與政治關(guān)聯(lián)牽扯。觀光客只有使用金錢。無視于國界,在四處環(huán)繞飛旋在地球上,既不制造朋友也不制造敵人。”[3] 科耶夫在《黑格爾導(dǎo)讀》中描述了歷史終結(jié)后人類的兩種生存模式:日本的貴族風(fēng)尚和美國的動物化社會。他認(rèn)為,“二戰(zhàn)”后美國豐富的商品物質(zhì)資源使美國人沉溺于享樂,建構(gòu)起了如動物般的需求-滿足機制。施密特認(rèn)為,國家存在的前提是“敵”與“友”的區(qū)分,人們只有在與“敵”的激烈斗爭中,才能產(chǎn)生與“友”的緊密聯(lián)系,才能成為人。在《人的條件》一書中,阿倫特也借用了科耶夫“動物”的概念,提出了“勞動的動物”這一范疇。在阿倫特看來,人借由工作進入公共空間,借由行動成為有面孔、有名字、能夠被看到的人,而勞動只會使人成為匿名的、欲望的、私人的“動物”。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不管是作為需求-滿足機制下的觀光客,還是作為大眾抑或是“不制造朋友也不制造敵人”的觀光客,都是施密特、科耶夫、阿倫特所認(rèn)定“非人類的存在”,被剔除到思想的外部。若從黑格爾的范式來看,觀光客是無法成為成熟的人的,他總是幼稚的、欲望的、無意識的,概言之,“觀光客”是人向“動物”的墮落。
但東浩紀(jì)卻拒斥單純地將觀光客視為如動物般的存在,當(dāng)然,他也認(rèn)為觀光客并非阿倫特所謂作為行動者的人。他所謂的“觀光客”是一種全新的主體,其誕生于經(jīng)濟全球化和民資國家主義并行的“雙重構(gòu)造時代”,因而也表現(xiàn)出了作為“消費動物”和“具備普遍意志自由的身體”的雙層構(gòu)造,如此,東浩紀(jì)便將“觀光客”帶進了人文思想的觀察視野,并試圖以這種雙層構(gòu)造的主體為出發(fā)點構(gòu)建一種新的政治。
二、超越諸眾
事實上,麥克爾·哈特與安東尼奧·奈格里在《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創(chuàng)造的“諸眾”(Multitude)這一概念,與“觀光客”有著諸多相似。奈格里和哈特認(rèn)為,現(xiàn)代國民國家正朝著“帝國”“轉(zhuǎn)移變遷”。這里所說的“帝國”是指為了使全球化經(jīng)濟和文化交換活動更加順暢地進行,而在國民國家外形成的一種嶄新的政治秩序。在國民國家與帝國構(gòu)成的雙層結(jié)構(gòu)中,“管理者”分別以“規(guī)訓(xùn)”和“生命權(quán)力”的方式對人進行管理。“規(guī)訓(xùn)”與“生命權(quán)力”由福柯提出,前者指借由懲罰來驅(qū)動對象者之權(quán)力,后者指在尊重對象者的自由選擇的同時,借由不斷改變規(guī)則、環(huán)境等結(jié)果性地以管理者的目的來驅(qū)動對象者的權(quán)力。這使國民國家與帝國的對立模式與東浩紀(jì)討論的國族主義與全球化主義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同構(gòu)性:國民國家與國族主義一樣,是人作為人存在的層次,帝國與全球化則是人作為動物存在的層次。而“諸眾”是生活在帝國中的“嶄新的無產(chǎn)階層”,在國民國家即將消失的當(dāng)下,“諸眾”運動作為可能區(qū)別于帝國的“另一種選擇”(Alternative)而存在,表征為“生命政治”的自我組織形式。如此一來,“諸眾”便是橫斷雙層結(jié)構(gòu)的存在,是政治與經(jīng)濟、公與私、都市國家與家庭未切割的狀態(tài),為連接政治層面與經(jīng)濟層面提供了可能與參考。
但東浩紀(jì)指出,“諸眾”概念的致命缺陷在于它缺乏關(guān)于“諸眾”的力量如何與現(xiàn)實政治相聯(lián)系的戰(zhàn)略性和能動性理論,這使得諸眾的抵抗成為一種曖昧的、浪漫主義式的信仰告白。這一方面源于諸眾本就是帝國內(nèi)部產(chǎn)生的抵抗運動,只有帝國沒有他者的存在使諸眾運動成為帝國內(nèi)部的一種循環(huán)圖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大敘事崩潰后的后現(xiàn)代社會中,絕對真理和最后意義被消解了,諸眾運動失去了意識形態(tài)的指導(dǎo),其抵抗成為由私人性的生命為起點的公共的政治,將私我的生命直接帶到國家政治的層面,最為典型的諸眾運動即跨性別LGBT運動,社會性別(gender)的選擇作為一個私人性質(zhì)的問題本應(yīng)該被排除在政治討論范疇外,但當(dāng)前卻頻繁地作為一個政治議題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中。東浩紀(jì)將諸眾運動稱為“沒有溝通的團結(jié)連帶”,到最后,諸眾運動在抵抗什么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諸眾所形成的“團結(jié)連帶”本身,因而諸眾只能成為一種“否定神學(xué)式的共同體”[4]。
諸眾的另一個缺陷在于,諸眾的“團結(jié)連帶”是一種偽裝成“偶然性”的必然聯(lián)系。東浩紀(jì)引入了數(shù)學(xué)領(lǐng)域的“網(wǎng)絡(luò)理論”對人類社會進行結(jié)構(gòu)分析。他發(fā)現(xiàn)當(dāng)我們在面對他者時,會同時體驗到小世界網(wǎng)絡(luò)性(Small-world network)與大世界的無尺度性(Scale-free)。所謂小世界網(wǎng)絡(luò)性,類似于社會學(xué)中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即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經(jīng)由6個朋友的關(guān)系就可以認(rèn)識世界上任何一個他人,因而人們時常會產(chǎn)生“世界真小”的感覺。而大世界的無尺度性則是指,盡管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與任何他人建立平等的連接,但社會中總是存在極少數(shù)強大的個體,集中了龐大的連接資源,其本質(zhì)是一種“不平等”的結(jié)構(gòu)。這種小世界網(wǎng)絡(luò)性與大世界無尺度性普遍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與網(wǎng)絡(luò)空間。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技術(shù)賦權(quán)使得只有100個粉絲的賬號可以與有100萬粉絲的賬號進行一對一交流(私信),但他們本身鏈接的節(jié)點數(shù)量卻是差異巨大的。這意味著,盡管這是一種看似一對一的對等交流,但我們?nèi)詴惺艿截敻慌c權(quán)力之間巨大的差距。因此,東浩紀(jì)提出了“優(yōu)先性選擇”這一概念,推翻了我們所認(rèn)知的人與人產(chǎn)生連接是一種偶然選擇的常識性觀點;而旨在說明,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復(fù)雜性超越某個臨界點的時候,點與點之間的連接已不是一種偶然關(guān)系。正如我們在社交網(wǎng)絡(luò)中更愿意追隨本身就有更多粉絲的賬號一樣,新加入的點會更傾向于選擇更強大的點建立連接。這種看似偶然的必然帶來了階級的固化和社會流速的減慢。這一觀點在《弱聯(lián)系》中亦有過論述,東浩紀(jì)觀察到當(dāng)前的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已經(jīng)成為一種圈層固化的技術(shù),將人困在狹窄的信息繭房之中,人們看似可以通過網(wǎng)絡(luò)檢索任何自己感興趣、想了解的東西,但其獲得的只是搜索引擎按照用戶興趣數(shù)據(jù)提供的定制化的內(nèi)容。[5] 只要人們使用網(wǎng)絡(luò),就只能在別人定義的世界里進行思考,而生存在這種“偶然性”幻覺中的“諸眾”,也必然無法與他者建立真正的連接。“觀光客”的哲學(xué)即是對“諸眾”這諸種局限的超越與補充。
三、誤投的哲學(xué)
如果說“諸眾”是“否定神學(xué)式的”共同體,那么“觀光客”則是一種“郵件性的諸眾”(Postal Multitude)。“郵件性”是東浩紀(jì)對德里達“郵件哲學(xué)”的借鑒。在德里達看來,書信、電話等媒介如同明信片一樣,并不意味著從投遞者(A)寄出后一定會到達接收者(B)手中,時常會因噪聲等干擾因素的存在而導(dǎo)致投遞失敗。如此,德里達建構(gòu)了這樣一個郵件空間,在這個空間中,資訊如幽靈一般朝四面八方郵遞式地散播,其結(jié)果充滿了未知性與不可確定性。相較于德里達對這種不確定空間哲學(xué)的關(guān)注,東浩紀(jì)在此更強調(diào)投遞失敗的結(jié)果,即“誤投”(Mis-delivery)所產(chǎn)生的后果。他認(rèn)為觀光客是以“誤投”的形式與他者形成幽靈式的關(guān)系,正是“誤投”使觀光客與觀光地產(chǎn)生了連接,是“誤投”將偶然性帶回到這個世界,“誤投”使人們逃出信息繭房,使已經(jīng)固化的圈層邂逅到新的欲望。
概言之,觀光客的哲學(xué)就是誤投的哲學(xué)。人們總是借由觀光邂逅了各種各樣的人,看到了在本國絕對不會碰到的事物,從而建立一種排除在地性的偶然連接。一個對藝術(shù)毫無興趣的人,前往意大利或法國旅行的話,也一定會去博物館觀看蒙娜麗莎的畫像或是文藝復(fù)興時期的雕塑,進而可能在欣賞的過程中產(chǎn)生本不可能出現(xiàn)的感悟與觸動。當(dāng)然,“觀光”也充滿了誤解,正如“誤投”本身也指代傳達效率的損失一樣,生存于表面哲學(xué)世界的觀光客也并不一定會對觀光對象有著正確的理解。東浩紀(jì)曾在泰國一家名為“航站樓21”的商場中遇到了一個偽東京街區(qū)。在一般日本人看來,這個街區(qū)充滿了外國人對日本的想象元素:鳥居、紅燈籠、偽裝成日語的片假名(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是一個讓日本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而這種偽街區(qū)遍布全球,除了東京,還有偽威尼斯、偽羅馬、偽巴黎……東浩紀(jì)認(rèn)為,偽街區(qū)的出現(xiàn)代表著人們已經(jīng)完全不在意真實的城市是什么樣的,而僅僅是想要置身于自己“想象”的城市中。[6] 但正是這種誤解的存在才可能產(chǎn)生新的連接與溝通,因為觀光地要成為觀光地,就要引起觀光客的興趣,鳥居、燈籠、無意義的片假名構(gòu)成的“假事件”(Pseudo Events)成為吸引觀光客前來東京旅行的中介物。他如此形容“誤投”與“誤解”產(chǎn)生的連接:人總是想要與某個人產(chǎn)生連接,但卻無法順利達成,一番努力過后敗興而歸,但是事后回想起來,卻又忽然產(chǎn)生某種像是連接的東西已經(jīng)形成的感覺,這種感覺推動著下一次“誤投”的發(fā)生。[7] 從這一點來看,“誤投”絕不是一種否定性的經(jīng)驗,它本身具有某種啟蒙性作用,使人們能用包容、友好、好奇的態(tài)度去看待和面對他者。
觀光客的哲學(xué)還代表著一種“不認(rèn)真”的生存態(tài)度。旅游本質(zhì)上是一種出于某種偶然萌生的想法,前往一個不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去看不是一定要看的東西,接觸不是一定要接觸的人的一種非必要的消費活動。對觀光者來說,觀光地的一切都是商品與展示物,是中立的、無為的,偶然被他們所凝視的。從這個角度看,觀光地所發(fā)生的一切對觀光客來說幾乎沒有任何意義。觀光客并不介入觀光地的生產(chǎn)結(jié)算,也并不完全了解當(dāng)?shù)氐纳鐣v史,他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如鮑曼所說,觀光客被密封在一個透明的水泡之中,與所有事物都保持著距離感,并由此產(chǎn)生不認(rèn)真、不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東浩紀(jì)認(rèn)為御宅族是典型的“不認(rèn)真”的觀光客,他們從漫畫/動畫原作中,隨意地抽取部分角色或設(shè)定,按照自己的興趣進行“二次創(chuàng)作”。文藝活動中的“不認(rèn)真”發(fā)生在作者“死”后,但此時的“作者之死”不僅僅是闡釋學(xué)或接受美學(xué)所謂的,作為唯一意義來源和作為最權(quán)威解釋者的作者的脫冕,更代表作者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對作品的控制,讀者可以對作品進行隨意剪裁、拼貼,并衍生出來龐大的“二次創(chuàng)作”產(chǎn)業(yè)和為了“二次創(chuàng)作”而創(chuàng)作的“原作”。從這一點看,泰國商場隨意抽取日本元素進行再創(chuàng)作搭建的偽東京街區(qū)和全球范圍內(nèi)流行的偽城市文化,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不負(fù)責(zé)的“二次創(chuàng)作”。因此東浩紀(jì)說:“二次創(chuàng)作者是資訊內(nèi)容(contents)世界之中的觀光客,反過來說,所謂觀光客,就是現(xiàn)實中的二次創(chuàng)作者。”[8] 這是東浩紀(jì)對《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御宅族如何影響社會》《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2:游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中提出的“數(shù)據(jù)庫消費”“數(shù)據(jù)庫動物”等議題的當(dāng)下思考。
若將《觀光客的哲學(xué)》這本書的寫作視為一種隱喻性寫作,“觀光客”的范疇就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游客,而成為那些跳出自己所處圈層,在不同政治、經(jīng)濟、文化、趣緣圈層間游走的群體。“不認(rèn)真”的生存哲學(xué)也不僅僅指觀光客按照自己理解去消費和使用那些自己感興趣的商品(即誤投),而是指大眾在面對那些自己不理解的議題、偶然映入眼簾的事物時,用一種“自己也不懂”的態(tài)度去處理。這是東浩紀(jì)針對當(dāng)下社交網(wǎng)絡(luò)中“反應(yīng)過剩”問題做出的回答。東浩紀(jì)認(rèn)為:“人們對于眼前的危機過剩反應(yīng)了,知識分子或是言論媒體等,照理說應(yīng)該對于如此反應(yīng)過剩的社會現(xiàn)象采取不同的觀點建議才對,但是,眼見公共言論似乎是跟著起哄做不到的樣子,這是太奇妙的傾向。”[9] 在他看來,越認(rèn)真的人反而越容易被輿論裹挾,被同質(zhì)化的信息誘導(dǎo),進而產(chǎn)生強烈的排他情緒,最終演變成“一言不合就開撕”的網(wǎng)絡(luò)現(xiàn)象。太認(rèn)真的人不會遇到“陌生人”與“他者”,只會陷入“無盡的自我循環(huán)之中,并最終導(dǎo)致我們‘被自我想象洗腦’”[10]。因此,只能以觀光客的態(tài)度與萬事萬物保持距離感,以“自己也不懂”的謙虛態(tài)度來面對信息爆炸的網(wǎng)絡(luò)世界,并在與他者的邂逅中捕捉一些共鳴的情緒,進而與其他有著相似共鳴感受的“觀光客”一起創(chuàng)造連接他者的公共性。正如東浩紀(jì)所說:“(觀光)是偶然被打開的狀態(tài)。觀光客雖然沒有團結(jié)連帶,但相對地,觀光客與偶然邂逅的人相互交談。諸眾出門是抗?fàn)幱涡校^光客出門是游山玩水。抗?fàn)幱涡须m然有敵人,但觀光卻并沒有敵人。”[11]
行文至此,再回看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東浩紀(jì)思考的,是在這樣一個雙層構(gòu)造的世界中,在人一面如動物般消費,一面又如人一般討論政治的時代中,公共性從何處產(chǎn)生?黑格爾以國民國家的形式來探討這種公共性形成的可能。奈格里和哈特認(rèn)為這種公共性會產(chǎn)生于帝國內(nèi)部。東浩紀(jì)則提出了公共性產(chǎn)生的第三種可能:公共性既不產(chǎn)生于帝國內(nèi)部,也不源自國民國家,而是從全球化與國族主義的縫隙中產(chǎn)生,產(chǎn)生于“誤投”的空間中。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注釋:
[1] [日] 東浩紀(jì):《觀光客的哲學(xué)》,黃錦容譯,臺北:唐山出版社,2023年版,第130頁。
[2] 東浩紀(jì):《弱いつながり:検索ワードを探す旅》,幻冬舎,2014年版,第48—51頁。
[3] 同[1],第113—114頁。
[4]“否定神學(xué)”即指神正是由于其不存在而存在,不可存在之物是因為不存在而存在的悖論式修辭。
[5] 同[2],第9頁。
[6] 同[2],第113—117頁。
[7] 同[1],第201—226頁。
[8] 同[1],第50頁。
[9] 轉(zhuǎn)引自黃錦容:《觀光客的三種身份認(rèn)同》,載《觀光客的哲學(xué)》,唐山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1頁。
[10] 韓炳哲:《他者的消失》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頁。
[11] 同[1],第172—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