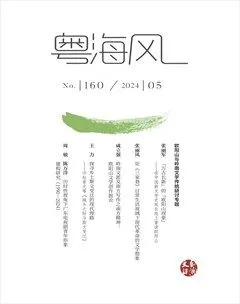中國古代繪畫中的鞍馬形象研究



















摘要: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中,關于鞍馬題材的繪畫屢見不鮮。文章試以鞍馬繪畫的題材分類為切入點,在展現鞍馬作品在不同時期的主題功能與繪畫表現的同時,嘗試回答鞍馬題材在繪畫上何時受到關注?關注的目的是什么?不同時代的表現有什么區別等問題,進而探討作品背后的圖像內涵與階級訴求。
關鍵詞:鞍馬繪畫 時代特征 主題分類
一、中國古代鞍馬題材繪畫的主題分類
中國古代鞍馬題材美術創作能夠記錄現實生活、表現文人志氣、弘揚時代精神,從作品價值看,可以從“現實價值”和“文化意蘊”兩個維度對鞍馬在中國古代繪畫中的表現進行概括;從表現形式看,主要以卷軸畫、壁畫為主,還有巖畫、畫像石、畫像磚等門類,涉及交通出行、運動娛樂、狩獵出游等多個方面,并且不同時期作品的社會功能、形式風格和思想觀念也有所不同。
(一)實用性:世俗生活中的鞍馬圖像
1.交通出行
車馬作為主要的陸上交通工具,從先秦以來就是王侯將相出行的首要選擇。歷朝歷代關于車馬出行的描繪不勝枚舉,僅已發現的漢唐墓室壁畫中關于“車馬出行圖”就不下百余幅。這些墓室壁畫中的“車馬出行圖”記錄著墓主人生前出使拜見、祭祀喪葬、任官出行等多種社會出行活動。其中,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的《出行圖》,不僅描繪了墓主人6次赴官上任的出行場面,更通過多變的隊形把眾多的車馬人物連接起來,形成一個相互獨立又統一的整體。東晉顧愷之卷軸形式的《洛神賦圖》(見圖1宋摹本)在內容上雖屬人物畫范疇,卻也是公認的最早畫馬杰作。創作者在卷首便借3匹不同放松姿勢的馬,勾勒出曹植一行于洛水畔停歇時的情形,鋪墊了洛神出場的氛圍;而卷尾處則通過馬車上飄揚的旌旗和華蓋上的羽毛來映襯馬的奔速之快,極具文人之思。唐代宮廷畫家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則描繪了虢國夫人及其眷從踏青游春的情景,駿馬氣定神閑,彰顯出皇家御馬的富貴之態。
此外,馬匹還常用于信息傳遞。像嘉峪關5號墓中的《驛使圖》便描繪了一名役使手持信件,騎驛馬疾速前行的場景,馬匹線條簡括,毫無拖沓之感。
2.運動娛樂
馬匹不僅廣泛應用于出行、郵驛,還是古代運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東臨淄齊國故城遺址出土的“楊木雙騎紋半瓦當”便記錄了春秋戰國時期,樹干兩側的人進行賽馬活動的場景。現藏于陜西博物館的唐代“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在壺腹兩面精心雕刻了兩匹奮首鼓尾、屈膝銜杯的舞馬。唐代章懷太子墓出土的《打馬球圖》(見圖2)僅寥寥數筆便勾畫出鞍馬矯健飛奔的體態,再現了球手在馬上激烈爭奪馬球的場景。唐李邕墓中的《胡人打馬球圖》壁畫雖畫面有殘缺,但中間的兩馬基本完整,均膘肥體壯,在騰空、起躍中展現出馬球運動的激烈程度。
而產生于東漢的馬戲,更在驚心動魄間展現著力與美。像元代趙雍的《馬戲圖》(見圖3)便描繪了馬戲藝人在馬上表演雜耍的情景,眾馬交錯跑動,在疾馳的奔馬上藝人或鞍里藏身,或剪腿回環,場面激烈,令人眼花繚亂,生動地再現了元代的馬戲表演。
3.狩獵出游
除了交通出行、運動娛樂,鞍馬也是狩獵活動的重要參與對象。如章懷太子墓中的《狩獵出行圖》就以俯瞰的視角對墓主人率領人馬在山道林木間的狩獵活動進行全景式的描繪,人馬裝備齊全,疏密得當,鞍馬數量雖多形態卻不雷同,形式統一卻不刻板,展現了畫者極高的鞍馬繪畫水平。五代胡瓌的《出獵圖》則以卷軸的形式描繪了胡人攜鷹打獵的情景,畫面中獵手在馬上商談,人和馬幾乎全副武裝,蓄勢待發,且馬匹“裂耳犁鼻”的特點,則是契丹人坐騎的顯著特征。胡瓌的《卓歇圖》(見圖4)還描繪了契丹貴族狩獵歸來后立帳休息的場景,在嘈雜的環境中,騎從們或牽馬休息,或整理馬鞍,人馬皆有疲憊之態,而契丹首領則飲酒觀舞。眾多人物、鞍馬各盡其態,正如湯垕所言:“畫番部人物,用狼毫制筆,疏渲駿尾,緊細有力,于穹廬什物,各盡其妙。”
元朝劉貫道在描繪皇家狩獵活動方面也毫不遜色,他的《元世祖出獵圖》(見圖5)就表現了元世祖率隨從出獵的情景,位于畫面中心的元世祖身穿白裘坐于黑馬之上,其他人物分散做圍獵狀,人馬裝備皆刻畫精細。此外,有關佛教故事的壁畫也有狩獵題材,如莫高窟第249窟穹頂上的北魏《狩獵圖》就描繪了獵人騎馬回身彎弓射虎的情景,作者對駿馬的眼、耳等細節都進行了刻畫,動感與裝飾感極強。
4.戰爭廝殺
冷兵器時代,馬作為優良兵器,與人配合起來極具殺傷力,是重要的戰爭武器。南陽新野縣武氏祠出土的《胡漢戰爭畫像》便以敘事性的手法表現了鞍馬在胡漢民族戰爭中發揮的優勢。而清代郎世寧的《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記述了乾隆帝在西域、西南多地的軍事行動,在騎兵的坐騎上能看到傳統筆墨結構與西方明暗手法的融合,鞍馬造型生動準確,毛發油亮。
此外,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也有許多描繪戰爭的場景,像第285窟南壁《五百強盜成佛圖》中官兵所騎的戰馬,是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具裝鎧馬形象。第332窟中取材于《長阿含經》的《八王爭舍利圖》則描繪了正在激戰的兩隊騎兵,其中多匹戰馬在往復奔馳,畫面具有強烈的動感。而第12窟南壁取材于《法華經》的《作戰圖》則以俯瞰的視角描繪了攻城時的情景,真實地反映了戰爭場面。
5.婚喪嫁娶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車馬儀仗圖》和《車馬游樂圖》是目前僅見的繪有鞍馬形象的漢代帛畫。其中《車馬儀仗圖》中的車馬、儀仗,是為彰顯死者的尊榮權威、助喪送葬之用。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46幅婚嫁圖中,位于第85窟的《親迎圖》畫面雖有殘缺,但仍可看到新郎在夜間騎馬、舉火前往女家迎親的場景,表現了鞍馬的迎親伴嫁之用,也符合“執燭前馬”之俗。
(二)象征性:政治外交中的鞍馬圖像
1.國家實力
作為中國古代描繪四方異邦前來朝貢的一種宮廷畫類,“職貢圖”具有“所冀圣明柔遠之德,高于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于千古”的文化功能,是彰顯國運昌盛、宣揚國威的符號以及體現政治認同的象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唐代閻立本的《職貢圖》(見圖6)便通過描繪不同國家向唐王朝進貢奇珍異寶的場景,展現當時大唐帝國“有唐貞觀萬國寧,殊方異域皆來庭”的盛況,并在畫面中以坐騎來凸顯隊伍里的高位者,可謂集政治性與藝術性于一體。而與《職貢圖》內容相近的北宋李公麟的《萬方職貢圖》,也描繪了一支熱鬧的進貢隊伍,但已無閻立本版本的紀實性。在那個積貧積弱的時代,李公麟刻意忽略了“未必諸番真入貢”的現實,將番人表現為“鄙野乞索之態”,出入乘象馬,在自我安慰式的想象里,君臣共同沉湎于崛起稱霸的幻想中。
除了朝貢隊伍,歷代描述番人貢馬主題的“貢馬圖”也是“職貢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宮廷畫家周朗的《拂朗國貢馬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便在構圖上首次呈現了異域使者向中國皇帝貢獻名馬的完整場景,并與跋文共同體現元朝的浩蕩國威。任賢佐的《三駿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也描繪了這一“天馬來朝”事件,但與周朗的《拂朗國貢馬圖》相比,除了鞍馬比牽馬者矮,還通過圉人明顯的西域特征來暗示番人貢馬的主題。還有清代郎世寧的《哈薩克貢馬圖》(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以進獻的白馬“雪團花”為中心,將不同批次的使者和貢馬組合到一起,雖有紀實畫的性質但不拘泥于完全真實的場景再現,并配以《大宛馬歌》來表達清王朝的政治意圖,不僅滿足了清朝皇帝的西域想象,還展現出清朝上承漢唐舊疆、下啟后昆新識的全新西域敘事與國家意象。
此外,軍事檢閱也是統治者展示國家國威與軍事實力的手段。清代郎世寧的《乾隆皇帝大閱圖》(見圖7)就以肖像畫的形式描繪了乾隆皇帝身騎駿馬,頭戴金盔,由騎兵開路護航,在京郊舉行閱兵時的場景,在西洋畫風里表現出了乾隆皇帝“勤兵務政”的尚武精神與國力的昌盛。
2.政績功勛
西周穆王命人創作的《穆王八駿圖》是最早宣傳統治者戰勛功績的御馬圖像,這8匹駿馬不僅是周穆王大破徐夷、巡游天下的見證,還表現了統治者的光輝形象,引得后世帝王紛紛仿效。像秦始皇就通過在陵墓中陪葬兵馬俑來彰顯自己一生橫掃六國的不世之功,那些靜立的馬俑形態準確,造型生動,氣勢恢宏,寫實性極高。而祁連山前的《躍馬》《臥馬》則是霍去病不朽功勛的見證,是對霍去病征戰匈奴的英勇形象的具象寫照,具有人物紀念碑式的藝術效果和象征意義。
唐太宗李世民為紀念給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6匹駿馬而下令雕刻的“昭陵六駿”(見圖8),不僅生動展現了馬匹或站立,或奔跑,或徐行的不同姿態,還再現了雄健駿美的馬體與剛毅堅強的神情,無愧為浮雕石刻中的佳作。明代永樂帝更是模仿唐太宗的《昭陵六駿》,為自己在征戰中戰死的八匹駿馬作《八駿圖》,并推崇“龍馬”這種龍頭馬身的神獸來為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發揮輿論力量。
3.身份地位
中國古代社會等級制度森嚴,車馬的數量、儀仗有著嚴格的等級形制,是統治階級權力地位與氣勢威儀的外在象征。例如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唐代壁畫《張議潮統軍出行圖》畫面雖人物眾多,鞍馬造型多樣,但在熱烈非凡的氛圍里,從騎兵儀仗隊伍到舞者、樂隊、后衛一切都組織有序。對于甘肅實際的掌權者張議潮更是以紅袍白馬襯托其特殊性,在這支聲勢浩大卻井然有序的隊伍里,統治階級的威嚴和權勢得到彰顯。
相較《張議潮統軍出行圖》,明朝宮廷畫家創作的《明世宗出警圖》(見圖9)不僅人馬數量更多,車馬形制也異常夸張,在以皇帝及其儀衛為主的畫面里,展現了萬歷皇帝出京謁陵的盛況。而明代宮廷畫家商喜在《宣宗出獵圖》中為了突出明宣宗朱瞻基的帝王威儀,先是用緩坡和樹木將其與隨從分開,再使朱瞻基以身騎白馬的形象出現在畫面上方的山坡上,使明宣宗的身份地位在對比中得以凸顯。
(三)隱喻性:寓意言志向的鞍馬圖像
1.自我隱喻
作為南宋遺民,龔開身具才華抱負卻不愿入元出仕,將黍離之悲寄于詩畫。他送給友人張之翰的《瘦馬圖》(見圖10)不僅描繪了一匹毛稀肌瘦、脊柱肋骨畢現于外的老驥,還自跋“一從云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經言馬肋貴細而多,凡馬僅十許肋,過此即駿足,惟千里馬多至十有五肋。假令肉中畫骨,渠能使十五肋現于外,現于外非瘦不可,因成此相,以表千里之異,居劣非所諱也。”[1] 借先朝瘦骨嶙峋、無處可歸的千里馬隱喻自己寂寞無主,潦倒失意,以千里馬自甘形瘦,暗示自己雖處境艱難卻絕不食元粟的志氣,那多節突兀的肋骨不僅是凡馬與駿馬的不同,也是龔開與仕元派的區別,是他堅定遺民氣節的寫照。
與《瘦馬圖》用意類似的還有明代遺民張穆的《七十龍媒圖》(廣州藝術博物院藏),畫面同樣對鞍馬的骨節進行了突出強調,反映了在遺民畫家這個群體中,“節”與“忠”是他們常常考量的問題。但與《瘦馬圖》以飄擺的馬尾營造秋風蕭瑟之感不同的是,《七十龍媒圖》借嚴霜后殘留的枯木塑造悲涼的氛圍。可見遺民畫家的不平之意、不能直說之言,皆借圖像中的種種元素傳達。正如余英時所言:“蓋易代之際極多可歌可泣之事,勝國遺民既不忍隱沒其實,又不敢直道其事,方中履所謂‘諱忌而不敢語,語焉而不敢詳’者,是也。物不得其平而又不能鳴,其聲迥蕩曲折,于是隱語之系統出焉。”[2]
2.懷才不遇
伯樂與千里馬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也常用來隱喻賢明統治者與良臣之間的關系。出身南宋宗室的趙孟頫不僅“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且“經明行修,聲聞涌溢,達于朝廷”。這樣的千里馬自然渴望得到伯樂的賞識,他在《人騎圖》(見圖11)中就通過人馬和諧共進的氛圍與“世有識者,許渠具眼”的題跋來暗示自己渴望如畫中駿馬那般得遇良主,能夠“被騎”,隱晦表達了自己愿為君王效勞的意愿。乾隆皇帝“神駿固難識,識矣貴善御。松雪閑作圖,正警予懷處”[3] 的題詩更是直接點明了趙氏的欲說還休之意。
但元廷政治的復雜性和趙孟頫的出身注定他只能如皇家馬廄中被安排去充當車衛儀仗的千里馬一樣,難有作為。故他筆下的駿馬雖有千里之相但大多活動于苑囿,受奚官調教,只能“老向天閑無戰功”或是“肥哉空老死”。這種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處境也讓他在《胭脂驄》(見圖12)中發出了“騏麟腰裊世常有,伯樂不生淹棧豆”[4] 的哀嘆。
可悲的是,趙孟頫這種“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的心聲,在他兒子趙雍身上也得到了體現。趙雍在《駿馬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中通過對四馬與圉人把“揩癢馬”圍在中間的描繪,將畫面中心聚焦到“揩癢馬”上,借其人才閑置的寓意,暗示了自己不被賞識的處境。
3.諷刺批判
元代任仁發雖職小勢微,在鞍馬畫上卻與趙孟頫齊名,他的《二馬圖》(見圖13)將士大夫的品行與馬的肥瘦相關聯,開肥馬喻貪官、瘦馬喻清官之先河。畫面中一肥一瘦兩匹馬前后而行,花馬膘肥肉厚,昂首踏步,瘦馬肋骨鮮明,步履沉重。自題:“予吏事之余,偶圖肥瘠二馬,肥者骨骼權奇,滎一索而立峻坂,雖有厭飫芻豆之榮,寧無羊腸踣蹶之患。瘠者皮毛剝落,吃枯草而立風霜,雖有終身擯斥之狀,而無晨馳夜秣之勞。甚矣哉,物情之不類也如此。世之士大夫,廉濫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國,不失其為廉。茍肥一己而瘠萬民,豈不貽污濫之恥歟。按圖索驥,得不愧于心乎。因題卷末,以俟識者。”[5] 以馬言志,在一貪一廉的對比中,諷刺了官場的腐敗,坦言為國為民的志向,傳達了對朝政官員的批判。
傳為北宋李公麟所繪的《明皇擊鞠圖》(見圖14)在畫面中描繪了16名賽手騎馬擊球的場景,位于中心的9人(其中還有4人女扮男裝)或控馭監閫,或俯身擊球,或躍馬持杖,姿態不一,布置不凡。但從《宮詞》《唐書·郭知運傳》等關于唐代打馬球的史料來看,唐玄宗時代的宮廷里并不存在這種女扮男裝的情況,那這一改變究竟是為何呢?通過同時期晁說之“閶闔千門萬戶開,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齡巳老韓休死,明日無復諫疏來”[6] 的題詩,再結合當時宋徽宗的荒唐事跡,可以發現李公麟不單是借畫暗示唐玄宗因沉溺于打馬球而帶來政治危機,更多的是在諷諫當時喜歡看宮女打馬球的宋徽宗,批評他耽于游樂而不問政事。
4.述懷言志
北宋李公麟的《免胄圖》(見圖15)表現的是唐代名將郭子儀談笑間以單騎退兵的歷史故事。畫面中心的郭子儀儒服免胄,四周雖兵馬環伺,卻神態從容鎮定,與回紇首領在一拜一抬間盡顯儒將風范。身后隱于云煙和旗幟中的胡兵,人馬陣容散亂無紀,與規整嚴肅的唐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場充滿緊張威嚴的對陣中,李公麟借有勇有謀的郭子儀與威風凜凜的唐軍,抒發了渴望名將驅除韃虜,重拾國威的政治愿望,做到他自己所言的“吾為畫如騷人賦詩,吟詠性情而已”[7]。同李公麟一樣借古抒懷的,還有南宋劉松年。他在《便橋見虜圖》中再現了唐太宗率“六龍千騎”與來犯的東突厥對峙,最終與對方在便橋結盟并使其退兵的歷史場景,畫面里胡騎的俯伏聽從之態與六龍千騎的“中華帝王之尊”形成了鮮明對比。劉松年更是借李世民這樣的明主,暗嘆當時南宋孝宗的懦弱無能,抒發了對時政與統治者的不滿,傳達出自身的華夏正統意識。
被譽為“瘦馬御史”的清代書畫家錢灃在《桐柏雙駿》中也以兩匹雖腹細肋突但風骨崚絕的瘦馬形象來隱喻自己不畏強權的性格、堅毅不屈的氣節以及清正廉潔的為官取向。正如他在《自題畫馬》中所言:“蹴踏邊沙歲月深,骨毛消瘦雪霜侵。嚴城一夜西風疾,猶向蒼茫傾壯心。”
二、中國古代鞍馬題材繪畫的時代特征
目前可見的,從原始到先秦時期關于鞍馬的繪畫主要是巖畫、漆畫等記錄性繪畫,像《狩獵圖》《車馬出行圖》(見圖16)中鞍馬多為交通工具,畫面主要表現馬在現實生活中的功用,其創作主要以模仿為主,并不具備鞍馬意義和審美特征。這一時期的視覺圖像遺留雖不多,卻產生了“穆王八駿”和“伯樂三馬”這兩個重要的馬畫主題。
秦漢時期,鞍馬開始作為獨立的藝術形象出現,其形象通常符合良馬的標準,表現馬運動的狀態,并且常通過對出行場面、馬匹種類、裝飾物的刻畫,來彰顯當權者的權勢地位,凸顯其威儀。誠然,偶有“馬踏飛燕”圖式里走出的鞍馬,已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和鞍馬審美特征。專題馬畫和畫馬名家在魏晉皆已出現,且得益于人物畫的發展,無論是顧愷之關于創作的“以形寫神”論,還是謝赫關于品評的六法,皆為鞍馬畫的發展提供了借鑒,使其不僅獲得了技法上的突破,也開始具有獨立欣賞價值,如《洛神賦圖》《北齊校書圖》等卷軸畫中的鞍馬,已側重于對馬的姿態、神韻的刻畫。
盛世大唐,銳意進取。鞍馬作為獨立的繪畫科目,數量空前提升,僅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中列為“神品”的九人里,留有鞍馬作品的便占一半,并且皇室貴族中也不乏畫馬高手。詩人更是帶動品評馬畫之風,畫家們前所未有地以聚焦視角深入細致地刻畫牧馬、調馬、飲馬等多種鞍馬動態,代表性的有曹霸《九馬圖》、韓幹《照夜白》(見圖17)等,這些駿馬多為御馬名駒,膘肥體壯,厚肌圓臀。除了放牧、行獵等常見場景,畫家還不厭其煩地描繪它們在出游、打馬球等生活場景中的表現,展現出大唐繁榮盛世和進取社會中鞍馬昂揚奔騰之神韻。誠然,皇親貴族和宮廷畫家筆下的禁中御馬極具“騰昆侖,歷西極”的氣概;但無法忽視的是,另一種具有平民色彩的野樸簡放風格也在韋偃的帶領下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五代繪畫中鞍馬在造型上雖仍有唐代鞍馬畫風,但受社會動蕩的影響,在題材上已由御廄里雄壯肥碩的大馬轉為安靜祥和的途中之馬。
至宋,隨著花鳥畫和山水畫成為主流,鞍馬題材的繪畫不再盛行。從北宋宮廷收藏著錄《宣和畫譜》來看,“畜獸類”中收錄的鞍馬題材畫家共11人,作品有102件,其中晉代2件,唐代100件,而五代、北宋為0。雖有北宋人物畫家李公麟善畫鞍馬,但相較于唐代已無盛況。正如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評述“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8],但與畫家及作品數量銳減相反的是,詠畫馬詩的數量顯著增加。唐代的詠馬詩有160多首,但其中僅有12首詠畫馬詩;而到了宋代,詠馬詩有近300首,其中詠畫馬詩有150多首,占據了一半的數量。[9] 可見宋代尚馬之風雖不及唐代,但宋人對馬圖的收藏和畫馬酬唱卻帶來了宋代詠畫馬詩的繁榮。金代宮廷馬畫受宋代文人馬畫的影響很大,但相較于宋代馬畫,金代尤其是后期的馬畫更加注重內心世界的描寫,并且以文學故事為繪畫題材,如宮廷畫家張瑀的《文姬歸漢圖》(見圖18),在金代末期也成為一種潮流。
元代鞍馬形象繼唐代后再度成為重要繪畫題材,而且多有創新,在鞍馬形象的刻畫上不再側重于寫實再現而是蘊含著文化內涵與共識。鞍馬成為異族統治下文人士大夫宣泄自我情緒、標榜品行氣節、隱晦表達志向追求的圖像載體。創作者通過對鞍馬主體性的突出、人馬關系的互動、空間環境的營建等,塑造出具有人格象征意味與多重文化意象的視覺形象。
明清鞍馬繪畫雖整體呈衰落之勢,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明代統治者對于馬的熱情,重新點燃了宮廷鞍馬的創作,畫家通過發展“驄馬行春”“五馬圖”等主題,賦予鞍馬繪畫新的社會政治內涵。而清代西方傳教士的介入,不僅為鞍馬繪畫帶來了技法、理念上的革新,像郎世寧的《百駿圖》(見圖19),還強化了它的政治功用和紀實功能。
三、中國古代繪畫中鞍馬形象轉變原因探析
誠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10],不同的時代土壤孕育出不同的藝術之花,因此對不同朝代鞍馬形象的改變應予以多維觀察。
在政治方面,借鞍馬彰顯國家實力,紀念政績功勛,體現身份地位,為歷代立國興邦的政治手段之一。尤其是漢唐這種起于馬背上的強悍政權,統治者往往將鞍馬看作江山穩固、社稷安危的保證,因而鞍馬成為重要的藝術表現題材是必然的。此時健碩雄武的肥馬、駿馬便成為審美風尚,鞍馬的形象既有健壯有力、威嚴霸氣的,也有步調較為舒緩,具有悠閑雍容之態的,且在配飾、鞍韉等細節上也會進行統一的刻畫,鞍馬在姿態神情中展現著盛世的風采。而在朝代更替抑或社會動蕩之際,萎靡干瘦、飽經滄桑的老馬、瘦馬、病馬以及途中之馬便占據創作主流,畫家借鞍馬傳達的也多為懷才不遇之遺恨、國破家亡之悲憤,鞍馬形象更是毫無昂揚威武之態。而且,無論是昂揚進取的盛世王朝還是腐化黑暗的末代王朝,總有才學之士要么“藏之于廟堂”,要么“流落于江湖”,而受經世致用的儒家觀念影響,許多文士棄政后不甘落寞,往往需要有情感寄托和真情表露的載體,鞍馬畫便成為他們常用的抒情言志的表達方式之一,這也是鞍馬畫能發展到明清的重要原因。
在思想文化方面,隨著杜甫、蘇軾等詩人、文人逐漸參與到馬詩、馬畫的創作與品評中,越來越多的文人士大夫投入到鞍馬畫的創作中。鞍馬題材繪畫逐漸成為文人士大夫闡述文藝觀點的一種媒介,反映理想的一種方式。這不僅使鞍馬繪畫在文化內涵上得到了豐富,也讓這個畫科有了長久存在的文化依據。尤其在文人掌握話語權的宋朝,理學的出現直接將唐人建功立業的外在追求內化為性情上的涵養,鞍馬風格也相應地由磅礴霸氣轉為靜雅內斂;同時,在“格物致知”思想的影響下,畫家們在創作中強調秩序與極致,更多地關注馬在精神、個性等方面的內涵,使鞍馬繪畫在形制材料與風格技法方面的表現形式都發生了改變。
在繪畫方面,畫家基于不同目的創作出形式豐富、滿足不同階層審美需求的鞍馬圖像作品,像寶馬英雄、伏櫪老驥等鞍馬形象都是畫家樂于表現的繪畫內容。并且得益于人物畫等畫科的發展,鞍馬繪畫在技法、審美的表現上都得到調整,獨立成科后又能反哺其他畫科。但隨著軍政的分離,文治時代的到來,與俗世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鞍馬題材,逐漸不能滿足文人畫家的審美取向與理想追求。因此宋及以后的畫家開始轉變表達方式,大多選擇山水這種不易落“俗”又不違背文人隱逸思想的題材,畫馬名家急劇減少,鞍馬畫也開始逐漸走向衰落。
此外,在胡化傾向嚴重或為異族建立的王朝,像李唐皇室、元朝皇室和清朝皇室。受草原游牧生活習俗的影響,上層階級對馬的感情更深厚,與馬的聯系也更密切,相應地,鞍馬畫、鞍馬畫家也隨之出現。像唐代便出現大量專職鞍馬畫家,元代在山水畫昌盛的情況下也有鞍馬畫的生存空間,清代宮廷畫家對鞍馬畫也有專門的投入,而這背后都離不開皇室的支持。
結 語
縱觀中國古代繪畫中的鞍馬形象,從御馬名駒、高貴種馬到嶙峋瘦馬和伏櫪老驥,鞍馬畫在功能和內涵方面逐漸呈現出多樣性和寬容性。這些不同的鞍馬形象有著不同的圖像意涵,折射出不同時代的社會觀念、藝術理念及審美趣味。從威風凜凜的朝堂貢馬到瘦骨嶙峋的伏櫪老驥,從傲骨錚錚的戰馬到肥哉老死的立仗馬,繪畫表現的對象不斷寬容,這既是社會形態的變化結果,也是創作者命運境遇的折射,特別是文人士大夫階層,他們將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抑郁苦悶,以及社會形態、自身遭遇、世俗情感等問題,用鞍馬畫的方式,象征性、圖像化地隱晦表達出來。盡管不同時代審美不同,但中國古代對鞍馬繪畫的評判標準基本源于上層社會,鞍馬題材繪畫的附屬、服務與消費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
(作者單位:吉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注釋:
[1] 楊鐮:《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
[2]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展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5頁。
[3] 陳云琴:《松雪齋主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頁。
[4] 〔元〕趙孟頫:《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
[5] 張瑞生:《私家藏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頁。
[6]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99頁。
[7]《宣和畫譜》,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頁。
[8]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7頁。
[9] 俞露:《宋代詠畫馬詩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
[10] 〔南朝梁〕劉勰:《增訂文心雕龍校注》,黃叔琳等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5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