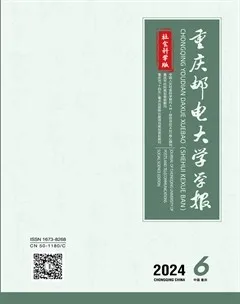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子商務知識產權制度變革與創新研究(20VHJ013)
作者簡介:黃薇君,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與數字法學研究,E-mail:huangwj@cqupt.edu.cn。
摘 要: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一代技術的勃興,算法逐步成為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的新型手段,且主要呈現為算法檢測機制和算法通知機制,二者基于同一技術原理,屬“同一事物的兩個面”。算法技術的異化和濫用都有可能導致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倫理風險,從算法技術本體來說,建立模型、數據輸入以及輸出結果三個階段皆存在一定隱患;從算法應用主體來說,成本考量、侵權責任規避以及利益誘導都會成為主體濫用算法的因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應有舉措。以技術倫理學“內在主義研究進路+外在主義研究進路”為邏輯思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結合,可被提煉為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整體的宏觀切入點,以及算法“科技向善”、禁止知識產權濫用、電商平臺自治權三個微觀切入點,同時對應法治、文明與公正、誠信、自由及民主價值觀。遵循“技術本身技術應用”理念,進一步針對算法程序設計的三個階段,建議將其納入公共利益考量、建立信息共享機制、設立算法“反通知”程序,同時在算法運用限度上,目前應堅持算法過濾的非義務屬性和完善惡意通知的治理措施。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
中圖分類號:D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4)06-0065-12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一代技術的勃興,算法逐步成為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的新型方式,但同時,算法技術內生性及應用性的內外部問題導致其存在的價值危機日益凸顯。因此,如何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才能消解算法治理帶來的價值隱患,如何融入才能在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中實現技術手段與技術目的相統一,直接影響著我國數字法治建設與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雙重成效,亟待法學界進一步探討。
一、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技術透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最開端的問題,是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的場域。換言之,算法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中怎樣得以應用,是本研究的起點。
(一)算法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中的應用類型
用于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的算法系一種內容過濾技術,主要通過語義識別、圖像處理、深度學習等技術對品牌圖片、商品樣本、圖書文字等知識產權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從而挖掘相關特征并建立索引數據庫,然后算法模型根據平臺中檢索內容與數據庫的比對結果自動做出相應反應。
傳統電商平臺知識產權治理規則包括主動審查和被動審查兩種方式,即“紅旗規則”與“通知規則”。內容過濾技術的加持使得二者操作流程發生巨大轉變——人工審查模式被算法自動化決策模式替代,進而演變為“算法檢測”和“算法通知”機制。兩種機制基于同種技術原理,本身就是“同一事物的兩個面”,處于同一流程中(見圖1)。
圖1 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技術流程示意圖
1.算法檢測機制
為避免內容過濾技術與內容過濾機制的混淆,特此將算法主動進行內容過濾的治理模式稱為“算法檢測機制”。算法檢測是一種事前的、自動的、全局的排查模式,電商平臺將平臺內經營者上傳的所有信息與索引數據庫進行匹配,若滿足特定條件,即自動采取禁止上傳、下架商品、屏蔽鏈接等措施;若匹配結果存疑,則將該情況轉送至知識產權人判斷;若匹配度低,則正常上架且展示于店鋪頁面。如阿里巴巴打造的主動防控“鵲橋”項目,即由智能算法模型將主動識別的疑似侵權樣本推送給權利人二次校驗,校驗結果不僅即刻被納入算法模型調整的參數當中,而且同步支持權利人實施一鍵移除的操作。
2.算法通知機制
算法通知流程表現為“查找侵權行為算法化——發送侵權通知算法化——處置侵權信息算法化”三個階段[1],知識產權人或知識產權人委托專業代理公司通過自動監測系統查找侵權商品,并由系統自動向電商平臺發出侵權通知,電商平臺端在收到通知后也將由算法自動進行相應處置。算法通知首先嶄露頭角的仍在版權領域[2],谷歌的《透明度報告》(Google Transparency Report)顯示,2020年谷歌共收到有關版權侵權的投訴多達65億條[3]。在這些海量通知中,正是因為對侵權行為的搜索自動化,版權人才從人工審查中抽離出來,轉而選擇第三方機構。例如中國版權協會版權監測中心(以下簡稱“12426版權監測中心”)可以“針對版權方委托作品,在指定范圍內進行7*24小時版權監測”,然后“向侵權平臺發送下線告知函”[4]。
(二)算法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中的應用范圍
受制于算法的數理結構,數據成為算法治理中的必要元素,這也引發了學者們對算法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中作用限度的思考。首先,電商平臺領域中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涉及作品、商標、專利等多重客體,算法過濾技術似乎在可用數據表達的文字、圖片、語音等文件格式中存在更大的適用空間,同時數據匹配的技術邏輯使得對知識產權侵權的判斷標準呈現為目標數據對索引數據庫的覆蓋程度,因此極有可能因目標數據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算法比對結果。其次,知識產權侵權識別本身極富專業性,就算是作為人類的電商平臺經營者,對于混淆性商標侵權或專利侵權等行為都很難識別[5],又如何要求輔助人類的算法系統可以準確判斷呢?這也是目前內容過濾技術適用最多的場合仍是版權領域的重要原因。最后,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是,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與網絡版權算法治理差別較大,無論是電商平臺還是知識產權人掌握的信息皆與實際線下產品之間存在一定距離,因此,電商平臺(算法過濾)對知識產權的審查范圍應是作為信息存在的商標、作品數字件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圖片等[6]。
本文認同上述觀點,且無意夸大算法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侵權治理中的功效,但同時也認為法律制度對此的安排可以為算法的適用范圍保留一定余地。首先,隨著深度學習在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等領域中的成功運用,算法能夠進行深層次的數據挖掘并提取最關鍵的普遍規律,從而發現和總結人類都無法感知到的隱性知識。也就是說,知識產權侵權判定對人而言雖存在技術難度,但這恰恰為基于統計分析的算法提供了機會,這也難怪有學者覺得一個經驗豐富的法官可能并不如算法做出的判決更加公平及準確[7]。其次,隨著文本匹配、圖像識別圖像識別技術可以實現“即使物體位置、角度、距離等發生變化,仍可有效識別處理,確保最終判斷結果的正確”,這意味著,在這種技術輔助下,完全有可能通過算法識別網站中的商品圖片,判斷該商品是否侵犯了專利權(至少外觀設計專利)。(參見趙佩佩:《計算機智能化圖像識別技術研究綜述》,《電腦知識與技術》2023年第21期,第109頁)等技術的逐漸成熟,算法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保護中呈不斷擴展的趨勢;阿里巴巴就表示“治理場景覆蓋假貨、一般商標侵權、盜圖等多種侵權行為”,同時還發布了圖書版權保護計劃[8]。最后,法律制度的體系化意味著,版權、商標權及專利權各自領域內的專門立法可以根據各自權利內容調整相應條款,但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為行文簡潔,以下涉及我國法律文本名稱時,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省略。、《民法典》《網絡安全法》等基本法中,不宜對不同類型知識產權做出具體區分。本文出于“知識產權”這一綜合及整體視角,更為聚焦算法在電商平臺過濾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中的共性特征。
二、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風險識別
算法倫理審查的基本進路,遵循的是從危害后果中倒推倫理缺失的邏輯思路,通過對算法引發的現實后果進行類型化處理,從而將其抽象為某種算法權益[9],故識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倫理風險是推導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點的先行步驟。
(一)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倫理風險樣態
根據目前技術倫理學既有的主要研究進路,對算法治理的倫理分析可分為外在主義和內在主義兩種研究進路。前者是一種傳統的研究進路,主張對技術的應用進行倫理反思[10];后者則認為技術倫理的評判應該提前到技術的設計階段[11],是近年來興起的一種研究進路。據此,算法治理的倫理風險也存在于技術應用及技術本身兩個層面。
算法兼具“科學技術”與“賦能手段”的“波粒二重性”[12],其技術風險與運用風險也因“算法+應用場景”模式的構造而呈現出具體的風險樣態,這表現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活動中,則是算法對知識產權侵權判定的偏差結果以及算法通知的惡意使用。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算法系統都會對平臺內經營者造成嚴重且不可挽回的損失,尤其是在“雙十一”大促銷這樣的高峰期里,其影響更是惡劣,甚至還有可能成為電商平臺或知識產權人打擊競爭對手及擾亂市場競爭的最佳武器。這絕非杞人憂天,一篇實證論文就指出,“在收集的全部案例中,惡意投訴類案件共有16例,其所占比例達到31.3%”[13],真正進入訴訟階段的案例尚且如此,那么電商平臺惡意通知的所占比例可能會更高。當然,該數據并不能說明算法在惡意通知中的作用,但伴隨算法通知數量的暴增,算法惡意通知的發生也會更加頻繁。
(二)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倫理風險成因
同樣的,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活動中,“風險來源兼具人源性與物源性特征”[14]105-117,算法技術和算法運用生成的風險也能回溯到兩者來尋找相應的成因。
1.算法技術本體原因
一是建立模型階段。算法的效率主導已然決定了算法存在公平價值缺位的危險。算法著眼于所處理數據之間的相關關系,而非因果關系[15],反映在追求效率的電子商務場域,就是:通過數據分析、趨勢預測等獲得經濟利益成為衡量算法水平的最核心標準。正因如此,算法模型的設計環節往往不會被納入公共利益考量。一方面,以合理使用為首的公眾使用蘊含著強烈的倫理基礎和價值理性[16],但算法并不理解倫理價值的意義和內涵,無法體現對公眾利益的重視;另一方面,算法作為一種運算規則,擅長的是數據統計,屬定量或概率分析性質,而合理使用情形具備多元化特點,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就曾將其描述為“整個版權法中最復雜的條款”參見Dellar v. Samuel Goldwyn,104 F.2d 661,662(2d Cir.1939)。。
二是數據輸入階段。數據是訓練算法的必要元素,然而正如“GIGO”定律即“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是計算機領域常用的概念,表示數據的干凈整潔狀態將會直接影響程序運行的結果。所言,如果訓練輸入的數據有所偏差,那么導出的結果也會不盡如人意。從主觀角度出發,知識產權人及其代理人希望盡可能擴大自己的知識產權范圍,有可能將其沒有權利的對象納入算法系統的索引數據庫中,使得電商平臺進行知識產權治理必需的侵權比對母本存在嚴重錯誤。2019年,“視覺中國”將人類歷史上第一張黑洞照片“占為己有”的新聞引得國內一片嘩然,后來被扒出國旗、國徽也未能幸免,令該網站深陷負面輿論。從客觀角度出發,知識產權制度無法實現對數據的全面刻畫。首先,并非所有知識產權都能以數據方式展現。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實質為一種技術方案,而“本身通過文字描述技術方案和權利要求就存在模糊性”[17]。其次,知識產權侵權的判斷標準難以被完全量化。例如,如何理解“相關公眾”對商標侵權判斷至關重要,但在目前尚未明晰其理論依據和考量因素的前提下,難以對其制定清楚明確的指標數據。
三是輸出結果階段。“所有信息與內容雜糅進既定的算法之中得出相應結果,結果也在系統內瞬間完成”[18],換言之,算法自動化決策的對象對決策結果沒有質疑或反對的機會。具象于電商領域,這體現為“反通知”程序的缺失。
《電子商務法》第43條規定了“反通知”程序,即電商平臺在收到知識產權人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后,應給予平臺內經營者抗辯的機會。但隨著算法技術的大量使用,這一救濟程序因為“信息不對等”[19]及“處理成本的嚴重不對稱”[20]而失效,使被投訴人的申訴權利無法得到實現。
2.算法運用主體原因
首先,算法成本是使用者在運用算法技術時最優先考量的因素,這一點對于電商平臺而言兩極分化較為嚴重。電商平臺開發或購買算法系統雖然會增加成本,但可以產生規模經濟的效果,因此,以阿里巴巴、京東等為首的頭部平臺企業不遺余力地投入到科技創新活動中。殘酷的是,并非所有的電商平臺都具備這樣的財力與實力,無論是尋求著名軟件的使用許可還是自主研發,都將面臨著資金不足的窘迫現實,無奈之下,他們更加青睞于價格較低的算法系統,也不得不接受隨之附帶的低準確率弊端。
其次,承擔侵權責任的法律風險是電商平臺選擇較為嚴苛的算法治理系統的主要原因。“通知刪除”規則從免責要件到侵權要件的衍變,迫使電商平臺更加重視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相較于資本更加雄厚、法律資源更加堅實、知識產權信息掌握更多的知識產權人而言,平臺內經營者處于弱勢地位。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人在確認電商平臺刪除侵權鏈接后,普遍選擇放棄對電商平臺的訴訟請求[21],讓電商平臺具有了采取更為嚴格的算法系統以保護知識產權的極大動力。
最后,利益的誘導促使知識產權人采用更為嚴格的算法系統,甚至誘發錯誤通知等商業誹謗行為[22]。知識產權是一種具有壟斷性的私權,從中獲利或排除競爭都是知識產權人的自然心理。因此,站在自身立場,知識產權人在利用算法系統發現侵權行為時,也更加傾向于“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個”的極端心理。比如,前述提到的實證論文中就顯示,“在16個個人投訴者中,有15人與被投訴者存在競爭關系,占93.8%”[14]110。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切入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一種法律原則,尚不具有可操作性。對此,需要先搭建“軟法”規范文本與治理實踐之間的橋梁[23],找到合適清晰的切入點,然后才能進一步構建最終的具體實現路徑。
(一)法治價值觀對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引領
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作為一個整體,其總體指導思想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法治價值觀”。
1.法治與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關系
算法作為一系列指令符號,并不能理解執行后的目標價值,更談不上它具有追求某個實施目標的自主性,而法律的規范邏輯恰恰是對主體行為的規制,因此,具有強烈價值評判的法律介入算法似乎有了難以逾越的障礙。但揭開算法的技術面紗,通過前述三個階段風險成因的分析來看,算法過濾系統在建模及數據輸入階段從來就沒有脫離人的參與,即便是自動化決策階段,也反而是因為缺少人的反饋才導致風險的發生,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才始終是法律規制的對象。
基于此,“型構算法與法律有機統一的法治系統”[24],不能是應對技術不能的后果救濟,而需提前到設計之初并運用于系統的整個流程,包括運用于算法開發者、算法管理者(電商平臺或第三方機構)、算法運用者(電商平臺、第三方機構或知識產權人)等多重主體;同時,算法在網絡世界中的治理作用也迫使法律算法化,“需要確立的原則是‘法律先于技術’‘法律融入技術’‘法律歸化技術’”[25],充分發揮算法對法治建設的賦能作用。
2.法治價值觀重塑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法治價值觀具有雙重含義,一是法治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元素之一,二是法治場域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的受體。一方面,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應體現中國式現代化法治的本質要求。法治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就已然說明中國法治具有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包含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現代意蘊,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也應“彰顯人本主義”[26]。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專門提出“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網絡信息服務、網絡安全保護、網絡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等要求,故而與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實施都成為工作重點。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算法“科技向善”
以“四善端”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認為這是“仁義禮智”四德的源頭,是人之為人的根據。為代表的儒家價值觀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歷史基礎,使得“科技向善”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同一指向。
1.“技術中立”向“科技向善”的觀念轉變
針對“技術中立”的含義,目前大多研究存在三種理解:功能中立、責任中立及價值中立。“功能中立指的是技術在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過程中遵循了自身的功能機制和原理”[27],當其場景化于網絡時,即為聞名的網絡中立(net neutrality)理念。如果說功能中立對立法產生了主導作用,那司法實踐則與責任中立的概念密切相關。責任中立是將技術本身與技術實踐分割開來,最初因環球城市制片公司訴索尼公司案中的“實質性非侵權用途”(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規則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42 (1984)。而確立。
上述兩個角度事實上都蘊含著價值中立的內里,按照這一學說,技術“本身只有‘工具性’而沒有‘目的性’”[28]。但是,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勃興,“技術價值中立”的言論受到愈來愈多的批判。算法兼具技術屬性與社會屬性,其具有的決策機制使之成為構建社會秩序的新方式,加之深度學習技術愈加成熟,算法很難再被認定為具有“價值中立性”。
在此背景下,倫理學轉向對技術問題的關注推動了科技倫理的理論發展,“科技向善”逐漸成為包含算法在內的科技活動應秉持的價值追求。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將“科技向善”寫入指導思想,彰顯了中國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立場和態度。
2.文明及公正價值觀與算法“科技向善”的契合
“科技向善”最為首當其沖的意義應是“幫助人類變得更強大、更幸福,擁有更好的未來和數字文明”[29]。就目標而言,算法的廣泛使用應落腳于服務人類,使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最為先進和便利的科技生活;就方式而言,“人機互動”或“有選擇性”的使用[30]回歸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將算法置于作出決策的輔助性工具地位,為人類的內在價值留出應有之地。
同時,“科技向善”的基準還包括“以信息分享/控制為核心的數字正義”[31],正義直接指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公正”一詞。2021年9月,北京互聯網法院發布了《數字正義視閾下的互聯網司法白皮書》,其中強調“數字正義是人類發展到數字社會對公平正義更高水平需求的體現”,凸顯出“數字正義”與傳統正義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的技術性和時代性。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禁止知識產權濫用
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明確提出“完善規制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法律制度”,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法律中的具體落實。
1.知識產權濫用的判斷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6號)第3條第1款規定:“對于民法典第132條所稱的濫用民事權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行使的對象、目的、時間、方式、造成當事人之間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認定。”同時,在被稱為“《電子商務法》實施后的惡意投訴第一案”(以下簡稱“惡意投訴案”)中,法院也根據“主觀上存在明顯過錯,系惡意”“客觀行為不具有正當性”的雙重判斷標準得出“被告行為屬惡意投訴”的結論參見杭州鐵路運輸法院(2018)浙8601民初868號民事判決書。。可以看出,識別知識產權濫用,應結合主觀及客觀要求進行考察,主觀上知識產權人須有過錯,且這種過錯應是一種惡意,表現為行為人明知相應的行為缺乏法律依據仍故意為之;客觀上知識產權人行使權利的行為缺乏合理性,并導致了損害的產生。
2.誠信價值觀是禁止知識產權濫用的基礎
誠實守信作為民法中的“帝王原則”,適用于任何民事行為,知識產權的行使自然也不例外。實質上,誠信原則就是禁止知識產權濫用的理論基礎。誠信是從正面對知識產權的正當行使作出了要求,禁止知識產權濫用則是從反面對知識產權的不正當行使予以否認。
誠信原則與禁止知識產權濫用的結合在知識產權立法及司法中皆有體現。最為清晰的表述是2020年修訂的《專利法》第20條第1款的明確規定:“申請專利和行使專利權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濫用專利權損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2019年修訂的《商標法》雖未在條文中體現二者的緊密關系,但第7條明示了“申請注冊和使用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司法實踐中,仍以前述“惡意投訴案”為例,法院最后總結為“江某的惡意投訴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契合《電子商務法》第42條第3款規定。
(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電商平臺自治權
隨著近年來超級平臺2021年10月29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互聯網平臺分類分級指南(征求意見稿)》,該指南按照用戶規模等將互聯網平臺劃分為超級平臺、大型平臺和中小平臺三級。的迅速崛起,電商平臺亦呈現出“從純粹提供技術服務的中介地位向實際的平臺生態控制者地位轉型的趨勢”[32],這種控制在技術的加持下產生異化,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將電商平臺自治權歸正返本的根本遵循。
1.電商平臺自治權的來源及異化
首先,電商平臺獲得自治權最根本的原因是技術賦能[33]。其一,電商平臺具有決定經營者能否進入該平臺的“生死大權”,這種“守門人”的身份直接體現出電商平臺對于網絡用戶的支配權;其二,基于數據是關鍵生產要素以及平臺是數據主要提供者的現實背景,電商平臺在本質上控制了數據的生產機制;其三,依托“冪律法則”與“增量式賦權機制”[34],電商平臺持續擴大規模及賦能,最終具備了巨大的市場影響力及社會公共性。
其次,法律為“公權力私權力近年來,不斷有學者提出網絡平臺具有“私權力”這一觀點,強調平臺雖是“私主體”,但對平臺內的用戶及其行為具有事實上的支配力和影響力,這種單方管理權屬于典型的“私權力”。(參見劉權:《網絡平臺的公共性及其實現——以電商平臺的法律規制為視角》,《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45-46頁;周輝:《變革與選擇:私權力視角下的網絡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頁)私權利”的治理架構提供了規范基礎。從憲法層面來說,電商平臺“享有蘊含于憲法所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之中的營業自由”[35]。即使電商平臺在當下被逐步打上公共性質的烙印,但它屬于市場主體的本質卻不可否認。《電子商務法》第32條賦予電商平臺“制定平臺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的權力,同時其第41條要求電商平臺“應當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
最后,網絡用戶與電商平臺的契約也使電商平臺對網絡用戶行為的管理具備了合法性。如在美團App中進行搜索,可發現“美團用戶服務協議”“大眾點評用戶服務協議”“美團企業版服務協議”等多項用戶協議;若需入駐外賣平臺,用戶亦須隨之簽署“美團外賣開店說明”等專款協議。上述協議依具體情形給予了電商平臺對網絡用戶個人信息的收集及利用、對網絡用戶賬號(包括錢袋寶賬戶)直接采取措施、向網絡用戶提供廣告促銷服務等權力。
正因如此,電商平臺具備了“準立法權”“準司法權”“準執法權”[36],但電商平臺獲得權力的來源也正是權力異化的起點。加之網絡平臺逐漸被理解為基礎設施公司(infrastructural firms)[37],電商平臺與網絡用戶之間的契約也很難再被定義為一種“平等的關系”;面對電商平臺千篇一律、冗長繁瑣的格式合同,即使網絡用戶能夠全面理解合同條款,也只有“接受”和“退出”兩個選擇。
2.自由及民主價值觀對電商平臺自治權的歸正
電商平臺具有的“私權力”屬性意味著,電商平臺作為市場活動主體,具有自我規制的自由意志,但這種自由還應受到民主價值觀的約束。一方面,電商平臺為獲得更多消費者的認可,平臺內“正品”“真貨”的訴求也將倒逼電商平臺對自身加以管制。因而,“保證平臺自治的空間、賦予平臺所需的權限”[38]成為電商平臺自由價值觀嵌入的節點。同時,電商平臺的自我管理還需借用“元規制”(meta-regulation)理論,其核心含義為“對自我規制的規制”(regulate self-regulation),即“外部規制主體有意地引導規制受體制定自己內部的規則以應對公共問題”[39]。也就是說,電商平臺應當發揮法務部門的監督作用,甚至可以設置獨立的監察機構,對平臺制定規則、數據收集、算法設計等活動過程進行內部審查,以及定期完成數據審計、算法審計等工作。當然,保障電商平臺自主決策也意味著法律應對算法這一新科技具有包容度,不因科技本身難以規避的風險而苛責電商平臺承擔責任。
另一方面,電商平臺“私權力”的制衡還需民主價值觀的破解,強調“算法應用的公共性價值”[40]。公眾參與條件方面,電商平臺應提高自身治理的透明度,將包括平臺規則、服務協議、算法治理模式、糾紛解決程序、裁決結果等在內的情況公之于眾,接受公眾監督并為公眾提供以質疑、投票、建議等多種形式進行參與的渠道;參與程序方面,則應保障公眾參與的便利端口及多元方式,禁止以任何差別待遇、“二選一”機制、材料提交高標準等阻礙網絡用戶或其他相關主體行使參與權。
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具體實現
法治價值觀作為總體要求,是完善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最終歸宿。具體對策應依托第三部分的三個微觀切入點來提出,即秉承“內在主義研究進路+外在主義研究進路”的技術倫理學兩種研究進路和本文貫穿始終的“技術本身技術應用”理念,同時兼顧算法程序的整體流程,以算法程序設計在先、應用在后的順序分別提出具體建議。
(一)針對算法程序的設計
算法技術本身的倫理缺失潛伏在算法設計的三個階段,結合前述回應算法技術的“文明”和“公正”價值觀,以及限制算法技術與應用疊加后平臺私權力的“民主”價值觀,以下將依照“建立模型數據輸入結果輸出”的流程線進行具體闡述。
1.建模中納入公共利益考量
公共利益考量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典型體現是合理使用制度,而“技術無法創設法律”“創造性選擇和實踐的變化”以及“技術的不足”使學者質疑將合理使用嵌入算法設計的可行性[41]。但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的不斷提高,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相信“合理使用的未來也是算法”[42]。正如丹·伯克(Dan Burk)所述,合理使用情形并非一定要預設明確清晰的描述性代碼作為比對參數,還可以通過司法案例中積累的以往數據推導出特定的司法決策模式,在后期的數據對比中進行相應特征匹配[43]。
需注意的是,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對公共利益的考量不僅包括版權合理使用,還應涵蓋商標及專利領域;除了上述提到的通過司法實踐總結特征進行建模的方式之外,亦可利用圖像識別、文本匹配等技術針對典型樣態嘗試用代碼進行標記。當然,這只是提出了一種技術運用方向,如何具體實現還需依托技術研究成果,故對于算法設計者的要求只限于其是否在設計中納入了公共利益考量,至于這種“納入”設計的質量如何,并不是導致其承擔法律責任的必要因素[44]。
2.數據收集中建立信息共享機制
一是電商平臺與知識產權人合作互助。除非上升到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領域,公民的民事權利都只能由權利人本人行使[45],加之知識產權人最了解自己的知識產權狀態,故無論是事前將知識產權權屬情況告知電商平臺,還是事后電商平臺尋求知識產權侵權確認,知識產權人都應該積極配合電商平臺,甚至應該成為請求權利保護的主導者,即使在算法治理情形下,這一點也無區別。二是電商平臺向消費者及時公示信息。消費者不僅是假冒偽劣商品的直接受害人,也是電商平臺的基礎用戶,因此,消費者作為電商平臺知識產權治理的參與者,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方面,向消費者共享信息能幫助他們“非常便捷地熟悉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的類型或習性”[46],一定程度上緩解買家和賣家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另一方面,消費者對平臺知識產權治理過程及結果的知悉,也能反向成為社會公眾監督算法治理的強大力量。消費者參與共治在電商平臺不斷實驗中已得到顯著發展,例如淘寶“眾議院”制度、在糾紛處理程序中的大眾評審機制,以及阿里巴巴將“打假無疆”系統與“公益3小時”平臺打通[47],無疑能為未來行業標準及立法規制提供寶貴借鑒。
3.結果輸出后設立算法“反通知”程序
算法檢測應以有效、便捷的糾錯機制作為目標,以最大程度遏制過濾錯誤的產生。例如在屏蔽、下架、未正常展示商家及其商品或服務信息時,自動彈出帶有“商家已獲授權”“商家上傳的內容構成合理使用”等選項的彈窗,商家點擊選項即可提交對錯誤過濾的異議[48];在算法通知中,當電商平臺收到知識產權人的投訴后,仍需將此信息轉送給被投訴人,并設計方便、清晰、定點的“反通知”界面,使平臺內經營者能快速定位被投訴的商品或服務,且可直接提出針對性申辯。
其實,“反通知”程序并非只能作為一種對抗方式出現,知識產權人還能借此通過電商平臺尋找到潛在的合作對象。例如,通過油管(YouTube)的內容身份(content ID)模式,一些店鋪經過多年經營,已收獲一大批穩定客戶,面臨知識產權侵權投訴有可能關閉店鋪時,若能在轉通知給知識產權人時提供“知識產權許可談判”等選項,給予雙方達成知識產權許可協議的機會,則不僅能讓知識產權人以持續獲得未來許可費用的方式替代一次性的、低數目的侵權賠償,而且能讓平臺內經營者繼續經營自己的店鋪。
(二)針對算法程序的運用
算法程序運用包含兩個層面——是否運用與如何運用,即知識產權算法治理能否義務化及如何正確使用算法的問題。對于前者,應以平臺私權力的“自由”價值觀來源作為基準;對于后者,則應以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誠信”價值觀作為引導。
1.算法過濾的非義務性
首先,電商平臺作為市場活動主體,理應具有自我管理的自由。《電子商務法》第41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但如何建立卻未見詳細說明,這就為電商平臺自治留下了空間。其實,如果法律責令所有電商平臺都必須采納算法治理模式,反而會對電子商務行業產生巨大障礙。無論是開發、維護還是升級算法過濾軟件,都將是一筆不菲的費用,頭部電商一般都擁有與之相匹配的雄厚財力,但那些初創公司卻無力承擔。如此,法律無疑為可能與當今巨頭企業競爭甚至取代這些巨頭企業的新服務企業創造了進入市場的壁壘,從而成為穩固電商巨頭們地位的“幫兇”[49]。
其次,電商平臺用戶的言論自由也應受到足夠重視。電商平臺雖不像內容平臺或社交平臺一樣以發表用戶創作及言論為主要活動,但基于商業言論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50],且用戶(包括平臺內經營者及消費者)從事的展示商品信息、交流買賣事宜、分享購物體驗等也難以與用戶言論相分離,因而電商平臺對網站上的所有信息進行篩查難免會有監視用戶的嫌疑。
實際上,即使“歐盟新法《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指令》第17條間接引入了內容過濾義務……也將版權的主動審查義務限制在在線內容分享服務提供者這一特殊類別之內”[51],我國也確實不需要拔高電子商務領域知識產權侵權治理標準,以免阻礙電商產業的創新發展[52]。
2.惡意通知的治理措施
惡意通知的治理措施可分解至“事前事中事后”三個階段。一是對算法通知的啟動應適當提高合格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規定,向電商平臺發送的通知一般包括知識產權權利證明及權利人的真實身份信息、能夠實現準確定位的被訴侵權商品或者服務信息、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通知真實性的書面保證。其中,知識產權人的真實身份信息應隨時保持更新,包括知識產權人委托進行知識產權侵權過濾或識別的機構,以便電商平臺在收到自動通知時能將聯系人的準確信息導向被投訴人;同時,還可增加“善意相信聲明”“準確性和授權聲明”等主觀要件[53],即在與電商平臺達成知識產權保護合作時,可先行簽署上述文件以承諾未來履行誠信通知義務,也可在發送通知時要求必須隨附簽名的上述聲明,否則投訴系統將自動判定該通知不符合標準。
二是投訴過程中允許被投訴人提供擔保以替代必要措施的實施。《指導意見》第9條規定了平臺內經營者的反向行為保全制度,但這項申請必須向人民法院提出,受到舉證責任和法院審判時間的限制,“實難滿足申請人獲得救濟的及時性要求”[54]。相比之下,《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中規定僅向電商平臺提出的擔保制度更具靈活性和便利性,不過,如何設定擔保具體條件、擔保金額如何計算、“暫時中止”如何限定時間等內容還需法律文件、司法實踐或行業標準的細化。
三是投訴結果應被直接納入電商平臺的誠信記錄。頭部電商企業的做法或許可以為此提供一些思路,比如:京東制定的“知產維權投訴人賬戶分類處理規則”即是按照投訴人賬戶的誠信度分類,對提交的投訴采取不同速度的處理流程;“阿里巴巴誠信投訴機制”也是阿里巴巴根據歷史投訴的相應數據指標(包括投訴成功率、賣家申訴成功率以及投訴量),將誠信賬號納入誠信投訴機制以提升維權效率。據此,電商行業可以逐步推廣“黑白名單”模式。一方面,電商平臺根據前期掌握的數據,對平臺內用戶進行信用定級,將平臺內用戶(包括知識產權人、知識產權人委托的代理人以及平臺內經營者)發出的通知或反通知依據用戶信用度分層處理;另一方面,電商平臺可“設置不同梯度的失信標簽”[55],以商業聲譽倒逼投訴人的誠信行為。
五、結 語
在算法治理崛起的背景下,法治、德治與“技術之治”構成了新型治理框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應有舉措。電商平臺知識產權算法治理的法治建設應具有全局性、綜合性和多元性,為此,我們應從自算法設計到算法應用的全局視角,拓展“以綜合治理為特點的融合性法治”[56],不僅要對法律制度進行優化,同時要為算法科技的發展保留一定謙抑性,并結合硬法突出的責任制和軟法著重的標準制,以多元保護手段實現算法治理在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中的最大功效。
參考文獻:
[1] 焦和平.算法私人執法對版權公共領域的侵蝕及其應對[J].法商研究,2023(1):187-200.
[2] 張吉豫.智能社會法律的算法實施及其規制的法理基礎——以著作權領域在線內容分享平臺的自動侵權檢測為例[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6):81-98.
[3] 以版權問題為由提出的內容要求——Google透明度報告[R/OL].(2020-12-16)[2024-01-29].https://transparency-report.google.com/copyright/overview.
[4] 12426版權檢測中心官網[EB/OL].[2024-07-08].http://www.12426.cn//m/survey.html.
[5] 蘇冬冬.論《電子商務法》中的“通知與移除”規則[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149-159.
[6] 王遷.論“通知與移除”規則對專利領域的適用性——兼評《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63條第2款[J].知識產權,2016(3):20-32.
[7] SUNSTEIN C R.Governing by algorithm?No noise and (potentially) less bias[J].Duke Law Journal,2022(6):1175-1206.
[8] 2022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年度報告[R/OL].(2023-04-26)[2024-02-03].https://files.alicdn.com/tpsservice/5940733116dc7fd7fadcf72754e4ba1f.pdf?spm=hello-am.home.0.0.72ca7e92mIcGX3amp;file=5940733116dc7fd7fadcf72754e4ba1f.pdf.
[9] 李林.智能算法倫理審查進路的完善策略[J].學術交流,2023(4):74-86.
[10]蘭立山.算法治理的技術哲學反思[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3(4):87-94.
[11]POEL I,VERBEEK P P.Ethics and engineering design,science[J].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006(3):223-236.
[12]林洹民.自動決策算法的風險識別與區分規制[J].比較法研究,2022(2):188-200.
[13]孔祥俊,畢文軒.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惡意投訴的規制困境及其化解——以20182020年已決案例為樣本的分析[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107-118.
[14]賀溦,張旖華,鄧沛東.風險視角下數字平臺私權力的法律規制[J].西安財經大學學報,2023(5).
[15]CHANDLER D.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The rise of the correlational machine[M]//CHANDLER D,FUCHS C.Digital objects,digital subjec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23-42.
[16]林秀芹.人工智能時代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J].法學研究,2021(6):170-185.
[17]祝珺.電商平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研究[J].知識產權,2020(4):66-73.
[18]趙宏.公共決策適用算法技術的規范分析與實體邊界[J].比較法研究,2023(2):1-16.
[19]雷剛,喻少如.算法正當程序:算法決策程序對正當程序的沖擊與回應[J].電子政務,2021(12):17-32.
[20]李安.智能時代版權“避風港”規則的危機與變革[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107-118.
[21]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課題組.關于電商領域知識產權法律責任的調研報告[J].人民司法,2020(7):65-73.
[22]王文敏.電子商務平臺中知識產權錯誤通知的法律規制研究[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1):177-191.
[23]周江偉,趙瑜.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的實踐導向:可靠性、問責制與社會協同[J].治理研究,2023(5):111-127.
[24]張新平.算法與法律的沖突及其化解[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4(2):135-146.
[25]齊延平.數智化社會的法律調控[J].中國法學,2022(1):77-98.
[26]張凌寒.中國需要一部怎樣的《人工智能法》?——中國人工智能立法的基本邏輯與制度架構[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4(3):3-17.
[27]鄭玉雙.破解技術中立難題——法律與科技之關系的法理學再思[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1):85-97.
[28]肖紅軍.算法責任:理論證成、全景畫像與治理范式[J].管理世界,2022(4):200-226.
[29]司曉,馬永武,等.科技向善:大科技時代的最優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3.
[30]郭春鎮,勇琪.算法的程序正義[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3(1):164-180.
[31]張吉豫.數字法理的基礎概念與命題[J].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5):47-72.
[32]李小草.電商平臺經營者角色演化及主體規范模式嬗變[J].現代法學,2022(5):194-209.
[33]勞倫斯·萊斯格.代碼2.0:網絡空間中的法律(修訂版)[M].李旭,沈偉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5.
[34]范如國.平臺技術賦能、公共博弈與復雜適應性治理[J].中國社會科學,2021(12):131-152.
[35]金善明.電商平臺自治規制體系的反思與重構——基于《電子商務法》第35條規定的分析[J].法商研究,2021(3):41-52.
[36]劉權.網絡平臺的公共性及其實現——以電商平臺的法律規制為視角[J].法學研究,2020(2):42-56.
[37]RAHMAN K S.Regulating inform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ternet platforms as the new public utilities[J].Georgetown Law Technology Review,2018(2):234-251.
[38]張曄.論知識產權協同保護格局的完善——以電子商務平臺為中心[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2(4):98-105.
[39]馬平川.平臺數據權力的運行邏輯及法律規制[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3(2):98-110.
[40]羅有成.算法安全的理論內涵及治理實踐建構[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6):149-157.
[41]YU P K.Can algorithms promote fair use?[J].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Law Review,2020(2):329-364.
[42]ELKIN-KOREN N.Fair use by design[J].UCLA Law Review,2017(5):1082-1101.
[43]BURK D L.Algorithmic fair use[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19(2):283-308.
[44]萬勇.人工智能時代的版權法通知移除制度[J].中外法學,2019(5):1254-1269.
[45]HEALD" P J.How notice-and-takedown regimes create markets for music on Youtube:An empirical study[J].UMKC Law Review,2014(2):313-328.
[46]李雨峰,鄧思迪.互聯網平臺侵害知識產權的新治理模式——邁向一種多元治理[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55-165.
[47]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中國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發展研究報告(2021)》[R/OL].(2022-04-29)[2024-03-02].https://cnipa-ipdrc.org.cn/ckfinder/userfiles/files/2022429164700.pdf.
[48]刁佳星.算法時代合理使用制度的困境與紓解[J].中國出版,2023(3):33-38.
[49]BRIDY A.The price of closing the value gap:How the music industry hacked EU copyright reform[J].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mp; Technology Law,2020(2):323-358.
[50]劉聞.論商業言論自由的法律邊界[J].江西社會科學,2016(8):164-169.
[51]熊皓男.NFT交易平臺版權責任否定論[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6):54-62.
[52]萬勇.著作權法強制性過濾機制的中國選擇[J].法商研究,2021(6):184-196.
[53]何煉紅.論算法時代網絡著作權侵權中的通知規則[J].法商研究,2021(4):186-200.
[54]馬更新.“通知—刪除”規則的檢視與完善[J].政治與法律,2022(10):147-160.
[55]李曉秋,李雪倩.民法典時代電商平臺專利惡意投訴之規制路徑[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122-131.
[56]孫文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論邏輯與實踐理路[J].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2023(4):22-33.
Incorpor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algorithmic governance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e-commerce platforms
HUANG Weijun
(School of Cyber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With the rise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algorithms have emerged as a novel means for gov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infringement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governance primarily manifests in two forms: algorithm detection mechanisms and algorithm notification mechanisms, which, despite being based on the same technological principles, represent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However, the alienation and misuse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y can lead to ethical risks in IP governance on e-commerce platforms. Potential pitfalls exist at three stages: model establishment, data input, and output results. Additionally, factors such as cost considerations, evas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ies, and profit incentives can motivate entities to misuse algorithms. Integr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th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of IP on e-commerce platforms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combining the rule of law with moral governance, and is a crucial step toward modernizing China’s legal framework. Using a technical ethics approach that combines both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perspectives, the integr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with algorithmic governance can be distilled into macro-level and micro-level focal points: a macro focus on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of IP on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micro focuses on promoting “technology for good”, prohibiting the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nhancing platform autonomy. These correspond to values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and justice, integrity, freedom, and democrac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itself -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algorithm program design across the three stages, including incorporating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 establishing information-sharing mechanisms, and setting up an algorithmic “counter-notification” process. Furthermore, regarding the limits of algorithm application, it is currently suggested to maintain the non-mandatory nature of algorithm filtering and to improve governance measures for malicious notifications.
Keywords:core socialist values; e-commerce platfor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gorithmic governance
(編輯:刁勝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