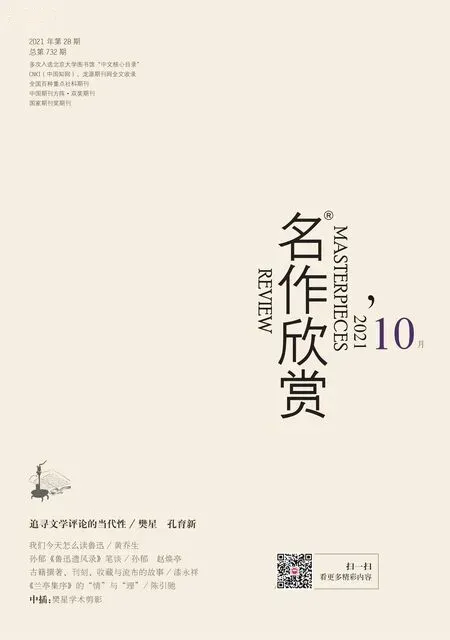知人論世與讀者的話語霸權(quán)
——《鶯鶯傳》的闡釋傳統(tǒng)及其反思
江蘇 滕漢洋
知人論世與讀者的話語霸權(quán)——《鶯鶯傳》的闡釋傳統(tǒng)及其反思
江蘇 滕漢洋
知人論世的闡釋模式屏蔽了元稹對(duì)于小說主旨的說明,導(dǎo)致張生乃元稹自寓的觀點(diǎn)主導(dǎo)了對(duì)作品的解讀傾向,使絕大多數(shù)讀者沉迷于在其中發(fā)現(xiàn)唐代士人獵艷經(jīng)歷和對(duì)張生的“忍情說”進(jìn)行道德批判的快感之中。《鶯鶯傳》的接受史,實(shí)際上是讀者的話語權(quán)不斷膨脹而作者的話語權(quán)不斷消解的歷史。
元稹 《鶯鶯傳》 闡釋傳統(tǒng) 反思
通常情況下,文學(xué)作品一旦宣告完成并廣為傳播之后,對(duì)作品的話語權(quán)也隨即由作者一方轉(zhuǎn)移到讀者一方,相關(guān)作品也因之由作家的個(gè)人表達(dá)變成一種社會(huì)共享話語。然而對(duì)于作者來講,這一過程雖然必不可少,卻隱含著某種不可控制的危險(xiǎn),受制于作家個(gè)人表達(dá)能力和讀者的認(rèn)知能力以及語言詞不達(dá)意、言不盡意的可能性局限,讀者在追尋和闡釋作品的同時(shí),偏離作者預(yù)設(shè)表達(dá)意圖的解讀乃至直接的誤讀時(shí)有發(fā)生。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羅蘭·巴特所宣稱的“作者死亡,寫作開始”,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對(duì)于這種情況,作者和讀者雙方似乎也并非完全沒有認(rèn)識(shí)到,為了將這種解構(gòu)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一方面,作者往往在作品中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出現(xiàn),試圖對(duì)讀者的閱讀理解進(jìn)行引導(dǎo)和控制;另一方面,讀者一方也試圖構(gòu)建一些解讀的規(guī)范以求作者的本心。然而,這種作者與讀者雙方共同避免偏差的努力,卻有可能因?yàn)橹c(diǎn)的不同而南轅北轍。唐傳奇《鶯鶯傳》的闡釋傳統(tǒng)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示。
如同中唐時(shí)代的許多愛情傳奇一樣,作為一種社會(huì)消遣性的文學(xué)讀本,《鶯鶯傳》可以說是當(dāng)時(shí)都市風(fēng)流的產(chǎn)物,才子佳人的遇合與分散,艷情的強(qiáng)調(diào)與渲染,似乎都昭示著這類作品迎合市民趣味的世情化、娛樂化特質(zhì)。但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唐傳奇“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有時(shí)候還可以作為行卷、溫卷來使用,相對(duì)于古代士大夫抒情言志的主要載體——詩、文來講,其在諸體文學(xué)中的地位似乎并不低,甚至被當(dāng)作個(gè)人綜合性文學(xué)修養(yǎng)的展示方式之一。雖然我們?cè)凇耳L鶯傳》之類作品中,并未發(fā)現(xiàn)此種具有投獻(xiàn)功能的痕跡,但考慮到這類作品一般都具有極強(qiáng)的傳播效應(yīng),而作者本身多為在社會(huì)序列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士人,其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須受到禮法的約束,創(chuàng)作者對(duì)其創(chuàng)作意圖初始化的重視應(yīng)該是可以被確認(rèn)的,也就是說,作者至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會(huì)被完全認(rèn)為是一種毫無寄托的游戲之作而受到不必要的非議和指責(zé)。因此,在唐代的一些著名的單篇傳奇中的某個(gè)位置,作者常常跳出來,用第一人稱的視角交代故事的來源、對(duì)此具有共同興趣的同道為何人、這一故事所具有的意義等信息。這一據(jù)說是沿襲自史書序贊體例的慣常表達(dá)模式在白行簡的《李娃傳》、沈既濟(jì)的《任氏傳》等愛情傳奇乃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李朝威的《柳毅傳》等神怪題材作品中都有所保留,可見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現(xiàn)象,同時(shí)也與此類作品多以“傳”為名的文本形式本來就直接導(dǎo)源自紀(jì)傳體史書相關(guān)。與此類似,在敘述了張生與崔鶯鶯令人感嘆和惋惜的愛情故事之后,元稹在《鶯鶯傳》的最后也做了遵從慣例的表達(dá):“時(shí)人多許張為善補(bǔ)過者。予常于朋會(huì)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在這一段話中,元稹對(duì)于自己創(chuàng)作《鶯鶯傳》的意圖做了明確的說明,那就是通過張生的經(jīng)歷,告誡如同張生一樣的年輕友人們“知者不為,為之不惑”,即以小說中張生所謂的“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的方式抵御美色乃至一切外在的誘惑。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鶯鶯傳》實(shí)際上可以看作一篇宣揚(yáng)年輕的讀書人應(yīng)該秉持禁欲主義觀念的小說文本,是元稹借友人張生的經(jīng)歷來表達(dá)自己對(duì)于抵御外界誘惑的看法,明顯具有勸世諷世的創(chuàng)作目的。
按理說,這類文字出自作者之手,應(yīng)是我們解讀相關(guān)作品意蘊(yùn)和理解其主題內(nèi)涵的重要立足點(diǎn)——起碼是立足點(diǎn)之一。畢竟,張生作為年輕的應(yīng)考舉子,在本應(yīng)該全身心投入讀書學(xué)習(xí)的時(shí)刻,一旦遇見“顏色艷異,光輝動(dòng)人”的鶯鶯,心中“內(nèi)秉堅(jiān)孤,非禮不可入”的道德堤防瞬間崩塌,雖然最終抱得美人歸,但在與鶯鶯纏綿悱惻之際卻忘記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最終贏得一個(gè)“文戰(zhàn)不勝”的落第結(jié)果。這對(duì)于一個(gè)尚未科舉及第而正在考前集中復(fù)習(xí)的年輕讀書人來講,難道不是值得警惕的嗎?在小說中,張生與鶯鶯分手后所發(fā)表的一番“忍情”的理論,雖然被魯迅指為“文過飾非”,但卻更為明確地表達(dá)了這一主題內(nèi)涵。張生在比鶯鶯為妲己、褒姒,稱其為“尤物”“妖孽”的基礎(chǔ)上所提出的“忍情”理論,固然無法獲得絕大多數(shù)現(xiàn)代讀者的認(rèn)同,但這一翻版的紅顏禍水理論,無論我們贊成與否,在古代社會(huì)卻是很有市場(chǎng)的一種論調(diào)。古人一方面認(rèn)識(shí)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但對(duì)于迷戀女色卻又時(shí)時(shí)心存警惕。例如,關(guān)于“好色”的討論,在中國古代便有極強(qiáng)的倫理政治和文學(xué)傳統(tǒng)。戰(zhàn)國時(shí)期的宋玉在其《登徒子好色賦》中設(shè)置了三個(gè)對(duì)于“好色”持不同立場(chǎng)的人物——登徒子、宋玉和章華大夫。在賦的開篇,“好色”成為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詆責(zé)宋玉的借口,但這一負(fù)面的道德評(píng)判遭到了宋玉的有力反駁。宋玉一方面從登徒子與“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的妻子育有五子的角度說明登徒子才是真正的好色者;另一方面則從自己對(duì)“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的東家之子的誘惑所采取的斷然拒絕態(tài)度,來證明自己具有坐懷不亂的道德定力。雖然賦中章華大夫?qū)τ谂澳坑漕仯念櫰淞x”亦即“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態(tài)度較登徒子和宋玉而言更符合人倫之常情,但宋玉的態(tài)度在賦中顯然被視為論辯中的勝利一方——在美色的誘惑面前,深刻的自我抑制和精神制裁被視為一種具有道德堅(jiān)守意義的美德而受到推崇。濫觴于宋玉的這一道德敘述模式在漢代司馬相如的《美人賦》中幾乎被原樣照搬,并最終形成一種道德文學(xué)敘述的傳統(tǒng),直到清代蒲松齡《畫皮》之類的鬼魅故事中,依然可以見到其影子。如果我們循此思路觀照《鶯鶯傳》的敘事結(jié)構(gòu),元稹恰是對(duì)這種道德文學(xué)敘述的承襲。在小說的開篇,張生即宣稱:“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于心。”而張生嗣后的經(jīng)歷也表明,所有這一切都是因?yàn)椤昂蒙彼隆V徊贿^在宋玉、司馬相如那里,“好色”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道德污點(diǎn),深厚的道德修養(yǎng)的加持成為他們抵御誘惑的定力。而在張生這里,“真好色”成為堂而皇之的自我標(biāo)榜,并最終使他成為愛欲的俘虜而迷失方向。
因此,“好色——忍情——補(bǔ)過”的敘述結(jié)構(gòu)在《鶯鶯傳》的核心處儼然存在。《鶯鶯傳》的主旨并非是津津樂道一則“始亂終棄”的凄涼愛情故事,而是想通過友人張生的經(jīng)歷告訴身邊具有同樣困惑的年輕讀書人:在科舉的愿望未能達(dá)成之前,必須嚴(yán)格控制“好色”的欲望,而一旦沉迷于愛欲的泥潭,除了當(dāng)機(jī)立斷地提出分手,自身便不會(huì)得到反省的機(jī)會(huì)而回歸理智。這應(yīng)是符合中國古代道德文學(xué)敘事傳統(tǒng)的解讀,同時(shí)也是符合故事邏輯的解讀。
然而不幸的是,文學(xué)作品通常被認(rèn)為來源于生活,尤其是小說這種具有明顯的事件性、現(xiàn)實(shí)性的文學(xué)體裁,更被許多批評(píng)家認(rèn)為是現(xiàn)實(shí)的某種投射,乃至是作者個(gè)人經(jīng)歷的投射。解構(gòu)浮于文字之上的虛構(gòu)性敘述,顯露現(xiàn)實(shí)的底色,似乎是讀者在理解此類作品時(shí)本能的條件反射。我們對(duì)古代文學(xué)作品解讀時(shí)所最為常用也是被認(rèn)為最為合適的“知人論世”的解讀方式,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這樣的一種認(rèn)識(shí)。而一旦采用這種被認(rèn)為是恰當(dāng)?shù)慕庾x方式,《鶯鶯傳》的意蘊(yùn)和主旨便會(huì)呈現(xiàn)出另一番模樣,因?yàn)樗苋菀资棺x者成為歷史的考據(jù)癖者,糾纏于歷史的真實(shí)而非文學(xué)的真實(shí),將小說中的人和事與歷史事實(shí)和作者的個(gè)人經(jīng)歷對(duì)號(hào)入座,乃至將小說視為一種個(gè)人的自傳,從而對(duì)文學(xué)研究的本意失去興趣,對(duì)作者于小說中的任何宣示視而不見。
從歷史事實(shí)來看,《鶯鶯傳》中的張生的確與元稹的真實(shí)經(jīng)歷有相當(dāng)部分的重疊,而且元稹本人也和張生一樣“美風(fēng)容”。更為重要的一點(diǎn)是,元稹似乎對(duì)于女色有著特殊的偏好,而其對(duì)于女性的道德觀卻存在瑕疵。元稹在編輯自己的文集時(shí),曾前無古人地列出了“艷詩”的條目,雖然按照他自己的解釋,這類詩歌主要在于描寫女性的容貌服飾,且具有“干教化”的目的,與艷情的描寫乃至色情的暗示毫無關(guān)聯(lián)。所謂的“艷詩”,在現(xiàn)在能看到的元稹文集中已經(jīng)無法準(zhǔn)確地指實(shí)為哪些作品,但考慮到元稹當(dāng)時(shí)的詩名,這種宣示很難讓人相信,因?yàn)榕c元稹同時(shí)的李肇已經(jīng)明言當(dāng)時(shí)人的詩歌“學(xué)淫靡于元稹”,稍后的李戡也曾將元稹與他的好友白居易捆綁在一起加以批評(píng),說他們的詩歌“纖艷不逞”“淫言媟語”,產(chǎn)生極其不良的社會(huì)影響,深惡痛絕的態(tài)度溢于言表。與此相關(guān)的是,在“詩言志”的批評(píng)模式下,元稹的一部分詩歌所表達(dá)的感情也被視為虛偽矯飾,尤其是在對(duì)待女性的態(tài)度上顯示出道德修養(yǎng)的缺失。如其千百年來感動(dòng)無數(shù)讀者的三首悼念亡妻韋叢的《遣悲懷》,在一部分人眼中,不但沒有體現(xiàn)對(duì)于亡妻的深情,反而是虛偽矯飾之至。陳寅恪對(duì)于其中的“惟將終夜長開眼,報(bào)答平生未展眉”評(píng)曰:“所謂長開眼者,自比鰥魚,即自誓終鰥之義。其后娶繼配裴淑,已違一時(shí)情感之語,亦可不論。唯韋氏亡后未久,裴氏未娶之前,已納妾安氏。”雖然陳氏自己也認(rèn)為不能以今人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元稹做苛刻之評(píng)論,但其在對(duì)“長開眼”過度闡釋的基礎(chǔ)上所推導(dǎo)出的元稹的女性觀所展現(xiàn)出的褊狹,還是令人吃驚的。至于清人潘德輿對(duì)于其中的“潘岳悼亡猶費(fèi)詞”一句評(píng)曰:“安仁《悼亡》詩誠不高潔,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婁百事乖”一句又評(píng)曰:“元九豈黔婁哉!”可以說相較于陳寅恪的解讀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已經(jīng)完全溢出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范疇之外,具有人身攻擊的嫌疑了。客觀來講,以上這些對(duì)元稹詩歌的解讀一定程度上與解讀者認(rèn)為《鶯鶯傳》中的張生就是元稹自己的認(rèn)識(shí)相關(guān),尤其是對(duì)于后代讀者而言,《鶯鶯傳》中張生所表達(dá)的獵色觀及其拋棄鶯鶯所展示出的對(duì)于女性的歧視,與元稹自己的詩文中所表現(xiàn)出的女性觀念如出一轍。讀者也就很容易由對(duì)小說中張生的反感,走向?qū)π≌f作者元稹的非難與攻擊,進(jìn)而由文學(xué)的欣賞轉(zhuǎn)向?qū)Ρ徽J(rèn)為是元稹原型的張生的道德評(píng)判。更何況,如果說張生就是元稹,似乎也有歷史背景的現(xiàn)實(shí)根據(jù),并不能被完全看作是空穴來風(fēng)。因?yàn)樘拼娜说墨C艷奇聞,很多是被指名道姓的當(dāng)作事實(shí)予以記載的。如被稱為“閩學(xué)鼻祖”的唐代著名文人歐陽詹與太原妓的愛情,就是一段佳話,小說的敷衍之外,確實(shí)可以得到他自己的《初發(fā)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等詩的印證。即如與《鶯鶯傳》同被列入中唐三大愛情傳奇的《霍小玉傳》,也被明確地記載為是中唐著名文人李益的真實(shí)經(jīng)歷;《李娃傳》雖然對(duì)于其中的男主角鄭生避其名諱,但作者白行簡在小說中也直言:“予伯祖嘗牧?xí)x州,轉(zhuǎn)戶部,為水陸運(yùn)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從側(cè)面說明小說所依據(jù)的是客觀的歷史事實(shí)。因此,對(duì)于讀者而言,元稹所生活的時(shí)代,讀書人枯燥的讀書行役生活中,獵艷的行為并不罕見,相反卻是比比皆是。由此,在熱衷于歷史索隱的讀者眼中,元稹的為人及其并不嚴(yán)肅的女性觀念,加上時(shí)代風(fēng)氣的沾染,張生為什么不可以是元稹呢?這似乎是知其人而論其世的必然結(jié)果。
于是我們看到,在知人論世的解讀模式下,從北宋時(shí)期王铚的《傳奇辯證》開始,到現(xiàn)代學(xué)者陳寅恪的《讀鶯鶯傳》、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乃至當(dāng)代的諸多唐傳奇研究者,《鶯鶯傳》的主人公張生就是年輕時(shí)期的作者元稹,而崔鶯鶯就是他在與出身高門大姓的韋叢結(jié)婚前夕拋棄的情人這一觀點(diǎn),幾乎被毫不質(zhì)疑地加以接受并得到進(jìn)一步的論證。甚至,為了彌合小說與元稹真實(shí)經(jīng)歷上的某些齟齬不合之處,一部分研究者不惜改動(dòng)小說的文本。如王铚為了配合自己的考證,將小說中張生“年二十三”改為“二十二”;更有一部分學(xué)者如陳寅恪等人在元稹的詩歌文本中尋找崔鶯鶯的原型,那就是元稹多次提及的“雙文”,以證成其說。經(jīng)過這樣嚴(yán)密的索隱鉤沉,張生乃元稹自寓,成為絕大多數(shù)人閱讀《鶯鶯傳》時(shí)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先入為主的看法。雖然元稹在小說中一再地宣稱張生乃是其友人,張生作為一個(gè)“善補(bǔ)過者”的形象也是其朋友圈的共識(shí),而且在小說的末尾也對(duì)讀者基于這一傳奇故事的認(rèn)知試圖加以限制和引導(dǎo),但卻被這眾聲喧嘩所屏蔽,或者被認(rèn)為是一種掩蓋自己早年不良經(jīng)歷的企圖。這恐怕是元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事情。于是,在《鶯鶯傳》的接受過程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文學(xué)的解讀始終難成氣候,甚至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處于失語的狀態(tài),而倫理的道德的解讀始終占據(jù)主流。讀者對(duì)于這篇小說的閱讀興趣,不在于情感意象,不在于文學(xué)敘事的策略,而是沉迷于在其中發(fā)現(xiàn)唐代士人獵艷經(jīng)歷和對(duì)張生拋棄鶯鶯而又美其名曰“補(bǔ)過”進(jìn)行道德批判的快感之中。一個(gè)原本可以進(jìn)行深度解讀的文學(xué)文本,至此淪為文人的八卦和好事者的談資。
縱觀《鶯鶯傳》的一部接受史,作者元稹對(duì)于小說的主題意蘊(yùn)的敘述,可以說始終處于被有意或無意忽視的境地。而讀者在知人論世的解讀模式下,以己之心度古人之腹,對(duì)小說卻得出了完全不同于作者的認(rèn)知。正所謂“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筆者在這里無意于對(duì)這兩種解讀進(jìn)行對(duì)錯(cuò)和優(yōu)劣的評(píng)判,只是想說明,在文學(xué)作品實(shí)際的接受過程中,作者確實(shí)可以被視為弱勢(shì)的一方,因?yàn)槲膶W(xué)文本一旦形成之后,作者基本上就失去了解釋的權(quán)力,其意蘊(yùn)與主題都有賴于讀者在闡釋的過程中確立,而對(duì)作品進(jìn)行解讀的方向和思路,又取決于他們選擇以何種方式進(jìn)入文本。文學(xué)作品的解讀絕不應(yīng)像羅蘭·巴特宣稱的那樣,被視為是作者向讀者進(jìn)行話語權(quán)的讓渡,而應(yīng)是兩者的合力所形成的共識(shí)。接受美學(xué)固然承認(rèn)讀者的重要性,但也強(qiáng)調(diào)其立場(chǎng)的客觀性和閱讀方式的科學(xué)性,并強(qiáng)調(diào)從作者、作品、讀者“三位一體”的角度研究文學(xué)。而在中國的文學(xué)閱讀傳統(tǒng)中,知人論世被認(rèn)為是文學(xué)解讀顛撲不破的真理,這一方法表面上看對(duì)于作者極其重視,但卻很容易使讀者淪為歷史考據(jù)的操手而導(dǎo)致話語霸權(quán),使歷史與美學(xué)的二元化批評(píng)向一元化傾斜。這一現(xiàn)象在中國古典小說的閱讀傳統(tǒng)中表現(xiàn)得極其明顯。《鶯鶯傳》的傳統(tǒng)闡述模式,不過是為此提供了一個(gè)具體而微的例證。
①羅蘭·巴特:《作者之死》,趙毅衡編:《符號(hào)學(xué)文學(xué)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頁。
②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11頁。
③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頁。
④元稹:《敘詩寄樂天》,《元稹集》卷三十,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51頁。
⑤李肇:《國史補(bǔ)》卷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頁。
⑥杜牧:《李戡墓志》,吳在慶:《杜牧集系年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44頁。
⑦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91頁。
⑧潘德輿:《養(yǎng)一齋詩話》卷六,《清詩話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8頁。
作者:
滕漢洋,文學(xué)博士,現(xiàn)為鹽城師范學(xué)院副教授、南京師范大學(xué)博士后,研究方向?yàn)樘扑挝膶W(xué)。編輯:
張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