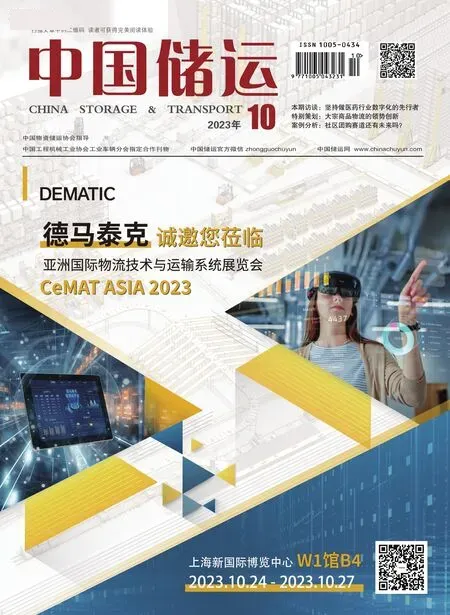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制度建構
——以物流行業為視角
文/荊培才 付偉
在新業態經濟模式下,物流行業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靈活就業人員加入其中,成為這一行業的生力軍。物流行業的靈活就業人員與其他行業的靈活就業人員一樣,都脫離了傳統勞動關系而被排除在《工傷保險條例》的保障范圍之外,當遭遇職業傷害風險時,其合法權利無法得到切實保障。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條例》保障范疇,本文以物流行業為視角,對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制度構建進行了探索。
一、案例引入
案例:李某經過壹米滴答快運公司某網點面試后從事貨車司機工作。某日,李某在貨物運輸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嚴重傷害。(李某所駕駛車輛為壹米滴答快運公司所有,某網點為壹米滴答快運公司加盟網點。壹米滴答快運公司提供車輛給網點使用,網點對車輛進行管理和使用。同時,雙方約定加盟方應為加盟網點所聘員工辦理社會保險,發生工傷事故糾紛由加盟方自行處理。)后李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其與壹米滴答快運公司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并判令其所受傷害屬于工傷。法院以壹米滴答快運公司未以公司名義向李某安排工作、發放工資、進行考勤與考核為由,認定李某與壹米滴答快運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李某受傷不屬于工傷,駁回了李某的訴訟請求。從以上案例看出:傳統勞動關系的存在是認定工傷的前提,李某與壹米滴答之間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勞動關系而被排除于工傷保險的保障范疇,以物流行業為視角構建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制度就顯得迫在眉睫。
二、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制度建構前提
(一)工傷認定“去勞動關系化”。根據現行《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工傷認定的前提是勞動關系的存在。在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處于強勢主導地位,勞動者處于弱勢被主導者地位,勞動者依附于用人單位,具有從屬性。在傳統用工模式下,將勞動關系與工傷保險強行捆綁在一起的做法并沒有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所以其中的不合理性并沒有引起關注。但在新業態形勢下,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依附性逐漸減弱,兩者之間已經不存在這種傳統勞動關系了。正是因為這一關系的缺失,靈活就業人員被排斥在了《工傷保險條例》的適用范圍之外。工傷保險本屬于社會保險制度的內容,更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堅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公益等基本理念。而且,我國《社會保險法》中一直用“公民”來表述該法的適用主體,進一步說明《工傷保險條例》中的“職工”不合理地縮小了社會保險保障對象的范圍。鑒于此,應解除勞動關系與工傷認定的捆綁。(二)堅持強制性原則。強調堅持強制性原則,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方面,雇主是以盈利為目的主體,利益是雇主的首要考慮要素,獲得利益最大化是雇主追求的目標。因此,受利益驅使,雇主基本不會從保護勞動者的角度出發自愿為其雇員投保并承擔保險費用;另一方面,盡管參加保險的受益者是廣大勞動者,但勞動者的保險意識、認知水平等個體差異很大,每個人的具體就業情況也千差萬別,自愿加入社會保險保障體系按期繳納保險費用在實踐中困難重重。因此,再次強調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必須堅持強制性原則。(三)建立健全“預防、康復、補償并重”的工傷保險模式。1884年,德國出臺了世界上第一部保險法——《勞工傷害保險法》,確立了“預防為先”“康復優于補償”的工傷保險理念。所謂“預防為先”,是指德國每年提取5%的工傷保險基金用于工傷事故的事前防范,以此降低工業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所謂“康復優于補償”,是指德國工傷保險制度的側重點在于為受傷勞動者提供最好的傷后康復(包括醫療康復、職業康復和社會康復),盡可能使勞動者重返工作崗位,而不是僅僅給予受傷勞動者及其家屬經濟上的補償。這一做法不僅降低了各工作部門的工作成本,還使勞動者獲得了全方位的工傷保障。而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是以補償為主,對于預防和康復關注較少。物流行業中,許多靈活就業人員從事物流運輸,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比較大,對于這類型的受傷人員而言,“康復”就顯得尤為重要。鑒于此,有必要建立健全“預防、康復、補償并重”的工傷保險模式。
三、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制度建構具體措施
(一)利益保障最大化原則指引下明確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的保障范圍。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規定,工傷認定的三要素是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原因。三要素在傳統工作模式下界限清晰,基本沒有認定難度。但在新型就業模式下,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時間范圍不清(比如長途運輸大車司機,中途停車休息時受到傷害,“中途停車休息時間”是否屬于工作時間)、工作場所靈活多變(比如快遞業務員的流動性工作地點),工作原因界限模糊(由于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工作場所與生活場所交叉導致)。因此,傳統法律意義上的“三工”不應當作為物流行業靈活就業人員工傷認定的要素。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以《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規定為基礎,特別注意此類人群工作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列舉工傷的構成和排除情形,客觀、實際地來解決工傷認定糾紛。對此問題,也有學者提出采納商業保險中“意外傷害事故”認定標準來認定工傷的觀點,即只要是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客觀事件為直接且單獨的原因致使身體受到的傷害,均可以認定為工傷。[1](二)利益均衡原則指引下確定繳費主體。利益均衡原則指導下確定繳費主體,全方位考慮雙方的利益關系,適當對靈活就業人員利益傾斜,最終達到利益和諧狀態。確定繳費主體,是工傷保險制度得以運行的關鍵要素之一。結合實際情況,主要分兩種情況確定繳費主體:一種是有雇主的情況;另一種是難以確定雇主的情況。對于第一種情況,因為有明確的雇主,所以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由雇主承擔繳費責任即可。對于第二種情況,目前主要有四種觀點:觀點一,全民免費參保;觀點二,物流行業、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的受益平臺(受益人)繳納;觀點三,靈活就業人員自行繳納;觀點四,靈活就業人員與受益人按比例共同繳納。[2]當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數量巨大,并且每年都以上升趨勢激增,再加上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均衡,很難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全民免費參保。同時,在新型就業模式下,靈活就業人員與平臺并沒有形成傳統勞動關系,物流行業、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的受益平臺并不是靈活就業人員的受雇單位,讓平臺作為繳費主體無理無據。而對于靈活就業人員,特別是處于社會生活底層的絕大多數人,參保意識薄弱、經濟條件限制等等原因決定了這一群體很難實現自愿投保。從誰受益誰負責的角度出發,雖然靈活就業人員和受益人之間不存在傳統勞動關系,但受益人畢竟是通過靈活就業人員來獲取利益,有利益就應該有責任,所以觀點四無可厚非,并可由由雙方按照工作風險、靈活就業人員對受益人的貢獻率等因素協商確定承擔比例。(三)強制性原則指引下確定繳費方式。繳費方式有強制繳納和自愿繳納兩種觀點。工傷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險,其本身就有保障性、福利性等特點。之所以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的保障范疇,就是為了最大化地保護這一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3]為此,筆者窮盡一切可能損害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利益的做法,明確指出:雇主確定的,由雇主承擔繳費責任;雇主不好確定的,堅持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由靈活就業人員和受益人按比例共同承擔繳費責任。否定自愿繳納方式是因為:一方面,靈活就業人員可能因為自身原因(保險意識不到位、僥幸心理作祟、經濟條件富裕等)不愿意繳納極少數額的保險費用,進而自動放棄了與切身相關的工傷保險權益;另一方面,受益人本來就不愿意負擔靈活就業人員的保險費用,在自愿繳納方式下,受益人便可以在獲得利益的情況下明目張膽、有理有據地不承擔繳納責任。“自愿繳納”方式使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權益保障有名無實。進一步講,靈活就業人員既然納入了工傷保險的保障范疇,理應堅持工傷保險的強制性原則,即強制繳費主體必須按照相關規定繳納費用,并賦予受益人強行代繳靈活就業人員個人應繳納部分的權利。(四)利用網絡技術便捷工傷保險關系的轉移和接收。在傳統工傷保險關系中,勞動關系的存在是認定工傷的提前,也是勞動者向用人單位主張工傷保險權益的依據。但勞動者與某一具體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勞動者從原先的工作單位調離進入另一個新的用人單位,原先的具體勞動關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具體勞動關系),當舊的勞動關系被新的勞動關系所替代時就會涉及勞動者人事關系(其中包括工傷保險關系)的轉移和接收問題。靈活就業人員不僅會面臨同樣問題,而且會因為工作變動的經常性而導致工傷保險關系轉移和接收的頻發性。工傷保險關系的轉移和接收,往往涉及數個勞動保險經辦機構,勞動者本人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到各經辦機構辦理相關手續。有時候,由于勞動者對辦理程序了解不清、申請材料準備不全、各經辦機構之間工作銜接不到位等原因,會耗費勞動者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勞動者對此苦不堪言。對于靈活就業人員而言,其中的困難不言而喻。鑒于此,筆者建議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健全網上辦公系統,加強數據完善和共享,通過網上申請網上審批現場確認的線上線下結合辦公模式,提高工作效率,保證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關系的連續性,切實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建構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制度,將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問題的解決落實到位,切實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權益,必將是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大勢所趨。